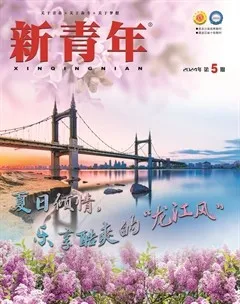外卖员送来温暖的诗
修红宇
在五月,读一部由真正的劳动者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我这个月重要的计划之一。从打工仔王十月的小说、矿工诗人陈年喜的非虚构故事集、皮村工友的散文集等作品中,我接过了外卖员王计兵送来的诗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自从小区里搬进来几位外卖员租户,我车库门前便成了他们的停车场。每次我开车出库,都要先费尽力气挪开那些电瓶车。为此,我常向家人抱怨,可家人总说:“外卖员也不容易。”我觉得腰有伤还要搬车的自己更不容易,便用《宇宙探索编辑部》里唐志军的台词回复他:“不理解,不原谅!”
“如果这本书能打动我,”我对他说,“我就理解并原谅外卖员”。
王计兵,初中辍学,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辗转各地打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忘“抓取靈感创作”。在即将步入知天命的年纪,他成为一名外卖员。六年来,他赶了15万公里的路,创作了四千多首诗,出版了3本诗集,被称作“外卖诗人”。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是他的第二本诗集,素净的封面上,画着一位忙碌的外卖员——盯着他看,像登陆了某外卖平台,在查看外卖配送进度——夜蓝色的护封如同保温袋,呵护着书中诗行,给人一种它们尽管早已被“出餐”,读起来仍温暖的感觉。
感觉温暖,是因为王计兵的诗行间总有光:从宿舍的窄窗斜插进来的阳光,“像剑一样”(《天空》);多年来遭遇过的白眼,“越来越像星星在夜里熠熠发光”(《七夕遐想》);在没有路灯的乡下小路,电瓶车灯照耀的光,“像一种救赎/仿佛世界的开端”(《夜行》)……诗人从平常日子里捡拾起柴一样的光,在内心点燃梦想,并坚信“所有的光创造了太阳”(《春光》)。
感觉温暖,是因为王计兵投向外卖员的目光中,有着暖暖的温度。他们在雨天与他并肩骑行,“天蓝色的外卖装像一小片晴空”(《阵雨突袭》),他让普通的劳动装有了诗意;他们蹲在墙角打盹,紧搂着的外卖箱“像一块巨大的橡皮”(《拐角处》),他希望橡皮能擦去沉重的情绪;午夜街头,瘪了的轮胎让他们看上去“像一份超时的订单”(《午夜推行人》)那么狼狈,但他们努力推车的姿态落在他眼中,“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他看到平民英雄身上的光芒……
读王计兵的诗,那份温暖会从纸页间传递到心上。那天,当一位外卖员看到我,连忙将电瓶车抬离车库门口时,我连忙说:“不碍事,车能开出去!”看着他微笑着离开,我想,他定是驶向春天,为一位幸运的顾客送去温暖的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