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诗亦成于“诗”的展览——“长风几万里:第四届唐诗之路艺术展”策展札记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李白《关山月》
此次“唐诗之路”系列展的主题“长风几万里”,即来自李白的这首《关山月》。
在唐诗中,从内容到结构,甚至意象选择,这首《关山月》都颇具代表性。
《关山月》是汉乐府旧题,在内容上也承袭了古乐府,抒写边塞军旅生活与征人思归之情,意境却比乐府古辞更开阔。全诗结构层层承续转折,以苍茫雄浑的月出天山开篇,经由长风万里、飞度玉门之豪迈,转至战事延绵、征人难归之悲壮,最后落于戍客与思妇之间跨越重山的互相遥望和叹息,深沉低回、悠远沉静。于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基调随之而出:旷达与寂寥、豪迈与悲悯、壮烈与沉静。这些两极“对位”、充满张力的情感,最终归流于悲而不怨、哀而不伤的情境与意境中。
这便是典型的边塞诗。在“起、承、转、合”的结构中,将壮景、历史、家国、民生以及由之而来的种种情志、层层意境,融于一体。由物景起兴,寓情于景、借景生情,以古述今,进而超越一时一事,在宏大壮阔的时间与空间中,写跨越古今之事、抒亘古恒永之情、述人心同然之理。
这是唐诗的动人之处和永恒价值。这也是我们此次展览,将关切的重心回归于“诗”的根由。我们以之为创作和策展的“起兴”——以读诗孕诗兴、以诗兴牵展事。
1.始于读诗的展览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生命经验中,唐诗都有着几乎无可替代的位置。
260年前,清人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成书,在此后的200多年里,这本书一直是中国人的开蒙读物,至今依然。可以说,唐诗所代表的,不只是盛唐的熙攘繁华与意气风发、包容豁达与慷慨侠烈,而且是千余年来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气度、精神世界的基石。在唐诗所开启的世界里,有石头城上、乌衣巷里的古今之叹,有月照孤舟、野渡无人的幽思寂寥,有登临绝顶、览尽河山的意气风发,也有柴米油盐、牵衣顿足的百姓日常。通过这一切,我们可以真实具体地看到、深切刻骨地感受到,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
前三届的“唐诗之路”艺术展,我们关切的重点在“路”——浙东这条孕生出无数名篇的唐诗之“路”,并在这条“唐诗之路”的行走中,以当代创作与古人遥相应和,以诗性的兴发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这第四届“唐诗之路”展,我们开始重新发掘“诗”自身的意义,以读诗为创作的起兴,以作诗来构造整个展览。
我们读诗,常见因景生情、咏物述怀,这“景”与“物”便是诗人诗兴的开端。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抑或“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均意在于此。一种由起兴所激发的、特别的物我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之而生。在这种关系里,“物”或“景”并非外在于“我”、区隔于“我”的观察客体,而是导向这样一种境界:“我”之胸中自有秦关汉月、长风万里,或是可以以一己之“心”感通天地万物之“灵”。
故而,诗人作诗,春兰秋桂之清幽高洁、生机勃发,所通向的是“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之气度风骨,这是借咏物以言志;湖畔烟柳、雀鸟空啼,所通向的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海桑田,这是对古今之变的感怀。而黄云千里、北风吹雁,虽为送别,却从常见的低回流连中超越而出,打开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慷慨悲歌与洒脱旷达,这里蕴含着唐人特有的昂扬与骄傲,也是“盛唐之音”的代表。
我们读唐诗,则又有一个由“入诗”而“出诗”的过程:由读诗人到读自我、由见己“心”到见人间百态之常情常理。亦即,我们读诗,常从以身代入、感同身受开始,以“有我”之思臻于“有人非我”之境,直至体察人间况味。而更重要的是,无论作诗或读诗,皆讲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讲究能由鱼水见江河、由江河见瀚海、由瀚海见天地氤氲。
这一点,正是我们此次展览的一大线索:以唐诗为起兴,由“入诗”而“出诗”,在“有我”—“无我”—“有人非我”这层层演进的三重意境中,贯通古今、体察人世。
2.作为“起兴”的《登幽州台歌》
于是,一個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唐诗的经典之作比比皆是,当我们将重心回归于诗,并以诗为起兴时,便需考虑选择怎样的诗、以哪首诗为展览的“起兴”。
较之以往,这次“唐诗之路”展览,将视野从“山水”延展到了“边塞”,并将边塞诗作为创作和展览的聚焦点。由此,展览的目光由浙东延伸至敦煌,并首次走出浙江,于北京、敦煌两地举办;或者说以北京为开篇、以敦煌为承续,两者相互联结、遥相呼应。
尽管说到边塞和边塞诗,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但事实上,在唐代,北京和敦煌都是边塞之地。譬如王昌龄的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所咏叹的“龙城飞将”便处在东北边塞,即幽燕之地。由此,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古幽州台,也称“黄金台”,是当年燕昭王为招揽天下贤士而建造。据考证,“幽州台”便在现北京大兴一带。尽管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颇有争议,有说是后人假托陈子昂之名而作。但传统说法认为,该诗的创作背景是陈子昂因谏受谤入狱,后又欲征讨契丹立功报国,却再次遭贬抑。在此情形下,陈子昂登古幽州台,感怀宦海沉浮、壮志难酬,继而心生悲凉而作。
就诗歌本身而言,它是唐代最负盛名的怀古诗,同样也是非常特别的边塞诗。
全文对幽州台没有一字描写,却皆为登台感慨,并且这一感慨超越了具体的人、事乃至时空,进而生发出一种横亘于古今、天地之间的具有伟大和永恒意味的孤寂感。而这种具有超越意味的宏大深远的孤寂感,也只有在同样空旷宏阔、苍莽无尽的边塞荒原上,才能生发而出。
全诗寥寥数语,却在古人不及见而来者不可见的永恒时间之流中,生发出贯通古今的悲怆孤独之意;亦在苍茫无尽的天地间,生发出一人独对宇宙的孤清寂寥之感。于是,一种时间无限延绵、空间无限辽阔共构关系油然而生,营造出浩瀚空旷、雄浑沧桑的意境。而人之悲怆感慨,在此情境中,终亦化归于浩茫永恒。故而,这首诗所抒发的囊括宇宙人生的深沉悲凉,也被后人称为诗坛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的那种苍凉,也是历史中的苍凉时刻。在他因一人独对天地、俯仰古今而生的悲怆里,不仅有孤独,还有自负和骄傲,甚至因骄傲而孤獨。这是从初唐到盛唐的诗人们独有的一种骄傲——视野的辽阔带来了心胸的开阔和心境的超然。亦即,当人的视野格局在“世界意识”和“宇宙意识”中被无限扩展时,生命的深度和广度也被打开扩大了。因此,陈子昂的悲怆并非悲哀,孤独中带有苍茫之意:以有限面对无限,以此时此地之“我”面对苍茫天地和深邃历史。此时的“我”,是为以一己之生命通达宇宙万物之大生命的“大我”。于是,人之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生命能量,赫然显现。

这种张扬的生命能量和人的骄傲,是唐人的一大特点。这不仅带来了唐代文化与生活的开放格局,也带来了唐人的大心胸与大关怀;落实在唐诗中,便表现为一种大浪漫与大悲悯——对天地宇宙最高远处的热烈追求,对人世间最微末之生命与生活的感同身受。
盛唐时代的边塞诗即为此中典型。
3.边塞诗中的大浪漫与大悲悯
总体而言,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背景、集中表现各类边塞题材的诗歌。边塞诗的发展成熟于唐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边塞诗派。其诗风或雄浑豪放,或瑰丽浪漫,或沉郁隽永,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成就令人瞩目。闻一多在《唐诗杂论·四杰》中写道:“五律到了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了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
目前学界尚存“狭义边塞诗”和“广义边塞诗”之说。“狭义边塞诗”,有时间和空间的界定,一般指“地理方位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至安西四镇,时间上限制在盛唐和中唐”。而“广义边塞诗”,则指“描写与边塞生活有关的一切诗篇,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均是边塞诗的题材”。诗人们或抒报国壮志、发反战呼声,又或怀古咏史、借古喻今、记写现世,但凡与边塞生活相关者,均可归入边塞诗之列。
在这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中,存有边塞诗在基调上的不同。就“狭义边塞诗”而言,从初唐到盛唐,边塞诗的基调以雄浑壮丽、慷慨悲壮为主,内容则重在“立功塞上”的壮志豪情。而“广义边塞诗”,则可追溯至《诗经》中的征戍类诗歌。盛唐之后乃至两宋、明清,亦多有“边塞”主题的诗作。尽管诗风上仍以雄浑豪放为主,但中晚唐以后,由于国力式微与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很多诗人开始反思和反对战争,抒写征戍之苦、民生之难,诗风亦由此偏向沉郁苍凉、深沉悲切。两者相较,大体而言,从初唐到盛唐,诗人们面对边塞的荒凉之地、战争的死生难料,他们慷慨悲歌、化悲为壮;但至中晚唐,诗歌基调则常表现为悲压倒壮。
文学界通常认为,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很大不同在于:中国古代诗歌,大体以抒情诗为主。这是沿着“诗言志”的传统而来的,以诗歌表达情感、抒发志向,以诗来传递人的“胸中意气”。而边塞诗的可贵之处,很大程度上即在于,它将复杂而矛盾的情感集于一体:既有对绝域风光的忧惧,也有对壮美山河的惊叹;既有对漫长边役的幽怨,也有对立功塞上、戍边卫国的向往和骄傲;同时,还交织着对早日归乡的渴望与忠于职守的坚持。
正是这些思绪的变换和情感的矛盾,使边塞诗有了更深的情感层次与内容厚度,而真实深沉的情感也带来感人至深的力量。这样的复杂情感中,蕴藏着一种大浪漫与大悲悯。
所谓大浪漫,意指以极致的浪漫雄奇,映衬自我生命的活泼与张扬,体现出从个人到民族的广阔胸襟和盎然生机。因之,边塞诗尤具任侠之气和自由精神,这既是唐人典型的精神气度,更通向人之超越性“大我”的一面。所谓大悲悯,意指诗歌中强烈的社会意识,诗人关注的不止于精神世界与超越价值,更有着对百姓日用的深沉关切与民生艰难的感同身受。因之,边塞诗里亦蕴有深刻的士人精神和社会意识,导向了人之社会性“大我”的一面。这两个“大我”面向的贯通,隐含着一种“伟大人格”的挺立。
李泽厚认为,中国人所主张的个体精神是指向人之内在伟大人格的,既有精神世界的独立自主、顶天立地,更有“自任以天下之重”“天下为公”的宏大气度。“中国的‘个人主义是精神上的……是个体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顶天立地、不受羁绊的伟大人格……它重在个体精神上对现实的抗争和超脱,而不是不要这个现实(包括自己的肉体生命)的灵魂上天。相反,这种个体精神、伟大人格经常是为这个世界服务的。”
因此,对于素来颇具家国之情、慷慨之志的边塞诗(尤其是“狭义边塞诗”)而言,无论言志还是抒情,其所蕴藏的诗心、引生的诗意、营造的诗境,皆是超脱于个人得失悲喜与书斋情致、文人意趣的。它通向一种洒脱旷达、高远壮阔的大开大合、大情大性,以及真实质朴、感同身受的情真意切、坚毅慈悲;它所追求的,不重精致幽微,而在于通达和真切。
这一点,构成了此次聚焦边塞诗的“唐诗之路艺术展”的一大要旨。
4.“起、承、转、合”的展览构造
唐诗的结构讲究“起、承、转、合”。在唐诗里,几乎每一首都完满自足,通过“起承转合”这一结构,情感逐渐生发、意义逐层开启,直到最后一句,诗篇全貌显现,意境浑然天成,诗人的情感也在此时达到最高处。无论是豁然开朗,还是高昂热烈,抑或深远悠长,乃至戛然而止,此时的诗与诗人均打开或转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便是作为结尾的“合”。
从“成诗”的角度而言,其中的“起”和“转”尤其重要。
起,即为起兴,所谓借景生情即在于此;但此时人与景或物之关系,却并非处于观察或比拟的主—客关系中,而更在于互相生发、浑融一体的状态。或亦可视之为一种“内”“外”贯通的身心关系:由“身”之感与知作用于“心”,而“心”中志气与意气亦影响着对外物的感知,如此往复“身”“心”之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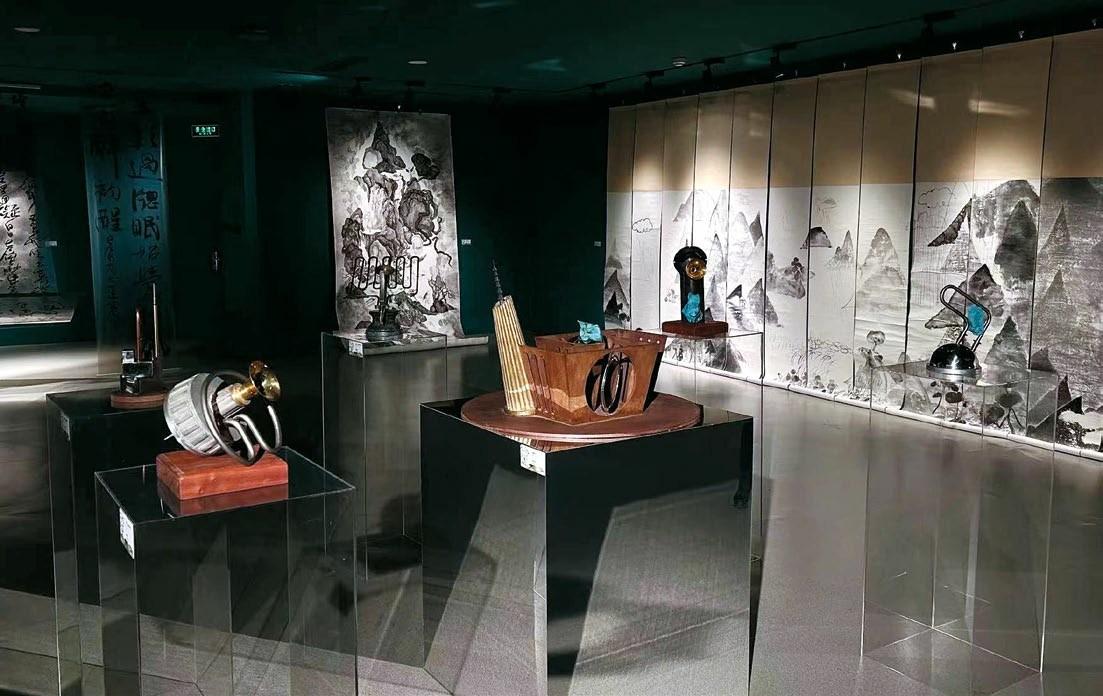
转,是转折也是转机,情感或基调于此处出现转换或转化;其中的关键在于,借由此“转”,将全诗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或是打开一个新的局面。王维《终南别业》中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既是全诗的“转”,更一语道出“转”之意义,故而,这两句诗一直为后世诗家所激赏。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言:“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俞氏认为,其“妙境”正在于水穷之处便是云起之时,一个新的维度由之打开——“水穷”所导向的空间之“穷”,却打开了时间的新维度,新的转机便由之而生。与此同时,“水穷”和“云起”,在本质上皆为“情语”;故而从“水穷”到“云起”,也意味着心境的变化——随着新的时空维度的打开,新的生命维度和人生境界亦随之开启。
沿着这一思路而来,此次“唐诗之路艺术展”,我们将关切的重心回归于“诗”本身。我们努力突破常规的展览模式,不做板块切分,而是以唐诗的典型结构——“起、承、转、合”来构造整个展示内容。如此,在视觉叙事和情感节奏上,整个展览既是对唐诗的回应,也可视为一首由艺术作品抒写而成的“诗”。
展览开篇即以初唐边塞诗的名篇《登幽州台歌》作为起兴。清人黄周星曾评价此诗为“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我们借此牵引出一种以“我”独对天地古今的大胸怀、大气魄。由此,为展览奠下主基调——人之生命能量,以及超越个人得失境遇的“大我”意识,亦为人的“志气”与“意气”。这既是“盛唐气象”所蕴含的精神气质,也是边塞诗豪迈雄壮之气度背后的精神内核。我们将其作为贯穿展览的主要精神线索或者说“一级脉络”。
随之而来,我们进一步牵引出两条“次级脉络”:俯仰古今、独对天地。这两条“次级脉络”,一条借“春华秋月”之永恒、“秦关汉月”之亘古,通向永恒时间之流中的古今对话,进而导向一种贯通古今、古今同在的诗意;另一条则从“大衍迁化”的自然造化到“以心为境”或“心眼”之下的天人关系出发,通向“会心宇宙,反观人世”之诗境,使天地造化的“无情”与人世沧桑的“有情”互衬、自然空间与文明空间相互交织。
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唐诗之路艺术展”将目光由浙东延伸至敦煌,首次走出浙江,于北京、敦煌两地办展。首展于北京,继之以敦煌,使两地遥相呼应、渐次深入。通过这一展览,我们将“一片孤城万仞山”之“山”、“青海长云暗雪山”之“山”,亦纳入“青山行不尽”的行旅之中,以期借此打开“唐诗之路艺术展”的新格局与新气象,
因此,在“承”的部分,我们借由多媒体影像的强烈的视觉效果,将“起兴”时生发的情感与叙事推向一个极点。而北京展的最后,我们以艺术家在敦煌的驻地创作或围绕“边塞”与边塞诗主题展开的专题创作收尾。这一尾篇,既是北京展的“转”与“合”——以万重青山之无尽,“合”于平沙莽莽之无际;同时,也是这届“唐诗之路艺术展”的“转”——以万里长风飞度玉门雄关之意,由浙东山水“转”入敦煌边塞,由天地苍茫“转”入大漠孤烟,进而借此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5.结语
对唐诗颇有研究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认为,唐诗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触动人心的力量,在于它有一种“现代性”。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现代性”?
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在唐诗中看到了真实鲜活的“人”和“人生”。正是在这种对“人”之生命历程的关切中,一种“刚性”的气质和力量自然生发。并且,诗篇所抒写的情感与愿望,亦是人所相通的,即所谓“人心同然之理”。
马一浮先生曾言:“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以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在他看来,人心天然具有兴发感怀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为“志”亦为“仁心”,而“诗”则是将“仁心”之感付诸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可以说,诗既因“仁心”而成,亦是“仁心”之外显。更重要的是:因诗之源头——人心至诚之“感”与“情”,通达于“宇宙天理之流行”,从而成了一切文化的根本和源头。
这正是我们今天依然读诗,亦将展览回归于“诗”的初衷。也正基于此,我们的展览以唐诗名篇为“兴”,希望通过“诗”本身,使展览与观众的共同起興,既牵引出展览之“诗”,更引生出观众心中之“诗”。
注:任晓栋,本次展览联合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蒋林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