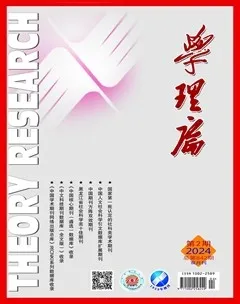《声无哀乐论》的内涵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关联
孙思冰 姜楠
摘 要: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在哲学史、美学史、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魏晋时期音乐美学的代表作,认为音乐的价值不在于情感的表达或情绪的激发,而在于音乐本身的纯粹性和美学上的追求。嵇康主张音乐应该超越情感和功利,追求自由、和谐和纯粹的美。《声无哀乐论》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其音乐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主体自由”“中和”等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仍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声无哀乐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嵇康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4)02-0045-06
中国的音乐美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早在先秦時期,各类典籍中便记载了大量有关音乐美学的论述,一类是散见的诸子语录,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一些重要范畴与命题;另一类则是关于音乐美学的专门著作,如《墨子·非乐》《荀子·乐论》。这一时期,儒家以“修身”为本的音乐功用论与道家崇尚自然的音乐审美意趣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基调。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淮南子》两部杂家著作对先秦诸子的音乐美学进行了综合与发挥,形成了一种以“感应生发”为中心的音乐美学。《乐记》则将“感应论”与音乐的“修身”功能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正统的儒家音乐理论体系。魏晋之前,中国的音乐美学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内容,但仍然缺少对音乐在社会功用以外价值的重视,使得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更像是道德学说或政治学说的附庸。直至魏晋时期,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关注人在道德以外的才情风貌,发觉了艺术在社会功用之外独立的审美价值,而音乐美学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正是魏晋时期音乐美学的代表作。嵇康在其中批判了传统的音乐观念,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理论。嵇康认为,音乐的价值不在于情感的表达或情绪的激发,而在于音乐本身的纯粹性和美学上的追求。他主张音乐应该超越情感和功利,追求自由、和谐和纯粹的美。根据嵇康的观点,真正优秀的音乐应该摆脱情感的束缚,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追求音乐本身的美感。与此同时,嵇康认为具有最高审美价值的“平和之声”可以通过形式美感染人心,产生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嵇康的音乐美学通过细致的论述,将音乐的独立形式美与传统乐论的功用论相结合,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又继承传统,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美学理论。
一、《声无哀乐论》的内涵
嵇康的音乐美学理论,以批判两汉之间儒家正统的道德“感应”论为重点,剥离束缚音乐的道德外衣,还原音乐以审美为核心的本来样貌。为了证明“声无哀乐”这一观点,嵇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一)“音声”与“哀乐”的定义
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常存一种缺点,即轻视对基础概念的严谨定义,而中国的字词又常常具有丰富的语义,这就影响了一些学术观点在传达上的准确性,引起诸多辩难。但是,中国并非没有严谨逻辑的传统,先秦时期名家、墨家对名实问题的一系列探讨,已经显露了中国逻辑学的雏形。可惜的是,两汉时期的学者并未能够继这种学术路向而有所发展。直到魏晋“玄学”兴起,逻辑学方才在当时盛行的清谈辩论中又一次得到发展。“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1]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辩题之一,自然有着严谨周密的逻辑理路,而其逻辑的起点,便是对“音声”“哀乐”的严谨定义。
《声无哀乐论》全篇采用主客问难的形式,以“秦客”代表传统的“道德感应论”提出辩难,以“主人”代表“声无哀乐论”给予答辩。在“主人”答复的第一段中,他便认为传统的乐论“滥于名实”,应当予以纠正。“主人”首先便提出了“音声”的定义:“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2]316在嵇康看来,“音声”与色彩、气味一样,仅仅是自然产生的,无关于人类情感。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嵇康言“声无哀乐”,却非“乐无哀乐”。在嵇康前的中国音乐理论中,通常都会以“乐”作为讨论的中心,但是嵇康却提出了“音声”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在嵇康的语境中,“音声”与“乐”属于不同的概念。嵇康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他对“乐”的定义:“乐之为体,以心为主。”这明显可以看出“音声”与“乐”之间的差别。“在《声无哀乐论》中,‘声(音声)不等于‘乐。‘乐的存在,是根本的存在,而‘乐中之‘声的‘声(音声),是作为‘乐的一个要素而存在。”[3]在嵇康看来,“音声”是音节、韵律等音乐的形式因素,而作为整体的“乐”则是一种需要主体参与的人文活动,在主客交互之间得以形成。因此,“声无哀乐”并不等于“乐无哀乐”。
对于“哀乐”这一概念,嵇康同样严格限定了其范围。一般看来,“哀乐”作为一个泛称可以指代人类的一切感情因素,但是在《声无哀乐论》中,“哀乐”特指一种具有社会内容的情感表现。“秦客”开篇的问难便是:“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2]315可以看出,“秦客”所说的“哀乐”之中包含着一种政治景象。嵇康明确反对“音声”中存在这种包含社会内容的情感,但是并不否认音声与人类感情之间存在联系。实际上,嵇康承认“音声”可以促使人产生感情。“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2]319嵇康认为“音声”可以引发人的爱憎,但爱憎这种感情仅仅是对于“音声”自身品质好坏的一种反映,一种审美判断,并不夹杂其他内容。与此相对,“哀乐”这种具有内容性的情感,只能是预先存于心中,然后由“音声”引发出来,并非“音声”本身的内容。由此可见,嵇康所说的“哀乐”,是指超出审美评价之外的感情,是包含第三方内容的感情,也就是一种道德性的感情。
嵇康对“音声”“哀乐”内涵的详细划分,展现了其立论的精密与严谨。读者只有明确了二者的定义,才能正确地理解“声无哀乐”的含义。
(二)“音声”不载“哀乐”
确定了“音声”与“哀乐”的定义,则可以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主要判断便是“音声”中不具备“哀乐”这种具有社会内容的情感。嵇康从两个层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即“音声”的生成层面与主体的接受层面。
“音声”的生成是“音声”是否具有“哀乐”的基本,如果在生成层面都没有“哀乐”这种情感参与,那么成品的“音声”自然也不会具备“哀乐”。在此前的“感应论”中,音乐的生成必然具有人类情感的参与。“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樂。”[4]《乐记》认为,音乐是由于心感于物,心动而生。所谓心动,也就是心的感情活动。生发于不同的感情活动,音乐也就自然带有不同的特色,通过这种特色听众就可以感受到“哀乐”,这正是“声有哀乐论”的基础。但在嵇康看来,“音声”的生发只遵循自然之理,并不以人心为决定因素。“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2]321这段文字清晰地展示了嵇康对“音声”生成规律的认识。在他看来,“音声”的生成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适应“金石”“管弦”等乐器的特点,才能达到“和”“谐”这样的艺术标准。也就是说,“音声”的善,不依赖于人心,而是依靠“音声”自然之理。嵇康的音乐生成论,断绝了传统“感应论”对创作的扭曲,突出了艺术创作规律的重要性,体现出了一种艺术的自觉。
“音声”的生成无关于“哀乐”,那么在主体的接受层面,“音声”同样不能直接地为主体带来“哀乐”之感。嵇康通过三个层次论述了主体对于“音声”的接受。首先,嵇康指出了“音声”接受过程中经常出现“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这种现象,即同样的“音声”却给受众带来了不同的情绪感受。如果认为“音声”中含有固定的情感内容,那么这种现象必然无法解释。其次,嵇康进一步解释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嵇康认为,受众的情感体验并非“音声”所传递出来的,而是由于个人心中有所感怀,经“音声”的引发而自然流露。个人心中所感怀的内容,实际上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情感经历。“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2]316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音乐形式及音乐接受的效果也自然会产生不同。“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2]316个人内蕴情感的不同,也会在面对“音声”时产生不同的表现。最后,嵇康指明了“音声”接受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道理,即“哀乐”是内在于人心,个体间存在差异,在接受过程中由音声引发显现,但绝非特定的“音声”与特定的情感有着必然性的联系。
(三)“音声”之作用系于审美
嵇康之前的乐论在评价音乐的价值时经常把社会功能放在首位。比如《论语》记载了孔子评鉴音乐的方式,“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48可以看出,孔子除了称赞音乐的形式美外,更为重视蕴藏于音乐之中的道德内涵与政治理想。嵇康主张“声无哀乐”,因此也提出了针对音乐新的评价标准。嵇康在文中数次强调音乐中“和”的作用,“音声有自然之和”“声音以平和为体”[2]325。笔者认为,被嵇康视为音乐本质的“平和”并非类似其他乐论中具有超越性、形而上的意义,否则便否定了其“声无哀乐”的立论基础。嵇康强调的“平和”标准,即音乐创作中达到曲调和谐、优美,亦即形式美的标准。同时,嵇康的论述中也涉及音声的“善”。“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无关“哀乐”,则嵇康所说的“善”必然不是孔子所说的道德内容。嵇康所说的“善恶”,仅仅是音乐本身艺术水平的高低。因此,音乐的“善”也就是“美”,嵇康将音乐评价的标准最终归结于“美”之上,彻底地回归于艺术形式本身。
以“音声”的形式美为基础,嵇康论述了“音声”实际的社会效用以及其作用机制。嵇康虽然不承认“音声”能够承载或引发特定的情感内容,但是并不否定“音声”能够引发受众的情绪变化。“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2]324“音声”的不同风格,可以引起受众情绪上或躁或静的变化。躁、静不同于“哀乐”,躁、静仅是情绪上的波动,并不指向特定的情感内容。“音声”通过引起情绪的波动,进而使受众释放预存于心的情感内容。因此,妥善地利用“音声”引发躁、静的功能,才能够使“音声”产生社会效用。
在《声无哀乐论》的最后一段中,嵇康详细论述了音乐如何发挥移风易俗的社会效用。粗看之下,这种观点似乎偏离了“声无哀乐”的观点。但如前所述,嵇康分别定义了“音声”与“乐”这两个概念。“音声”是纯粹的音乐形式,而“乐”则多了更多的含义,是一种受众投入身心的文化活动。嵇康详细叙述了音乐发挥移风易俗作用的过程:“故乡校庠塾亦随之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酢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2]328由此可见,“音声”只是礼乐活动中的一部分,必须配合其他方法一起才能发挥出教化的作用。“音声”是“乐”这一文化活动的客体方面,受众作为主体参与“乐”的活动,最终获得“哀乐”的社会效用。嵇康对“音声”与“乐”的划分,显示了其析理精妙之处,并且使“声无哀乐论”回归于儒家传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并非强为求全,而是通过细致的推理、论证,为儒家的音乐教化论注入了一种更为科学的因素。
二、《声无哀乐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关联
《声无哀乐论》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它的音乐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主体自由”“中和”等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音乐本于自然的“天人合一”精神
“天人合一”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观念,指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它强调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以及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天人合一”精神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艺术理论与创作中,亦时刻体现着这种审美取向。“天人合一”虽然可以概括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在各家理论的具体论述中,对于“天人合一”却有不同的解读。根据对天的不同理解,“天人合一”也存在三种路径。第一种以“人格天”概念为核心,“人格天”具有意志性,可以主宰世界运行与人的命运。这种观念下的“天人合一”,即人的行动顺从天的意志,受天支配。第二种以“自然天”概念为核心,“自然天”是世界运行的准则,具有规律性。这种观念下的“天人合一”,强调人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第三种以“形上天”概念为核心,“形上天”代表最高的超越性准则,被称作道或理。这种观念下的“天人合一”在于人的本性与天的同一,尤其是道德性上的同一。三种“天人合一”观念虽然有较大区别,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相互渗透的情况,难以清晰地切割。中国文化这种内涵丰韵的“天人合一”精神,同样深深地融于各种艺术理论之中。
“天人合一”作为一种贯穿于中国文化始终的精神内核,在嵇康之前的音乐理论中就有体现。先秦两汉的音乐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派具有代表性的乐论,一派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音乐美学,另一派则是由孔子、孟子、荀子最终到《乐记》集大成的儒家音乐美学。老、庄的音乐美学以道为核心,道即自然生化运行的规律,而真正有价值的音乐必然是道的体现,也就是自然天成的音乐。在道家看来,人为造作的音乐虽然能够带来一定感官上的愉悦,但并不具有最高的审美价值,并且可能损害人的精神。老子认为:“五音令人耳聋”[6]45,庄子则说:“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7]353这体现了道家对于音乐形式美的轻视与批判。摒弃形式美的“大音希声”才是道家推崇的音乐审美境界,这种无声之乐不借助形式上的要素,而是审美主体与客体一种内在统一。道家“大音希声”的说法一方面否定了音乐形式美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又启发了一种超越物我,“天人合一”的艺术审美境界。《乐记》作为儒家乐论的集大成之作,提出了“感于物而动”这一观念。在音乐的生成层面,音乐是人感情的抒发,而感情因人心与事物的交汇而产生。反过来讲,在音乐的接受层面,人可以通过音乐感受感情,再由这种感情体悟特定的事物。这样,整个音乐活动就是一种人心与物相互感发的过程。在这个交互过程中有一个中心,即德。《乐记》特别推崇“德音”这一理念,德是天地赋予人与物的一种美好本性,通过音乐活动的心物交感,使人向自己的道德本性复归,这正是《乐记》追求的最高价值。《乐记》以道德本性沟通天与人,构建了一种道德化的“天人合一”精神。道家与儒家乐论中的“天人合一”精神,均对嵇康的音乐美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在嵇康那里得到了发展与融合。
嵇康在音乐的生成上秉持一种自然本体论,这种观点与道家乐论有相似之处,却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嵇康认为:“音声有自然之和”,强调音乐创作顺应客观的创作规律,达到和谐、优美的形式效果。虽然同样认为音乐活动应当顺从规律性,但嵇康与道家对“自然”的认识却并不相同。道家所说的“道法自然”,除了强调事物运行的规律性,更加赋予自然一定的超越性,具有主宰世界生成、转化的能力。而嵇康的“自然”只是说明事物运行变化的客观规律,并不具有形而上的属性。因此,道家更为推重由“自然”生发而出的“天籁”,嵇康则认为只要是遵循音乐规律的创作,均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嵇康的音乐生成论,强调主体的创作能力与音乐客观规律的配合,体现了一种创作中的“天人合一”精神。在对于音乐社会效用的论述中,嵇康并不否认儒家乐论“移风易俗”的观点,却对其作用机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乐记》认为,“移风易俗”的基础是心、物之间的感应能力,音乐作为中介传递出特定的情感与社会内容,引发受众的情感与道德体验,从而达到主体本性(道德性)的发现。嵇康则认为,作为纯粹艺术形式的“音声”并不具有承载内容的能力,其主要功用在于调节受众的情绪。“音声”必须与承载内容的诗、规范行为的礼等相互配合,才能成为“乐”这样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审美活动。“乐之为体,以心为主。”[2]328在“乐”的审美体验中,审美主体与客体通过人心相统一,最终达到调节情绪、体悟情感、规范行为的社会效用。嵇康的音乐功用论不再强调神秘性的情感体验,而是注重利用音乐接受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最终达到主体全身心投入的“天人合一”状态。综合来看,嵇康的音乐美学在其以自然为本的哲学基础上,继承了前人乐论中的一些有益观点,剔除了其中神秘、玄妙的因素,形成了自己以规律性为首的“天人合一”理念。
(二)审美独立的“主体自由”精神
在一般的认知下,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重,注重个体在社会和家族层面的责任和义务,而对于个体的自由表达和选择相对有限。尤其是在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中,强调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和责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师生关系等,提倡个体应当以利他为主,服从社会和家族的规范和秩序。这种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独立选择。但如果详细推究,儒家传统,尤其是原始儒家的教义中,并不缺乏对“主体自由”的推崇。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大力提倡周朝的文化传统。而周代文化的一个特色,便是将人从原始信仰中解脱出来。“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8],远鬼神而近人事,即一种对人文精神的发扬,对个人价值的认可。孔子虽然也有“天命”之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5]226却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5]64孔子虽然承认“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决定性作用,但是并不抹消个体自由选择的空间。孟子对此则有更进一步的论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9]222“天命”是超脱于主观之外的外在决定因素,非人力所及。而在另一面,人力亦有自己的作用领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9]302孟子对“天命”与人力做出划分,实际上是开拓了主体自由的空间。同时,孟子的“立命”“养气”“四端”等观点,进一步阐明了道德发源于人心,道德修养与主体自由的同一性。在孟子后,荀子更是激进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进一步扩大了主体能力的作用空间。综合来看,儒家虽然强调个体的道德与社会责任,但是在根源上将这种义务视为主体的自由选择,道德是以自由为基础的。纵览儒学的发展史,一旦喪失“主体自由”这种精神要素,那么儒家传统便会丧失生气,沦为桎梏自由、戕灭人性的统治工具。
相较于儒家,道家对“主体自由”这一精神的提倡更为直接。首先,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顺应。道家认为宇宙万物都遵循道的规律,人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和谐并不是束缚个体,而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即通过顺应自然的道,个体能够达到内心的自由、自然和无为。主体自由精神在道家中表现为对于外在规范和束缚的超越,通过顺应内在的道德原则来实现自由。其次,道家强调无为而治的理念。无为并不是消极无为或者懒散,而是指放下功利心和私欲,追求心灵的宁静和自由。“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6]253道家主张返璞归真,回归到本性的自由状态,不被世俗所困扰。主体自由精神在道家中表现为摆脱物质欲望的束缚,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再次,道家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不仅超脱于万物,更要超脱于形躯。庄子认为,形躯作为一种物理性的存在,与万物一样处于一种生灭变化流程之中。因此,形躯无法超脱于外在束缚和求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主体并非形躯,而在于自我精神。因此,真正的“主体自由”就是自我精神超越于一切经验,无有桎梏,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总体而言,道家哲学中的“主体自由”精神强调个体超越外在的规范和束缚,追求内心的自由、自然和无为。通过顺应自然、追求内心的宁静和超越功利的态度,个体能够达到自我精神的绝对自由。
魏晋时期是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动乱时代,纷乱的社会形势促使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并且动摇了两汉正统价值观的根基。苦于生命之无常,魏晋知识分子不再信任不确定的外在价值准则,而是重视对生命内在价值的发掘。这种思想倾向贯穿于艺术领域,促进了对各种艺术形式审美价值的重估,使魏晋时期成为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艺术的自觉,即剥除附着于艺术形式上的道德含义与政治内容,仅从审美的角度去肯定艺术的价值与意义。这种自觉,不仅是艺术形式的独立,同时也是对精神生命审美需求的肯定。主体的审美需求从此脱离了道德属性,取得了独立地位,这也正是“主体自由”精神的体现。在嵇康的音乐美学中,他通过反对“感应论”为音乐正名,确立了音乐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的地位。除此之外,嵇康对音乐审美体验的论述,更是大大超越了前人。“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鐘。”[2]316嵇康认为,人心中存在最为基本的审美需求,出于感情和欲望,而无关于道德。其诗云:“弹琴咏诗,聊以忘忧。”[10]26对音乐审美需求的满足,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情感体验,减少不良情绪的困扰。“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10]21随着审美层次的上升,主体更可以借由音乐审美活动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可以看出,嵇康对音乐审美的认知,超脱了道德性与功利性,仅关注其独有的审美体验。嵇康对音乐形式美的代表“郑卫之音”也给予了极高评价:“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虽然他也认为过于精妙的“郑声”可能损害人的情志,但也从反面证明了音乐审美的巨大效果。嵇康对音乐独立审美价值的肯定,树立了审美需求的正当性,体现了一种道家的精神自由理念,冲破了传统儒家乐论的道德藩篱,将“主体自由”精神于艺术领域贯彻、发扬。
(三)不可偏执的“中和”精神
“中和”精神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特质。“中和”精神强调平衡、适度与调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一种克制内敛、含蓄包容的特色。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5]94这种“中庸之德”在音乐领域的体现,便是“中和”之美。孔子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44称赞其在情绪表达上的节制。孔子认为《韶》“尽善尽美”[5]48,则是强调其形式美与道德内容的平衡。《中庸》对“中和”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1]在道德修养中,“中和”即情感抒发的克制与适度。《乐记》推崇的“和乐”,其关键同样是情感表达的收敛。除了情感表达上的适度原则,音乐上的“中和”精神还强调音乐内部元素的协调与配合。《庄子》中描述了“地籁”的特点:“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7]46不同声音之间的呼应、配合,形成了一种多层次的协奏。而“天籁”则是:“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7]50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真正优美的音乐必然需要不同乐器、音色、曲调的配合,通过精妙的搭配,形成抑扬起伏的乐章。“中和”精神在音乐美学中,一方面要求音乐有节制的情感表达,另一方面又强调音乐形式内部的协调之美,这两方面均对嵇康有着重要影响。
嵇康音乐美学中的“中和”精神,大致有两个要点。第一,嵇康提倡“音声有自然之和”,也就是音乐自然形式中的和谐之美。他认为:“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2]316“和比”也就是音乐形式的内在协调,包括音调、音色、节奏与韵律等要素的配合,达到一种内在和谐。对于音乐形式内部要素的特征,嵇康有着清醒的认识。“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2]324嵇康注意到了不同乐器的音色特质以及相适应的曲调节奏,并且强调各要素互相之间的和谐搭配。“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2]324纷繁复杂的音乐要素,最终都必须搭配汇聚成和谐的节奏韵律,这也正是嵇康所说的“自然之和”。第二,在嵇康的音乐功用论中,他提倡对形式美的克制。虽然嵇康不吝于对“郑声”形式美的赞誉,但同时他也认为:“自非至人,孰能御之。”[2]329音乐审美不仅能给人以愉悦的情绪体验,同时也能摇荡人的情志,若过度沉迷其中,就超过了正常审美的界限,反而有损无益。因此,音乐的形式美应当保持一定的限度,与审美主体的审美层次相适应,如果达到“至人”的境界,则自然可以欣赏“郑声”。
除了音乐理论本身,在论理的过程与方法上,嵇康也秉持了一种“中和”精神。《声无哀乐论》的阐发是极具针对性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批判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传统功利主义乐论。文章通过“主人”对“秦客”的层层辩驳,条分缕析地全面批判了“感应论”的音乐观点。但是,嵇康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又回归到“移风易俗”的音乐功用论。这种回归并非屈从于正统的强为求全,而是为“移风易俗”提供了一种更为科学、现实的路径,是对传统观点的一种超越。在对音乐本体的论述中,嵇康一方面继承了道家乐论中自然本体的观点,同时又去除了其中超越性、神秘性的因素,形成了自己以规律性为中心的音乐自然本体论。综合来看,嵇康音乐美学的理论构建中,坚持了批判与继承的统一,基于传统构建了自己新的理论体系。嵇康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也正是“中和”精神的最佳表现。
三、结语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通过科学、细致的论证方法,批判了唯道德论的儒家传统乐论,挣脱了两汉经学对音乐美学的束缚。由于其立论的精妙,与“言意之辩”“养生论”共同成为魏晋“玄学”中的三个中心议题。这三大议题虽然论域不同,却又相互关联,透露出了魏晋时期一种共通的精神要素。“声无哀乐论”内含着一种音乐上的“言不尽意”,音乐不能直接地承载情感,正如语言不能完整地表达意蕴。“声无哀乐论”的“声—乐—心”范式与“言不尽意”的“言—象—意”范式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对称性。二者均否定了传统对“声”“言”功能的无限夸大,又承认了“声”“言”自身领域内的确切作用。这种论述解除了“声”“言”对“天人感应”的依附,赋予了“声”“言”二者独立的地位与价值。《声无哀乐论》与《养生论》同为嵇康所著,其共通之处便在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养生论》认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12]229精神在生命中居于根本地位,欲“养生”,则必须先保存精神。嵇康认为理想的精神状态是:“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12]231-232“声无哀乐论”证明了音乐不受外物牵连,音乐审美活动可以达到排解愤懑、舒缓情志的作用。因此,音乐审美正是达到精神自由的一种有效方式,是“養生”不可或缺的条件。魏晋“玄学”代表着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冲破了唯道德论的桎梏。“声无哀乐论”作为“玄学”中的代表观点,正是这种生命意识在音乐领域的贯彻,生命的觉醒带来了艺术的觉醒,由此揭开了中国音乐自觉的新篇章。
对于嵇康“声无哀乐论”中体现出的音乐自觉,一些观点认为其属于一种音乐上的自律论,并将其与西方的音乐自律论相比附。西方的音乐自律论认为,音乐的规则在其自身,本质仅在于音乐的结构,绝不表达除音乐以外的内容,对于音乐的理解也只能从其自身的角度加以分析、解读。虽然嵇康的音乐美学凸显了对形式美的重视,并且强调音乐的自身规律,但他并未彻底否定音乐与外在的联系,而是通过“乐”这一文化活动将“音声”与主体统一。因此,嵇康的音乐美学绝非一种纯粹的自律论,在中西理论的比较中,我们更应该重视其思想内涵在本质上的不同。作为一种发源于中国的音乐美学理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沾染了诸多中国文化独有的精神特质。虽然在理论观点上与西方乐论或有相通之处,但其更大的价值则在于通过音乐美学展现出了“天人合一”“主体自由”“中和”等中国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205.
[2]嵇康.声无哀乐论[G]//嵇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3]修海林.有关《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评价的若干问题[J].音乐研究,2006(3):28-31,84.
[4]吉联抗.乐记译注[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1.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6]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8]李学勤.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86.
[9]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0]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G]//嵇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11]王国轩.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46.
[12]嵇康.养生论[G]//嵇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