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放弃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传植/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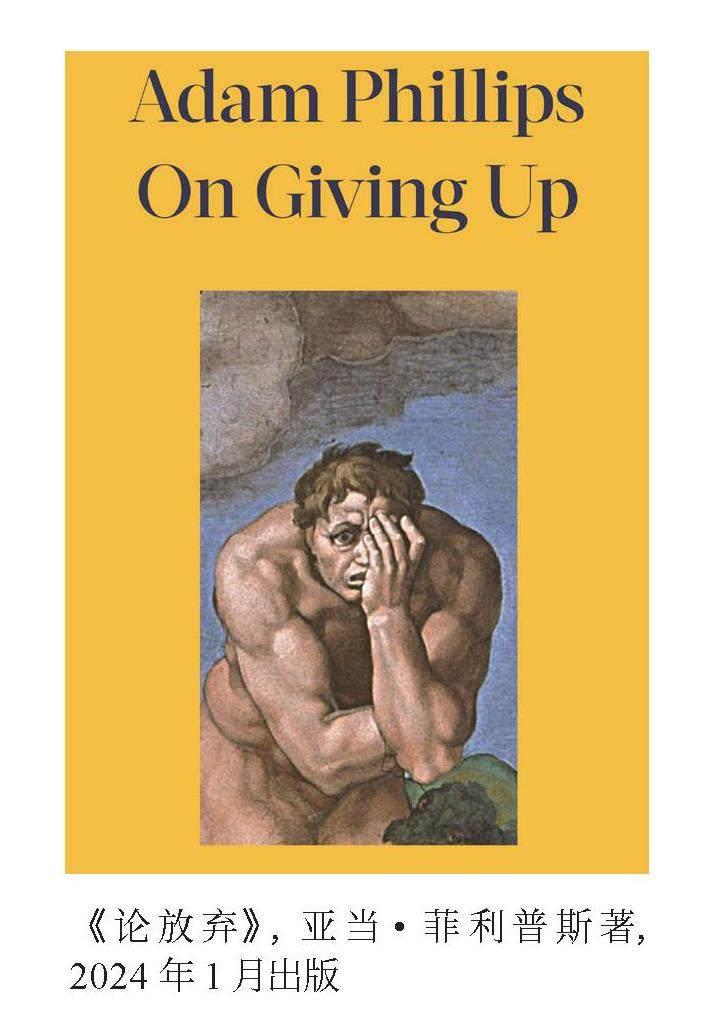

当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改变时,我们放弃;当我们相信自己不能改变时,我们放弃。
人们在谈到放弃时,通常是指放弃吸烟、饮酒、吃巧克力,或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享乐之事。总体而言并不是谈论放弃自杀,尽管人们想要放弃的是这些被认为是自我伤害的行为习惯。放弃某事可能有益,但讲到“某人放弃”总不是件好事——正如酒徒劝大家都来喝酒——有一种文化认同在于:人生是、也必须是值得享受的。若非如此则可能是宗教性的。
简单来说,牺牲可好可坏——同时也让我们错以为人能够选择自己的损失。我们会倾慕或立志于“放弃”,也会为“放弃”感到不安。正如真正的希望或绝望需要我们放弃什么,我们在放弃时究竟想象自己在做些什么,其中的本質是一种深远的暧昧不清。当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改变时,我们放弃;当我们相信自己不能改变时,我们放弃。
所有新的思考也与老生常谈的“牺牲”有关,我们应该放弃什么以获得我们所应希冀的生活。为的是我们的健康,为的是我们的星球,为的是我们的情感和道德康乐——而实际上却是富人的利益——我们如今被要求放弃了许多。但在这鼓吹自我牺牲的狂欢之外,究其深处,是放弃一切的绝望和恐惧。为了逃脱“生命不值得奋斗”这一想法,我们依靠宗教、心理治疗、教育、娱乐、商品和艺术帮助我们对抗这种挣扎。而如今愈来愈多的人靠着憎恨,偏见和迁怒面对生命。如此一来我们愈发被诱惑进入尼采的所谓“一种虚无意志,一种反生命的意志,一种对生命最基本前提条件的拒绝”。
对政治和个人关系的持续幻灭,对自由言论的需求和恐惧,对各类外在因素强迫达成共识的畏惧和渴望,都造成了一种充满威胁和义愤的文化氛围。如同是我们对生命的矛盾态度——这种活着的感受,即使转瞬即逝,也支持着我们——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张力,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症状。因此尽管我们至今无法想象或描述不存在牺牲概念的生活,以及其秘密的伙伴——妥协——有关我们通过牺牲希望以及能够获得什么的概念也变得模糊不清。系统地阐释个人和政治观念则过于确信或是不稳定。而牺牲的概念本身则依靠知晓自己的欲求。
放弃总是为了使某事更好而做出的牺牲。无论做任何事或是做任何决定时,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无法避免:我们需要放弃什么?这种选择在定义上是排他的,并揭示出某种偏好。这一工作中总是存在一种想象性的交换,为了得到某物,总是放弃某物。无论我们放弃了自信,或是言论自由,或是社交,或是需求,或是某种含义,甚至是放弃生命本身,似乎是因为我们脑海中考虑到了回报,而无论我们对这种交换可能并不自觉。我们希望从牺牲中获得之物永远值得讨论。牺牲及其不满总是值得讨论的,放弃某物或某人总能揭示我们想要得到的事物。
因此我们需要记住,放弃以及其各种形式,无论其表现为何,其本质总是一种礼赠(也如其名“give up”总是向上的,而非向下的,似乎面向更高的权威)。放弃某物是为了寻求自我认定的优势,自我倾向的欢愉,而这一过程正如其他很多心理过程,我们无法理解或预测。似乎我们在生命的特定时刻会被给予指令:“放弃吧”或“放弃之”,从而一种隐秘的渴望、希望和交易便会开始。
我们会尽当前所能去计算牺牲的效果,我们想从中得到的未来(从来不清楚牺牲是请求还是强迫,或二者皆是;牺牲是操纵还是绝望的投降,或二者皆是)。在人生中,我们会被要求尽自己的所能得到他人或自己所希冀的生活。我们问自己,需要失去什么以获得我们自认想要的东西。有时这些行为是一种“全知”的动物的表现:声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解自己的需求并拥有如何满足这些需求的好想法,是他能够想象做的唯一事情。牺牲、放弃则是一种预测。
被弃的儿童得到收养,战争中被打败的军队选择放弃——投降,向鬼神投降的人则会死亡。在这些迥然不同的例子中,似乎有一种东西被移交,一个必要的协议达成,一种临界点到来,一种危机发生,一种交换进行。就像放弃既关乎转变和转换,又关乎成功和失败。(放弃的整体思想是一种教化:当放弃成为一种选项,我们永远无法避免对其继续评估和评价。)当我们认为自己无法继续,就会放弃某事或某物。似乎放弃永远是一个关键时刻,尽管我们非常想将其最小化。
但放弃作为其他事情发生的前奏和先决条件,作为一种预期,作为一种勇气,是欲望消亡的一个象征。同样,它也会为其他欲望腾出空间。换句话说,放弃是尝试创造不同未来的行为。
艺术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玛丽恩 · 米尔纳(Marion Milner)在名著《自己的生活》(A Life of Ones Own)中描述自己试图“断定(她的)生活的目的”:
……我发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我决定开始写日记,写下每天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希望由此发现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也受到蒙田(Montaigne)文章的启发,他坚持主张所谓的灵魂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通常完全相反。
作为一个现代人,她选择先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为此她援引蒙田所言,对于那些“所谓的灵魂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通常完全相反”。她认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灵魂,与自己真正想要的事情有关,与做使自己快乐的事情有关;她认为自己必须要有生活的目标,即使她还不清楚其为何物。但蒙田也提醒她有一部分自我——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与自认为所希冀的想法完全相反(每种本质都暗示着另一种)。这意味着这种意义上,她并不想要生命的目标;让她开心的和她所想要的事情其实也无关紧要。或者另有其他事情对她更加重要。“生命有目标”或“我们追求的是幸福”的想法,或许只是过度简化了自己,使得心智变得狭窄。
在这个伟大的项目中,米尔纳有了重大发现。她认识到自己有两种注意力:“狭窄的注意力”和“宽广的注意力”。值得一提的是,她只需要日常语言便可明确自己想要和所想表达的东西,而这种注意力吸引到了她。
狭窄的注意力。这种感知似乎是自动化的,这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的焦点狭窄,由此满足眼前利益而忽视其他。我认为它如同一只“寻水兽”,用鼻子仔细嗅着地面,根据气味四处寻找,完全不顾周围的环境。它看待事物根据是否符合自己目的,将其视为达到自身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对其本身并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对日常生活实际大概是必要的,因此我从生物学的视角推断其对心灵而言是自然而然的……
宽广的注意力。第二种感知会在不追求事物目的的情况下发生。此时由于个人没有欲求,便没有必要从事物中择其一,因此能够同时看待整体。关切事物的同时又对其一无所求,这似乎是第二种感知的基本要素……如果我们偶然发现了保持宽广注意力的诀窍,神奇之事便会发生。
所谓“神奇之事”指“使无聊和疲倦产生不可估量的满足感”,第二种注意力“带来第一种完全无法想象的快乐”。宽广的注意力使得世界重新充满魅力,而狭窄的注意力消磨之。狭窄的注意力创造了一种人,这类人过度定义自己;而宽广的注意力则提供多种选择,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和他人。米尔纳在此描述的“宽广的注意力”显然是摒弃了目的、欲望和传统意义上的满足(这是一种自我遗忘);她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如何努力获得这种宽广的注意力,尽管达尔文主义和弗洛伊德学派会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却仍在贪婪地追寻目的。她认可这是一种布莱克(Blake)所谓的“灵视”。它认为任何美德的意識形态都只能是一种挑衅。
至于“寻水兽”,狭窄的注意力则是已知过程的一部分,这个人知道自己的需要,并将需要(以及对满足的渴望)作为自己的决定性特征。而在宽广的注意力下,人无法预先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无法假设需要是关键,或是行为的目的,或是唯一能做的。(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精神分析写作应该被当作社交的叙述或实验进行阅读。)
米尔纳为我们提供了两种观点,两种看法。需要注意的是,她认为两种注意力都是必要的。米尔纳并非要辩称,或是要教导,或是要劝说我们要牺牲一种而取另一种,她希望我们能够利用两种不同的注意力应对不同的事情。这并非事关放弃,而是关于拓展自己的能力,或是关乎诗人威廉 · 燕卜荪(William Empson)所谓的“跨越矛盾”。站在一方立场来获得矛盾的恩惠和利益是不可能的。
我们能否不过度地描述牺牲,不夸大地描述其为一种悲剧或是闹剧?我们能否警惕不被内在优越干扰而产生这种优越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否能够谈论放弃——重新描述放弃——作为我们道德和情感复杂性的实用线索,而非单纯地作为另一种我们最喜好去谈论的人身磨难。
人总是会产生需求,多数情况下不会处在无欲无求的状态。需求意味着缺少些什么,而现在已经老生常谈的看法是,我们需求的是我们假定自己缺乏的。我们的挫折成了欲望的关键,需要什么事物或人便是感到其缺席。因此表达或是认识到这种欠缺似乎便是任何一种享乐或满足的先决条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挫败感或欠缺感成了任何一种满足的必要先决条件。
“缺乏总是在场的,”拉康(Lacan)写道,“某物从惯常处消失了。”而如果存在这么一个惯常之处,则意味着无论缺乏的是什么,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被当作理所应当——具有或应当具有一个常规的、熟悉的、可靠的位置;正如母亲应该在生命中有一个孩子,日常的一天会有三餐。似乎缺乏感来自权利感;似乎我只会对我正当合法的权利缺失时才感到缺乏;似乎我真正意义上已然知道了自己的所需,尽管我不能或不愿意告诉自己这一事实。
我想主张的是,自己的一部分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另一部分则不需要。同理,也有一部分自己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另一部分自己则不需要。两种自己都有其自由,它们之间相互激发——我们的欲望来自我们知晓和不知晓的所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欲望和无欲相配,成为一种悖论,而非矛盾或冲突。
用以描述欲望的语言中存在一种紧迫性尺度的变化,从须要(need)到愿望(desire),再到想要(want);我们能够没有想要的事物,却不能缺少须要之物;我们也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摒弃愿望。愿望是须要和想要间的模糊地带。如果我们在失去须要之物后无法存活,我们在失去想要之物后又会怎样呢?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概念上的划分,正如欲望——无论如何描述它——需要仔细检查、区分和控制。它也常常需要一种共识——无论强制与否——因为我们称作欲望的想要似乎既专横又必要。正如亨利 · 詹姆斯(Henry James)对真实的定义——“这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想要是不可能不被知道的。上帝曾经是欲望的权威——定义它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如今非宗教的唯物主义文化中,欲望已经取代了上帝,或者说成了上帝的代名词,成为事物的动因。当达尔文主张生存和繁殖(以及自然选择)是演化的驱力,他将欲望置于问题的关键,是真正的驱动力。
婴儿,足够幸运的话不会过度地被卷入和母亲的欲望纷争中,尽管随着成长便会出现事关食物和其他欲望的对立情绪,像是睡眠问题和攻击性,这就构成了家庭生活。无论孩童情况如何,又想要如何,父母都需要负责作为孩童欲望的权威和管理者,告诉孩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又是什么。没有其他一种动物如此关心欲望,尽管其他动物也会经历资源不足和竞争威胁。动物行为学研究人类之外的动物,并不会让人类成为快乐的希望者。一种说法有些粗略却不失偏颇,人类历史正是一种被自己的欲望折磨的生物史,而生物的本质因欲望和欲望带来的享乐而无法安定,而生存本身也依靠欲望。
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之一——囊括了儿童发育,以及语言在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他以非宗教的唯物主义科学观探寻了欲望的本质;而达尔文在进化论中重新描述了饥饿和性欲的精神生理学,以及如今变迁为消费资本主义的欲望。这种文化适应确实使得欲望极快地增生;对我们而言,从乳房到超市,从父母到无限而鲜明的令人满足的客体[批评家里奥 · 博萨尼(Leo Bersani)认为儿童意识到家庭之外存在享乐是其发展的重要时刻];文化适应组织起了欲望,并变化成为其形态。教养和教育让我们知道了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当然也有所谓伟大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教导我们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满足欲望。人类本质的理论终究是在讨论人须要和想要的是什么。而作为现代生活特色的育儿手册则紧随其后。
而精神分析则是将欲望进一步推向了对善良、邪恶、慷慨、诚实、狡猾的欲望;关乎生物学需求(以及伴随的情感参与)如何转变为道德品行(以及伴随的情感冲突)。这样一来,所谓的生物学转变为可行的社交能力,并成为其一部分;欲望变为或未能成为同情心;需求使得我们变得残酷和善良。现代人类——至少在所谓的非传统社会中——离开家是为了寻找并了解父母无法提供的事物;家庭则界定、定义并尝试培养孩童的欲望,尔后现代孩童的欲望却超越了家庭之所能提供。
无论其他定义如何,家庭是欲望的教化之处,也是挫折的产生之处;由于家庭或多或少地满足了孩童的必要和想要,孩童也在此经历了挫折。这是因为使我们感到满足之人、感觉良好之人,也将成为使我们感到挫折、感到难受之人。在弗洛伊德看来,我们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动物:在我们所爱之处,我们也会在沮丧中憎恨,而在我们憎恨之处,我们认为爱正在被积极剥夺,被剥夺我们想要、须要和可能拥有的东西。在这个描述中,我们总是被发现有所欠缺而我们总是只关注我们须要和想要的东西。如今这才是我们或多或少熟悉的非世俗的唯物主义视角下的现代生活。无论我们对自己有什么抱负和理想,它们都是以生存为基础的,而生存则以欲望为保证。
弗洛伊德和随后的精神分析学家非常擅长展现我们为何常常错误认识自己的欲望图景,并为此感到烦恼。或者如果说不是错误,至少是极其令人感到挫败的。或用詹姆斯的话来说,是一种错误。欲望总是在各种程度上令人挫败,但我们也能通过这么多方式来讨论之。这些讨论将加深挫败感,或是加深它们描述的挫败感。
相当讽刺的是我们谈论和描述欲望结构的方式,将欲望看作一种特定的威胁或困扰。举例来说,欲望会被再次描述为吸引力的实验;或是偏好的测试。人类得以维生之物,似乎成了消解人类之物——好似我们与自己和他人的接触媒介,成为我们结构性异化的源头——我们会同弗洛伊德一样反思,我们想要欲望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还会注意到弗洛伊德没有发现的,我们非常擅长找到破坏欲望的图景和描述。
资料来源 The Guardian
本文节选自亚当 · 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的《论放弃》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