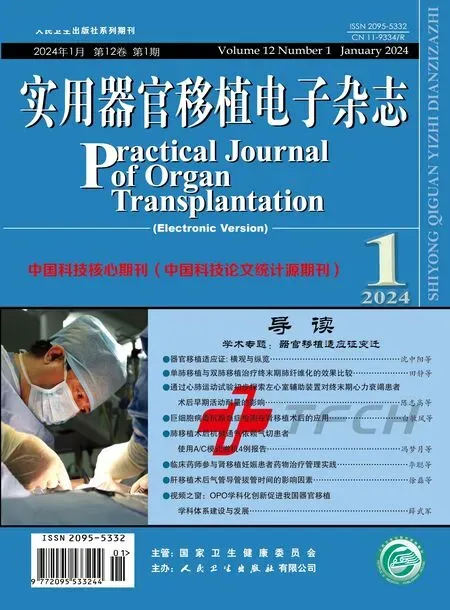器官移植适应证: 横观与纵览
沈中阳,薛武军(.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移植医学研究院,天津3009;.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西安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006)
适应证是熟知未必详知、常用未必用准的医学概念,是通用名词——指征(indication)在医药领域的专属化用语,其融汇指示与征象等基本词义,用以指向性表述某一临床措施的具体适用情形、证据或理由。适应证具有指示性与适当性双重基本内涵,同时具有复杂性、时代性两项基本特征。适应证通常是其所属时代背景下科技进步程度和医药发展水平的生动写照,追溯适应证变迁历程可发掘医学进步的内在动力与演进规律。
关于适应证的定义性表述不尽一致。在我国的《辞海》中定义为:适合于采用某一治疗措施的疾病或情况;在《斯特德曼医学辞典》中定义为:启动疾病治疗或诊断试验的基础,其匹配用于疾病病因的认知(因果适应证)、疾病呈现的症状(症状适应证)以及疾病的性质(特定适应证)。在证据医学时代,也有医学典籍将适应证简要概括为:使用某种检查、药物、程序或手术的正当理由,旨在强调适应证是启用某种医学干预的证据。适应证常以赋予具体内涵的适应证标准(indication criteria)指导和规范临床实践,故应避免与表述某一特殊医学状况的临床诊断相混淆。当前,基于循证医学原理形成的医学指南或共识等,日趋转变为适应证的引申表述形式,用以指导临床实践。
禁忌证(contraindication)是适应证的反义词,通常指某一诊疗措施的风险明显大于益处而拒绝接受的原因或理由,用以指示或预示医学干预措施的无效或危害,临床上常用绝对禁忌证和相对禁忌证评估风险与预测结局。针对某一特定个体而言,适应证与禁忌证是并存的矛盾体,常可展现医学诊疗的整体性、复杂性和特殊性。与确立适应证相比,判别禁忌证往往更具系统性和整体性,查找、发现、评估及管控禁忌证是临床诊疗的重要任务和临床决策的必要前提。适应证在临床药学领域又特化为“适应症”(label indications),特指某一药物适用的临床症状或应用情形,其反义词为“禁忌证”(off-label indications),临床上应依据证据或理由出具用药处方[1]。
现代器官移植学发轫于20 世纪初,继而以1954 年12 月23 日默里(Dr.Joseph E.Murray)教授实施的同卵双生兄弟间的成功肾脏移植为先导,各实体器官移植相继跨入临床应用阶段,并伴随社会与科技的进步而日臻成熟与规范。器官移植学的基本使命是克服重要脏器的终末期功能衰竭,横观与纵览器官移植适应证的演变历程,将加深器官移植医学特殊性、先进性、复杂性、时代性的认知与思考,进而促进科技创新与学科发展。
器官移植适应证变迁的内在动力源于其特殊内在属性,即征用异体器官资源的社会伦理属性和免疫排斥异体器官的科技属性[2],社会与科技以双元与整合[3]方式促进新兴技术与交叉学科的涌现,驱动器官移植适应证的不断变迁。适应证变迁的动因与动机直接来源于器官移植临床实践[4]。诸如:为扩大供体资源及其利用,派生了一系列亲体移植技术、边缘器官修复与利用技术、肝移植系列创新技术(劈离式、辅助式、多米诺式)[5];为克服同种异体器官排斥反应演化出高致敏或ABO 血型不相容器官移植脱敏方案、肾移植供体交换计划等;为发挥器官移植技术的属性优势,催生了肝移植肿瘤学的复兴,派生了系统移植肿瘤学的新兴[4];为避免器官资源浪费,引发了对肝脏、心脏、肺脏等器官移植“至重者优先”(sikest first)适应证原则上限的伦理质疑[6]。此外,生物医药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正在显著改变器官移植适应疾病(丙型肝炎等)[7]和制约疾病(HIV 感染)的临床结局,同样促使了器官移植适应证或禁忌证的悄然变化。
总之,社会与科技的不断进步,始终贯穿在器官移植学的发展进程中,并绘就了器官移植适应证生动、多彩的历史画卷。当前,再生医学、异种移植、AI 技术等正在加速发展,社会与科技正处于飞速进步的VUCA 时代,器官移植适应证也必将呈现出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的演进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