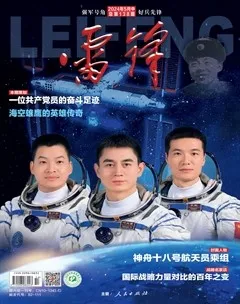终生难忘陈毅老院长的教诲 我办的是外交学院,不是劳动大学
王光明


1961年夏,我从成都市第14中学考入外交学院。外交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外交工作的需要,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于1955年9月成立。外交学院是以服务中国外交事业为宗旨,培养一流外交外事人才的小规模、高层次、特色鲜明的外交部唯一直属高校。它被誉为“中国外交官的摇篮”。
1961年10月,在国务院会议上,正式任命陈毅副总理兼任外交学院院长。陈毅副总理兼任院长期间,纠正和抵制了当时社会上一些“左”的影响,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关系知识课程,初步形成了学科核心教材,为学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放暑假前,也是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前夕,他到外交学院礼堂作了一次报告,时间长达3个小时。他除了谈国内国际形势外,还专门谈了学院的教学问题和学生的学习问题。他说,搞外交工作就是要把外语学好。不要让外国人听到你的外语像中国话,听不懂。他还说,要少看电影少看戏,要有达摩祖师面壁九年的精神,把外语学好。我们在日内瓦开会,外国人赞扬我们翻译的水平好,不仅词达意而且口气都翻译出来了!好的翻译就像快刀砍乱麻,非常利索;不好的翻译就像钝刀子割肉,半天割不下来。1956年招收的本科生(从1955年到“文革”前只有1955年、1956年、1959年、1960年、1961年招收了本科生)由于参加运动多、劳动多影响了学习,有少部分留校补课。陈老总说:“我办的是外交学院,不是劳动大学!同学们不好好学习,那是浪费国家的公粮!”这句振聋发聩的话,我记了一辈子。他还说,干外交工作,知识面要广。不一定要成那方面的专家,但一定要了解。他推荐同学们读《东周列国志》《资治通鉴》。他说,春秋战国时,那么多国家,他们如何搞外交的?值得学习。为此,学院还专门请历史学家吴晗作《资治通鉴》的辅导报告。那个年代,学校就又红又专问题谈得比较多。学院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外语书;另一种是怕说自己是白专道路,不敢去学习,热衷于政治和政治活动。他说,这两种倾向都要不得。他举例说,一种飞行员飞行技术很好,但政治立场不好,一起飞就往台湾跑。另一种飞行员政治立场很好,但飞行技术不好,一起飞就被打下来。这两种飞行员我们都不要。我们要的是既立场好又技术好的飞行员,这就是又红又专。在他的教育思想引领下,从1955年到2015年60年间,外交学院培养了近500名驻外使节,2万多名优秀外交人才。其中,优秀的代表有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我们61届学法语的45位同学,近一半当了司局级干部,在外交各条战线上奉献了一生。
1966年6月,中央领导分头到首都各大院校了解情况。周总理到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邓小平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陈老总则到外交学院。8月的一天黄昏,他到学院主楼北边看大字报。因天已暗了,我们给他打手电筒看的。看完后,我们把他带到宿舍,宿舍就在主楼北边,离看大字报的地方很近。我还把他带到我住的宿舍,他坐在我的床上。他同大家一起聊天,这时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王屏将军(之后调回部队担任军委装甲兵副政委)赶到。他对陈老总说:陈老总,我晚到了,对不起!陈老总对他说:“没关系,大家都来看大字报嘛。”在聊天中,我用四川话问他:陈老总,我们学校编的《法汉字典》说你是1905年出生的。他用他浓厚的四川话回答我:“你们把我估计过高了!我是闹义和拳那年出生的。”
聊天过后,陈老总一行到礼堂见全校師生员工。我作为学校的基干民兵把守礼堂大门。这时,一位中年妇女进门,我把她挡住了。她说她是龚澎,这名字如雷贯耳,我知道她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还是乔冠华的夫人。只是未能谋面不认识,我连忙把她让进礼堂。讲话中,陈老总介绍了不久前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情况。他说,主要是号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还谈到了一年前,他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他说,中央决定在1965年国庆节前,他以外长名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反击帝、修、反对我们的围攻。这时他说,有的人不敢见记者,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说,那有什么好怕的,论阅历他们没有我丰富!论资历他们更不行!他的这一翻话对我启发很大。在之后工作中,我三次借调到外交部新闻司陪法国记者采访,尤其是1975年5月,我陪法国《快报》国际部主任戈尔戴到西安、南京、无锡、上海采访。1992年3月,我率解放军滑雪代表团参加在瑞士举办的国际冰川滑雪比赛。这正是1989年6月“政治风波”之后,西方不跟中国军队交往,虽然代表团身份不高,又是体育队,但是第一个穿军装的团队到西方国家。我们代表团乘机抵达苏黎世国际机场,出了机舱门,一群记者就把我围住了,我从容地用法语回答了他们的提问。1997年6月,我当总领队率解放军仪仗队、军乐团,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这时在香港云集了3000多名中外记者,我跟队员们说,记者要采访,让他们来找我。陈老总的教诲,给了我底气。我采用的办法是:有时借题发挥;有时反问;有时王顾左右而言他。
1966年10月,我在成都。一天下午,我约好另一位成都考入外交学院的同学袁俊林(他学英语),到位于成都祠堂街《四川电影院》背后的“半节巷”,去拜望陈老总的父亲。所谓“半节巷”,按北京话说就是死胡同。这条小巷住的人家不多,只有十几户人家。陈老总的父亲住在靠里面北边的一个川西民俗小院。这是20世纪50年代,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为陈老总父母找的一处住处。本来给两位老人找了四川军阀杨森的公馆,他们认为大太,还是住普通的民房。我们俩按响了门铃,这时出来一位中年妇女,问我们有啥子事?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外交学院学生,是成都老乡,来看陈毅院长的父亲。知道情况后,她把我们带进屋,坐在堂屋里。这时她进到里屋将老爷子扶着出来见我们。我看到老人家穿着传统的长衫,弯着腰,留着白色的长胡子,身材比较高。落座后,我们说,我们是陈老总的学生,又是老乡,今天来看您。老人家年近九旬,交流起来已不太方便,我们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陈老总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但他对我的教诲永远记在心上。他的音容笑貌,永久留在我的脑海里!
(责任编辑:卜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