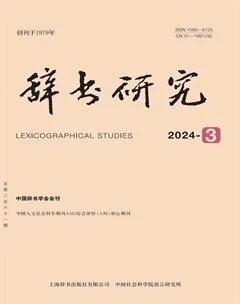弘扬中国辞书精神,铸造学术词典精品
王祝英?冯英梅?杨丽
摘 要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收录条目约两万两千条,全景式展现了敦煌文献语言的面貌,是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词典从编纂到出版历时二十余年,是一个系统的长期过程。文章从选题策划编写、编辑出版、相互协作三个方面介绍了打造这一学术词典精品的实践过程,指出作者团队和出版社在各环节守正创新、精益求精,发挥工匠精神,才能铸造高质量的辞书精品。
关键词 敦煌文献 词典 集大成 创新 精品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3—2025年国家辞书出版规划项目、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部词典共计550万字,全景式展现了敦煌文献语言的面貌,既能解决读者阅讀敦煌吐鲁番文献特殊词语理解方面和疑难俗字、通假字辨认方面的障碍,又为汉语史、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了全面丰富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词典出版后,获得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被誉为“敦煌学的三峡工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获浙江大学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特等奖(该奖设立以来唯一的特等奖)、浙江省第二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3年文轩好书奖、2023年四川好书奖。
回顾这部词典从编纂到出版的20余年历程,深感一部优质词典的问世是一个系统的长期工程,其中有三点尤为关键。首先是立意高远,在选题规划阶段就要树立高标,守正创新,并在编写实践中落实到位;其次是精益求精,在编辑出版环节要发扬工匠精神,一丝不苟,细细审读打磨;第三是各方团结协作,紧密配合。
一、 守正创新,持之以恒,编一部集大成的学术词典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从2000年正式启动编写到交稿用了20年的时间,先后有20余人参与其中,堪称20年磨一剑。这部词典的主编和总设计师是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他是著名敦煌学家和语言学家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项楚先生的学生,曾跟随蒋礼鸿先生编纂过《敦煌文献语言词典》,一直从事近代汉语和敦煌文献研究。学界此前对敦煌文献字词的考释基本上局限于变文、王梵志诗、歌词等通俗文学作品,而数量更为庞大的社会经济文献、佛教文献、道教文献、通俗辞书基本上不被关注,有鉴于此,张老师提出在汇集、吸收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把字词收集考释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敦煌文献,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填补敦煌学研究领域大型语词工具书的空白。项目提出之初,张老师就强调词典的原创性,不但内容要创新,编写体例方面也要创新。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选题变成了上下两册的巨著,目标顺利圆满完成。词典共收录条目约两万两千条,不仅条目总数多,在释义举例时,还把敦煌文献与其他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互相比勘,探源溯流,对大量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纠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错误校释,力图勾勒出每一个疑难字词产生、发展、消变的历时脉络,形成了集大成、探源流、明规律、释疑难的鲜明特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创新性。
首先是编排方式创新。敦煌文献字多俗写,一字异形或一词异形的情况特别丰富,同音别字也触目皆是,识读不易。以往的大型字词典,字词编排或按音序,或按部首,异体俗字、同音别字条目往往分列在不同部类及笔画之下,与正条不在一处,不利于相互比较辨别,词义关系也不易说清。本词典以现今通行的繁体字为字头,以字统词,将异体俗字、同音别字条目与其正字、本字条目全都排在一起,异形词也附列在某一主条之下,这样就把不同形的字、词串联在一起,形成了异体字、通假字、异形词三种群,副条与主条关系一目了然,有利于相关字词的比较互勘,也大大节约了篇幅。如繁体字头“國”字群,“國”下收有“囯”“国”“圀”“” “”五个字形:“囯”是六朝前后出现的会意俗字,“囗王为國”;我们现在通行的简化字“国”是会意俗字“囯”的增点字;“圀”为唐武则天新造字,寓意“四海攸同,八方来朝”;“”为“圀”的变体;而“”又是“圀”字俗省。这五个异体条目顺序排列,其孳乳演变,脉络清晰,一目了然。这是辞书编纂体例方面的一项创新。同时为方便检索,在书后设置笔画索引,“同”“通”类字词一样可以据形检索。每个群的创立看似简单,其实是建立在对敦煌文献语言整体全面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预先要对字、词进行大量的整理与比较认同的工作,这大大增加了编写的难度和工作量。
其次是使用资料创新。本词典收录的条目和引用的文献均来自第一手资料,从源头上保证了字头、词头和例句文字的可靠可信。以往的辞书及相关研究著作,引用敦煌吐鲁番写本资料,主要依靠后人的整理本。但由于写本文献整理特殊的困难,后人整理的文本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疏失。词典凡例规定,引用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一律根据原卷(据影印本、缩微胶卷或彩色照片),标明卷号、书名及篇名;或在篇题前注明考古编号,引例后括注影印图版册数及页码。词典引用了五万条以上的写本用例,全部直接摘取自写本原卷,并经逐句逐字反复核对,包括合成后安排专人逐条复核原卷,写定时逐一比对原卷,主编统稿时核对原卷。特别是词目字,凡例规定一般按原卷摘录。如初稿原准备收录“個個”条,核实引文时发现写卷中都作“个个”,再核查全部写卷也没有“個個”或单个字写成“個”的,“個”这样的写法其实是宋代以后刻本文献才流行的,所以词典最后收录的条目是“个个”。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爬梳,词典还收录了不少不见于其他工具书的条目。例如“画指”这个条目,《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都没有收录,但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出现了“画指为信”“画指为记”“画指为验”这样的话,《词典》据以收录,而且还有实物图片为证,图文互证,更有助于词义的说明。
第三是按语创新,回答“为什么”。一般普及型词典通常只回答“是什么”,但本词典定位为学术词典,凡例中明确提出了“明其得义之由”“穷其渊源流变”的高标准,也就是说,不光要回答“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让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词典条目下的1.6万多条按语,就是作者这方面努力的集中体现,学术含金量高。然而敦煌文献内容无所不包,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需要反复斟酌确定。比如“敦煌”这个地名,规范的写法是“敦煌”还是“燉煌”,以前众说纷纭。作者在按语中阐明了这个地名用字产生演变的过程: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立郡至北凉承平十三年(455)的简牍、石刻、写本中,一律都写作“敦煌”;北魏中期至宋初的石刻、写本中大多写作“燉煌”,少数作“敦煌”;唐代有“燉煌郡之印”,用的是从火的“燉”,可见这种写法当时已约定俗成,并被官方所认可。作者指出“燉”其实是“敦”受“煌”影响而类化的增旁俗字,“敦煌”为较早的写法;有人说“燉”为正体,“敦”是其俗写假借,显然是不正确的。这条按语起到了穷源流、明规律、匡正前人谬说的作用。辞书中为补充说明某一问题,在释义、举例后加按语是古有先例的,但像本词典这样按语数量大又富有学术含量的,确实是前无先例。
意大利语言学家斯卡利格说:“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转引自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 1983)我国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1981)也曾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这些话都道出了词典编纂的艰辛与不易。这部词典因为规模庞大,写作本就不易,加上对上述三大特色的追求,更给编写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和工作量,其中的辛劳确实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有时一个词条要花费几天的时间编写修改,字形要分辨清楚,释义要字斟句酌,引文要核实,按语更是花费精力。张涌泉老师说这是他付出心力最多的一部书。他的学生回忆说,好几个大年夜,张老师还在和他们讨论词条的问题。主编之一的张小艳从2001年跟随张老师读博士开始,就一直在进行阅读写卷、摘录词条、撰写条目的工作,廿载青丝成华发,一部词典见证了她从博士到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的成长历程。编写工作异常艰苦磨人,但作者们沉浸于敦煌文献之中,探赜索隐,不时的发现和收获会让他们欣喜不已。板凳已坐十年冷,笔下不写一句空。发现疑问,解决问题,将一个个字、一个个词语解释清楚,将发现和研究成果变成一个个条目、一行行文字,他们身上体现着的正是“文化担当的爱国精神、守正创新的科学精神、执着专注的工匠精神、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杜翔 2023),也就是中国辞书精神。
二、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打造辞书精品
2019年初,词典稿件陆续提交出版社,因为选题的独特价值和作者团队的学术权威性,所以一开始出版社就下决心将词典作为重点产品来打造,在出版的各个环节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力争做成精品。
(一) 制定审读细则
打造辞书精品绝非易事,因为辞书对质量和规范性有着特殊的要求,每个词条无论注音释义,还是引例按语,包括体例格式都需要字斟句酌,仔细打磨推敲。加上稿件字数庞大,又陆续成于众人之手,百密一疏也是难免的。所以编校方面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高度重视,不敢懈怠。稿件是分字母陆续来稿的,在预审了部分稿件后,我们和主编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凡例和稿件发现的问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审读细则,包括用字、注音、释义、引例、排序、照应等各个方面。所有的条目必须一条一条审读,尽可能发现问题,注音是否正确,释义和引例是否一致,引例有疑问的要核对,排序不对的要调整,前后矛盾的地方要标记……稿子比想象中看得更慢,有时要查核相关资料,一小时看不了几个条目,而时间又非常紧张。因为稿件专业性太强,为避免改错,编辑改动的地方必须用颜色标记,有疑问的必须返回作者处处理,除硬伤性字词差错之外,不能擅自改动或增删,绝对不能造成新的审读错误。
在审读过程中,每个字母审读完后都要交给作者处理疑问,作者返回后将新的注意事项或要统一的地方補充到审稿细则中,不断修改,不断增补。所以这个审读细则从最开始的三页到最后的三十多页,涉及上百项的处理。例如题名统一问题。敦煌写卷大多为残卷,原卷有题名者极少,即使原卷有题名的,不同写卷题名也往往不尽一致。今人编目整理时,同一号同一内容被定成不同的题目更是常有的事。词典凡例规定引用敦煌写卷标题尽量尊重原卷题名,同一书题名太过纷杂的酌情统一题名;原卷没有题名的,则根据内容或参考后人的整理研究成果拟题。但由于敦煌文献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书稿规模庞大且成于众手,稿件中会出现不同条目下同样的引文内容,卷号相同,但题名不一样的情况,或者引文不同,但卷号相同,题名大同小异的情况,就需要查核是否题名有问题。如稿件中北敦7364号(北8405;鸟64)的引例出现了《悉昙颂》《俗流悉昙章》《俗流悉昙颂》三种题名,其实这三个标题的引文都来自同一篇,但原稿却用了不同的篇名。所以我们事先就确定将引例篇题的核查作为编辑审读的专项工作之一,尽力做好这方面的规范统一工作。
(二) 斟酌推敲释义
释义是词典的灵魂。条目释义要做到准确简明概括,需要反复推敲比较。像“乏羊”条的释义,原稿释为“虚弱有病的羊”,“乏”有“虚弱”之义没有疑问,但为何释为“有病”,编辑审读中有些疑惑。在肯定这是西北方言词语后,编辑查阅了《兰州方言词典》《新疆方言词典》《西安方言词典》《西宁方言词典》等资料,发现“乏”有“疲乏、疲倦”的含义,新疆方言中还有“没有力量”之义,但都没有“有病”的意思。又请教了甘肃本地的朋友,知道当地现在还有“乏羊”的说法,指冬春之际青草不接时缺乏营养的羊。将这些材料反馈给作者后,作者团队斟酌后将释义改为“体质虚弱的羊”,并补充了按语说明。又如“梬枣”条,原稿直接释为“黑枣”。看见黑枣,一般读者会下意识地理解为一种枣类。但编辑在西北旅行时曾吃过这种水果,知道它和枣子有比较大的差别,它实际上是一种野生柿类,又称“软枣”“野柿子”“小柿”等,形状与常见的柿子相似,果实个体较小,北方地区常见,但南方人很少见到。作者根据编辑的反馈意见对释义做了进一步补充,避免了可能引起的误解。又如“倒首”条,原稿释义为:犹“倒产”,生产时婴儿的头后出来。复审提出“倒首”即倒头,就是头先出,婴儿出生时头先出为顺产,与分娩时婴儿脚先出的“倒产”意思应该不一样。为保证释义无误,责编建议作者对该条引例“从于产门,倒首而出”再仔细推敲一下,根据上下文确定原文究竟是讲顺产还是逆产。作者最后确认这段文字所述为正常的生产,遂修改了释义,避免了一个大的硬伤。
敦煌文献里包含了大量的宗教文献,其中又以佛教、道教居多,要解释这类词,需要熟悉相关知识及文献,不能望文生义。如初稿将“人风”条释为“同‘仁风。佛家仁慈的风教”,从字面上,“人”“仁”古通用,“仁”有仁慈之意,没有什么问题。但责编对佛教知识有一定的积累,进一步推敲后,认为引例中的“仁”应指“能仁”,是“释迦(akyā)”的意译,指佛陀或佛教,因此建议将“人风”的释义改为指佛家之风教,得到了作者的认可。
(三) 注意引文核实
书稿的引文都直接引自写本原卷,这是本词典的一大特色,保证了资料来源的可靠可信。但由于手写不易辨认、原卷清晰度不够等原因,也会造成失误。如“鸿梁”条引用伯3251号《菩萨蛮》:“昨朝为送行人早,五更未罢至鸡叫。相送过鸿梁,水声堪断肠。”编辑审读时觉得这个“至”字不顺畅,查阅原卷,发现字形似乎介于“至”“金”之间,但从文意看“金”字应该更合适。疑问反馈给主编,原来作者是根据黑白图版录文的,此字原卷略有涂改,但作者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一点。主编当即查检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彩色照片,确认此字原卷确实有涂改,从修改痕迹判断,应该是原本错成了“至”,后来又在原字上改作了“金”。这样顺利解决了这个引文疑问,词意也就更加顺畅了。
敦煌文献用字复杂,不能按我们今天的繁简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很多简体字和繁体字在写本时代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在敦煌文献中“辞”是“辝”的俗字,与“辭”本来是两个字;“”是“与”的俗写,而“与”与“與”古代本来并非同一个字;“向”字敦煌文献中常借用作“餉”,指片刻、一会儿,本字作“曏”,这个字今天作“晌”字,是元代以后才产生的新字,敦煌文献那个时代并没有出现,等等。我们不能根据现在的繁简观念随意统一,有疑问时需要查核原卷,做到改必有据。
(四) 处理相关照应
词典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与一般图书不同,它会涉及很多相关照应的处理和体例的统一,改动某处的一个字就会造成全书多个地方需要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编辑过程中就需要做专项处理,如条目的收录、多音字的注音、参见条目、释义的详略、附件与正文是否矛盾重复、行文风格是否一致等,一项也不能少。就拿参见条目页码填写来说,编辑处理时需要对照两台电脑,一台定位查询所参看的条目页码,再在另一台上将页码手动添加到参看条目处,这样读者可以根据页码准确找到参看的地方。由于詞典收录了大量的疑难俗字、异体字、通假字、异形词,同一个字形可能出现在好几个字词群中,编辑在处理参看专项时,必须逐条阅读二者之间的释义,比较按语的相关性,仔细辨别、确定无误后再进行添加。如S部“薩”字下“艹”条末标注参看“”条,编辑通查条目后发现,“”这一字形在词典中共有两条,一处义为菩提,另一处义为菩萨,而这里“薩”字下的“艹”为“薩”的省文,应参见对应菩萨义的“”。如果看到菩提义的“艹”时就直接添加,不进一步对比分析,很可能就会出错。这样的问题看似细小,但一不小心就会造成硬伤。这就需要编辑每添加一处页码,都要对词典文档内容进行通读,遇到所参看的内容有多个字形相同的条目时,需要认真甄别,疑问之处还需团队讨论或请教作者,以确保参看页码的准确无误。
(五) 解决排版难题
词典中俗字、疑难字较多,很多字在现有字库中找不到,有的字虽可以找到,但调用到排版软件中又不能显示或者直接乱码。书稿中共有9200多个造字,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造字首先要造对,不能有笔画错误;其次要造得好看,美观匀称。在排版过程中,造字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是未仔细辨识构件,照排人员直接采用现有规范字形中的相近构件,造成或缺笔或多笔,或繁简用错,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拿“逃”字头下的条目“”与行文中的“”来说,它们右上侧的部件分别为“土”和“匕”,从电脑上看很容易忽略,照排人员没有注意到二者的细微区别,就将它们误造为一个字。还有的部件粘连,造成字形内部构件不清晰甚至重合。如“”字为上“禾”下“衣”,造字时“衣”字上一点与“禾”字下一竖粘连在一起,造成点与竖重合,导致点缺失。有的造字会被拆分成两个字,如王勺勺,直接读,似乎作为人名没有什么问题,通过对照原卷,才发现是两个“勺”部件构成的一个字。这样的问题极其考验编辑对文字的敏锐度和前后照应的能力。还有的造字部件都对,但整体构形很不美观,怎么调整得协调、美观,就需要编辑和照排人员反复沟通,更多时候要亲自守着排版人员来调整。
除造字之外,截图字对排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敦煌吐鲁番写卷中的有些手写字形笔画粘连,辨认不易,转录时经常有分歧。为增加可信度,作者在引录时就会用截图处理。书稿中这样的截图字有6100多处,这些截图字多数随正文编排,有些为说明字形演变要根据内文做放大处理。行文中的截图字字号大小要和前后文字一致,否则会造成行距忽大忽小的问题;颜色浓淡也要调整,不能太黑,否则就是满版黑疤,非常难看。截图字因为截取自写本原卷,会有底色和脏点或者多余的笔画,必须一一处理。有些截图字笔画复杂,同样大小看不分明,就要适当放大。这些都需要编辑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处理,不能一键解决所有问题。
在新书首发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先生发来贺信说:“此书俗字、异体等怪字繁多,排版也非易事,出版方劳苦功高。”这确实是知者之言。
三、 相互协作,发挥团队作用,是词典高质量出版的关键
词典的出版,有赖于各个环节的精诚合作、协调配合。
首先是作者团队的鼎力支持。词典编写团队成员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著名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他们均为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具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和开阔的研究视野,在专业领域享有很好的声誉。第一主编张涌泉教授是资深的敦煌文献研究专家,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对稿件要求非常严格,可以说是我们接触到的最认真的作者。从内文审读到彩图、封面设计,小到按语用字的底色灰度,他都会提出意见和要求。作者团队有个编写群,编辑团队有个审读群,编辑和主编还有一个项目群,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沟通处理。对我们审读的反馈意见或建议,张老师会一一细心回复;对我们提出的有价值的疑问,他会不吝表扬;碰到他们自己的硬伤,他会主动承认错误,并分享到编写群里;对我们应该看出而没有看出的问题,他也会毫不客气地直接批评。张老师和团队成员的严谨细致与实事求是,让我们在审读时不敢也不能掉以轻心。虽然有时我们会为了一个问题产生争议,但最终大家都能找到一个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
这部稿子让我们见识了一流学术团队的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敦煌文献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内容无所不包,要把疑难字词解释清楚,需要反复斟酌确定。比如词典中有收录“透贝”一词,编辑提出疑问后,作者在群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了准确解释它的意思和得名之由,主编先后通过各种方式请教了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东华大学等单位的七八个专家,编写团队又对专家意见反复商讨,最后才修改定稿。可以说每一个词条的背后都凝聚着编者的汗水和心血,也体现了他们的智慧和执着。
其次是特约编辑和审读专家的严格把关。虽然我们的责编都是古典文献学或古代文学的硕士博士,也有敦煌学专业的背景,但考虑到词典的特殊性质,我们在社内编辑初审的同时特意加了一道外审程序,约请了四位博士审读书稿,特约编辑与社内编辑共同把关,相当于初审多一双眼睛多看了一遍。复终审约请的是资深编审郑红老师、骆小平老师、左大成老师、杨宗义老师等人,他们都是语言文字和词典方面的专家和老编辑,有着丰富的大型辞书审读经验,提出了不少作者和责编忽略的问题。除出版社审读外,我们和主编商量,又约请了近代汉语研究专家、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周志锋教授通读全稿。周老师曾长期担任宁波大学学报主编,也是一位资深编辑。他审读非常专业细致,除指出了不少字形和释义问题外,还对释词的规范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如释义用语“指”“比喻”“形容”应该区分,释义要注意语意轻重等,为词典的规范化做出了贡献。
术业有专攻。考虑到词典的百科性质,在付印之前,主编又出面約请了不同领域的顶尖专家,如长于历史文献、佛教文献的郝春文教授,长于天文历法的邓文宽研究员,长于语法词汇的杨永龙教授,长于文学的伏俊琏教授,长于石窟壁画艺术的赵声良教授等,请他们分别审定了相关条目。专家们都给了我们很好的意见与建议,如邓文宽研究员提出历书中断句要注意的问题,并指出伯5548号《唐乾宁二年(895)具注历》引文“廿七日癸壬、木、定,蛰虫坏户”中的“癸壬”不太对,一查,果然“壬”原卷不太清晰,仔细辨认其实应该是“丑”字。这样一道道把关,确保了词典的质量,也让我们学习到从不同角度把握稿件的诀窍。
三是出版社团队成员的相互支撑与各部门的紧密配合。550万字的书稿需要逐字逐句审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年来,编辑们周末的大部分时间也都用在了书稿审读上:初审,处理外审和复终审意见,反馈修改建议,处理作者增补材料,相关照应处理……词典中许多条目都有造字,在用排版软件制作笔画索引时,无法识别造字的笔画和笔顺,因此需要人工干预,逐一清数造字的笔画、笔顺,才能将其安插到正确的位置。这是一项重复、繁琐且费时的工作,必须耐着性子,十分小心,才能保证准确。尤其是一些相似造字,多一点少一笔,很难区分。更有同一个字造出两个字形的情况,令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不细心辨认,就会出错。所以在检查索引时,我们动用了十多位编辑和校对人员花了好几天时间集体会战,第一道笔画笔顺做完后又互相检查,查漏补缺,最大程度地保证索引的正确,而且从索引核对中也可以发现正文可能忽略的问题。在印制环节,烫金和内封浮雕压印都很考验手艺。尤其是浮雕压印,力度稍微重一点颜色变深变黑,稍微浅一点立体效果不好,制作部人员和设计师一起守着印刷厂的师傅反复调了多次,才调出了想要的颜色与效果。
辞书是一个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标志。这部沉甸甸的词典让我们深入敦煌文献语言的世界,对敦煌文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作为辞书出版人,我们深深体会到作者编写的艰辛,也深深明白优秀的辞书对文化传承发展的意义,出版这部词典,用实际行动践行、弘扬“中国辞书精神”,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也无怨无悔。
词典出版后受到学界和读者的欢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售罄重印,这让我们深感欣慰,所有的等待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江蓝生先生(2022)曾说:“辞书编纂是一个永远有遗憾、很难达到完美的工作,一部大型词典通常需要用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打磨才能臻于成熟、完善。即使是一部成熟的词典也不能一劳永逸,仍要随着时代和语言生活的变化而不断修订改进。”词典的修订工作永远在路上。我们将和作者团队一起努力,精益求精,让这部词典更加完善,更好地服务学术和读者。
参考文献
1. 陈原.编写辞书的精神和态度——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的讲话.辞书研究,1981(2).
2. 杜翔.中国辞书与中华文明传承.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12-06.
3. 江蓝生.《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理念与学术特色.语言战略研究,2022(1).
4. 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Ladislav Zgusta)主编.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王祝英 巴蜀书社 成都 610023;冯英梅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成都 610207;杨 丽 四川辞书出版社 成都 610023)
(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