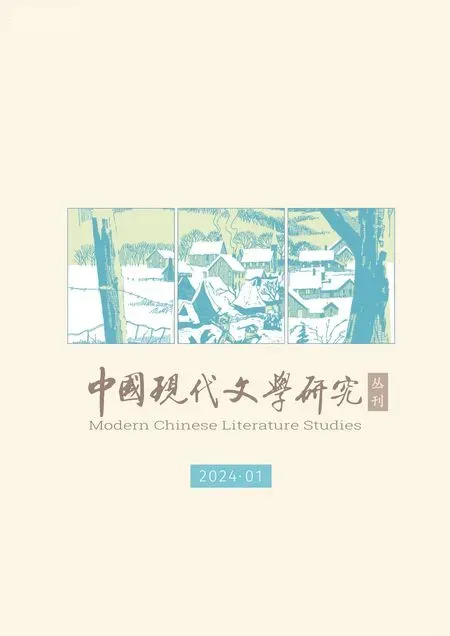曹禺戏剧伦理叙事的特征及其剧场性效果※
刘 璨 刘家思
内容提要:曹禺戏剧的剧场性很强,与其民族化的伦理叙事关系密切。曹禺戏剧不仅描写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的不同层面,而且往往是交织起来表现,呈现了生活的复杂性,表现了思想的深刻性。他以深入人物灵魂的内视角展开伦理书写,在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发展历程中展示伦理问题的重要影响力,其伦理叙事不仅是多向的、复杂的,而且充满悖论性,但都蕴含着破坏性。这种伦理叙事不仅加大了塑造人物的力度、反映生活的广度和表现思想的深度,而且增强了戏剧的艺术张力,扩张了现场的交流场域,激活了作品的剧场性,既使精英内涵通俗化,又使世俗生活陌生化,还使性格描写精细化,反映了曹禺执着的艺术追求,呈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曹禺戏剧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学文学性与剧场性兼具的文体范式,收到了既可读又可演的预期效果。其奥秘,自然在于曹禺对戏剧艺术执着的剧场性追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戏剧审美风格。这不仅仅是一个技巧运用的问题,也涉及曹禺戏剧的方方面面。1参见刘家思《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民族化的伦理叙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曹禺戏剧是以伦理叙事为主体的。从《雷雨》开始,伦理叙事一直强劲地主导着曹禺的创作路向。他以写人为中心,总是从伦理问题切入,表现了特定历史境遇中人们在伦理关系中难以自主的复杂状态。对于曹禺戏剧的伦理书写状况,我们已经撰写论文《论曹禺戏剧创作中的伦理问题》,对其伦理环境、人物伦理身份的生成、伦理自觉与伦理选择以及作家的伦理立场与伦理表达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刘家思、刘璨:《论曹禺戏剧创作中的伦理问题》,《文学跨学科研究》2021年第3期。,但限于篇幅,对于曹禺戏剧伦理叙事的基本特征及其剧场性效果等问题未展开研究。这个问题是影响曹禺戏剧接受效果的重要问题,不研究不行。因此,本文试图借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方法,就曹禺戏剧伦理叙事的特征及其剧场性效果诸问题进行一点探讨,以期就教于大家。
一 曹禺伦理书写的力度与特征
任何剧作家的作品不可能不书写人类的伦理问题,然而对于伦理书写的重视程度、描写视角以及用力所向都影响艺术效果。如果说将伦理叙事作为一种点染,或者是简单地用外在的旁观者批判立场,或者是脱离人物描写讲伦理道理,都是会失败的。曹禺的戏剧不是这样,他将伦理叙事作为戏剧故事构成的主体,用深入人物灵魂的内视角展开伦理书写,在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发展历程中展示伦理问题的重要影响力,形成了多向性、悖论性、破坏性三个特征,呈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一)多向性。在曹禺的戏剧中,“剧中人物总是被置于一种亲缘、情感、主奴等多重关系构成的网络之中”2刘家思、覃碧卿:《非常态的三维放大与扭曲变形——从人物关系预设看曹禺戏剧的剧场性追求》,《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其伦理叙事呈现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多向性。因为社会的复杂性和生活的丰富性,导致了伦理存在着不同层次和多向性,甚至是复杂性。伦理是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要求,在人类社会,虽然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普适性的伦理要求,但因为文明的程度不同,社会的境遇不同,社会伦理规范是不一样的。即使文明程度和社会境遇完全相同,由于个体的身份不同,其伦理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而个体的伦理行为也会不一样。曹禺戏剧的伦理叙事就充分反映了种种复杂状态。一方面,曹禺戏剧的伦理叙事在同一个层面呈现丰富性,是多重交织的。如《雷雨》是一部家族伦理叙事的经典之作,孔子所讲的“父父、子子”与孟子说的“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是其基本的伦理要求。但是,在周家内部,个体的伦理行为并不是这样的。作为周家的一家之主,周朴园有着很强的事业心,也有着封建伦理理想。他认为自己的家庭符合封建伦理规范,是最有秩序的。他始终按照这种理想去维护家庭伦理,不仅要求蘩漪在孩子面前要做一个服从的榜样,还幻想他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能叫别人说一句闲话。但是,他注意到了“父父、子子”与“长幼有序”,可是没注意到“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因此导致了家庭伦理崩溃,不仅出现大儿子与妻子乱伦的丑相,而且引起了双重乱伦的罪恶,造成了妻离子散的结局。同时,他在社会上尽力做一个慈善家,可又在包修江桥时故意淹死工人,谋取抚恤金,并用警察镇压罢工的工人。这种丰富性充分显示了封建伦理的虚伪性和末日气象。另一方面,不同层面中又呈现出复杂性。曹禺戏剧的伦理叙事不是单一的线形发展的,而是多线并进,不是将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交织在一起,就是将家庭伦理或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结合起来,因而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北京人》的艺术描写将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紧密结合,二者互为作用。曾公馆曾经是士大夫家庭,如今已经败落,不仅与邻里关系紧张,而且家庭关系也充满矛盾,混乱不堪。虽然他们对于租房的袁任敢父女俩表面友善,可背地里极端蔑视;他们向邻居杜家借债未还,不能信守诺言及时还账,被频频逼迫以楠木棺材抵债,却还迟迟不答应。在家庭内部,曾思懿既不孝敬老人,也不友爱平辈,还不慈爱晚辈,弄得全家鸡飞狗跳。这种家庭伦理的混乱加剧了邻里关系的紧张状况,而邻里的伦理失范也造成了家庭伦理的混乱。这恰恰显示了黑暗时代的本质特征。在抗战时期,展现这种混乱状态的背后,还隐隐约约显示出民族国家的伦理规范问题。这种多向性,显示了曹禺戏剧内涵的丰富性。
(二)悖论性。曹禺戏剧伦理叙事不是简单地进行伦理教化,一味展开道德批判。伦理总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道德关系是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并依据对伦理关系的正确认识而自觉进行道德建构和维护。当人们对于自在的伦理关系缺乏认识,甚至无视伦理时,就会出现道德问题,进而带来伦理关系的崩溃。然而,伦理关系和道德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关系,这种共鸣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往往呈现出复杂状态。曹禺戏剧的伦理叙事不是简单的伦理批评和教化,而是充分展示它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悖谬性,因而曹禺对伦理主体既有批判也有同情。从《雷雨》到《北京人》,从《日出》到《桥》,从《胆剑篇》到《王昭君》,无论是描写家庭伦理还是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在个体身上都充满悖论性。蘩漪在家里与前妻之子乱伦是不合伦理规范的,但是从年龄、出身以及受教育的程度,从人性中的爱欲,从周朴园对她的专制和冷酷,从倡导民主与个性的社会新思潮来看,她的这种乱伦行为又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蘩漪身上充满着伦理的悖论与张力。曹禺对此充满着同情与理解,甚至将她看作是“英雄”。他说:
我欢喜看蘩漪这样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贫弱的,我知道舞台上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做成一种不可相信的参差。不过一个作者总是不自主地有些姑息,对于蘩漪我仿佛是个很熟的朋友,我惭愧不能画出她一幅真实的像,近来颇盼望着遇见一位有灵魂有技能的演员扮她,交付给她血肉。我想她应该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这样的不幸的女人里,蘩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1曹禺:《雷雨·序》,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显然,曹禺是从时代背景和蘩漪的遭遇中来理解和同情她的非伦理的行为的。这显示了曹禺的伦理价值取向:当社会伦理规范落后于时代,成为生命的桎梏时,就可以打破它。这体现了曹禺尊重生命的现代性情怀与视野。在《日出》中,潘月亭与陈白露之间的关系是不合社会伦理规范的,但是潘月亭可能并没有家室(剧中未提及),他们之间相互信任与理解,似乎又潜存着几分值得理解与同情的因素。《家》将瑞珏送到郊区去生产,致使其身亡,表面上是符合伦理要求的——不使死者高老太爷得血光之灾,是孝敬长者的表现,可是它建立在牺牲晚辈的基础之上,则又极其荒谬。《王昭君》响应号召,主动离开汉元帝,前往匈奴,为国家安宁尽责,符合国家的伦理规范,显示一个国民应有的伦理取向,但她从此远离汉宫,别亲弃君,并不圆满。显然,这种悖论性特征,自然也反映了曹禺伦理观的现代性取向。
(三)破坏性。伦理关系旨在维持人际关系和社会的稳定。伦理关系一旦形成,就要求人们遵从伦理规范。当人们认识到某种伦理关系时,就会维持这种关系的稳定;当人们出于种种原因,打破这种关系时,就会陷入混乱状态,破坏已经拥有的稳定环境和秩序,打乱人们已有的生活状态,危及人们的生存意志。曹禺戏剧对这种状况进行了突出表现,这就形成了曹禺戏剧伦理叙事的第三个特征——破坏性。从《雷雨》、《日出》、《原野》到《北京人》、《家》,甚至从《蜕变》到《胆剑篇》、《王昭君》,都显示了这种“破坏性”。在《雷雨》中,周萍与四凤乱伦行为的曝光,立即打乱了所有人预设的人生定位,从而将整个戏剧推向高潮;在《家》中,觉新结婚闹洞房时,高克定、高克安等人的胡闹,趁机泄欲的丑行一拉开,立即揭露了高家内部污浊不堪的乱象,接着高克定骗取妻子沈氏的首饰银钱,在外嫖娼宿妓,这种丑行被识破后,高家从此走向溃败。《胆剑篇》中的伯嚭卖国求荣,被越国君臣所利用,戏剧立即形成了转折。可见,曹禺戏剧的伦理叙事不是谋求和谐结局,而是呈现伦理选择的不当对现有生存秩序的危害。曹禺戏剧的这种伦理叙事特征,显示了伦理问题本身拥有的巨大力量。它告诉人们:无论是对于家族,还是对于社会,或者是对于国家,不同层次的伦理规范,都是个体必须遵守的。一旦不遵守,就会招来大祸,轻则毁灭家庭,扰乱社会,重则毁灭国家。曹禺之所以凸显这种破坏性,除了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之外,也反映了他对戏剧艺术的追求。
总之,曹禺戏剧的伦理叙事显示了伦理与道德的密切关系及其在文学描写中的独特意义。他以深入生命与灵魂的笔力描写特定境遇中的伦理行为,显示个体的伦理认知与道德判断在一个黑暗时代不由自主的状态,揭示了它潜在的巨大力量,即不仅能够促使个体生命陨落和毁灭,而且能够打乱现有生存世界的社会秩序,危及民族国家。它告诉我们,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必须注意伦理关系的建构与完善,与时俱进地引导个体的伦理行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曹禺戏剧,必须把握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曹禺戏剧的伦理叙事所展示出来的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复杂性、悖论性、可变性和破坏性。
二 曹禺戏剧伦理叙事的剧场性效果
剧场性是戏剧重要的特征。“所谓剧场性,是指戏剧家预设的戏剧对受众所拥有的‘现实’审美裹挟力和‘剧场’审美感知度的规定性,是一种支配受众的艺术强度。”1刘家思:《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第41页。曹禺以执着的现实主义精神进行戏剧创作,致力于对社会现实作出深刻的描写,对人类与自然、宇宙与命运、个体与群体、民族与国家的伦理关系展开探索,营造了强烈的剧场性。全面审视曹禺的戏剧,便可发现,伦理叙事不仅加大了塑造人物的力度、反映生活的广度、表现思想的深度,而且形成了戏剧的艺术张力,扩张了戏剧现场的深层交流,激活了作品的剧场感应,呈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一)精英内涵通俗化。曹禺是戏剧大师,深谙戏剧艺术的本质,懂得“一个弄戏的人,无论是演员,导演,或者写戏的,必须立即获有观众,并且是普通的观众”2曹禺:《日出·跋》,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戏剧的主要受众既然是普通的观众,戏剧创作自然要寻找适合普通受众接受的艺术形态。因为,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品质是高雅的。戏剧并不是大众艺术的同位语,而是要以精深的思想作为灵魂。曹禺戏剧对宇宙与人生、人类与自然、民族与国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对生命展开了鲜活的书写和表现。《雷雨》所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是作者“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1曹禺:《雷雨·序》,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1卷,第7页。这种形而上的探索与思考,有着明显的哲学家思想的深奥,是适合精英阶层的审美需要的。然而,如何将这种思考赋予大众接受的可能性,曹禺是动了心思的。这就是将这种哲学思考灌注在伦理叙事之中。它借助两个乱伦故事的主角的人生突围来表现,将严肃的思考寄寓在通俗化的戏剧故事之中。这种叙事方式,不光使描写家族题材的戏剧将精英内涵作了通俗化表现,而且在描写社会题材的作品中也让高深的思想融汇在大众接受的框架体系中。从《蜕变》到《王昭君》,都是以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指向的,但曹禺从国家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关联性切入,效果惊人。如《王昭君》的叙事是以国家伦理为基础的。匈奴单于呼韩邪来长安求亲,要迎娶大汉帝国的美人为阏氏,汉元帝命令宫女参选,王昭君自愿请行。王昭君凭借其德行昌懋,聪慧知礼,被选为单于阏氏,奉旨出塞,封为宁胡阏氏。本来,王昭君在汉宫生活安稳,她的姑姑也对她充满期待,为她争取到了高升“美人”的机会,而她这一选择就打乱了常态,不仅使她姑姑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改变了她作为宫女的稳定生活。而成为阏氏后,她与单于的爱情生活、与王公大臣的关系就立马摆在她面前,这就将国家伦理的宏大叙事转换成了具体可感的人间爱情故事,接近了普通受众的审美要求。显然,伦理叙事能够化大为小,化深为浅,化雅为俗,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叙事范式,在戏剧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世俗生活陌生化。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描写现实生活,反映世俗人生的生存状态,揭示社会问题,传达作者的独特思考,是戏剧的主要宗旨。但是平庸的世俗生活并不具有戏剧的品格。写进戏剧中的生活尽管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必须要符合戏剧艺术的审美要求,要能够激活受众的审美情趣。因此,戏剧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戏剧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不管在什么情形下,形成艺术的陌生化,是一个通行的路径。显然,艺术的陌生化就是以新奇感来激活受众审美接受的欲望。曹禺戏剧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审美吸引力,还在于他的戏剧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效应。这与伦理叙事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说,曹禺戏剧的伦理叙事使世俗生活拥有了陌生化的品质。因为伦理关系是以个体的人生为表征的,反映出个体私密性的内容,这往往能够形成陌生化的效应。《雷雨》的双重乱伦叙事的爆炸性刺激效果自然无须赘述,其他作品也都拥有了陌生化的新奇感。《原野》既是家族伦理叙事,也是社会伦理叙事。仇虎是焦母的干儿子,是非常老实忠厚的焦大星的好朋友,可他与焦家有深仇大恨,因为不仅他家的田产被焦阎王抢占了,而且他的父亲、母亲和妹妹都被焦阎王害死了。因此,他从监狱里逃出来后,直奔焦家而来,就是要复仇。可是,仇人焦阎王已经去世,他首先碰上的是焦大星的媳妇,自己曾经的未婚妻,这就使戏剧有了陌生化的机制。仇虎如何应对?受众要去探秘。这就能够激活受众的审美欲望,使戏剧拥有了剧场性活力。《蜕变》是关于国家伦理的叙事。抗战爆发后,全国形成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尽责的国家伦理要求。然而,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医院院长及其一班人是如何表现的呢?医院里腐败不堪,肆意侵吞公物,贪污公款,当听到上级派了梁专员来视察,庶务主任马登科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急于设法应付。院长秦仲宣不仅生活腐化堕落,其“姘头”在医院气焰嚣张,而且他对医院疏于管理,失职渎职,还大吃大喝。这种违反国家伦理要求的丑行自然也形成了剧场的艺术张力,能够激发受众的审美兴趣。可以说,伦理叙事为曹禺戏剧营造剧场性做了准备。
(三)性格描写精细化。戏剧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剧场性的内核是人物。人物描写的成功与否,决定着剧场性的强弱和戏剧的成败。因此,一个优秀的戏剧家,总是会将人物放在戏剧创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创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以强化剧场性。作为戏剧大师,曹禺精于戏剧人物的刻画。他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人员,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我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上。”1曹禺:《看话剧〈丹心谱〉》,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5卷,第253页。然而,戏剧人物的塑造不同于小说人物的塑造。小说可以通过叙述徐徐讲来,慢慢完成人物的刻画,全面地呈现其性格心理、思想感情、人生状态和命运遭际。但是,戏剧人物一上场就必须要显示其性格,要能彰显其命运遭际,否则剧场性就不强。那么,如何尽快凸显人物性格,显现其命运状态,是戏剧家普遍的用心所在。综观曹禺的戏剧,其人物描写都很成功,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曹禺将人物置于伦理困境中。众所周知,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是在人际交往中显示的,戏剧家必须建构好有利于人物性格与命运表现的人际关系,而伦理关系的建构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人物的精神与性格会主导其主体行为取向: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通常会遵从世俗的伦理规范,一个性格温和稳重的人也会顾及社会基本的伦理规范,一个先贤者往往能够遵从伦理却又不同凡响地引领新的风气,一个拥有现代知识者往往不会规规矩矩遵从庸常社会的伦理规范,一个被压抑、被伤害的人则会不顾伦理关系反抗周围世界。因此,伦理叙事能够形成道德关系集中的人物境遇,使人物的精神与性格得到集中表现,从而形成戏剧的感染力。
在曹禺笔下,从蘩漪到周萍,从陈白露到潘月亭,从仇虎到花金子,从愫方到曾皓,等等,都是在复杂的伦理关系中集中显示其精神性格。他们既矛盾又极端,既阴鸷又偏激,既忧郁又坚定,但都不妥协、不缓和、不退让,特异的行动形成了各自的性格张力与命运魔力,任其如何左冲右突,都始终只能在天设的陷阱里打滚。曹禺总是以伦理场域中人物性格的多面性激发剧场活性。如《雷雨》第三幕中对四凤的描写尤其典型,基于伦理欲望,却又限于父母在家和已经被周公馆辞退的伦理环境,四凤希望周萍来见最后一面,就显得非常犯难。作者精细地表现她做出这种伦理选择时的复杂状态。曹禺“用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表现她这种复杂的心理,其中灯光亮度的调适就是一个重要手段”1刘家思、刘桂萍:《论曹禺戏剧的光色艺术及其剧场性追求》,《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这既描写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又刺激了受众,强化了剧场性。在曹禺戏剧中,这种状况是很普遍的。如《雷雨》中,蘩漪第一次与周萍相见,周冲在场,他们皮里阳秋的谈话就生成了剧场撬动受众思维的力量,形成了裹挟注意力的场势;而“喝药”那场戏也是由复杂的伦理关系和特定的伦理行为将戏剧“逼”向了白热化。在《日出》中,“救孤”一场戏之后,方达生、潘月亭和陈白露的结尾戏,也是因为伦理关系的复杂凸显,赋予了戏剧场面的活性。在《蜕变》中,“禀报”那场戏,则是因为国家伦理规范与个体私欲取向的冲突而形成了强烈的戏剧效果。在《北京人》中,“议婚”那场戏,也是因为复杂的伦理关系而使硝烟弥漫的战场变成了一场阴阴阳阳的闹剧。在《原野》中,仇虎与焦母第一次正面展开“龙虎斗”的那场戏,还是因为伦理关系的催化,使整场戏显得富于韵味。如此等等,伦理关系的介入,使人物性格呈现出多重性,有了各种特异的举动与表现,显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与思想,这就能够博取受众的同情和共鸣,从而增强剧场性。
可见,曹禺戏剧的伦理叙事,不是简单地依据社会学来设置剧中人物关系,而是从营造剧场性的目的出发预设伦理困境,使人物跌入宇宙这口“残酷的井”里,无论他们怎样自以为是地做出最佳的伦理选择,“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1曹禺:《雷雨·序》,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1卷,第8页。。这样,不仅人物性格的描写更加精细而立体,而且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张力,同时还使其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陌生化的效果,在新异独特的形态中形成了牵引力。于是,一种既适合精英接受又适合大众接受的普适性剧场裹挟力就自然形成了,戏剧的剧场活性在一种世俗的伦理悲剧背后被强化,从而产生了主导受众接受欲望的多重可能性。因此,曹禺戏剧告诉我们,伦理叙事与剧场性营造有着密切的关系。
伦理叙事是文学的基本形态,戏剧创作绕不开伦理问题,曹禺的戏剧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描写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的不同层面,但曹禺的戏剧绝对不是简单地从一个伦理层面来叙事,而往往是交织起来表现,既呈现了生活的复杂性,又表现了思想的深刻性。他将伦理叙事作为戏剧故事构成的主体,用深入人物灵魂的内视角展开伦理书写,在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发展历程中展示伦理问题的重要影响力,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增强了戏剧的艺术张力,激活了作品的剧场性,显现了曹禺戏剧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