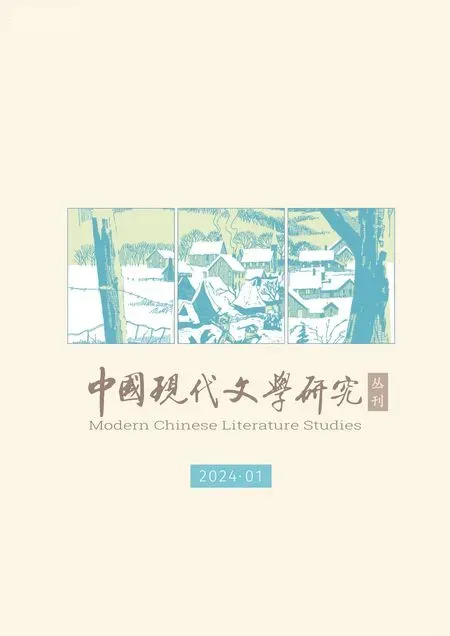鲁迅“透底”修辞的哲学底基※
曹禧修
内容提要: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在鲁迅看来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也是鲁迅论人论事不可逾越的底线;是鲁迅“透底”修辞的底基,也是鲁迅生命哲学的重要基石。鲁迅叙事,往往一两句话便把伦理批评推到人生存与发展的底端,从而使其荒谬性一目了然,不仅展示其“透底”修辞的妙处,也显示了其“透底”修辞的哲学底基。如果说鲁迅“透底”修辞的哲学底基在其小说叙事中还算比较含混和模糊,那么在其杂文叙事中却是清晰和明确的,尤其是《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这两部长篇杂文可算是《阿Q正传》的理论版。
人们常把鲁迅叙事比喻为投枪匕首,能一击致命;从风格学上讲,是说鲁迅叙事长于批判;从修辞学上讲,则是说鲁迅叙事长于“透底”。所谓“透底”,有两层意思:一是叙事语言直抵事物形态学的规定质,把事物存在的底基展示给读者。二是指叙事语言击穿事物存在的旧底基,抵达新底基。1曹禧修:《“透底”与“立人”:鲁迅修辞论的两大理论基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9期。无论哪一种透底,透底必有其底基,也即“透底之底”,否则就如鲁迅所说,必然落入“无底洞”的荒谬中:“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来只剩得一个无底洞。”1鲁迅:《透底》,《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从普遍意义上讲,底基直指事物质的规定性,它是事物彼此相区别的哲学质素或者说哲学分界线。因此,我们讨论鲁迅透底叙事的底基,实质上也就是讨论鲁迅叙事的哲学基石。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鲁迅:《忽然想到 (六)》,《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统观《鲁迅全集》,一言以蔽之,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也是鲁迅论人论事不可逾越的底线;是鲁迅“透底”修辞的底基,也是鲁迅生命哲学的重要基石。
一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礼记·内则》), 这是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对男女分界的一种伦理划定。由男女七岁之后不同席、不同食,可进一步推定男女七岁之后不同泳、不同行、不同台演戏等。据说非洲土著男女之间的避忌更加夸张,做女婿的即便是遇见自己的岳母,也得把身体伏在地面上,还得把脸埋进泥土中。无论古老中国的礼仪,还是非洲土著人的禁忌,其初衷固然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运行而制定的一种伦理规范。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传统礼仪中的人们来说,要从理论上驳斥这一伦理规范的荒诞性往往费力不讨好,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此,鲁迅在其杂文《奇怪》中的驳斥方法却颇简单:短短一句话就把这个伦理问题推到“个体生存”的底端,从而使其荒谬性一目了然,不仅展示其“透底”修辞的妙处,也显示了其“透底”的哲学底基。
……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3鲁迅:《奇怪》,《鲁迅全集》第5卷,第571页。
男女不同席、不同食、不同行等,这是可以做到的;然而,要禁止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绝对不被另一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又如何能够做到?——倘若不能禁止空气流通,便只能禁止个体生命的自由呼吸了,这显然突破了个体生存的限度。鲁迅由此便向男女禁忌伦理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然而,这个伦理难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男女分界的伦理法就不免要破产了。
既然人活着就不能不呼吸,同时也没有选择性呼吸的特异功能,那么给人加上辅助工具又怎样呢?让读者忍俊不禁的是,鲁迅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进: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凯末尔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1鲁迅:《奇怪》,《鲁迅全集》第5卷,第571页。
为了解决男女之严防这个世界性难题,男男女女各自头戴防毒面具、身背防毒箱体生活。就像火药用来制作鞭炮、指南针用来看风水,科学在中国又一次用来解决中国伦理性难题,真正让人啼笑皆非。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2鲁迅:《安贫乐道法》,《鲁迅全集》第5卷,第568页。在杂文《安贫乐道法》中,鲁迅同样展示了其“透底”修辞的哲学底基不是别的,而是“个体的生存”。不过,请注意:鲁迅在此并非要否定安贫乐道之“道”,也并非完全否定安贫乐道之“法”,而是在否定安贫乐道之“法”中“十全大补的功效”。
劝人安贫乐道的方法很多,但是较为普遍也较有说服力的大概有两种。
其一,教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要有兴趣。其隐藏的逻辑是,人只要对自己工作感兴趣了,那么一切其他事情便可从道、从简、从贫了。不过,在鲁迅看来,这仅限于活络轻松的职业者,而对于重体力的劳动者来说并不适用:“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1鲁迅:《安贫乐道法》,《鲁迅全集》第5卷,第568,568,568、569,568页。也就是说,一旦突破个体生理的限度,“兴趣说”便必然破产。
其二,采取“现象对比”的描述法来劝人安贫乐道,比如说:“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2鲁迅:《安贫乐道法》,《鲁迅全集》第5卷,第568,568,568、569,568页。然而,只要把其中的时间节点从“大热天气”推送到“秋凉”时节,相反的现象怕是就要大跌眼镜了。鲁迅说:“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3鲁迅:《安贫乐道法》,《鲁迅全集》第5卷,第568,568,568、569,568页。一旦突破个体生理的限度,这种现象描述法同样会破产。
选择个人感兴趣的工作固然有助于人们安贫乐道,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兴趣再大大不过身体的限度。一旦对生命的安全有碍,再浓厚的兴趣也无助于安贫乐道的选择。只要个体的身体无法抵挡凉风的攻击,“席卷天下”的快乐便荡然无存,而身体的限度又是因人而异的。因此,鲁迅认为“安贫乐道”之“道”也好,“法”也罢,在具体的理解和实践中不仅要尊重人的生理限度,还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4鲁迅:《安贫乐道法》,《鲁迅全集》第5卷,第568,568,568、569,568页。于此,鲁迅进一步提出了道德伦理的个人差异性的问题。无论人普遍的生理限度,还是人特殊的个性化差异,总之,人的生存和发展是鲁迅对传统道德伦理批判的一条底线原则。
二
“精神胜利法”是鲁迅对国民劣根性极“透底”的一种批判。对于带病者阿Q,鲁迅的立场具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两面性:既哀怜、同情,又痛责、怒批。或许因为小说叙事文体的问题,鲁迅这矛盾的两面立场和态度在《阿Q正传》叙事中颇为含混和模糊,然而在其杂文叙事中却是清晰和明确的;而且无论同情,还是怒批,均基于对人之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尊重,尤其是对个人生存底线的尊重,对个体生命限度的理解与同情,对不顾个体生命限度的痛责和愤怒。
《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两篇杂文近两万字。不过,两篇杂文最奇特的,不是它们的文字长度,而是两篇杂文字里行间满含着鲁迅对于“精神胜利法”带病者的同情、理解和哀怜,对人性弱点的悲悯,同时对蹂躏人性、戕害人性者的愤怒。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篇杂文可算是《阿Q正传》的理论版。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这样起笔,自然让读者心里陡然一惊。依照常情常理,生病是身体给身体的主人找不自在,又如何能是一种福气呢?然而鲁迅笔头陡然一转,提出了“福气病”的两个前提条件:一必须是小病,不是脑膜炎或癌症之类的大病;二必须手头要有存款,不必为衣食担忧;两者缺一不可。看似讨论“福气病”不可或缺的两个前提条件,实则讨论支撑个体生命两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一者个体生命的身体基础,二者个体生存的物质金钱基础。任何一个基础条件出现危机,必促使身体的主人公从高雅之士转向卑微的俗人。可是,人性是向上的,做不成雅人的人们便只能在虚幻的想象中继续做“雅人梦”了。于是,人人都怀有大愿,区别仅在于有些人的大愿从来模模糊糊,自己捉不住也说不出。而在所有人的大愿中,有两个人的大愿颇特别:
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1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从想象的奇特、瑰丽和夸张等方面来看,这两个人的大愿绝不会输给阿Q。从想象的本质上讲,他们都是以幻想形式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从而逃避眼前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
其实,这两个大愿中,各有其奇特和美妙的一面。第一个大愿的奇特和美妙就在于,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阿Q们全部的人生烦恼: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之外,有一个好看的姑娘亦且只有一个好看的姑娘,他从此没有了性饥渴;有一个卖大饼的伙夫亦且只有一个卖大饼的伙夫,他从此不用担心肚子的饥饿;不仅如此,而且一切与争夺食品和性爱权利相伴而生的嘲笑、谎言、欺骗、捆绑、敲诈、勒索、掠夺、殴打、杀戮等邪恶亦不复存在,一切的一切无不彻底丧失了其存在的可能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即便阿Q可以转世,但转世后阿Q还得面对人世间的种种屈侮和凌辱,因为转世后的阿Q依然得活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还得为自己争夺食品和性爱等权利而努力、而拼搏、而挣扎,还不得不面对嘲笑、谎言、欺骗、捆绑、敲诈、勒索、掠夺、殴打、杀戮……然而,这个美丽的大愿却使主人公从此没有了人世间的一切烦劳和困苦。
如果说第一个大愿的核心构件是人生存的物质基础:一个好看的姑娘和一个卖大饼的师傅,前者满足性欲,后者满足食欲;那么,第二个大愿的核心构件则是人生存的精神基础:一个人口吐半口鲜血,却依然病恹恹坚持移步到阶前去欣赏秋天的海棠。无论哪一种基础,鲁迅在《阿Q正传》中没有直接阐说,也不可能直接阐说,然而在其杂文中却有直接阐述。《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两篇杂文共计九个部分(包括《病后杂谈之余》的附记)均以此为重心展开。
人有物质和精神两大层面的基本需求,其中的精神需求,用鲁迅的话说,也就是“雅”的需求。这两大需求,实则轻重不一,因为人类向“雅”的精神需求的核心构件实质上依然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正如鲁迅所说:“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1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67页。因此,人类看似有物质和精神两大基本需求,不过其核心需求还是物质需求,没有物质基础的保证,一切需求都将丧失存在的根基。
“魏晋人豪放潇洒的风姿”历来脍炙人口,其中阮籍和陶渊明两个人洒脱的故事尤为文人学士所喜闻乐道:“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1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68、169页。这两人潇洒的风姿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阮籍何以求为步兵校尉就可以做成步兵校尉,而陶渊明让官田种上秫苗就可以种上秫苗,如果没有非比寻常的社会地位,没有这社会地位带给他们非比寻常的物质基础,他们还能如此洒脱吗?同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人人耳熟能详的雅诗背后的物质基础更是一目了然,如果没有竹篱、秋菊、房屋、南山等物质基础所支撑的悠然人生,这雅诗还能“雅”出来吗?所以说,摆上酒杯的桌子下面,其抽屉里一般都藏着一个算盘,如果在抽屉里找不着这把算盘,那这算盘必然藏在了雅人的肚子里。
从鲁迅的切身体会来说,鲁迅这次所患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鲁迅依然忍不住从“养病”想到了“养病费”,不得不从病床上爬起,又是讨版税,又是催稿费,由此亦与阮籍和陶渊明有了相当的隔阂。不过请注意,这隔阂看似是心灵的差距,实则是物质基础的差距。
在哲学上,人们普遍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部分,然而鲁迅却认为物质基础才是其基础的基础,是其底基中的不可或缺的基石,它包括人赖以生存的身体和物质金钱两个部分。
三
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不仅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而且还要经受各种形式的摧残,那么人性必然扭曲变态,民族劣根性由此而形成,这其中就包括精神胜利法的病态。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最深重、最复杂、最顽固,那是因为中国国民所经受的摧残最残酷、最无情、最无道。对此,我们自可从中国民众历史上所经受的种种酷刑中略窥一斑。于是,在近两万字的杂文《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中,鲁迅转而谈起了中国历史上的酷刑。鲁迅没有就此展开全面阐述,而仅仅选择从中国酷刑之一种的剥皮法说起。
鲁迅把中国式剥皮法按实施主体分为流寇型和官家型两大类,前者以张献忠、孙可望为例,后者以明代、清代两朝的皇帝为例。
张献忠式剥皮在明末清初的野史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1转引自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0页。
把一个活人身上的皮,从头剥到屁股再剥到双腿,直至如飞鸟展翅高翔,这个被剥皮的人还须历经数日不死,否则行刑者必须死。虽然中国的解剖学在明代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线上,然而其酷刑医学却独独穿越到了现代医学的水平。张献忠不过一个穷苦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然而却能把剥人皮的酷刑演绎到“艺术”与“科学”兼备的神奇高度。如果没有悠久的酷刑传统,刽子手纵然是艺术和医学的双料天才,其剥皮术也绝对做不到如此“完美”。试想,这是多少血肉之躯换来的结果,这里需要多少被虐者和施虐者的血肉才能磨砺如此“神奇”的剥皮之刀!
孙可望式剥皮法在清朝禁毁书籍,即屈大均《安龙逸史》中有记载。南明永历六年,也即清顺治九年,南明皇帝永历躲在贵州安龙府,秦王孙可望杀了忠臣陈传邦父子,被御史李如月所弹劾,其结果不是孙可望被追责,而是李如月反遭永历皇帝痛打四十大板,被孙可望剥皮示众。因此,李如月们的人皮被剥落的过程,也是正义、忠诚、善良等民众信仰被邪恶碎尸万段的过程。《安龙逸史》的记载共有三个连缀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李如月被五花大绑捆至朝门,他的面前摆着一筐石灰和一捆稻草。于是李如月与刀手有了如下对答:
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
第二个场景:
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
第三个场景:
……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1转引自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1、172页。
流贼式的摧残惨无人道,而官家式的摧残则远在流贼之上。鲁迅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2鲁迅 :《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第185页。大明一朝的剥皮始于永乐皇帝。当年永乐为做皇帝,虐杀了一大批建文帝的忠臣,景清、铁铉、齐泰、黄子澄、茅大方等无一幸免。
永乐皇帝的凶残有据可查,鲁迅从史料堆中选摘永乐皇帝日常行政事务中的两条“上谕”为证。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3转引自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第186页。
齐泰、黄子澄、茅大方、铁铉等忠臣被虐杀后,他们留在人世间无辜的妻子、女儿、儿媳,包括她们肚子里尚在孕育中的生命,永乐皇帝一概谕令:活着的做“淫贱材儿”,死了便“着狗吃了”。其凶残程度,于此可窥一斑。
中国人向来既被同族屠戮,又惨遭异族屠戮。然而不免令人困惑的是,相比同族官家的暴虐,异族的官家似乎对汉民反而更优待一些。俞正燮甚至由此为清朝歌功颂德,一是认为宽假奴隶的汉皇居少数;二是认为清朝“廓清”了堕民丐户。究其实,鲁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典籍考之未详。在金元时代,汉民中原本蓄奴的主子也成了奴隶,换个角度来看,奴隶与蓄奴的主子,一并高下,一视同仁,地位等同了,奴隶的地位仿佛得到了提升,进而被误读为得以宽假,实际上却是蓄奴的主子降为了奴隶,并非奴隶提升了身份和地位。至于清朝“廓清”了堕民丐户更是一场误会。绍兴的堕民迟至民国之初依然存在,依然需要给大户服役,依然不容许与良民通婚。因此,清朝“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1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第187,186、187页。。清朝虽然没有剥皮的酷刑,却有凌迟、灭族、文字狱等酷刑,而禁毁历史典籍等愚民政策更是触目惊心,汉民所受异族官家的屠戮并不会比同族官家少。
就对民众的暴虐而言,官家与流贼,同族与异族没有实质的区别,如果说官匪一家,并不夸张。拿孙可望来说,他先是明朝的造反者张献忠的养子和部下,张献忠死后便投靠了被造反者永历皇帝,被封为秦王,成为保明拒清的柱石,是吃官家饭的,再后来索性又投降了清朝,继续屠戮汉民和非汉民,他既是流贼,也是官家,他既是同族的屠戮者,又是异族屠戮者的刽子手。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2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第187,186、187页。“不像活在人间”的中国人便只能活在虚幻中,活在“精神胜利法”的病态中。因此,便有了《病后杂谈》开头所说的第一大奇愿:诚愿这个世界上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姥姥姥爷,没有七大姑八大姨,没有任何他者,除了自己还活着之外,便只剩下一个好看的姑娘和一个卖大饼的商人。“精神胜利法”病态是现实病态人生的投影。
四
关于“病中赏秋海棠”,鲁迅说:“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1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2页。官匪一家,中国人时常命悬一线,其生存境遇恰与李如月“仆地‘剖脊’”,不可能还有“病中赏秋海棠”的雅致,这就造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复杂病象,这从学者俞正燮为清朝歌功颂德的现象中亦可略窥一二。
读过野史的俞正燮何以为清朝歌功颂德?鲁迅说:“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2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第188、189页。清朝对于中国历史典籍禁毁删改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全毁、抽毁、挖剜、窜改等,可谓花样百出。例如在《四部丛刊续编》中,其中《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便被删掉了: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3转引自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第189页。
这里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只是汉民所受异族的凌虐和屠戮,更是清朝销毁历史罪行的居心和手段,正如鲁迅所说“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4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第188、189页。。在历史典籍中,“贼”“ 虏”“犬羊”“淫掠”“夷狄”等词都是犯忌讳的,悉数被窜改,比如“金贼”窜改为“金人”,“豕突河北”窜改为“长驱河北”,“蛇结河东”窜改为“盘结河东”……甚至不容许出现“中国”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与“夷狄”构成对立,而要想从清朝政府窜修过的《四库全书》中读出中国作者的“骨气”,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阿Q们之所以能够从痛苦的凌辱中迅速脱身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祖传法宝,这个法宝就是“忘却”。中国人“忘却”的根性是“长”在这个民族深重灾难中的,与这个民族所受的苦难是血脉贯通的。汉民头上的“辫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644年清军入关后,多次下令汉民一律剃发垂辫,不少汉民因为抵抗留辫而被杀头,汉民头上这根“辫子”毋庸置疑是汉民族的耻辱,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根辫子不仅“种”定了,而汉民“种辫”的血泪史也便渐渐被忘却了。随着岁月的增长,大家甚至觉得头上这头发不能全部留下,也不能全部剃掉,全留的是“长毛贼”,而全剃的则是和尚,只有剃一小部分,留一大部分,才算是一个正经合法人。街头上的卖艺人还会拿这头上的小辫子玩出许多精巧的小花样来,并以这些小花样来赚钱糊口。随着时间推移到晚清,有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子,先行剪掉了辫子,回到国内却不得不花一笔不菲的价钱装上一条假辫子作为护身符。如果没有这条假辫子,重则被砍头,轻则被围观、被呆看、被冷笑、被恶骂,甚至被恶骂为“里通外国”的汉奸,而这围观者、呆看者、冷笑者、恶骂者,并不只是满族人,更多倒是他们的汉族同胞,正是这些汉族同胞不惜以“汉奸”的罪名直斥反抗清朝统治的义士。
浙江吴兴南浔镇嘉业堂私人藏书楼的创办人刘承干是一个有着民族情结的藏书家,他对明朝遗老深有同情,对清朝的文字狱深有不满。他刻过不少清朝的禁毁书籍,如屈大均《安龙逸史》《翁山文外》,蔡显《闲渔闲闲录》等,在每一种新刻书的结尾,刘承干都会写一篇跋文。然而在这些跋文中,这位对明朝遗老深有同情的文人却以清朝遗老自居,字里行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其民国时期的文章,文中“儀”字为避清朝废帝溥仪的讳而缺了最后一笔。鲁迅认为,并非这位藏书先生“食古不化”,因为“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1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4页。。其根源在于这位藏书先生像阿Q一样是“忘却”了,他会选择性地忘却自己汉民的身份,而且这种忘却甚至会成为一种无意识,成为一种自然习惯,这种自然习惯促使民国时期的他会以清朝的遗老自居而不问遗于何族,也不问遗在何时,只为遗老而遗老。
备受欺凌的阿Q只有遗忘才会“乐活”;同样,“不像活在人间”的中国人唯有遗忘才会“乐活”。备受欺凌的阿Q之所以能够永远“乐活”,是因为忘却这个法宝已经长在他的血肉中,植入他的骨髓中,与其神经脉络交融在一起,成为他的心理定式和思维习惯;同样,“不像活在人间”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永远“乐活”,是因为其血肉、骨髓、神经脉络中有着“遗忘”这个法宝,遗忘已然成为这个民族的心理无意识。
鲁迅说:“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1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5、175页。“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这就是说,“血泊”还在,还摆在士大夫们的眼前,一则说明残暴者对历史文献的删改涂写并不能完全遮盖其血的罪行,二则说明这残暴者血的罪行也还有为士大夫不能完全遗忘的所在。既然如此,当士大夫已然直面自己同胞“血泊”的时候,却依然从这血泊中寻出闲适来,那就免不了要走一条轻捷的小道了,这条轻捷小道就是鲁迅所说的“彼此说谎,自欺欺人”2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5、175页。。
不过,因为它有两手巧妙的“太极拳”的配合,所以这“彼此说谎”和“自欺欺人”也就被洗却了赤裸裸的谎言和欺骗的颜色。第一种太极拳姑且叫“浮光掠影”,也即遇事不可不认真,又不可太认真,仿佛有些关心然而又不可切实关心,因为“浮光掠影”,无论谎言和欺骗都涂上了一层“事实”的保护层;第二种太极拳权且叫“蔽聪塞明”。因为“蔽聪塞明”,故此能够既麻木又冷静,既麻木地自欺,又冷静地欺人。比如“君子远庖厨”就是这组合拳打出的一种自欺欺人的招数。君子远离庖厨,并非君子真正远离庖厨,他们只是暂时躲开鸡鸭猪牛被宰时候的觳觫,等到鸡鸭猪牛摆上餐桌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回到庖厨享用鸡鸭猪牛烹制的各种美味。质言之,他们只是在鸡鸭猪牛觳觫的时候选择了“蔽聪塞明”而已,因此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鸡鸭猪牛不觳觫的时候享用人间美味。同时,又因为他们能够“浮光掠影”,所以当他们摸着滚圆的肚皮的时候却依然能够高唱着“君子远庖厨”的道德高调悠闲度日。故此,鲁迅不得不为此惊叹:这“真是天大的本领!”1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5、176页。
明代建文帝的忠臣铁铉被永乐皇帝油炸后,这“天大的本领”便又有了一次施展的机会。
据明朝王鏊《震泽纪闻》等记载,铁铉被油炸后,他两个女儿被罚入教坊做官妓。数月后,终于拔云见日,两女分别向原问官献诗,永乐皇帝知道后被赦免,嫁给士大夫。
据鲁迅考证,遗民孙怡《茗斋集》后面所附《明诗钞》收有铁铉长女献诗,铁铉长女教坊献诗为:“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云鬟半挽临妆镜,雨泪空流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尊前重与诉琵琶。”2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第197页。可是,据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卷上)考证,这首诗是根据范昌期的《题老妓卷》略微修改个别词汇而成,试把这首教坊献诗与范昌期的《题老妓卷》比较,两者只有个别词句的增删修改,范昌期的《题老妓卷》原诗为:“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 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3鲁迅:《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75、176页。
显然,铁铉二女教坊献诗是伪作。
其实,铁铉二女献诗,被永乐皇帝赦免,嫁入书香门第,这事经不起推敲的并非这一点。从这首诗内容来看,它原本就不是现任官妓的口吻,而是“咏老妓之作”。从永乐皇帝一贯的凶残来看,如此仁义之事当属天方夜谭,这一点也为永乐皇帝的两则上谕所证实。
到底是谁把这首诗嫁接到铁铉长女身上,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么多人愿意相信这个嫁接。这就说明,以“浮光掠影”和“蔽聪塞明”组合“太极拳”而自欺欺人的并不是少数,“彼此说谎,自欺欺人”在中华民族中是极普遍的事情,他们不仅以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等方式歌颂吾皇仁义、圣皇英明、天下太平,还会掩盖罪恶、粉饰黑暗。
综上所述,与“精神胜利法”复杂病象相关的三个因素大致为:一是官家的愚民政策,二是“忘却”的祖传法宝,三是多组“太极拳”与自欺欺人的巧妙结合。
五
阿Q身上集聚了国民劣根性的诸种病症,鲁迅竟然对阿Q还抱以深深的同情,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存权是神圣的,然而阿Q却时时处处命悬一线,其生存境遇有如李如月“仆地‘剖脊’”,由此而祖传的劣根性,焉能不抱以深深的同情?不过,如果说“哀其不幸”自是人情之常,那么“怒其不争”,岂不是苛责太甚? 受虐者何以还要承当施虐者的罪责?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说:“个体为真,团体为幻。”1《章太炎政论选集 上册·国家论》,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页。国家民族祸福的实际承受者不可能是虚幻而在的“国家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中的“个体”,或者说“国民”。“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2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固然也包含在“凡事举”之中。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国家民族的发展的哲学根底同样是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如果说鲁迅的“哀其不幸”多基于人的生存,那么鲁迅的“怒其不争”则多基于人的发展。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中的“个体”不能“正视”民族国家的深重灾难,这个国家民族是不能“成什么气候的”。鲁迅杂文《中秋二愿》即其一例。
在《中秋二愿》中,鲁迅由“中秋赏月”想到“海宁观潮”,又由“海宁观潮”想到“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这一神奇传说。据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记载:“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4鲁迅:《中秋二愿》,《鲁迅全集》第5卷,第595页。这看似是个传说,实则是民族无意识心理的一个投射,鲁迅即刻就把这个传说推到民族无意识心理的底端加以分析:“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1鲁迅:《中秋二愿》,《鲁迅全集》第5卷,第594、594、595页。显然,这无异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被清朝武力征服的汉民族,无力改变自己异民族“奴才”的血淋淋的现实,也不敢直面自己这异族“奴才”的现实处境,于是便天才地创造了一条奇妙的逃路——借助生殖机关的虚假传说制造虚假的转败为胜的“胜境”,这就好比挨了重重一耳光的阿Q,实在无力以耳光回击对方,只好回以这是儿子打老子,仿佛打人的是儿子,被打的是老子,便转败为胜了。
在汉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中,诸如此类的妙计可谓屡见不鲜,并不只是“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还包括把征服者成吉思汗列为“我们的伟人”,称“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照此逻辑推演,我们下一步的宣传或许就是“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2鲁迅:《中秋二愿》,《鲁迅全集》第5卷,第594、594、595页。
汉民族通过生殖系统的虚假方式,也即以阿Q精神胜利法的方式寻求对满族的转败为胜,实质上是一种逃避,实质上是不敢正视被满族武力征服这残酷的现实,不敢正视自己做了满族“奴才”这血淋淋的惨淡人生,因而“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遭劫一次,……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3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251页。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4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251页。显然,鲁迅据此提出了自己生命哲学上的一个崭新命题,即“正视”5曹禧修:《鲁迅:站在坟墓前的哲学家》,《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5期。;而我们据此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鲁迅中秋节的两个愿望:“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攀亲戚,……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6鲁迅:《中秋二愿》,《鲁迅全集》第5卷,第594、594、595页。这两个愿望显然寄予了鲁迅对以精神胜利法的方式逃避现实者的极度不满和严厉批判的鲜明态度,并期待他们回过头来“正视”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