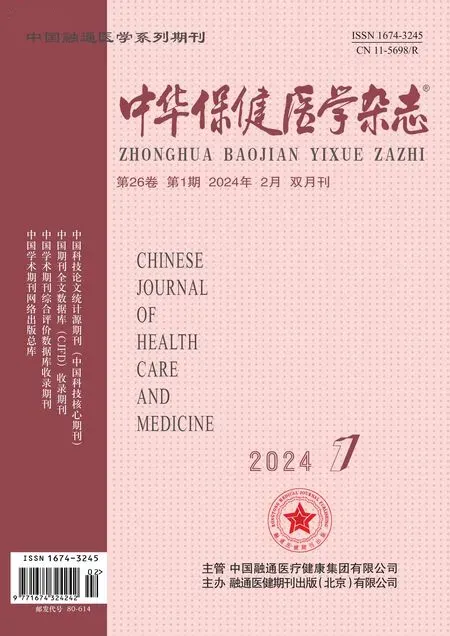不可切除肝细胞癌基于靶向免疫联合转化序贯外科手术方案的探索与经验
卢实春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其中约75% ~ 85%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1]。肝切除术是HCC患者获得根治和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起病隐匿,大多数HCC患者诊断时已处于中晚期,而失去了手术切除机会[2]。近年来,得益于不可切除HCC系统药物治疗的突破与非手术局部治疗技术的优化,新型的药物联合治疗方案加减局部治疗应用模式显示出了明显提升治疗有效率的价值。在不可切除HCC系统治疗中尤以抗血管生成靶向药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免联合)疗效突出、证据充分,故以此为基石的联合方案在业界迅速成为不可切除HCC转化序贯外科手术临床探索的重点。近年基于前瞻性队列的转化研究,在将不可切除HCC转化为可切除并取得远期生存获益方面的数据令人鼓舞。纵观现代肝脏肿瘤外科发展史,不可切除HCC转化治疗正逐渐显现出从“个案、经验性转化”向“系统性转化”发展的特征。
1 肝细胞癌转化治疗的概念与价值
对于中晚期不可切除HCC患者而言,传统的系统治疗和包括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等在内的局部治疗是目前常用的治疗方式。但无论是单一的局部治疗或系统治疗,抑或两者联用,本质上都不是根治性治疗。既往研究资料显示,部分中晚期可切除HCC患者直接行肝切除术后复发率较高,整体预后不佳[3]。因此,中晚期HCC患者的根治和长期生存仍存在很大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肝癌转化治疗指的是使用系统治疗、局部治疗抑或两者的多维度/多模式联合,使中晚期初始不可切除的肝癌转为可切除肝癌,从而实现更好的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获益,其中,不可切除原因包括外科学因素(如肝功能不能耐受,剩余肝脏体积不足、重要管道结构不能重建等)和肿瘤学因素(技术可切除,但切除后不能获得比非手术治疗更好的疗效)[4 - 6]。虽然尚缺乏头对头的对照研究证据支持,但既往研究提示,转化序贯外科手术方案可为患者带来无瘤生存和总生存获益,且转化手术切除是初始不可切除HCC患者获得更长OS的独立预后因素[7 - 8]。也就是说,通过实现根治切除,转化治疗序贯外科手术可为患者带来更好的长期生存获益。
2 以靶向免疫联合为基础的肝细胞癌转化治疗进展与经验
局部治疗技术的进步和系统药物治疗的突破为肝癌患者转化治疗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如何选择最佳联合转化治疗方案成为关键。除外患者意愿和基础肝病状况,客观缓解率和缓解特征是影响联合方案选择决策的重要因素。诸如药物的可及性、较快的起效时间,较低的肿瘤进展率,较深的缓解程度以及较长的病灶缓解时间等均是方案选择的主要考量。
在中晚期不可切除HCC患者中,局部治疗的转化成功率约5% ~ 30%,虽然相较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单药(如索拉非尼)更具潜力,但临床疗效仍然不够令人满意[9]。近年来,以仑伐替尼为代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抑制剂在不可切除HCC患者中呈现令人鼓舞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例如仑伐替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ORR分别达到54.2%和36.0%[10 - 11]。最新的LEAP-002研究(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CARES-310研究(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等大型Ⅲ期临床研究中,靶向免疫联合治疗的中位OS已突破20个月[12 - 13]。明确的疗效使其成为不可切除HCC一线治疗的指南推荐方案,同时也为该方案用于转化治疗探索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为患者提供根治性切除可能的同时,并不会导致转化失败患者失去从标准治疗中获益的机会。
目前,有关靶向免疫联合转化治疗的探索多见于小样本、回顾性临床研究,尚缺乏前瞻性、大样本的高级别证据,纳入的患者以巴塞罗那肝癌分期 C期为主,ORR约23.3% ~ 53%,而转化成功率的跨度也比较大,在10% ~ 51%[14 - 17]。本中心团队近年来持续开展靶向免疫联合转化序贯外科手术的前瞻性探索,自2019年正式启动入组以来,已积累了一定的随访数据与转化治疗经验。包含56例患者的Ⅱ期前瞻性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作为主要终点的转化成功率达到55.4%,根据mRECIST标准和RECIST 1.1标准评估的ORR分别为53.6%和44.6%,中位随访23.5个月时,56例接受转化治疗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为8.9个月,中位OS为23.9个月,其中转化成功组的中位PFS(15.1个月vs.4.5个月,P=0.004)和OS(36.0个月vs.14.9个月,P=0.004)明显长于转化未成功组[18]。此外,Cox回归分析显示成功转化是有利于PFS和OS的独立预后因素。2023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上,本中心进一步报道了该研究的100例扩展队列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结果[19]。100例患者中,基于mRECIST标准的ORR为54%,疾病控制率(DCR)为77%,基于影像学的转化成功率为51%,与Ⅱ期研究结果差异不大。其中,47例(47%)患者接受了手术切除。到中位随访17个月时,所有患者的中位OS为25个月,转化切除组和未转化切除组的中位OS分别为未达到和15个月。转化切除组的中位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 free survival,RFS)为25个月,未转化切除组的中位PFS为7个月。与Ⅱ期研究数据相比,在用药方案均一、样本量进一步扩大的同时,无论是ORR还是转化成功率均可保持总体稳定,OS数据也都一致地体现了转化序贯外科根治切除所带来的长期生存获益。安全性方面,靶向免疫联合方案整体可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TRAE)发生率约80% ~ 90%,其中30% ~ 40%为3级或3级以上TRAE,并可在术前得到有效控制。尽管转化后手术具有切除肝容积大、门静脉整形重建比例高、腹腔淋巴结清扫范围广等特点,但数据提示靶向免疫联合转化治疗并不会造成手术相关并发症或围术期死亡风险的增加[7,18 - 19]。这些前瞻性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确认了靶向免疫联合在不可切除HCC转化序贯外科根治治疗中的价值,也为后续更深入地开展转化探索提供了基本的数据参照。
转化探索深入推进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在靶向免疫联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TACE、HAIC、SBRT等局部治疗以进一步提高反应率。回顾既往报告数据,相比靶向免疫联合方案,靶向免疫联合局部治疗ORR更高,mRECIST评估的ORR普遍超过60%,转化成功率则多介于22% ~ 60%间。但在实际的手术切除率方面,靶向免疫联合局部治疗似乎并未带来数值上的明显提升[20 - 23]。由于不同研究的纳入人群特征、转化成功定义以及对可切除性的评估等存在差异,且现阶段缺乏头对头的对比研究,局部治疗的加入对于转化率提升和远期生存获益的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总的来说,以靶向免疫为基础的方案,加或不加局部治疗,均取得了可观的转化效率。新近的在晚期肝癌患者中开展的转化研究也因此多采取以靶向免疫为基础的联合方案作为治疗选择。
除了疗效层面的考虑,安全性和药物经济学等也是影响转化治疗方案选择的重要因素。从临床实践来看,治疗强度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TRAE发生风险上升。因此,在做转化治疗方案选择时,根据患者实际状况平衡好疗效与安全性至关重要。在可实现转化目的的前提下,避免治疗强度的不必要增加有助于提升患者生存质量、降低社会医疗负担。综合考虑疗效和安全性等因素,总体遵循“递进式的联合转化治疗”策略,即采取靶向免疫联合作为首选转化方案,在第1次返院评估时,对于部分病灶响应不佳的患者再考虑联合应用局部治疗,以通过更大的治疗强度促使患者进一步转化。根据团队既往实践的结果,叠加局部治疗患者与未叠加患者相比在无复发生存率上并未观察到显著差异,多数可转化患者通过靶向免疫联合方案即可实现转化[7]。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本中心研究将观察时长设定为48周,也就是说患者在1年内达到切除条件均可视为成功转化。基于临床研究报道的数据,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治疗时根据mRECIST标准评估的中位缓解时间为2.7个月(1.2 ~ 11.8个月)[11];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时根据mRECIST标准评估的中位缓解时间为1.9个月(1.1 ~ 9.2个月)[24]。由此可见,尽管靶向免疫联合的中位缓解时间在2 ~ 3个月,但仍有部分患者需更长时间才能观察到疗效响应。本中心团队既往治疗的患者中,也有在用药近1年实现成功转化的案例。因此,考虑到靶向免疫联合治疗起效时间在不同患者中的差异,足够长的疗效观察窗口将有利于更多患者获得根治切除机会,从而延长生存获益。
3 肝细胞癌转化治疗的挑战与思考
系统治疗加减局部治疗在转化治疗中的应用已积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需要注意的是,在被广泛、成熟地应用于常规诊疗之前,转化治疗仍有包括适用方案选择、获益人群筛选、长期生存获益验证、手术切除时机和术后辅助治疗选择等一系列问题有待探索和明确。
当前,系统治疗加减局部治疗的疗效已遇到一定瓶颈。除了持续开发新的药物和联合应用模式外,精确筛选能从现有联合治疗中获益的人群是提升不可切除HCC系统治疗或转化治疗的重要路径之一。通过预测生物标志物筛选最佳获益患者人群在免疫治疗中已显示出其临床价值,但尚不清楚是否可预测联合治疗的疗效。本中心研究提示,肿瘤组织预先存在的CD8+ T细胞或为预测联合治疗反应的潜在生物标志物[18]。另有报道显示,从预处理MRI中提取的影像组学特征可以预测不可切除或晚期肝癌患者对仑伐替尼联合PD-1抑制剂治疗的个体化客观反应,并相对临床病理特征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且与该联合方案下的总生存和无进展生存相关。未来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病理特征或可成为预测靶向免疫治疗疗效和预后的潜在方法,为选择适合联合转化治疗的获益人群提供思路。此外,肿瘤微环境、肠道微生物组学、炎症指标、肿瘤相关指标等标志物对疗效的预测价值也在积极的探索中。
在转化手术生存获益方面,现有研究表明,经转化治疗并成功序贯手术切除的患者中位OS长于既往报道的纯药物治疗或联合治疗,但当下大多数转化治疗研究中缺乏与传统治疗模式头对头对比数据及长期生存数据。因此,确认转化切除的真实长期获益,即明确外科手术在成功转化患者中的价值将是未来探索的焦点之一。目前正在进行的TALENTop 研究(NCT04649489)对比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后获得疾病缓解或疾病稳定且技术可切除的患者继续接受系统治疗与行手术治疗的生存获益差异,研究主要终点为治疗失败的时间,次要终点包括OS等。该项研究及其类似研究长期随访结果的发布,将为转化序贯外科手术治疗改善长期生存提供更多临床证据。
在术后辅助治疗的选择上,病理完全缓解和病理部分缓解的患者推荐分别接受PD-1抑制剂单药治疗≥6个月和原转化治疗方案6 ~ 12个月,病理无缓解的患者则由多学科团队根据病理检查和/或基因检测结果推荐方案进行治疗。该种治疗模式在本团队已积累一定的经验,但最佳的辅助治疗模式仍需更多证据来加以验证。同术后辅助治疗方案一样,转化后手术切除的时机以及系统治疗药物术前停药的时间等方面,目前均更多依赖于医生的临床经验,缺乏充分的研究证据和诊治共识,需要未来进一步探索。
总体看来,转化治疗是一项涉及多科室、全周期的诊疗任务。虽然承担手术切除环节的外科医生在转化治疗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不难看出,多学科团队在患者治疗方案选择、不良事件应对、术后恢复与长期生存管理方面的协同参与至关重要。相信随着转化经验的持续积累,转化理念的不断拓展,以及更多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出现,转化治疗有望向规范化、同质化、体系化深入发展。
志谢感谢默沙东医学事务部徐晓晨在文献检索与资料整理方面提供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