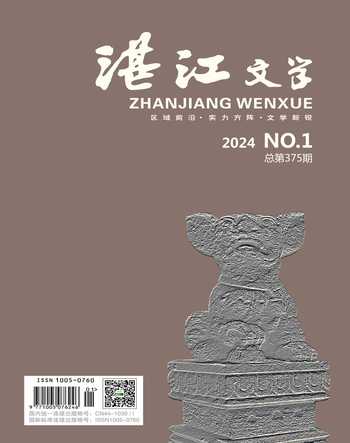往昔微光
吴丽萍
红皮衣
不知哪家亲戚,将不穿了的,也可能是不愿再穿的一件红色皮衣送了来。红皮衣里层夹着些许棉花,和约莫五六件其他衣服一起送来。它最显眼,大概是因为红色,加之皮质,亮红亮红的,隔着袋子也能看见它的鲜艳夺目。
母亲让她穿上。天太冷了,夹了棉的皮衣,穿上就不怕寒,不会感冒。如果生病,人受罪不说,还得花钱呢。
家里没多余的闲钱,在她印象中,母亲没有给她买过新衣服,穿的都是亲戚家送来的。母亲肯定很感谢这些亲戚,买衣服要一笔不小的花销。毕竟两个孩子都还在长身体,过一个年,衣服就短了一截。
这件红皮衣,终究不是她的尺码。肩缝紧接着脖子,袖口遮不住手腕,像是九分袖。秋衣比红皮衣还长一截,露在外面。于是她把秋衣袖子挽起来一段,藏了进去。
可冬天的风太寒了,像刀子,刮得手腕生疼。风趁机钻进了手臂,又溜进全身,她红了鼻头,微微颤抖。也有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她又悄悄地,趁着四下无人,把秋衣放下来。这一小片刻,窃喜地感受温暖,好似处在大大的火盆边烤着火,幸福地舒展开身子。
操场上,晨读课,老师让学生们围着圈坐下。冬天的阳光暖洋洋的,总能让人迷恋,不愿离去。
紅皮衣也被晒得暖暖的,把手放上边,有摸热水袋的感觉,她好喜欢。忍不住又多摸了几下,到后来干脆双手抱住自己。
移时,她感受到来自同学们异样的眼光,低头看了看皮衣。
她晓得了,因为没有替换的衣服,皮衣已经穿了好几周。领口、袋口、袖口、袖管都黑得发亮了。里面的棉絮也好似凑热闹一般,从小洞里冒出头来。这才发现,好些地方都裂开了,有十几道道。她没数,不敢数,她也不想数,怕数着数着掉下泪来。
都裂了皮了,原本该是白色的里衬也变成了灰黑色。她还是穿着,她想换的,可是换成什么呢?没有比这皮衣更保暖的外套了。
同学们笑就笑吧,她低着头,不说话,这样大概是听不到。看不到眼神,应该也就听不到了。她希望尽早下课,躲回家里去。
铝饭盒
太阳刚冒出来,挂在对面山尖上,她在门前刷牙。太阳很近,就在对面三四百米处的山上。可是她觉得凉爽极了。盛夏的早晨啊,都忍不住大口呼吸。
她们一家住在菜地里。父亲负责种菜,母亲负责卖菜,为了方便,就在菜地一角搭起一座房子。这房子是木板的墙壁,茅草的屋顶。
可是她很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感受这温暖的夏日晨光,因为早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淘米做饭、洗菜烧水、切草喂猪……
煮饭用的是高压锅,在小炉子上用柴火、炭火烧,没有电饭煲,也没有煤气灶。煤气是要花钱的。柴火是爸爸空闲时候山上砍来的,这个花的是力气,不花钱。她先在小炉子里铺好碳,拣了大颗一些的,再拿松柏和荆棘引火,松柏油性大,很容易点着。
高压锅早已不是银白色有金属光泽的,而通身都是黑的,裹着一层一层的烟灰。没有手柄,大概长年累月地在火上烧化了。
菜都是地里摘来的茄子、豇豆、丝瓜……她喜欢在河边洗东西,河水清清澈澈,所有脏东西也很快顺水流走,包括她心里的一点委屈。
土灶有点高,或者是她太瘦小了。她拿了小板凳,这样能省些力气。将菜都切好,放在一旁,这才来生火。她还不懂如何烹饪,母亲告诉她,菜烧熟就可以。
于是,菜熟了,米饭也熟了。
将碗筷都摆好后,她喊上父母。母亲忙着将菜上附着的泥土洗去,父亲忙着装车,再拉到市场里卖。菜叶上的水滴就是一家人的汗水。
吃完早饭。她抓了一把米,又将茄子干装在搪瓷杯中。这是她在学校的中饭。
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是淘米,早上出门的那一把米装到铝饭盒里,淘净,装上适量的水,再放到食堂里。那就是一个厨房,同学们把一铝饭盒的米、一搪瓷杯的菜都放在桌上,等着食堂的阿姨将它们一起放到锅里蒸。
食堂阿姨也是学校小卖部的老板。小卖部除了一扇门,这门只有她自己能进出,还有一扇四四方方的小窗。小窗已经够小的了,老板还安着防盗,只留着一块脸庞大的小口。
在课间,学生们一窝蜂冲向这个小口。酷暑难耐,拿出皱皱巴巴的两毛钱,一毛买一根辣条、一毛买一个冰果冻。
有穷人家的孩子,不是每天都能拿出两毛来买辣条和冰果冻的。但是同学们总是凑在一起吃,一根辣条能撕成3条,一个果冻可以你舔一口我舔一口。
午饭时间,住村子里的孩子都各自回家吃去了。全校大概有三四十位学生留校吃午饭,一个班平均五六位。
拿了饭和菜,她和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到教室里,课桌就是餐桌。她的饭总是能不软不硬。同学们把菜也聚到一起,有黄豆、豇豆干、茄子干、腐乳……大多都是些腌制得咸咸的菜干,夏天咸菜能放得更久些。
谁家的菜要是加了些肉,那真是了不得,还有同学带来了带鱼,一开盖把大家都馋得很。
同学们大方得很,将菜都均分,嘻嘻哈哈一起吃。
小轮车
秋风起,夜微凉,晨起又是淅淅沥沥一夜雨。家门前是土路,雨水泡得尤其泥泞。上面的车轮印子,一茬换了一茬。
上学的路,远得不像话,大概是因为年纪尚小。从家到学校,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经过一大片菜地、一家有两幢鸡舍的养鸡场、两家烧制空心砖和实心砖的砖厂、一座车来人往的桥、几穴坟……
起初,她要先花半小时从家走到路口,再在路口等客车。她实在太小了,别人的一步,她要走两步。每次赶到车跟前,都气喘吁吁。有时出门晚了,她错过了客车出发时间,又得走半个多小时到学校,而且上课就迟到了。要是能赶上车也还好,赶不上车的时候,是遭罪不少。
后来,母亲不知道从哪儿变出一辆自行车。这车轮子很小,黑色,和她倒是很相配。
虽说车的模样丑,身形也小。可是她依然很兴奋啊,有车,她就不用赶客车了,不受制于时间。
接下来的事就是学骑车。但是她得靠自己,父亲忙着翻土种菜、母亲忙着洗衣做饭,都没有时间教她。
好在这车确实是不大,虽然她脚还够不着地,可她很是勇敢。
家附近有一座半废弃的红砖厂,她就在砖窑边学骑车。一只手把方向,一只手撑着砖窑的墙,就这么一遍一遍来来回回地学。
这砖厂地方开阔,但是地上是无处不在的碎砖。学骑车,她不知摔了多少回,膝盖和手掌总蹭出血来。她不哭,爬起来,扶起车,又一遍一遍来来回回地学。
哈哈,有一天,她终于可以不扶着墙,能够两只手都把方向了。她感觉到脚在不断使出力气,风将耳边的头发轻轻拂过。
她要赶快回去告诉母亲:学会骑车啦!
从砖厂骑到家门口,母亲正在生火做饭。她激动得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喊,想和母亲分享这个好消息。却不知怎么刚骑到家门口就摔了一跤,引得母亲哈哈大笑,又赶紧跑过来将她扶起。
从此,上学的路变得短了。每次放学,她和同学一起骑车回家。在路过小桥的时候到河里玩一会水,在路过菜地小沟的时候抓一条泥鳅。她甚至在路过土坡的时候,爬上去捡些土块往路上扔,竟由此变得调皮捣蛋了。
猪圈房
隔着一条沟渠,就在路边,有一幢茅草房。它两开間,外间是厨房,里间作为卧室,放了两张床。说是卧室,其实也就是个睡觉的地方。
茅草房旁边是水泥砖砌的猪圈。
家里一儿一女,都长大了,不方便再睡一张床了,父亲想了法子,在猪圈上再盖一层,这样能多出两个房间。
用料依然是木板,可是木板也是东拼西凑的,并不是些整齐的材料。在猪圈上铺好木板后,父亲尽量不留缝隙,可还是避免不了有些缝隙,能看见猪在下面吃食、撒尿、睡觉。
猪粪的气味也常常随之而来,它们肚子饿的时候还嗷嗷叫。大概又因为春天,是个发情的季节,猪圈里两头猪都异常兴奋。
聪明的父亲在木板上铺了一层帆布,将缝隙都盖住。也许这样,可以盖住一些气味和声音吧。我心里也是这么安慰和暗示自己的。
在这间屋子里,没有床。她不介意的,她看见电视上也有不睡床,直接在地上睡的。她觉得这是一种新潮,于是,她拿了两床棉被,一床当垫子、一床当被子。
屋里还有张桌子,这桌子也是哪位亲戚搬家时准备丢弃的旧物。父亲拾了来,你看,现在用上了,还正合适。
桌子的上边,父亲为她开了两扇敞亮的窗户,且装上了玻璃。
在这间屋子里,她度过了小学、中学。底下的猪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因此,过年杀猪的时候,她都躲了出去。毕竟有了感情,猪是她的伙伴。她经常有些个什么事,猪都是第一位知道的。
母亲忙着生计,没有空余的时间,也不懂得如何教她。父亲老实巴交的,并不说几句话。她有什么事,就和猪说,猪在下一层,她在上一层,就隔着一块木板、一张帆布、一床垫被。
每当清晨醒来,窗外是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楼下是小猪咻咻咻吃着猪食。天气好的时候,有一米阳光,穿过木板间的缝隙,暖暖地铺开。
她揉揉惺忪的睡眼,嘴角上扬。是幸福,还有满足,再加一些更美好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