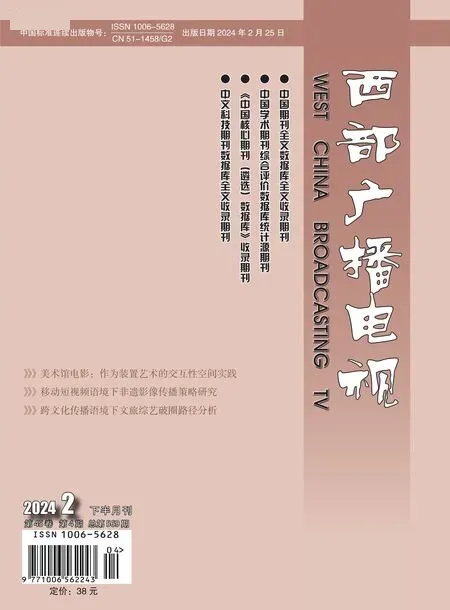中式伦理与温情主义
——评《忠犬八公》的本土化改编
何罗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在动物题材电影中,要论口碑和质量的“天花板”,必然绕不开忠犬八公的故事。由神山征二郎执导的《忠犬八公物语》于1987年8月在日本上映,以54亿日元的成绩登顶该年度日本票房冠军,不管是八公感人的故事还是高额的票房收益,都曾轰动一时,八公甚至走出日本本土,实现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美国好莱坞在2009年推出翻拍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其中保留了原版电影诸多的日本美学和风格元素。也正因为原版电影珠玉在前,观众对中国改编的《忠犬八公》持有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电影在上映之初并没有在市场上激起较大水花,但其后续的市场表现证明:导演徐昂对忠犬八公的中国式阐释,达到了对“既成”的创新突破,开拓了忠犬八公故事新的话语空间。
需要看到的是,《忠犬八公》在翻拍时面临的难题不只是难以逾越的原版,还有复杂的创作环境。翻拍作为与原创并立存在的电影创作模式,在我国电影市场中已经屡见不鲜。对外国经典电影进行翻拍创作,在原作的基础上填充本土化内容,不仅能复制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成功案例,在市场上降低制作成本和竞争风险,而且能减少原作进入国内时的“文化折扣”,使观众更容易理解与产生共鸣。因此,我国电影市场近年来掀起了翻拍的热潮,如柯汶利执导的《误杀》、宋灏霖执导的《五个扑水的少年》等翻拍电影在电影口碑和票房市场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绩。但是,原作带来的过高市场期待对电影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像包贝尔执导的《阳光姐妹淘》、李玉执导的《阳光劫匪》等翻拍作品,均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忠犬八公》正诞生于这一泥沙俱下的翻拍市场环境之中,其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实现票房和口碑的双重逆袭,是因为采取了独特的改编策略,这对于翻拍电影产业来说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因此,本文从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出发,探究《忠犬八公》在翻拍创作中的本土化策略,分析其体现的中国式文化语境,以期为中国电影翻拍市场提供借鉴。
1 表层符号的本土化置换
大部分国产翻拍片典型的疏漏在于对外国电影的本土化改编浮于表面,没有真正深入电影人物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空间,只是一味地照搬。因此,对忠犬八公进行中国式的本土化改编,要求创作者在创作语境和接受场域中由浅入深地展现故事的中国化精神内核。
影像作品常常借助于艺术符号进行文化表达,生动形象的艺术符号能直观地展现影片独有的文化特色。因此,艺术符号具有显著的消除文化隔阂的作用[1]。艺术符号的替换是本土化翻拍的第一步,但也是最容易流于表层的一步,创作者只有深入洞察故事的叙事结构,才能真正做到艺术符号本土性与时代性的接轨,将观众带入翻拍的叙事背景之中。
相较于悬疑片、推理片等类型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结构清晰明了,其主要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八公基于巧合被教授收留后,每天送教授上班,守候教授回家,即使是在教授意外去世后,八公也用一生去等待教授归来。在这个故事中,叙事的核心要素在于空间的固定和时间的流逝。故事发生在固定的送别场所,所以周围景观需要通过发生一些变化来凸显八公坚守的漫长,像《忠犬八公物语》运用了火车站这一主场景,用四季更替来呈现时间的更迭。但中国作为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铁路火车”在传统的文学意象里一开始便散发着生冷、坚硬的钢铁光泽[2]。而且,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火车很少被当作上班通勤工具使用。因此,中国版《忠犬八公》在进行艺术符号置换上是有所考量的,其将故事设定在山城重庆。由于横跨长江、嘉陵江,索道在重庆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其承载着重庆的城市记忆,即使在今天也是重庆的一张城市名片。再加上三峡水库建设和经济快速发展,重庆的城市景观在数十年里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充分展现出了四季更迭的镜头在影片中的作用:人群往来不息,房屋拆迁重修,而我是你在索道站前永恒的守候。在把握故事结构内核的基础上,《忠犬八公》不断引入其他艺术符号来完成对重庆的地域性景观展现,比如将八公的名字创造性地替换为重庆麻将文化中的八筒、通过加入地方方言来实现语言上的地域性认同等。这样一来,《忠犬八公》对电影时空成功锚定的同时,也消弭了观众对艺术符号的文化隔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体现重庆的地域性艺术符号,《忠犬八公》还在叙事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家庭的诸多共性艺术符号,展现了中国式文化。人类学家李安宅认为,中国式文化大而概之,在于一个“礼”字,“礼”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宽泛的含义,包括“民风”“民仪”和“政令”等,所以在社会学范畴里,“礼”大而等于“文化”[3]。“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意味着在中国传统概念里,饮食是文化的起源,因而餐桌在中国的家庭观念里有着重要含义。在中国,餐桌是家庭成员沟通最多的地方,也是家庭生活最日常的地方,餐桌是小家之间亲情的浓烈纽带。《忠犬八公》相较于《忠犬八公物语》便多了许多餐桌和饮食的相关镜头:日常生活和人物关系在餐桌上展现,在儿子离开重庆和女儿出嫁后,母亲李佳珍用一句“人吃的也不用我弄了”来表达对儿女的思念。就是因为在影片中体现了有关餐桌的文化符号,《忠犬八公》才能让全国观众都产生深刻的共鸣,感受到超出人与狗关系之外的家庭温情,而这也正是《忠犬八公》想深层次展现的中国式文化内核。
2 内在意蕴的创造化转变
任何艺术符号的使用都不是孤立的,符号是通过表层的形式来指涉更深层的意蕴。因而,翻拍更为深层的一步,在于能将翻拍作品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融合,体现出本土化的文化意蕴。《忠犬八公》中餐桌等艺术符号的使用,其核心目的便是要将原版中“忠”的内涵创造性转化为“家”的内涵,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镜像呈现。
作为微观视角的个体叙事电影,《忠犬八公》和《忠犬八公物语》主要展现的是中、日两国文化背景下个体小家的故事。中国和日本虽同属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但在不少镜头中仍体现出中、日两国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例如,从决定八公去留这场重头戏和戏中人物塑造上可以瞥见其端倪。在日本武家社会的影响下,“忠诚”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也是精神崇尚的最高要义。因而,20世纪不少日本影片都会塑造一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男性人物,用其人物关系作为武士道精神的载体。在《忠犬八公物语》之中,教授便是这样的存在,八公的去留全凭教授一人说了算,其他人物在塑造上是扁平的,甚至是隐藏的。影片故事发生时的日本,是极度父权制的社会,八公只与家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所以整部影片的人物关系显得极为简单。因此,在原版作品中,狗与人的关系便成为唯一核心,“忠诚”也就成为唯一的主题。
中国则呈现出与日本不同的家庭观念。在中国,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每个家庭都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家庭成员,且每个家庭成员都要为家庭生活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正因如此,中国文化格外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并将家庭视为应对危机的基本单元。中国的家庭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单位,在面对危机和挑战时,通常依靠家庭团结一致的力量来共同应对,缓解个人面对困境时可能感到的压力和孤独感。所以在中国家庭里,人物关系的纽带是复杂的,在翻拍的过程中影片也就不能仅限于人与狗之间“忠诚”这一个主题。中国版《忠犬八公》融合了中国的本土情境,对影片的文化内核作出了创造性转变:将“家”文化引入“忠”文化之中。《忠犬八公》不仅在人物关系之中加入了白举纲饰演的儿子这一角色,增加了父亲送别、父子矛盾等剧情,而且八筒在故事中的作用也产生了变化。要想让八筒留下,需要由冯小刚饰演的教授一一说服每一位家庭成员,解决家庭的人物矛盾。在全家接纳八筒后,镜头一转,是五人一狗拍全家福的场景,这正暗示着八筒就是家庭的一分子,在叙事中它充当了家庭和睦的见证者,见证了“姐姐”出嫁、“哥哥”远行及“爸爸”“妈妈”离开。到了故事的最后,八筒始终记得自己“把报纸拿给李佳珍”的使命,它等到“妈妈”李佳珍回来了才离开。层层叠叠的报纸不只传递出狗对人忠诚的厚度,更是传递出中国家庭温情的力度,也正是家庭的温暖、“家”文化的创造性内核才让这个故事满足了观众的期待。
3 美学风格的差异化呈现
影片文化意蕴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影片故事体量、时空背景的结构性调整,这种变化也会迁移到影片的美学风格上,《忠犬八公物语》和《忠犬八公》两部影片在美学风格上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如前文所言,《忠犬八公物语》的故事核心在于体现人与狗之间的关系,其主题意蕴是“忠诚”,这与日本武士道精神息息相关。除此之外,《忠犬八公物语》在美学风格上也呈现出鲜明的日式特色,展现出了日本文化中的神性色彩和物哀美学。而中国版《忠犬八公》将故事拉回到了家庭的柴米油盐之中,体现出了中国电影创作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日本自然灾害频发,一切美好都会在自然灾害的侵袭中消失殆尽,这使得日本形成了其独特的美的意识。这种美的意识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体现便是以悲为美,通过描绘一种悲哀荒凉的心境或者实境来营造一种相对凄凉、忧郁的悲凉之美,抒发对于生命的怜悯及对于岁月的感伤,即物哀之美[4]。《忠犬八公物语》用缓慢的叙事节奏刻画了这种纤细的美学,特别是影片中对于八公去世的刻画:八公死的时候是清冷的、孤零零的,死在了平凡的一天。死亡在日本“物哀化”的倾向下并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更多的是“超脱”和“干净”,所以结尾有了八公死后和教授相聚的超现实画面:八公在樱花飞舞的树林中向教授奔去,它的一生正如樱花一般,花期虽短,但留下了令人感动的真挚情感。动物被日本人认为是自然神旨意的传达者,许多动物都被赋予了神性的色彩。在《忠犬八公物语》中,教授去世的当天,八公突然有了大叫等反常的举动,像是拥有了未卜先知的灵性。而在故事的最后,出现了教授妻子在老家又养了几只秋田犬的镜头,似乎故事又进入了新的轮回。
中国版《忠犬八公》在主题意蕴转变之后,坚持中国现实主义的创作基调,以人的温度代替对自然的神性展现。例如,全片减少了呈现自然景观的镜头数量,增加了重庆“挑山工”失业离开、旧城拆迁改造等人文景观来展开叙事;在选择八筒这一动物演员时,没有像《忠犬八公物语》那样强调血统品性,而是选择了国内随处可见的中华田园犬;陈敬修教授去世前的一场戏,加入了外出考察“出远门”的情景设定,使得八筒的送别少了许多神秘主义的意味,让八筒的表现更为自然和贴近现实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不只是直面现实,还会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充满人情温度,《忠犬八公》就是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体现出了含蓄隽永的温情主义特色,是有温度的现实主义创作。所谓温情主义特色,就是在文艺作品中以关注人性温暖的那部分为主要特征,以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完整人性的涵咏为主题,从而发掘出日常生活的温暖[5]。比如,八筒最后去世的那一幕,它等到了离开很久的“妈妈”和“哥哥”,在与家人的相聚之中离去。影片通过艺术手法的处理,融入了创作者的美好愿景,表达了中国社会应有的“人情味”。有温度的现实主义创作是对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脉相承,同时温度也正是我国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区别于其他现实主义更高的要求: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在真实性基础上要求融入创作者的人生道德情怀[6]。导演徐昂通过展现一只平凡小狗一生的等待,实现了对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人与动物如何相处、乡土记忆如何追寻等诸多问题的投射和观照。
4 结语
翻拍电影应该是在原作基础上密切结合本土特色的创新,这要求创作者深入了解原作国家和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美学风格意蕴。虽然《忠犬八公》在翻拍过程中仍有部分情节存在“照搬”之嫌,如陈敬修外出去世一幕也是沿用了原版心脏突发疾病问题,而在全片的镜头之中缺少对这一情节的指涉和铺垫,但瑕不掩瑜的是,其通过对中国家庭文化的深刻展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人文关怀,成功书写了忠犬八公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