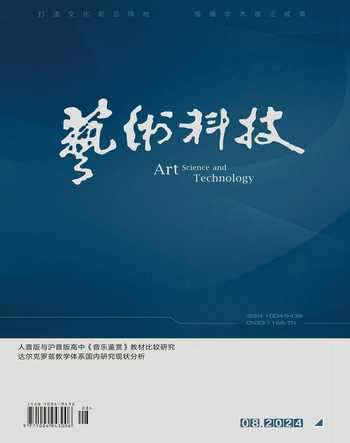王建中钢琴原创作品研究

摘要:目的:王建中是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的开拓者与先行者,对中国钢琴作品的民族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学界对其原创作品的分析较为稀缺。文章以《小奏鸣曲》为例,深入剖析王建中的原创钢琴作品,从音乐分析的视角出发,分析其如何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方法:文章运用文献分析法、音乐分析法等多种方法。首先,通过对王建中生平、创作思想、艺术风格等进行系统梳理,构建其音乐创作的整体框架。其次,对《小奏鸣曲》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解读其曲式结构和创作手法。最后,对王建中钢琴作品创作特征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结果:《小奏鸣曲》完美展现了王建中精湛的西方作曲技法,同时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精神。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使作品既保持了西方音乐的严谨结构,又充满东方音乐的韵味和情感。王建中的创作理念和实践,对后来的钢琴作品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中国原创钢琴作品的发展。结论:王建中作为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的开拓者与先行者,其音乐作品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后世的钢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王建中; 《小奏鸣曲》;中国钢琴奏鸣曲
中图分类号:J624.1;J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8-00-03
0 引言
近年来,关于王建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钢琴作品和声乐套曲上,其中钢琴改编作品是研究重点,主要从作品的音乐本体分析、民族化探究以及演奏技巧等方面展开。而有关其原创钢琴作品的音乐分析以及创作技法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有关《小奏鸣曲》的音乐分析也并非研究重点。本文以《小奏鸣曲》为例,对王建中鋼琴原创作品进行分析,重点关注曲式结构和创作技法,旨在为相关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参考和研究思路。
1 作曲家及作品介绍
王建中,祖籍江苏江阴,1933年生于上海,父母皆为高学历人才,精通多国语言[1]。王建中17岁时便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除日常教学之外,王建中常常去乡下采风,因而其前期作品颇具民族风味,这集中表现为对传统民歌及器乐曲子的钢琴改编,著名的作品有《百鸟朝凤》《梅花三弄》等[2]。2016年,王建中因病去世,享年83岁。可以说,王建中是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为后世创作者提供了较为宝贵的经验。
纵观王建中的钢琴创作经历,可以按照时间和风格分为两个阶段[3]:一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改编作品为主,代表作有《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云南民歌五首》等;二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作曲界掀起钢琴原创作品的新风潮,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小奏鸣曲》则作为原创作品拉开了作曲家创作的序幕[4]。
2 《小奏鸣曲》作品分析
本文通过划分三个乐章的曲式结构,重点剖析每一乐章中作曲家的创作手法,试图解读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2.1 第一乐章曲式结构分析
在第一乐章中,王建中采用奏鸣曲式的体裁进行创作[5],1~57小节为呈示部,58~153小节为展开部,再现部从154小节开始,一直到该乐章结束。
主部(1~17小节)。呈示部中的主部主题源自云南民歌的素材,旋律骨干音为“D-F-A”,分上下两乐句。第一乐句落在商音,作曲家采用西方复调式的旋律创作手法,第7小节左手旋律与前一小节右手的旋律交相呼应,通过这种衔接,旋律自然地过渡到第二乐句。前后两乐句为平行乐句的关系,第二乐句再一次重复主部主题,旋律落在羽音结束。
连接部(18~29小节)。连接部由第一主题发展而来。前4个小节由右手体现舞蹈节奏韵律,左手则演奏主旋律,织体与主部主题各异,其旋律发展形态也与主部主题相反,展现了作曲家的巧思。之后的几个小节旋律重新回归右手,并作上行模进处理,22小节调式随之发生改变,右手的“#F”音预示着旋律朝G宫转变,最终连接部结束在第29小节长时值的主音G音。
副部(30~57小节)。从第30小节起乐曲进入副部,共有两个主题,分别为E羽和D徵调式。第一主题从30小节开始延续至41小节,内部可划分为6+6的次级结构,前后主属呼应。旋律采用民间器乐曲中常用的手法“句句双”,以产生民歌特有的“一领众和”的效果(见谱例1)。
第二主题的节奏是第一主题节奏的延续,旋律一开始集中在音域较高的小字二组,而后通过连续的下行级进,移低一个八度并再现主题部分。51小节旋律开始重复上行级进的两个音,并随音乐的发展缩减其时值,营造音乐未完待续的感觉,直至57小节旋律最终落“D徵”,音乐力度渐弱,时值渐慢。
展开部(58~153小节)。展开部自58小节开始频繁使用变音记号,旋律材料来自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首先对主部主题发展,作曲家将其移高五度再次呈现,调性为#C羽调式,发展形式更为自由。旋律发展到73小节本应该终止,然而作曲家却截取最后的素材,并将其向上模进,之后又采用快速跑动的四组十六分音符强调模进后的音调,最终以短促的五度跳进音程收尾。从111小节开始,旋律快速向下跑动,模仿河流湍急的声音,这处华彩片段体现了作曲家的巧思,内含云南山水的意象。6个小节之后,再次使用重复、模进的创作手法连接下一主题。129小节进入下一主题,该主题将副部的第二主题移高大二度,旋律发展手法与原主题保持一致。在145和150小节处,以主部主题的材料模进,分别移高四度和五度再现,为试探性的音调,暗示旋律的回归。
再现部(154~172小节)。再现部位于154小节,作曲家对其进行压缩处理,只回归主部主题的音调,第一乐章就在这种热闹欢快的氛围中结束了。
2.2 第二乐章曲式结构分析
第二乐章是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A段为中板、抒情的,B段则更为活泼、跳跃。
A段(1~24小节)。A段围绕骨干音“D-F-G”展开,由两句平行乐句构成,第一乐句前8个小节是a主题乐思的呈示,右手旋律部分集中在高声区,柔美空灵;左手负责伴奏,织体较为简单,形态以三度叠置的音程为主。第一乐句的后6个小节是主题的又一次呈现,与第一乐章中的创作手法类似,作曲家在这里将左右手功能调换,音区下降一个八度。第二乐句中主题仅出现一次就结束在羽音。
B段(25~78小节)。B段整体风格较A段更为活泼,这不仅体现在速度节拍上,还体现在旋律方面。右手旋律主要集中在高声区,明亮而轻快,而左手的伴奏继续沿用引子中的织体,低沉地铺垫在旋律下方。主题总共出现两次,且第二主题是对第一主题的变化重复,二者都采用中国传统音乐技法“换头合尾”。B段最后通过横跨三个八度的音区呈现主题,暗示主题的回归,这种旋律创作手法也常见于中国传统民间器乐曲中。
再现段(79~104小节)。再现段是对A段主题的重复,第一乐句没有像A段一样呈现两个主题,只有6个小节,更加简洁明了。第二乐章最终落在羽音结束。
2.3 第三乐章曲式结构分析
第三乐章为“ABABA”的三部—五部式,亦可看作“A‖:BA:‖”,具有一定的回旋性,其速度为“vivace”(活泼的)。该乐章共围绕a、b、c三个主题进行,其中b主题与c主题的连接部分采用a主题的动机。
a主题的第一次呈示(1~11小节)。该主题采用固定音型,并运用模进、倒影等创作手法对第一小节的音型进行变化发展。此外,作曲家在谱例上标注“跳音”记号,给本就活泼的旋律增添了欢快感。
b主题的第一次呈示(21~35小节)。与a主题相比,b主题速度变更为“poco legato”(逐渐变为慢板)。两个四分音符连续出现在6/8拍的复拍子中,打破了原有的八分音符为主导的结构,产生了独特的听觉效果。
c主题的第一次呈示(39~54小节)。经过两个小节a主题材料的连接,旋律从b主题发展至c主题,此时回归原速。第三樂章正是从a、b、c三个主题的循环往复中发展而来的,因此笔者认为其具有回旋性的结构特征。
3 作品创作特征总结
3.1 简洁明了的曲式结构
作曲家的结构安排清晰明了。曲式结构方面,王建中套用西方作曲技法分析,这一特征在第一乐章中尤为明显。
以第一乐章为例,作曲家主要遵循奏鸣曲式的原则作曲。在乐章伊始就呈示出主部和副部主题。其旋律基本没有脱离中国传统五声音阶的范式结构。发展部调性虽然飘忽不定,结构却相对明晰。发展部到再现部之间采用西方作曲经典技法中的“假再现”过渡,承上启下,简洁明了,经过两次模进后旋律主题重新回归,并只再现了较为快速热闹的主部主题,安排有详有略,恰到好处地保留了乐曲的精华。
3.2 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
王建中的旋律创作技法较为简单朴实,按照西方作曲技法来看,其主要采用模进和重复的变化手法发展旋律。而从中国传统作品的创作角度来谈,其旋法及句法具有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特征。句法上,王建忠采用了“句句双”“换头合尾”等传统器乐作曲技法,这分别在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中有所体现。
作曲家喜用模进,特别是三度模进,类似古代诗歌“一唱三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连接不同材料主题时,作曲家善用快速进行的十六分琶音。鉴于王建中多次将中国古曲改编为钢琴曲的成功经验,笔者推断琶音的写作是从民族拨弦乐器演奏形式中汲取的灵感。
旋律线条上,王建中遵循中国传统的旋律写作手法,即横向的线性作曲思维。以此为基础,他还运用了“复调”的西方创作思维。在第一乐章的分析中,笔者明确指出其喜用左右手功能交替的手法。
在和声方面,王建中多采用二度叠置的和声效果。正如杜佳骏所说[5]:“二度是中国和声的基石……一些钢琴奏鸣曲创作中运用了二度的音程,通过个性化的叠置,丰富民族音乐的色彩,使其符合中国人的听觉习惯,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大二度的和声相较小二度更为柔和,为整体平缓的旋律增添了立体的听觉效果。
节奏节拍方面,王建中并不拘泥于传统固定的节拍,在第三乐章中频繁转换拍子,形式多样,有单拍子、复拍子,这有利于旋律的自由发展。
调式上,乐章与乐章不同,各乐章内部转换也较为频繁,但不变的是王建中始终在五声调式的框架下创作。笔者认为分析作品时可以紧抓旋律骨干音进行分析,如第一乐章就围绕“D-F-A”创作,主要集中在F宫和G宫;第二乐章为“D-F-G”,没有脱离Bb宫系统;而第三乐章由于调式更加迷离,可以就每句的骨干音进行分析。
4 结语
王建中的《小奏鸣曲》兼具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意蕴。笔者重点分析《小奏鸣曲》三个乐章的曲式结构:其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式,第二乐章为单三部曲式,第三乐章为三部—五部曲式,由此可见其曲式建构在西方作曲技法的框架模式下,较为清晰明了。
关于其作品创作特征,王建中创作的核心仍为中国传统民间素材,即追求钢琴作品的民族化。其和声运用二度叠置的效果,饱满又不失柔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以和为贵”,其句法也运用了中国民间器乐、声乐曲中的“句句双”和“换头合尾”等形式,充分保留了传统音乐的独特韵味。
研究《小奏鸣曲》,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作曲家对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创新运用。笔者坚信未来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作曲家,他们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创新,将中国传统音乐发扬光大,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 李谌熙.王建中钢琴音乐创作技法:以《百鸟朝凤》《山丹丹的花开红艳艳》《随想曲》为例[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22.
[2] 刘仕博.王建中钢琴改编曲创作特点及演奏技法浅析[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17.
[3] 杜燕.王建中钢琴作品《情景》的创作风格与演奏技法[J].黄河之声,2023(10):106-109.
[4] 张志远.王建中钢琴原创作品探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7.
[5] 杜佳骏.新中国初期(1949-1966)钢琴奏鸣曲创作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6.
作者简介:麻义曼(2001—),女,山东济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