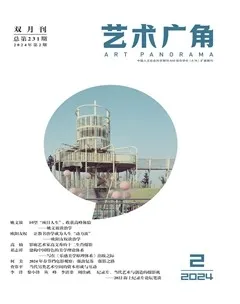探寻审美表达的中国道路:宗白华意境美学的四个突破
摘 要 宗白华的意境美学形成于中华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特殊时期,是民族文化的塑形力量在审美领域的典范体现。宗白华以融汇中西的学术视野对“意境”的新阐释,是中国现代“意境”理论形成完善的关键环节。文章从艺术冲动的文化属性、艺术题材的构成、艺术意蕴的生成,以及艺术理解与接受方式的角度,阐发宗白华意境审美思想对西式美学理论的超越与突破,从而揭示宗白华学术思想对中国式现代美学构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宗白华;意境美学;中国道路
对审美理论的中国式建制的探索,在中国现代美学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意境美学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宗白华关于意境的思考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其意境理论的核心思想基本完成。在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时期,这一高度凝练的理论体系寄托了宗白华关于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总体性认识与理解,它不仅是在内外高强度压力下,以高密度脑力投放形成的高浓度中国认知,更是中国智慧的典范。其中,对中国艺术特性的把握是贯穿整个过程的中心逻辑,二者相互融通、互为映照。
一、意境:一个具有全球理论视野的中国范畴
宗白华的意境理论来自于他的“写实、传神、造境”的艺术创造三步论主张,他在《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一文中说:“一切艺术的境界,可以说不外是写实,传神,造境:从自然的抚摹,生命的传达,到意境的创造。”[1]其中意境创造是艺术境界的最后完成。他指出,有人惊诧于西洋画的写实能力,认为中国艺术缺乏写实兴趣,是大错特错。中国艺术家写实的本事完全不输于西洋画家,只不过在中国,“写实终只是绘画艺术的出发点,以写实到传达生命及人格之神味,从传神到创造意境,以窥探宇宙人生之秘,是艺术家最后最高的使命……”[2]艺术创造具有不同艺术表达层面,只有到“意境”才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是中国艺术创造进阶的独特序列。
作为中国传统诗论、乐论、画论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进入近代后,“意境”出現的频率较之以前更高,逐渐成为描述中国文艺特性的核心概念,并被文艺家们不断以新的理论资源和理论视野更新深化,使其更富于现代气质,更符合现代中国对自身文化艺术的想象与传承。在宗白华之前,王国维已经把它(更多时候王国维用“境界”)当作诗词评价的最高标准。实际上,在王国维这里,他已经开始用康德、叔本华思想赋予这个概念以新意,并用西方艺术典型论深化了意境理论内涵,将其锻造为古韵气息浓厚的现代概念。朱光潜延续王国维的思路,进一步将中国古典理论与西方理论融汇沟通,用表现论理解意境,使意境理论更加缜密丰富。而宗白华更是化用歌德、尼采理论,强调了被朱光潜忽略的意境的理想性,尤其在中西比较的意义上,将其定义为中国艺术美质的典范,并将其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深层逻辑相连通,使其成为中国文明形态的代表。
20世纪20年代宗白华留学德国,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西方世界。欧洲和德国的文化艺术深深震撼着他,在丰富他的心灵和艺术素养的同时,也让他获得了一个从中国之外理解中国文化的视角,尤其是一战后西方对东方文化的仰慕情绪,让他有了重新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冲动。回国后的十几年间,这种冲动断断续续变成一些艺术思考和中西艺术比较方面的文章,而中国被动挨打的屈辱境地,一次次强化着这种冲动。空前的民族危机,不仅激发出国人身上过去不常见到的热情与壮怀,也唤起了学者们的创造激情。在这个历史转折点,“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见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1]显然,在民族危难之时,以世界学术视野,从中国人的文化艺术中提炼华夏民族的精神共性和独有美质,“化苦闷为创造,培养壮阔的精神人格”[2],是他这一时期研究的目标与动力。融汇古今学术精华,铸造中华审美话语,宗白华以贯通中西的学养和赤子情怀,完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理论创造。
我们今天的“意境”概念,无疑已经融入现代美学体系,人们自然会用现代甚至当代学理诠释它,这也造成了“意境”范畴使用中其内涵的模糊与游移。这里从对既有美学模式突破的角度,阐发宗白华“意境”理论,意在厘清内涵,显示这一理论的华夏文明底色。
二、“灵境”:“对待”模式的突破
对“意境”之美最常见的解释是情景交融,景中见情,情以景发,二者相互诱发以完成情感表达。但这种理解往往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能很好地将有感情的作品和有“意境”作品区别开,将“意境”等同于一般的抒情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概念是失效的。
究竟何为“意境”?宗白华对意境的表述,最有名的是这段文字:“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3]。之前他也说过:“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4]。可见,“灵境”是宗白华对意境的独到把握。
那么,“灵境”是什么?宗白华说“灵境”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这自然使人想到王国维的“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5]的说法,于是用情景交融理解“灵境”就成了自然的结果,这好像也讲得通。但如此一来,宗白华的“意境”就毫无特殊之处,想来宗先生也不至于用如此大的气力讲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问题。实际上,情景交融是“意象”而非“意境”的特征,作为一种特殊“意象”的“意境”,其内涵要远远超出情景交融[1],而这超出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由普通的“意象”到“意境”所发生的质变,所以他才称之为“灵境”。这个质变到底是什么,是我在研究宗白华思想时百思莫解的一个问题,直到我看到宗白华对歌德《浮士德》的解释。他说《浮士德》就是歌德描绘的一幅人生图画,但不是照着人生描下来的,而是另一种写法,他写道:
歌德以外的诗人的写诗,大概是这样:一个景物,一个境界,一种人事的经历,触动了诗人的心。诗人用文字,音调,节奏,形式,写出这景物在心情里所引起的澜漪……歌德在人类抒情诗上的特点,就是根本打破心与境的对待,取消歌咏者与被歌咏者中间的隔离。他不去描绘一个景,而景物历落飘摇,浮沉隐显在他的词句中间。他不愿直说他的情意;而他的情意缠绵,婉转流露于音韵节奏的起落里面。[2]
这幅人生图画,不过是歌德自身“生命”的“形式”,这是另一个歌德——创造出形式的歌德。歌德的人生境界,全由这幅图画象征出来了,虽然这图画看起来像实际的生活。这让人一下子就明白了这里的“质变”所在:“灵境”不是通过“景”所显示的与之对应的“情”,而是通过整体意象显示艺术家灵心妙趣,是超越了“情”的生命境界的映射。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他引用瑞士思想家阿米尔(Amiel)的话,“一片自然的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3]的含义,它绝不是说风景含情。因此,他的“灵境”概念就脱开了对“情”“景”进行主客二分的对应式理解,回到了王夫之所说的“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姜斋诗话》),“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方士庶《天慵庵随笔》)的情景。他说:“这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绘,像一照相机的摄影。”[4]艺术的意境绝不来自于模仿,而是天地相应的灵性创造。
宗白华所揭示的艺术形成的“意境”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艺术冲动的文化属性上,它突破了建立在“模仿”理论基础上的西方经典美学理解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西方艺术理论的情物“对待”模式对中国艺术理论的同化作用。产生于“模仿论”基础上的西方再现理论,经由古希腊的“哲理说”、文艺复兴的“镜子说”、启蒙时期的“关系说”等,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学艺术理解传统。到近代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这一传统受到了巨大挑战,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意识流等背离模仿论传统的艺术和文学创作手法纷纷出现,理论上的“对待”模式受到触动。现象学方法通过将对象包含进主体的方式缓解了这种对立,存在论哲学对东方思想的借鉴也大大拓展了西方理论的视野。宗白华的“意境说”在这种大背景下,无疑是从东方美学内部所做的理论扩展,而且是将东西方艺术融合在一起所做的總汇,是对世界美学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抒情”:叙事论模式的突破
宗白华“意境”理论的另一突出贡献,是他总结出中国艺术“意境”构成的题材特征,这就是强调以自然山水为“意境”基本的构成材料。“意境”在构成原理上虽然类似于象征,但却不是一种象征艺术,其中关键一点是“意境”的象征体不是任意的,而是独有的一类对象,这就是山水自然。
他说:“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展开我们音乐的灵魂,无尽藏的心源,只有山水的变幻灵奇是一种适当的象征素材,用来建造我们胸中的意境。”[1]“意境”的构成材料为山水自然之景,而不能以普通之人、事、物为题材。他借用薛冈《天爵堂笔记》里的话点出缘由:“山水义理深远,而意趣无穷。”首先,山水形象中包含的内蕴深厚绵远:“只有大自然的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才足以表象我们胸襟里蓬勃后尽的灵感气韵”[2],自然的山水具有无限的广度深度,而像人物、禽虫、花草等等,多出于画工之手,虽然看起来精妙工整,却是一眼就可以看透的;其次,山水形象意趣变换灵动。“山水变化无定形,可供心中意境底独创”,山水四时变幻不定,给艺术家以表现的灵活度,为艺术家表现心中灵境提供了无限可能性。这里,宗白华已经意识到山水自然是最具可塑性的对象,也最具心灵创造的可能性,正如郭熙所说“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态见也”,主观的印象可以帮助诗人画家观察自然,甚至对自然的主观化可以取代单纯的模仿。这种外在世界内在化的倾向正是中国艺术的悠久传统之一:抒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学者和台湾学者开始提出“中国抒情美学”概念,并对此进行了深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实际上,宗白华的中西比较艺术研究和中国“意境”理论的研究,是在现代美学史上最早对中国艺术的“抒情”特征做出阐释的。“意境”被宗白华作为中国抒情传统的最高范畴,认为它高就高在不是以按图索骥的方式进行创造,而是通过把世界内在化又把心灵外在化完成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高友工在论中国抒情传统时说:“抒情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创造力表现在,他们用符号构成表现了其内在的精神状态。相反,叙事艺术家则承认,他们通过对指涉性符号的运用,外在地投射他们所创造的世界……叙事艺术家将创作行为看作是人类行为,但不是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行为的,反之,抒情艺术家则认为创作行为是近乎卓绝的体验。”[3]宗白华“意境”理论要论证的,正是那些非指涉性的抒情符号,其中山水自然绝不是实指的生活之环境背景,而是精神生命的投射符号。这些山水自然无不内在化、有情化,这才有“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所以,他强调山水作为艺术题材创作“意境”的必要性,只有山水具有与日常行为的天然的区别度,作为非生活性符号进入艺术中,完成意境创造。内心中起伏摇荡的情思,任何固定的物象轮廓都难以表达,这时中国的抒情艺术家发现了山水自然,它的旷远变幻所带来的空间感受,突破了一切具体物象,实现了真正本源性表达。所以他才将“意境”与尼采的“达阿理索式Dionysius”(即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相关联,因为在尼采看来,来自本源的呼唤是不可以被写实化的。“灵境”就是内在世界“有情”了山水世界,山水世界的生动表情又凝固了内在心灵世界的灵奇。所以,山水成了追求“意境”艺术家们的最爱,“山水成为诗人画家抒写情思的媒介,所以中国画和诗,都爱以山水境界做表现和咏味的中心”[1]。
因此,中国艺术的“抒情性”是中国文化表达的模式,这就是作为意境的“有情有象的小宇宙”。它是中国人灵性的创造,是中国智慧、中国识见的文化表达,他说:“艺术意境的诞生,归根结底,在于人的性灵中……这微妙的境地不是机械的学习和探试可以获得,而是在一切天机的培养,在活泼泼的天机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体验中突然涌现出来的。”[2]可以说,“意境”并不是几个艺术家的创造,而是整体性的“中国心灵”的文化表征:“抒情特性,形成于自我与时机的契合,由个人历史的深刻性与丰富性所赋予,并因记忆和想象而持续……这印象性的和不确定的精神,正是抒情艺术家最终想获得的。”[3]这话用来解释宗白华的意境美学再合适不过了。
四、“创生”:表现论模式的突破
在分析意境特点时,宗白华讲了一个例子。他提到希腊神话中的水仙之神那喀索斯,临水自鉴憔悴而死;而中国的幽谷兰花,倒影自照,虽感寂寞却悠然自足。他用这个例子说明中西方艺术表现背后有着不同的艺术心灵在起作用。与西方不同,中国艺术心灵具有一种自足气质,它并非无欲无求,而是具有内在的意义创生机制;它不是对象化地聚焦于某一点,将之实在化,并在顺之或抗之中形成某种表达形态。中国艺术的自足性来源于其独有的结构,不聚焦、不固定、轻实体化,从而形成动态、灵活,意义随动而生的“创生”特性。所以,中国艺术不重在某种对象实体的描述刻画,而是借助对象的形式特征构造一个艺术空间,用他的话说就是“灵的空间”,这个空间充溢着活泼的生命律动,他说:“中国画中的虚空不是死的物理的空间架构,俾物质能在里面移动,反而是最活泼的生命源泉。一切物象的纷纭节奏从他里面流出来!”[4]这正是“意境”概念中特有的“创生”模式。
因此,“意境”创造,从艺术技巧上来说就是营造灵性空间,以方便意义的涌出。“意境”虽然以山水为材料,但实际上追求的不是山水之美,而是借山水形成一种可以让意义涌出的“结构”,不是一山一水、一树一石,而是全整的山水图,才有这个可能。就像书法艺术,中国字不像西洋字是由字母拼成,而是每个字占据一个固定的空间,写字时的各种笔划,如横、竖、撇、捺、勾、点结成一个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单位”,“成为一个‘上下相望,左右相近。四隅相招,大小相副,长短阔狭,临时变适。‘八方点画环拱中心的一个‘空间单位,”[5]。“望”“招”“适”“拱”,这不就是一个人境世界、一个灵性空间吗?
当然,与全整的山水表现相比,宗白华最为欣赏的是更加经济的山水自然的使用。意境“结构”追求的是传达功能的最大化,而不是材料占有的最大化。因此,他把道、舞、空白看作中国艺术意境的结构特点,就在于它们有极大的表现空间,这是中国诗境、乐境、画境、书境等共同具有的空间属性。他说:“庄子说:‘虚室生白。又说:‘唯道集虚。中国诗词文章里都看重这空中点染,抟虚成实的表现方法,使诗境、词境里面有空间,有荡漾,和中国画面具有同样的意境结构。”[1]虚境、留白等并不是空洞的无,而是留下巨大想象性空间的充实意象,生命的能量就是从这个虚灵的空间中显现出来,这也正是空间秩序显示的力量,与当代结构主义理论揭示出来的道理有相同之处,正如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所说:“人的思想的基础,不在于被模仿物和模仿物之间的相似,而在于组合物身上的规律性……结构中的各组成单元绝对不是一盘散沙……各个单元和它所属的虚在集合一起构成了一个智力有机体。”[2]结构中就包含了“创生”的动能。唯此宗白华才特别看重中国艺术中那些抽象的艺术形式,如建筑、音乐、舞蹈的姿态、书法、戏曲面具、钟鼎彝器的花纹等等,认为它们以简省朴素的方式,表征出不可言状的丰沛的“心灵姿式”。
这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流派形成鲜明对照,宗白华认为,某些西方艺术,那种对逼真的极致追求,乃至于反逼真而走向的抽象怪异,不过是生命的另一面表象:“西洋透视法在平面上幻出逼真的空间构造……逼真的假相往往令人更感为可怖的空幻”,“至于近代的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派等乃遂光怪陆离,不可思议,令人难以追踪。然而彷徨追寻是它们的核心,它们是‘苦闷的象征。”[3]
意境“创生”模式,从文本意蕴来源与生成角度,挑战了各式各样的文本表现论主张,张扬了东方“创生”智慧,为世界审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式。
五、“探源”:解释模式的突破
由于有意境的作品的非“对待”、非“表现”特征,其欣赏并不符合惯常接受模式,因此常常被“浅读”或“误读”,按照宗白华的看法,这是理解层面的误差所致,“意境”作品与非“意境”作品处于不同的理解系统。
他在《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中谈到,近代以来,对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心理学研究成了美学研究的中心,而对解释艺术作品至关重要的艺术意义、艺术理想、艺术对人生与文化影响等重要问题都交给了哲学家。换句话说,应该将文艺价值研究融入文艺研究中。因此,他提出艺术的“价值结构”问题,艺术不止关乎美,也关乎人生、文化,应该从价值论层面上重新看待艺术。他认为“艺术至少是三种主要‘价值的结合体”,包含形式的价值、抽象的价值和启示的价值[4]。其中,形式价值比较好理解,就是“美的价值”;抽象价值指“生命的价值”,实际就是生命体验或情感的价值;启示价值为“心灵价值”,指向的是启示宇宙人生的意义。
如果把这篇较早的文章,和他后来关于“意境”的文章结合起来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重在从价值论,而非审美论角度看待“意境”,对意境的阐释既不在景观的宜人,也不在情感体验的动人,而在启示宇宙人生意義的启人。那么,“启示”的呈现应该以何种方式完成?优美生动的对象,感人至深的情感体验,都是可以通过对审美对象的具体解释而让人理解,但“意境”接受由于没有直接对应的具体对象,就很难解释,一般的解释论并不适用。宗白华认为,“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因此,“领悟”既是意境创造,也是意境理解的方式,当然,更是获得启示的途径。
“启示”很特殊,因为它的对象不是某种知识或信息,可以传递或传授,也不是某种情绪情感,可以共情或同情的理解,而是非知识性的,对整个世界、人生、宇宙的通透,我们有时称之为真谛,宗白华叫作“真”或“真理”[1]。真理或真谛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来自于科学的永恒探求,抑或来自于上帝的神启,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来自于对自然律动、万物流转的体悟,所谓“道法自然”,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境”可以说就是这种悟道的审美化表达。因此,“意境”在宗白华这里代表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最高心灵的展现。
宗白华把意境创造和人格涵养紧密相连,并不把人格完全看作道德领域问题。他认为至高的人格来自于对世间万理的通透,超越了善恶美丑的判断,达至宇宙至理(可见他受老庄思想影响甚大)。艺术和哲学是相通的,“艺术要刊落一切表皮,呈显物的晶莹真境”[2],“意境”同时也是“真境”。艺术家的人格建立在以通透的宇宙生命理解为基础,所表现出的人生态度上。艺术家必要勘破现实世界的表层,从自然流转中悟得真谛,再以息息不止的生的精神,重塑一个元气淋漓、真义灌注的自然画面,方为有“意境”之作。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曾提出艺术反映时代、社会有两种方向,一是顺承性的反映,一是反省性的反映。前者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写实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艺术,顺承着现实的样子加以反映,增加观者精神的孤危、绝望。中国艺术精神属于后者,它即使在残酷的现实之下,依然“想超越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3]。所谓“反省性”,就是虽已了然现实却重在理想,以理想完成一个新自然世界的画面,这个画面就是“真境”,就是“灵境”,就是“意境”。这种理解“意境”的方式,我称之为“探源”式。这有点像中医,身体的个别痛处的医治,要返回到身体整体这个源头来处理;对“意境”的理解,也必须返回到宇宙人生整体的源头才能悟透。
宗白华意境美学对西式审美模式的突破,并非文化自尊意义上的理论对抗,而是有着必然的文化逻辑,他以意境之“诞生”为题,追踪的就是其内在的深层依据。“意境”概念触及的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这颗文化种子的外显形态。在模仿、形式、典型、理念等一众审美概念中,宗白华用“意境”范畴提亮了美学理论的中国色彩,并用它照亮了审美表达的中国之路。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研究”(L12AZW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迎新: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宏鹏)
[1][2]宗白华:《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第325页。
[1][3]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357页,第358页。
[2]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编辑后语》,《时事新报·学灯》1941年第126期。
[4]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5]王国维:《文学小言》,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1]叶朗先生在讲到“意境”时指出,近代以来,包括王国维在内,很多人是在“意象”即情景交融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意境”这一概念的。(叶朗:《美在意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从叶朗先生对“意境”的理解及其用老子和禅宗思想诠释“意境”内涵,约略可以见出宗白华先生的影响。
[2]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3][4]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第366页。
[1]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2]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页。
[3]高友工:《中国抒情美学》,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1]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页。
[2]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頁。
[3]高友工:《中国抒情美学》,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4][5]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页,第144页。
[1]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2]〔法〕罗兰·巴特:《结构主义活动》,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
[3]宗白华:《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宗白华:《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70页。
[1]宗白华认为,世界存在着由科学所面对的“自然结构”,同时也存在着由艺术所面对的“文化结构”,人类在这两种结构中都有真理探索的冲动。
[2]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366页。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