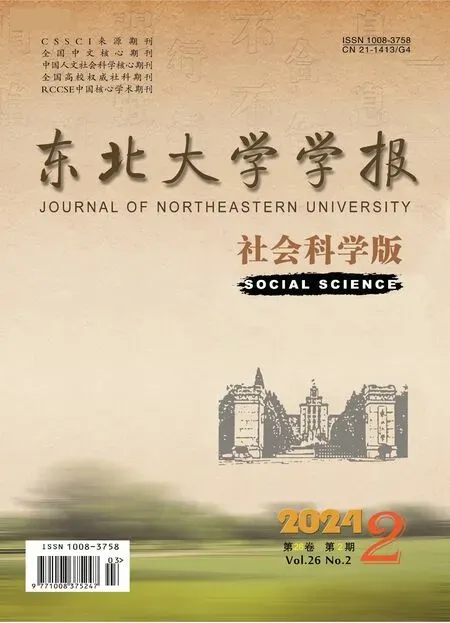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三次历史转向
张 畅,赵雪波
(中国传媒大学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北京 101121)
国际关系学是关于国际形势、国际交往、国际问题、大国关系等研究的知识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同的称谓,也有过不同的体认、关注和研究重心。比如在20世纪初,国际关系学曾被称为国际法、国际问题、国际学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关于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的研究采用了苏联模式,以“国际共运”事务代表国际事务,以国际共运史研究覆盖国际关系研究。这些历史现象以及对这些历史现象的认识,导致今天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起源认识出现了诸多分歧。不同于国际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创建于1919年的说法有较一致的认识,国内学界有关中国国际关系学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倪世雄和秦亚青认为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第一步(1)倪世雄、许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欧洲研究》1997年第6期;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卷。。梁守德和王逸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起点应从1963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算起(2)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学:简要评估》,《欧洲研究》2004年第6期。。还有人提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3年,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有许多理论与制度方面的探索,不应受到忽视(3)王亚琪、吴志成:《新中国7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创新》,《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5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进行了梳理,毛维准和任晓将民国时期学者们对国际关系史、国际法、国际组织的探索也认定在国际关系研究范围内(4)毛维准:《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2期;任晓:《回望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清华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还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关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科研已具备稳定的教学机构、成熟的课程体系和充沛的人才队伍,可以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那时已基本成型(5)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
很显然,在判断中国国际关系学起源问题上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20世纪30年代;二是1949年;三是1963年;四是20世纪80年代。相应地,每一种观点的原因可以分别表述为:旧中国历史应该纳入进来;1949年开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容忽视;1963年中共中央下发有关文件后,北大、人大、复旦等高校纷纷设立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科开始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与世界建立深度“国际关系”,也就无所谓国际关系学。这些观点和原因看起来似乎都各自成立,但是却让人顿觉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贯的。特别是考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压倒性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要么被遮蔽了,要么被代替了,而许多人又不承认国际共运史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这样一来,1949年至1963年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很长时段的断裂。
如何认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点,任何学科、学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任何学科、学术的发展都是历史发展大体系中的一环。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时候,能够把中国国际关系学放入中国历史进程的总框架中去,把它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总进程一并考察,那结果就大不一样。我们看到的将是和中国历史同频共振的中国国际关系史,而不是孤立的、割裂的、碎片化的、充满漏洞而又无法弥合为整体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史。
中国历史的进程不会停止,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历史进程也从未停止过,只不过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或者说,它有时候处于昌盛期,有时候处于低迷期;有时候处于勃发期,有时候处于转型期;有时候以国际关系的形式直接呈现,有时候又以其他话语的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指出中华民族复兴经历了三次伟大飞跃,第一次是1949年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富起来了,第三次是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强起来了。回顾前文所提到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节点,不正与中国近代历史的时间节点相一致吗?为此,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华民族复兴的三次飞跃理论指导我们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史的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学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在近代卷入国际体系的产物。中国的学人为了寻求救国出路,开始关注国际问题,开创了有关学术研究。但战乱年代是容不下平静的教室和课桌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在初期的探索筚路蓝缕,最终未成气候。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受到国家的重视,除成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院之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外交系,1963年又在北大、人大、复旦等学校成立国际政治系。这一时期,为适应两极格局形势,支持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大学专门设立了国际共运史专业。在后来相当长时间内,国际共运史成为一门直接或间接研究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显学”,国际关系学反而被忽视了。国际关系学的这一重大变化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历史转向,无论是研究性质,还是研究侧重点,都与旧中国时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不同。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二次历史转向。一段时间内整个学术界对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研究都被中苏关系所左右,研究的重心必然倒向国际共运史,而有关西方社会或中西关系的研究往往以内部参考的形式呈现,大大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但是改革开放开始后,形势完全转变,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也把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提到很高的位置。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史学术研究走入低迷,很多学校的国际共运史专业纷纷转向国际关系专业。历史进入21世纪,新时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力、影响力迅速提升,与此同时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不愿接受多极化格局,采取各种“出格”的行为阻止国际格局的改变,以致严重破坏了国际秩序,造成国际社会一轮又一轮新的动荡。时代呼唤理性的、公平的、和平的、有益于集体安全的国际秩序,也呼唤新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交往。事实上,西方已经有人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等新的理论体系。中国外交过去尽管有自己的原则、指导方针,但上升到理论体系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没有系统的、成熟的、能作为公共产品的理论体系,也就难免用美国和西方的理论做注脚。新时代呈现出新形势,也呼唤中国国际关系学进行第三次历史转向。
一、早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简要回顾
中国国内最早关注国际问题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开始意识到“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一方面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中国摆脱封建王朝的桎梏、谋求国家现代化密切相连。林则徐、魏源等改革派通过译介、著作等形式积极向国内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主张,萌发了近代以来中国最早的国际意识。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被划归政治学学科,以《钦定学堂章程》(1902)和《奏定高等学堂章程》(1904)为依据,晚清高等教育分科体系基本形成,其中有关国际问题的专业被划分到“政治科”中的“政治学”“法律学”和“政法科”中的“政治门”“法律门”,或者文学科中的“万国史学门”等科目中(6)郭德侠:《中国近代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9—84页。。在开展有关教学、研究过程中,大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如何统称这方面的知识,是用“国际问题”还是“国际事情”(“国际事务”),是用“世界政治”还是“国际政治”,抑或是用“国际法”还是“国际关系”?1933年,南开大学教授徐敦璋提出国际学概念(以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作为其英文对应名词),以统摄其时国内碎片化的国际问题研究。徐氏指出,国际学是一门研究各种国际生活的科学。这里的国际生活包含和统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法律互动;称其为科学是指将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国际现象的考察中,以期寻找国际事务的法则和因果规律(7)徐敦璋:《国际学的研究》,《外交月报》1933年第5期;张明养:《国际政治讲话》,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但这一概念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而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研究、教学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史、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外交学三个领域。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与教学以“世界之于中国”和“中国之于世界”作为两条主线。“世界之于中国”是指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史的介绍,找寻中国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路径。其中,王绳祖在金陵大学的讲义《欧洲近代史》可谓集大成之作。而“中国之于世界”则主要关注中国在“天下体系”式微后如何屈辱地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等著作为中国外交的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理论准备。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研究方面,民国学人认识到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国际组织虽然不能摆脱大国控制,却为中国提供了伸张正义、提升国际地位的平台。在巴黎和会失败和抗日战争爆发后,学者们认识到对国际组织原来那种理想主义的期盼需要调整。一方面,大国政治阻碍国际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多扮演求助者,而非施与者的角色,因而有“乞怜外交”之嫌(8)张君劢:《乞怜外交与国际地位》,《三民主义月刊》1934年第4期。。至于国际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可谓熠熠生辉。中国学人还参与到国际法的编纂和国际裁判实践中(9)如中国学者郑天锡于1936到1949年在海牙国际法庭任法官,梁鋆立则直接参与到国际法的制定、编辑和法律执行中。。此外,对西方国际法和先秦国际法的比较研究至今无出其右。外交学研究方面,学人们在学术与实践之间的穿梭探索也构成了羸弱的旧中国在世界舞台争取国际空间的一抹亮色。一批引介性专著如杨振先的《外交学原理》、王亚南的《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和刘达人的《外交科学概论》等为外交学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0)任晓:《回望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清华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学上承晚清以来开眼看世界,以西洋之学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志向,下启新中国独立自强,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夙愿,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储备了大量理论成果,还提供了学科建设的经验,为新中国储备了国际关系学的学术队伍。这一段历史理应纳入近现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范畴。
二、第一次历史转向:以“国际共运史”为重心的国际关系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让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世界分成两个半球。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为了保卫自己,也为了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新中国宣布“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国际格局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变了,中国的外交变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性质、目的、体系、重心也都改变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关系学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与西方“接轨”的国际关系学,另一套是完全接受来自苏联的国际共运史。
单从概念上就可以看出,与西方“接轨”的国际关系学其实是承继了民国国际关系学的脉络,又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扩容,最关键是以国家行为展开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年12月,国际关系学院成立;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便设立外交系,并且“下设国际法、外交通史、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政策等教研室”(11)王邦佐、潘世伟:《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32页。,主要关注对苏联东欧等国的政治经济的教学和研究;1955年9月,在周恩来的倡议下,外交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的基础上成立;1963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经周恩来批准,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其中,北大侧重第三世界亚非拉地区研究,人大侧重开展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研究,而复旦则主要负责欧美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12)王邦佐、潘世伟:《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第432页。。可见,当时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已经逐渐地、进一步地围绕专业设置、学科建设、研究重点进行全面的设计。否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做出设计、规划的观点是不客观、不真实的。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国家对新设立国际关系专业的高校的具体科研工作也做出了进一步的区分,中国人民大学侧重开展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研究,足以说明不能把国际共运史研究排除出中国国际关系学之外。换言之,从研究目的、学科属性上判断,国际共运史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或者说二者是一个整体,不能把国际共运史和国际关系史以及国际关系学割裂开来。
在建设与西方“接轨”的国际关系学的同时,国际共运史学科也开始建设。这一学科的建设开始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公共课程。这门课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教材,主要讲授苏共党史。为了形成独立的国际共运史人才培养体系,1956年人大开始招收国际共运史专业的研究生。1958年,人大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撰了中国首部国际共运史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同时把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提升为马列主义基础系,分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政治学两个教研室。1959年,国际共运史专业的本科生培养开始在人大等院校展开。到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国国际共运史这门学科逐步走向独立,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有了独立的大纲和讲义,并积累了系统的文献资料。共运史研究涵盖巴黎公社、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等内容,在当时成为一门“显学”,很多高校都设置了相关院系和专业。
正如开篇所言,国际关系学是国际形势的产物,其研究内容、重点都要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恶化,高层对形势的判断有所调整,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变化。1964年,中共中央出台加快国际政治人才培养的政策,人大马列主义政治学系改名为国际政治系,而国际共运史则设在该系下面。“文革”期间,国际共运史教学与科研工作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但是基本的教研队伍得以保留,专业课程也得到延续。按照有关学者的说法,这些积淀都为改革开放后“国际关系学”的重生提供了学术和人才上的储备(13)蒲国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发展70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高放:《建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2期。。
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际局势剧烈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有两大事件左右着人们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做出选择。一件是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特别是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不再采取过去“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另一件是苏东剧变,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国际关系学开始了第二次的历史转向,主要的现象就是国际共运史学术研究陷入低谷,而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则“正本清源”,回归C位,成为学术界和年轻学子追捧的“显学”。
三、第二次历史转向:“国际关系学”的回归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二次历史转向是从上而下进行的。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出指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这一讲话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复兴和国际问题的全新研究格局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和思想基础。国际关系的课程在一些传统国际关系学科很强的高校中重新开设。1979年和1980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交学院分别开设了“国际斗争基本理论”,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开设了“国际关系理论”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介绍”等课程(15)洪远:《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程述要》,《历史教学》1989年第11期。。从80年代开始,大量的中国学者纷纷前往美英等西方国家学习或访学,开阔了眼界,加深了与美英等国家在学术上的交流。一大批西方学术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者们也积极开展有关研究,创作了一系列专著和教材,整个国际关系学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二次转向以后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经历了一个从旧范式向新范式、从粗浅到深入、从直接引进到消化吸收、从借鉴学习到独立思考的转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入,中国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不过,这一时期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的理解还处在摸索阶段,对西方理论成果的引介也比较零散”(16)特约记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
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大改观。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系统化地引入西方经典理论,许多经典著作如《现代世界体系》《权力与相互依赖》《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纷纷被翻译成中文。在译介西方著作的同时,中国学界也积极跟进美国等国家学界有关研究,开展专题性研究。比如,针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王沪宁发表了《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引入了软实力的概念,也引发了中国如何提高软实力的讨论;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学界展开讨论和批判,以王缉思主编出版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突出代表;针对西方学者提出的“民主和评论”,中国学界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指出该理论的解释力瑕疵和美式霸权的内嵌性(17)李少军:《评“民主和平论”》,《欧洲》1995年第4期;王逸舟:《国际关系与国内体制:评“民主和平论”》,《欧洲》1995年第6期。;针对国家利益讨论,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突破以阶级为分析单位的分析方法,强调国家整体的、客观的、可排序的国家利益。
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从学科建制化角度来看,开设国际关系学院的学校日益增多,从传统强势学校扩散至其他综合性大学与专业性科研院所,如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中国传媒大学等等(18)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学:简要评估》,《欧洲研究》2004年第6期。。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很多学校把原来设立的国际共运史专业纷纷改为国际关系学专业。这不仅反映了从学术界到管理部门对国际形势的新体认、新判断,也反映了全社会希望融入国际社会的积极态度。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重点在于崛起中的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和中国本土文化如何滋养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两方面。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快速上升,中国崛起已不可阻挡,中国的国际角色也在进行着转换,这些心理、意识、思维等等都无可回避地体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中。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梁守德为代表的学者就开始呼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中国意识”。他多次撰文论证建立中国特色国际政治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主张在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定位、国家性质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应力求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形式与内容的统一(19)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2期;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论的“中国特色”》,《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进入21世纪,中国学界的这种理论创新的意志更加强烈。秦亚青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关系性”置于国际社会的本体,用关系理性代替个人理性刻画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将国际行为体塑造关系的互动定义为一个过程,弥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静态性和个人本位偏见(20)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卷;Qin Y.,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阎学通在整理先秦国家间(inter-state)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道义现实主义,将权力和国家声誉作为增强国家权力、提升国家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层面上实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21)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卷,第102—129页。。赵汀阳试图构建一个建立在整体主义基础之上,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的共在秩序,事实上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进行了哲学思想的铺垫(22)赵汀阳:《以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问题、条件和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赵汀阳:《天下秩序的未来性》,《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任晓等人提出“共生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是异质性的,双方具备彼此相互欣赏和包容的能力,因此可以实现“共存”,为多种文化的包容共存、全球事务的共同治理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建构奠定理论基础(2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国际关系学完成了几大转向。首先是学科建设从国际共运史转移回国际关系学本体,具体表现是国际共运史研究从“显学”变成了“微学”“冷学”,而国际关系学则从“微学”“冷学”成为“显学”。很多高校原来所设国际共运史专业“摇身一变”为国际关系学,没有国际关系专业的学校则纷纷设立此专业。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从个别学校迅速扩散到各高校,成为“大众化”学科。其次是研究问题的关注点从东方转向西方,再转向全球;从孤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转向积极活跃的资本主义阵营,再转向整个国际社会。学科的边界不再非此即彼、界限分明,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成为本学科研究的一大特色,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互动、交流、争论成为常态。最后,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大的转向是中国学者们从简单译介、引进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到积极开展评介、争论和批判,再到创建自己的理论、观点。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学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力争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国际关系学领域更大的国际话语权。而这也为即将开启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历史转向提供了方向和动能。
四、第三次历史转向:从全球治理到新型国际关系
世纪交替之际,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热词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概念当然并非21世纪才出现。早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就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该委员会出版了OurGlobalNeighbourhood:TheReportofTheCommunicationonGlobalGovernance,这成为全球治理的滥觞。全球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24)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u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多元主体、消除冲突,这样两大主题足以成为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期盼。在詹姆斯·罗西瑙等学者的开拓下,全球治理研究开始在西方兴起。美国学者霍华德·弗雷德里希(Howard Frederick)称这种因全球环境危机等发展问题导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转变为“范式转移”(25)Howard H.Frederick,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
最早向国内介绍全球治理理论的有俞可平(26)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唐贤兴(27)唐贤兴:《全球治理:一个脆弱的概念》,《国际观察》1999年第6期;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等人。蔡拓等人的系列著作《全球学导论》《全球治理概论》《全球学与全球治理》则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创立自己的全球治理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全球治理观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7/content_41805113_7.htm.
在各种因素主导下,全球治理已经成为近2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重心的一种转向。本文曾借助CNKI的文献视觉分析功能,就相关文献的发文趋势、关键词时空分布等,对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类CSSCI期刊中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的文章进行了分析,检索到3020篇文章。研究发现,以“全球治理”为主题的文章最早出现在1998年(1篇),其后在2020年到达峰值(362篇),2023年稍有回落(291篇);整体来说在2015年前呈稳步上升趋势,在2015年后呈迅速上升态势(见图1)。最初几年的文献主要围绕“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等概念展开探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相关文献开始转向有关“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以及“新型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路径的讨论。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和2012年国际电信世界大会之后,全球治理相关研究转向“气候治理”和“互联网治理”两个子领域。2015年以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实施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提出,全球治理相关研究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核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重点,突出强调“中国智慧”和“中国思想”。

图1 全球治理相关文献发文量时间分布图
全球治理理念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信奉的现实主义的对抗。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特别推崇现实主义,在国际上大力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思想,不断挑起冲突和战争。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一直是最大的流派,拥趸众多。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学界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并不得人心,国际社会所推动的全球治理对美国的现实主义形成了极大的掣肘。全球治理理念与现实主义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全球治理理念占据主导时,美国现实主义就收缩;反之,美国现实主义狂热时,全球治理理念就萎缩。从特朗普当政开始,美国向世界发起挑战,挑起和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激烈冲突,甚至直接喊出“去全球化”口号,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直到现在也难以回归理性。在美国带头下,整个西方的外交政策方向都发生了调转,俄乌冲突是其具体体现。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全球治理严重赤字。很显然,从结构关系上讲,全球治理作为国际关系策略和手段的选择,并不能完全主导国际关系,更不能代替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理念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内容之一,也无法代表整个国际关系学体系。国际关系学如果想要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并对其做出理论指导,就需要一种真正的转向。
真正能和“国际关系”一词相对应,又能体现新时代中国智慧的概念是“新型国际关系”。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概念。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是中国政府对未来国际关系的设计,中共十九大报告不仅提出了全球治理观,也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7/content_41805113_7.htm.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南,也成为未来我们认识、判断国际形势走向的重要指南。
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于旧式国际关系或传统国际关系而言的。传统国际关系发端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强调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开展国际交往。但传统国际关系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由西方强权国家主导,奉行丛林法则,往往通过战争形式改变现状、攫取利益。在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和平、发展、合作的今天,西方这些国际关系原则就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其陈腐、落后、过时的性质一目了然,因此也可以称其为旧式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要求改变这一切,提倡以相互尊重代替傲慢霸凌,以公平正义代替自私自利,以合作共赢代替对抗冲突。新型国际关系是对旧式国际关系思维的一种转向,并不是要取代既有国际关系秩序。今天的国际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因此新型国际关系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新型国际关系尚没有到来,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应然,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但是作为一种状态,它正在促使国际关系发生全局性的转向。
新型国际关系需要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做指导。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一定是有别于过去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一定要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定要超越和发展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过去以梁守德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曾为了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学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朝乾夕惕,今日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特点,将其拔高为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或新型国际关系学。无论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也好,还是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也罢,在国内都是有阻力的。有的学者反对,有的学者怀疑,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公认的学术体系,没有什么中国特色一说。至于说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由于新型国际关系尚不成型,更何谈理论?其实,这些顾虑是多余的,旧式国际关系的顽疾、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捉襟见肘”已经令西方学术界开始反思。2007年,阿米塔·阿查亚与巴里·布赞在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Pacific期刊上发表论文,发出“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问。他们借由罗伯特·考克斯的新葛兰西主义批判理论,为理论的多元主义和重塑边缘地区的理论主体性开辟了空间。在此基础上,2019年,阿查亚和布赞又联合出版《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百年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论就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理论的假设之上”(30)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表明,由西方发展起来的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概念——包括民族国家、权力、制度和规范——与当地学者在这些不同地区所感知和分析的现实之间的脱节正在日益加深。”(31)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3页。因此,他们认为要创立一门全球国际关系学,“希望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发展一门真正包容和普遍的学科,真实地反映国际关系学者日趋增长的多样性和他们的知识关切”(32)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302页。。
中国承诺要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或新型国际关系学就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阿查亚和布赞倡导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带了个好头,但他们的理论极有可能只是“去西方国际关系学”,或者是“西方国际关系学”和“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简单相加。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这样的理论是不够的,我们中国学者必须尽快站出来,创立真正符合国际关系现状和新型国际关系走向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或新型国际关系学。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介绍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思想,继承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概念,吸收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精华,还应该包含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经验和思想,更应该包含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判断、设计和规划。当然,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或新型国际关系学概念可以推敲、商榷,以寻找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
总之,第三次历史转向不是对历史的回顾,而是对现状的理解和对历史方向的判断;不是对理论进行总结,而是对理论进行呼吁。但这些理解、判断和呼吁并不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而是国际关系必然的结果。这一转向已经开始,这一结果也初露端倪。
结 语
中国国际关系学创立于旧中国,但勃发于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自然地完成了第一次历史转向,全面学习苏联,引入苏联“国际关系理念”——国际共运史;改革开放后,融合国际社会,学习美英等西方国家先进经验,让中国国际关系学开始第二次历史转向——“回归”国际关系学本体(其实是西方主导话语的国际关系学);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在急剧变化,旧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无法回答国际关系的现状问题,也无法适应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理念、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或新型国际关系学顺理成章将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转向,其实也是国际关系学的一次转向。第三次转向的过程以全球治理观为起点,以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为爆发点,其宗旨是改变旧的不合理的逻辑,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