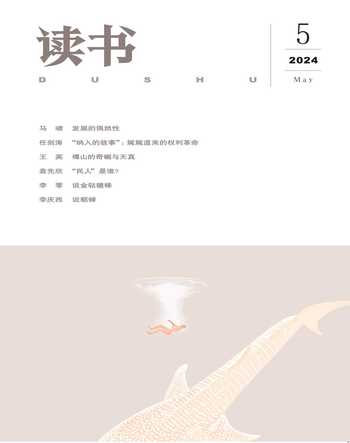俳句与二十四节气
李长声
日本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官僚从国土交通省下凡,到气象协会当头儿,上任三把火,要制订“日本版二十四节气”。理由是中国传来的二十四节气虽然给季节的变迁添彩,但冷的时候立春,热的时候立秋,不感到“违和”(别扭)吗?孰料,此举当即惹恼了俳人,群起反对,致使这把火未能像和式木房子失火那样呼啦烧起来。
俳人们为何反对呢?原来俳句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十七个音节,节奏为五七五,这是外形的限制;二是用季语,这是内容的规定。因为有这两个原则,俳句才成其为定型诗。
季语是表示季节的特定词语,用之使俳句有季节感,以致从古至今的俳句能统统归类为春夏秋冬。创办角川书店的角川源义也是国文学家、俳人,他说:“季节感是俳句的生命,第一要素。除去它就不再是俳句,甚至不过是川柳(注:与俳句同样十七个音节但不用季语,类似打油诗)或者一种警句。”用我们的诗词说事,譬如清人俞樾在试卷上写下“花落春仍在”,得到考官曾国藩赏识,这句诗若作为俳句,“花”和“春”就是季语,表示春。作俳句,字里行间必须用一个季语。例如芭蕉作:“此秋は何で年よる雲に鳥”(今秋复何秋,怎么一晃就老了,云中远去鸟),“秋”是表示秋的季语。季语如同一年四时的标签,其源头和基底是二十四节气。日本气象协会企图另起炉灶,“创造新日本文化”,好似给俳句、和歌等传统文化来一个釜底抽薪。
哪个词是季语,约定俗成,再加以选择,汇编为《岁时记》,供人作俳句时查阅,有点像韵谱。《广辞苑》词条下也有标注,类似我国《辞源》注明字头属于什么韵。《岁时记》是季语的词典,按春、夏、秋、冬、新年五部分编排,各部分又分为时候、天文、地理、行事、生活、动物、植物七项,解释并举例。《岁时记》的祖型是八世纪传入日本的《荆楚岁时记》。对于人来说,仿佛空间是具体的,而时间抽象,所以“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用具体的事物来把握抽象的时间,俳句《岁时记》可谓二十四节气以及七十二候在日本落地的扩大版。角川书店二〇二二年修订出版《俳句大岁时记》,收古今季语一万八千多。《岁时记》的季语解释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理解诗意的基础,从而形成俳句共同体。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诗型像俳句对季语这般“拜物”,作俳句就是玩季语。《岁时记》恍如庭园,已不是真正的自然。即便是写生,选用季语便带有先验性。季语因时变化,有的退出时代的舞台,所以坊间有《濒于绝灭的季语词典》,而社会发展,又不断产生新事物的季语。例如雾霾(日语:光化学スモッグ),一九六五年出现这种环境污染,一九七〇年引起社会重视,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考虑收入《岁时记》,却拿不定它算哪个季节的现象,《俳句大岁时记》中将其列为冬季语。季节感在城市生活中趋于淡薄,正如那首《北国之春》唱的:城里闹不清季节,老娘寄来小包裹。现而今维持季节感的,几乎除了商家应时叫卖“旬”(当令),就全靠俳句。四季分明,最分明在俳句里。说来我们也不是凭实际感受,而是靠挂历上的农历勉强维持对农耕的记忆。
公元前七世纪中国人用圭表测量太阳的影子,以日影最长的冬至为基准,到下一个冬至为一太阳年。把一太阳年二十四等分,即二十四节气。一节气大约十五天,逐一命名,这些名就是季语。再把每个节气细分为三,五天一候,共七十二候,基本是阳光底下的自然现象,具体地表示气象、动植物等的时节变化,季语更多了。又利用月有圆缺的周期变化,把一太阳年划分为十二月(朔望月)。一太阳年大约三百六十五天,而十二个朔望月合计三百五十四天,相差十一天,于是数年加一个闰月来调整。太阳的光和月亮的形(月相)组合,构成太阴太阳历,也就是农历。
三世纪日本,那时叫作倭,据史书《三国志》裴松之注:“魏略曰,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日本书纪》记载:至晚公元五五三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向日本派遣历博士。奈良县出土六八九年两个月的历书断简,是中国南北朝的元嘉历。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大衍历,但无人明白,三十年后的七六四年才使用,仙台市也有出土。正仓院藏有七四六年、七四九年、七五六年的历书片段,这是利用历书的纸背面记事留下来的。朝廷每年颁发的历书是具注历,完全用汉字汉文,想来没有多少人能看懂。平安时代中期(十至十一世纪中叶)随着假名的普及,出现假名历书,这是历书日本化之始。欸乃一声,渤海国使节给日本送来当时唐朝使用的宣明历,自八六二年,延续使用了八百二十三年。手抄历书,大约在镰仓时代(一一八〇至一三三六)兴起雕版印刷。一六八四年朝廷下诏引进明朝大统历,恰在此时,涩川春海搞出日本第一部历书,于是用国产,名为贞享历。兹事体大,井原西鹤和近松门左卫门都编了净琉璃,竞相搬演。
逝者如斯,明治四年(一八七一)政府要人们组团出访欧美,长达一年十个月,大隈重信留守。这是打败我大清十年前的事,尚未得到天文数字的赔款,日子过得穷。偏偏明治六年又赶上闰年,需要发十三个月的工资,这如何是好?天无绝人之路,而且人有改天之路,大隈重信采用了一个绝招—改历,把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定为阳历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一月一日,与世界接轨。这下子不仅没有了旧历(太阴太阳历)明治六年的闰月,而且明治五年十二月只剩下两天,也无须发薪,一举省下两个月财政开销。民众尚不知天下有阳历之说,蒙头转向,启蒙家福泽谕吉撰写小册子《改历辩》,普及太阳历和时刻法,一时间卖掉二十多万册,又大赚一笔,助他一八五八年创办的义塾(庆应义塾大学)渡过难关。
二十四节气反映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气候特征,不可能与海洋性气候的日本天衣无缝。日本古人当然察觉了这种龃龉,九〇五年编成的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集》中有一首短歌,咏立秋之日“秋来ぬと目にはさやかに見えねども風の音にぞ驚かれぬる”,意思是:已是立秋日,眼见未分明,一阵清风响,顿觉凉意生。二十四节气是节点,而秋季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并非立秋就骤变。人们在生活中日常以温度感受时节,而太阳的运行与气温的变动不完全一致。日本的地理南北细长,气候多样,即使搞一个“日本版”,各地的节气也难以一言以蔽之。二十四节气是广域的、統一的、人文的,五里不同风,一村一本《岁时记》没有意义。拿樱花来说,冲绳一月开,迤逦北上,开到北海道已是五月。北海道出生的作家渡边淳一说:北海道是没有季语的地方,冲绳也同样。因为《岁时记》先是以京都为准,后来改为江户。我国一九一二年改用阳历,并用农历,而日本彻底废除了旧历。这件事上未见他们惯有的二重性,但是为天皇保留了年号,事到如今,便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五个传统节日:正月、上巳、端午、七夕、重阳,都挪到阳历过。阳历比农历早一个来月,所以三月三日过桃节(女儿节),桃花还没开。七夕是星辰的祭日,但阳历七月还在梅雨里,难得见星星。这种“阴差阳错”是一般日本人觉得二十四节气与体感不合的一大原因。
江户时代大约二百六十年,四次改历。涩川春海结合日本实际,编出“本朝七十二候”。例如,立春的初候“东风解冻”不改,二候“蛰虫始振”改为“黄莺睍睆”;启蛰的末候“鹰化为鸠”改为“菜虫化蝶”;芒种的二候“鵙始鸣”改为“腐草为萤”;大暑的初候“腐草为萤”改为“桐始结花”;立秋的二候“白露降”改为“寒蝉鸣”,末候“寒蝉鸣”改为“蒙雾升降”;立冬的初候“水始冰”改为“山茶始开”;小雪的末候“闭塞成冬”改为“橘始黄”,大雪的初候“鹖鸟不鸣”改为“闭塞成冬”。日本没有老虎,只有熊出没,大雪的二候“虎始交”改为“熊蛰穴”。日本还增加了“杂节”,如节分、彼岸、土用,犹如在二十四节气的里程碑之外又立些路标。
明治改历,福泽谕吉在《改历辩》中把三月、四月、五月定为春季,又一位四睡庵壶公配合新历(太阳历),一八七四年重编《岁时记》,将春季伊始改为月初立春的二月,从立春之日至立夏前一天为春季。这样一来,一月就处于冬季,有违自古以新年为春天之始的生活习惯,于是他干脆在四季之外给新年单独立项。这个体例成为《岁时记》的定规,以至于今。《岁时记》被科学了一下,但俳句等传统文学不少都坚持用中国进口的原装。季语不是科学。时节冷暖是共同经验,具有普遍性,俳人们借以共有文学上的时间。
季语的作用在于表现季节感。日本人常说他们是特别有季节感的民族,这种季节感来自绳文时代—公元前一万年至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据说日本人的DNA是三重构造,很有点科幻,底层深潜着绳文人的印记。宗教学家山折哲雄这样说:日本文化是三层叠加而成的,最深层是日本风土养育的感性,也就是有继承自绳文人的信仰,《万叶集》中可见的思考方法、感受方法。以《万叶集》时代为起点,开始重层化,其上堆积着农耕稻作社会的观念和世界观。最上层堆积着明治时代以来近代化所产生的近代文明观念和思考方法。“平常我们是生活在最上层的近代意识中,但其实,中层的稻作农耕社会的意识、深层更古代的意识也残存于我们内心。”
动物以及植物也有季节感,如《文心雕龙》所云:“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影响万物之意)深矣。”绳文人以采集狩猎为生,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更直接,更密切,但是说俳句用季语表现扎根于日本人原始心性的共通不变的感觉,却不免匪夷所思。繩文人当然有季节感,但季节感是对于季节的感觉,不是概念,季节的概念来自二十四节气。传入日本后,掌握这种概念成为教养或学识。《万叶集》的和歌以恋歌和挽歌为主流,而尊重季节感、吟咏自然是旁流。大量地汲取汉诗文,产生二十四节气式自然观念,和“恋”一同咏“当季”成为原则。连歌重视“四季之词”,逐渐形成对四季景物的特定的联想和感情,便有了季语意识。俳谐(连句、俳句等)的季语意识进一步成熟,以至整理出《岁时记》。日本国文学家堀切实指出:“日本的季节感或者岁时感觉绝不是起初就自然发生的,就连歌、俳谐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制度发生的。”
日本人爱谈自然观。季节感是感觉,自然观是观念。物理学家、俳人寺田寅彦在《日本人的自然观》一文中比较日本列岛与西欧,认为日本的自然非常不安定,日本人尽量防备,但一旦自然狂暴起来,就不再反抗,在自然面前低头顺从,抱着“天然的无常”感觉对应。大概这就是日本人在震灾时淡定守序的情形,全世界为之点赞。不仅在自然面前,处于强大的占领者之下也如此。西方人信仰教义,日本人感受神力,但果真对自然逆来顺受,他们的祖先怎么能走出原始状态呢?只怕对于占领者也是在卧薪尝胆。所谓顺从自然、善于调和,可能是受了道教以及佛教的影响以后给自己的行为找到的理由。不反抗台风、地震等自然的狂暴,日本人活不到今天。为抗震,用木材建房,屡烧屡建,他们认为这就是顺应,并非反抗。葛饰北斋画的浮世绘,小船搏击滔天大浪,不就是征服自然的写照吗?日本自然观确实与西方有所不同,譬如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走进森林,而是在林外观赏。西方人剪掉枯枝,任树木自然生长,而日本人掐芽剪枝地造型,把自然风景变成宠物。他们爱的是人工的自然。季语是已经加工过的自然。宣扬不违逆自然、一切都顺从自然,似乎也意在摆脱中国自古主张的“人定胜天”思想,以示其文化独特。
最妙的是寺田寅彦这句话:“自然观不同,西方使科学发达,而日本发达了俳句这种极特异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