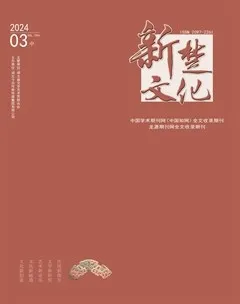李兴宗《观八阵图有感》发覆
【摘要】南宋李兴宗《观八阵图有感》收录于《全蜀艺文志》、诸葛亮集、《蜀中广记》《宋诗纪事补遗》等文献中,各种文献又有不同版本,致使该诗各种文本之间颇有差异,特别是那些因避清廷忌讳而改动的诗句,影响了对诗义的理解。兹广据版本,校勘同异,订为善本,且据以释读其诗义,并考证作诗之年代背景。
【关键词】《全宋诗》;李兴宗;《观八阵图有感》;校释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261(2024)08-0022-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08.007
李兴宗,字仲衍,号谦斋,洛阳人,后寓居夔州路(今重庆东部)。举进士,科名不详。庆元元年(1195年)知无锡县,庆元末居蜀,以刘德秀举荐,嘉泰中任国子监博士,嘉泰三年(1203年)与魏了翁等弹劾韩侂胄而去官离京。开禧二年(1206年)知信阳军,参与开禧北伐。开禧三年(1207年)至嘉定年间,为成都路提刑官,为官清廉,崖岸清峻,公私分明,颇孚时望。《全宋诗》收录李兴宗二首:《游青城山》《观八阵图有感》,《全宋诗订补》校补后首诗一句,并据《舆地纪胜》卷一五一补辑《宋别驾墓》一首,此三首皆作于巴蜀。其中《观八阵图有感》一首,有多种文献收录之,各种文献之间文本有差异,同一文献不同版本文字亦多有异同,有些文字有一些文本是对,有些文字所有文本皆错,有些文字的异同影响对诗义的释读,兹校勘文字同异,择善而从,校成定本,释其诗义。
一、文献著录与版本介绍
以现存文献考察,《全蜀艺文志》、诸葛亮集、《蜀中广记》《宋诗纪事补遗》收录了李兴宗《观八阵图有感》,其中各书还有版本间的差异。其中明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卷一五)最早著录之。《全蜀艺文志》为嘉靖《四川总志》中《艺文志》,明杨慎编纂,周复俊重编,后遂冠周氏名。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皆收录《全蜀艺文志》全文。《全蜀艺文志》版本有嘉靖《四川总志》本(简称嘉靖本)、万历《四川总志》本(万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本)、嘉庆二年(1797年)朱云焕刻读月草堂本(朱本)、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谭言蔼刻本(谭本)、光绪十一年邹兰生刻本(邹本)等,学者刘琳、王晓波以嘉靖本为底本,汇集其他版本,校勘异同,加以标点,整理成点校本,2003年线装书局出版(简称点校本)。诸葛亮集有以下版本:明王士骐辑《诸葛武侯全书》(卷十九),明崇祯十一年(1639年)吴天挺刻本(简称王士骐本)。明诸葛羲辑《汉丞相诸葛忠武侯集》(卷十二),清嘉庆刻《道藏辑要》本(光绪刻本同,简称诸葛羲本)。民国王缁尘整理《诸葛孔明全集》(卷十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世界书局铅印本(王缁尘本)。明曹学佺辑《蜀中广记》(卷二一),亦有明刻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六十),清同治光绪间陆氏十万卷楼刻潜园总集本(简称陆本),《续修四库全书》收录其影印本。《全宋诗》所录《观八阵图有感》即据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全宋诗订补》补辑《全宋诗》原不完整的两句诗。本文为方便,即以《全宋诗》及《订补》为讨论对象。
二、文本校勘与诗义释读
《全宋诗》录《观八阵图有感》,所据版本较晚,文字有不少错讹,《全蜀艺文志》点校本所校亦有问题。兹依據《全宋诗订补》录《全宋诗》所载原文,为便于解释,将原诗按内容分为四段,随文校勘,兼释其义。
“江从岷来触瞿唐,夏潦渍裂怒势张。霜浓水落洲渚露,纍纍江石堆作行。半斜半直半疏密,方营周匝门东出。相传呵护有鬼神,惊波不能移寸尺。想见当年诸葛公,纶巾羽扇挥秋风。令严部伍寂如水,出没变化机无穷。乾坤不足当经理,写留古法艮岑趾。
上滩下峡一千年,多少英雄测玄旨。小儿元子强多知,常山蛇势吾能窥。灞上枋头真绝倒,空使虬髯论握奇。
斵轮不可传其子,此公天机缄骨髓。柰何螟蝗生蝮蝎,炎刘已灰吹不起。天教三马食一槽,老马蹄啮暂咆哮。渭阳巾帼势将蹶,大星夜陨西军号。
呜呼兴废尽天意,中原扰攘今六纪,不堪骨肉自相残。欲拯涂炭嗟谁使,大官酣燕刍豢余,小官跼蹐尘埃里。举目厌厌九泉人,谁访草庐谈世事。向来韬略机莫投,而今投机欠良筹。君不见峡山深深茅舍底,有人抱膝高声讴。”[1]33314
第一段:“霜浓水落洲渚露”之“霜浓”,陆本同,它本皆作“霜沟”,霜,白色,霜沟,水沟也,“霜浓”于诗句义不通,误也。“纶巾羽扇挥秋风”之“秋风”,陆本同,它本皆作“愁风”,点校本据后刻之朱本、邹本亦改作“秋风”。“愁风”古人诗句亦常用,如宋穆修《河南穆公集·送葛源之太和主簿》有句“愁风九月急,飞鸟一帆轻”,《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张耒题画》有句“鹑傍陈根饥更啄,雀栖高枿瞑愁风”,《全宋诗》穆修诗以《四部丛刊》述古堂影宋抄本《河南穆公集》为底本,据四库本改“愁风”为“秋风”,风兴哀感是谓愁风,其实皆不必改。
此段描写八阵图之遗址景象。诸葛亮八阵图遗址所在说法不一,“小儿元子强多知,常山蛇势吾能窥”,用桓温故事,桓温字元子。《晋书·桓温》载:“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李兴宗所观八阵图遗址应在鱼复(今重庆奉节县白帝城)。夏季峡水暴涨,挟万钧之力量,席卷两岸,砂石俱下,风景丕变;秋冬之时,水落石出,八阵图即显现,行列规矩,秩序井然,诗人赞叹诸葛之神奇,所造之八阵图,巧夺天工。杜甫《八阵图》“江流石不转”,即此奇异者。《嘉话录》记载唐刘禹锡所见八阵图之景象,云:“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瀁,可胜道哉!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雷奔山裂,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惟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洒推激,迨今不动。”[2]八阵图遗迹历经沧桑,仍岿然不动,不得不让人感叹诸葛之天才与八阵图之神奇。
第二段:“空使虬髯论握奇”之“握奇”,万历本、陆本同,点校本据朱本、邹本亦改作“握奇”,并言兵书有《握奇经》;嘉靖本作“掘奇”,四库本作“倔奇”;《蜀中广记》明刻本及其四库本、王士骐本皆作“崛奇”。童第德《韩集校诠·寄崔二十六立之》注“心迹两屈奇”句,云:“屈奇,双声形况词,无专字,故借屈奇为之。《说文》有崛字,云:短高也,与高注《淮南》义合,大徐音衢勿切。手部有掘字,作崛奇、掘奇都通,无倔字。祝引选语,见潘安仁《西征赋》,今本创作构,倔作屈,与方所见本同。”[3]童氏说精妙,此乃双声联绵词,联绵词当中的字仅为标音符号,词义和字形不相干,凡音同音近之字皆可通用,故常一词多形,而握、奇非双声叠韵,握奇不是联绵词。《汉书·广川惠王刘越传》:“谋屈奇。”颜师古注:“屈奇,奇异也。”南宋释居简《唁赵恕可府录丁母夫人忧·其二》有句“素节尊勤俭,彤椽吐倔奇。”[1]28826李昴英《送荆门王广文之官》有句“惊座吐倔奇,倚麈觉我羞”[1]33172,掘奇、倔奇、崛奇、屈奇,皆奇异不凡之义。点校本言兵书有《握奇经》,乃不重版本,望文生义耳。前句“强多知”,讽刺桓氏并不精通八阵之法,若后句言空使其议论《握奇经》兵法,显然诗义矛盾。《全蜀艺文志》中此诗上一首为宋王刚中《滩石八阵图行》,诗中有句“握奇如枢运无穷,七纵七擒仍敢攻”,此“握奇”乃言兵法,李诗中“论握奇”或因此上下文影响而致误。故李诗中此二字可作“掘奇”或“崛奇”或“倔奇”,而不可作“握奇”。
“上滩下峡一千年,多少英雄测玄旨”,感叹千百年来,无数英雄窥测八阵图秘密,因之有多少兴亡成败的故事。“灞上枋头真绝倒,空使虬髯论掘奇”句用恒温北伐失败的典故,灞上、枋头皆桓温北伐军次之地。绝倒,形容做事匪夷所思,让人费解。虬髯亦指桓温。《晋书·桓温》:“少与沛国刘惔善,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须作猬毛磔,胡须如刺猬之长刺张开,故可谓为虬髯。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军第一次北伐,军次壩上,已望见长安,然最终未进而退。太和四年(369年),第三次北伐,打到枋头,势如破竹,致前燕欲弃邺城,后因粮草不继,最终大败而回。两次北伐初始皆极顺利,本可建立不世大功,但最终皆莫名失败,让人匪夷所思。“论掘奇”谓桓温所发奇异高妙之论,或指《桓温传》所载其上疏陈便宜七事:抑朋党、裁冗官、勤政务、明褒奖,重刑赏、遵前典、修国史等事,所言高于同时诸贤,皆可匡东晋朝政之失,刷新政局,振奋国家。然因北伐失败,一切高妙的政论皆付诸流水矣。
此段言桓温自恃才智,谓能窥测八阵图中蕴含之兵法,虽有有收复河山平定宇内的抱负,且有改革政弊之不凡主张,却因志大才疏,最终失败,让人唏嘘。
第三段:“柰何螟蝗生蝮蝎”之“蝮蝎”,诸本皆同,然皆误。蝮、蝎即毒蛇和蝎子,螟、蝗皆为食稻害虫,螟、蝗如何能生出蛇、蝎?“蝮蝎”乃“蝮蜪”之误,《尔雅·释虫》:“蝝,蝮蜪。”郭璞注:“蝗子未有翅者。”欧阳修《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有句“然犹到手不敢取,而使螟蝗生蝮蜪”,与此意同。皆以螟蝗比有纂汉之心的曹操,以蝮蜪比实际纂汉者曹丕。“老马蹄啮暂咆哮”之“蹄”,它本同,唯嘉靖本、万历本、点校本、陆本作“啼”,作“啼”,误也。蹄啮,马用蹄踢、用嘴咬,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倾轧。《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此处以喻司马懿与曹氏集团之间倾轧,故而还未兴起灭蜀之事。
此段谓诸葛亮治国行军之本领,乃天之所赋,不能传于其子。诸葛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天命已经不属炎汉,诸葛只能抱憾,最终陨于西征军中。此段诗句用意遣词,明显承袭欧阳修《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云:“火数四百炎灵销,谁其代者当涂高。穷奸极酷不易取,始知文景基扃牢。坐挥长喙啄天下,豪杰竞起如猬毛。董吕傕汜相继死,绍术权备争咆咻。力彊者胜怯者败,岂较才德爲功劳。然犹到手不敢取,而使螟蝗生蝮蜪。子丕当初不自耻,敢谓舜禹传之尧。得之以此失亦此,谁知三马食一槽。”[4]
第四段:“中原扰攘今六纪,不堪骨肉自相残”句,《全宋诗》缺字,《订补》补全[5]。此句嘉靖本、王士骐本、《蜀中广记》明刻本作“中原腥羶今六纪,胡雏骨肉正相残”,万历《总志》“正”讹为“止”,四库馆臣因满廷忌讳,《全蜀艺文志》四库本改为“中原扰攘今六纪,不堪骨肉自相残”,《蜀中广记》四库本改为“中原龙斗今六纪,胡雏骨肉正相残”,然诗义已全改了。清代四川方志一般空出“腥羶今六纪胡雏”七字,代以白方块,陆本亦如此。诸葛羲本录作“中原板荡今六纪,典午骨肉正相残”,典午代指晋朝司马氏,与原诗义格格不入,尤谬;王缁尘本“典午”更误作“炎午”。中原腥羶指中原之地被胡族占领,胡雏是对胡人的蔑称,《新唐书·张九龄传》: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6]此诗句中“胡雏”所指为女真金朝。此句原文对理解这首诗颇重要,当以嘉靖本为是。“举目厌厌九泉人”,诸本同,唯嘉靖本作“压压”。《诗经·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小戎》“厌厌良人,秩秩德音”,《毛诗注疏》云:厌,于盐反,安静貌。元汪梦斗《羁燕四十余日归兴殊切口占赋归·其三》有句“恰求谔谔廷中辩,亦似厌厌泉下人”[7],与此句诗意同,九泉人、泉下人,皆死人也。满眼皆死人,寂灭无声,更不用谈“谁访草庐谈世事”了。汪诗“厌厌”依据格律,应为平声字,不应读去声,李诗为古体,虽不必依据格律,然二者所用“厌厌”之音义皆用源自《诗经》。故不应依据最早的嘉靖本作入声韵之“压压”。
“呜呼兴废尽天意”,起承上启下之用,上感叹前史之兴亡,下启对时局之看法。“中原腥羶今六纪,胡雏骨肉正相残”此句原文最紧要。揆诸南宋史,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两国以淮水一线为界,宋王朝领土只限淮水以南,广袤中原俱归于金。“胡雏骨肉正相残”,指金至宁元年(1213年,宋嘉定六年)金廷内乱之事:大将胡沙虎弑金主永济,立金宣宗,术虎高琪又杀胡沙虎,金国国力已衰落,君臣苟安而已。一纪十二年,六纪七十二年。宋嘉定六年距绍兴十一年,正好七十二年。诗句与史实非常吻合,因此可推断此诗作于宋嘉定六年。
“欲拯涂炭嗟谁使……有人抱膝高声讴”言开禧北伐之败后宋王朝屈辱求和,朝政不清,权臣骄奢,小臣暗弱,满朝齐喑,完全不知抓住金廷內讧、敌国衰微之机,寻访良策,振作发奋,以复仇雪耻,而有志之士只能抱膝讴歌以泄满腔愤懑之情。李兴宗嘉定年间为成都路提刑官,奉节县时亦属夔州路,此诗或作于李兴宗归隐后,故有“君不见峡山深深茅舍底,有人抱膝高声讴”。
三、小结
古诗流传久远,鲁鱼亥豕多有,影响后人对诗本义的理解。李兴宗《观八阵图有感》一诗,有多种文献著录,文字差异不小,我们详细比较各文本,用校勘学的方法,还原诗的本来面目。其诗以八阵图起兴,感叹诸葛亮天纵之才,却不能逆改天命,后世之桓温,志大才疏,草草北伐,时机不对,以失败告终。以古讽今,亦以桓温北伐来言韩侂胄开禧北伐,挑起战端,注定失败。三者皆天运与时机不对,而今金人内乱,大宋报仇雪耻正在此时,然掌权的大臣只图享乐,无有大志,不知奋发,空有抱负之诗人只能望空兴叹,借咏古迹来浇胸中块垒。
李兴宗是位具有民族精神的爱国者,一生以恢复为志,却壮志难酬,《观八阵图有感》乃一首爱国情思之作,不应因四库馆臣以清廷忌讳改动诗句而使志向不明,其满腔爱国激情和壮志难酬的无限义愤总能感动世人。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53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韦绚,陶敏,陶红雨.刘宾客嘉话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9:94.
[3]童第德.韩集校诠[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2.
[4]欧阳修,李逸安.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740.
[5]陈新,张如安,叶石健,等.全宋诗订补[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496.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429.
[7]杨镰.全元诗: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194.
作者简介:
漆德文(1984-),男,江西省图书馆,馆员,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