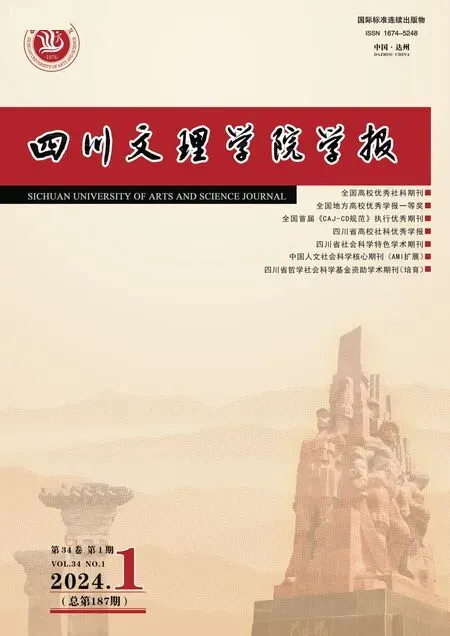数字化媒介及其趋势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研究
李冰封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一、数字化媒介的兴起,特征及其影响
数字化媒介又被称为“新媒体”,关于新媒体的说法或者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可以让都大家信服的结论,但有一些基本的要素是确定的,比如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客户端为支撑的大容量、实时和交互进行信息传播的新形态媒体。它与传统的书刊报纸、电视广播等现代媒体有了很多不同的特点,如数字化媒介个性突出,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精确推送服务;表现形式多样化,轻松实现文字、声音和视频画面无限实时传播,同时受众的选择也实现了自由多样化的选择。手机和互联网是其最为典型的代表。媒介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和沟通的工具或者说载体,一直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早期的口头语言、竹简、木简、丝绸、纸张、报刊、电报、电视等媒介,都是划时代的媒介,都对人类信息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到网络计算机的互联互通,人类的媒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文化的世界。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尼葛洛庞帝就提出了“数字化生存”的概念,[1]他认为,计算不只是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数字化生存的核心是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有三个方面的重大革命:第一,信息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DNA 将重塑世界,人们每天从媒介开始并参与媒介化生活,数字化媒介将改变人类的感觉世界。第二,电脑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充满“个性化”的“完美的人性世界”“图幻世界”“虚拟现实”将成为现实。第三,数字化时代来临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信息,获取知识,电脑将成为“无所不在的万事通”,新电子表现主义流行(网络医生与教师、音乐、电子艺术、离经叛道的各种沙龙)。毫无疑问,尼葛洛庞帝当年的预言充满洞见,短短三十年,我们已经数字化生存了。网络变得不再那么虚幻,虚拟世界不再那么虚拟,高清晰的像素不限于电脑了,一部手机足可以完成所有的数字化生存。
从在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数字化媒介的影响研究成为热点。如学者夏文蓉认为,数字化媒介是一种“辐射力最强的文化装置”,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推动力,同时还深入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得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特征,并“成为当代文化的有机构成”。当代文化的所有形式,哪怕是传统的戏剧、舞蹈、音乐会、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都必须经过数字媒介发挥“特定的功能”,并深深地打上“媒介的烙印”。[2]从现有的媒介化研究来看,学者们的研究已经纵深化,从网络技术到技术哲学,从媒介社会化研究到网络社会研究,从数字化生存到大数据、区块链和元宇宙的研究。也就是说,数字化生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从当代文化的媒介化趋势来看,媒介融合与影响、媒介社会化和媒介化社会已经逐步形成,所以媒介已经不再仅仅是人的延伸,不再仅仅是讯息的载体,人类已经从数字化生存到媒介化网络生存的转变。当然,当代媒介化研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一方面认为媒介化研究处于泛化研究,认为媒介化理论过于简单化,仅仅是一种“概念潮流”,只是具有“修辞价值”。[3]
二、媒介社会化的内涵及特征
数字化媒介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日益深入,媒介社会化和媒介化社会引发学者们关注。顾烨烨、莫少群《媒介化研究:理论溯源与研究路径》一文,立足于数字媒介社会化转型,把媒介化社会理论研究的源头追溯到齐美尔和吉登斯,他们认为,早期媒介的特征是“工具性”,媒介化社会中媒介的角色从“中介性”到社会的“媒介化”趋势,在这样的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裂变式”,媒介化社会呈现出“开放”“分散”的网络型结构。张晓锋在《论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三重逻辑》一文中认为,现代社会在媒介的发展和渗透下被不断地重新塑造,“媒介化社会正在形成”:媒介融合、信息依赖和环境建构成为媒介化社会的“三重逻辑”。[4]孙玮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来临是一种“文明转型和新型人类的诞生”,现代社会的媒介已经不是一种实现某种目的的现实工具了,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越来越隐形化”,技术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对立存在,成为剥夺“人类的自然本真”,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从而在主客观世界和社会构成方面“改变了人本身”。不但如此,数字化媒介“通过塑造身体的知觉经验,参与到人感知世界的实践中”,也就是说,数字化媒介不但参与了人的现实生活,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造人的感觉世界和理解世界的实践,“变为构成社会的基础性要素”“媒介化的社会存在”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并诞生一种“新型人类”。[5]这种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洞察到了数字化媒介事实上已经覆盖了人类的生存的诸多方面,技术已经延伸到人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日常生活无法避免的存在,比如,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信息获取与传送,阅读,交流和娱乐,甚至基本的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都无法离开智能手机的普遍性实践。
当今新媒介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造就主体的媒介化生存,这种媒介化的“主体”被称为是一种“新型人类”,传统意义上的本真状态被日益剥离,加入了非主体的经验和实践,同时,主体生活的环境被媒介不断地重新塑造,从报纸、电报、电视电影到网络,时空可以逆转,过去的生活可以清晰地被记录,被重新体验,人与环境的关系,不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网络,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型人类”:一是“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模拟人类有机体感官的身体体验 ;二是“制造非有机体的智慧主体”,即人工智能的出现。[5]这当然只是一种学术批评的概念,“新型人类”或许有些夸张,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确实给人类及其生活世界带来的今非昔比的影响。比如世界的“真实”概念被颠覆,“幻像”“仿像”或者“拟像”的世界已经清晰可见,它是真实的,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实的世界。媒介不再是“人的延伸”,也不再被“理解”,而是不断地进入人自身,重新塑造人类的感觉器官和精神世界,媒介成为人的一部分:“新媒体将以往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结成的‘失落的共同体’中的个体重新聚合起来,形成一种虚拟共同体。”[6]夏德元博士提出了“电子媒介人”的概念,他认为,“电子媒介人”是一种“掌握着传播新技术缔造着或接受了网络虚拟文化或称电子文化的新人类。”[7]
三、人的媒介化生存境遇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
人的媒介化生存是当代青年大学生面临的最为直接的现实文化境遇。媒介批评的声音从未停止,英国社会学家斯各特·拉什从晚期资本主义的异化出发,把随时弥漫在现代社会的零碎的、漂浮的、无理性的“信息”成为时代的幽灵或者说“符号的黑洞”,开启了学者对信息及其信息社会的重新审视和批判。陈力丹认为,整个社会信息化了,人生活在信息的海洋,被信息所左右和控制,带来的“信息的异化”。[8]第一,“信息爆炸和信息过载”使得人类在信息面前无能为力,社会资源被极度浪费。第二,“垃圾信息”充斥网络,用户被迫接受大量无用、有害的垃圾信息,特别是网络“水军”带来的广告和冗余信息,“造成时间的浪费和减损带宽、妨碍通信等实质性损害”。第三,网络病毒,恶意复制和袭击用户电脑,使得系统瘫痪,甚至盗用和篡改用户数据、文件,使得用户和机构损失巨大。第四,群体性孤独症。在互联网时代,人际交流日益网络化和数字化,各种社交APP把不同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特别是网络视觉化之后,传统意义上的亲缘和血缘关系,被完全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他们相信虚拟的空间比现实空间更加真实可靠,他们沉浸网络信息的海洋里,身边却是不可知的万丈深渊,他们与身边的朋友熟人很少交流,缺乏沟通,所以当他们面临不确定性的信息时,每个人失去了判断力和自信心,长期沉迷网络漂浮状态,使得一部分青年大学生思维浅薄化,他们往往越来越焦虑、孤独和恐慌。他们之所以每天沉浸在网络视频和各种社交媒体,其目的是“尝试用联系他人的方式以解决孤独的恐慌”,这就是现代人的“群体性孤独症”,也有学者称之为“媒体依赖症”。这也是当代青年大学生面临的直接的现实文化语境,从慕课到雨课堂,从学习到生活,从现实到网络,媒介化生存语境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技术悲观主义者对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充满忧虑。哈罗德·伊尼斯认为媒介会在传播时对它所在的文化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从而决定了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兴衰。麦克卢汉通过媒介与受众的不同关系,考察了媒介对人类感官世界的控制和操纵,“麦克卢汉通过分析媒介本身的感官偏向性, 来探究媒介之于人类心理认知和社会结构的影响。”[9]人及其感觉器官对媒介的依赖,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这引发了人类“媒介化生存危机”:即时方便的通讯使得“人际关系冷漠”,媒介无处不在,造成了“对私人领域的僭越”,低头族对手机的过度依赖,造成“独立人格的丧失”,大量不适当的报道,特别是自媒体泛滥视频,随意剪辑拼凑,虚假扭曲的报道,一方面误导青年人,一方面“加重社会运行的成本”。[10]事实上,近年来,由于抖音、视频号等各种直播平台,各种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疫情防控、转基因食品、高新技术等等虚假信息,被各种自媒体放大、扭曲,随意剪辑拼接,混淆视听,有些自媒体的科普知识,特别是疫情期间关于病毒的知识,既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很难分辨那些信息是真的那些信息是假的,很多不纯的动机引导青年大学生作出错误的选择和结论,给他们的人生和家庭造成很大的困扰,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
当数字化时代来临,一切突然发生,科普学者洛西科夫认为,我们生活于一个不再熟悉的世界,“数字化精神病”让人们的时间消失,过去和未来被压缩在永恒的“当下”。[11]在媒介化生产和生存的时代,一部分青年大学生往往深陷媒介及其技术构筑的“互联网”中,成为“网民”或“网虫”,他们往往失去了独立思考和感受世界的能力,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媒介及其后果对青年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确实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难题,需要我们研究和思考。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摆脱网络依赖症,对网络消息要有辨别力,要有批判性思维来抵御和分辨互联网世界的流言和谎言。
四、数字化时代青年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尤为重要
我们在看到互联网数字化时代的种种忧虑的时候,也要看到它给人类社会开辟了崭新的世界。对青年大学生来说,一方面,互联网数字化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广泛的学习机会,一部手机可以实现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微信读书,就可以阅读到古今中外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作品,超星读书和超星课堂,名家课堂应有尽有,国家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开通的数字图书馆已经为读者提供了可以学习的资源,百度的搜索功能可以为很多疑难提供解决方案,各种超大网盘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数据储存。也就是说,数字化时代的网络及其特征,为青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的益处也是不能忽视的。
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媒介化生活语境面临“生活媒介化”或“媒介深度化”的现实,各种文化思潮、话语、快阅读、公众号、影像短视频等通过各种媒介,汇聚成大量的网络信息,通过手机进行传播,形成某种话题主题或某种意识形态,很容易改变青年大学生对世界、社会和人生观念的看法。各种新兴媒介形成的网络世界,创造了青年大学生的精神空间,在这种非现实的虚拟空间中,是青年亚文化往往以“以狂欢化的文化消费来抵制成年人文化”,[12]可以肯定地说,新媒介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兴的交流技术,而且更是一种媒介素养的问题,所以媒介文化时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的培育与提升显得格外重要。
媒介素养,简单的说就是具有获取、判断和理解信息(知识)的能力。在媒介文化时代,我们每天面临着海量的信息,身处信息的海洋,垃圾信息、泡沫信息会不断的淹没、不断的干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如果不能正确获取有效信息,不能正确判断和理解信息,我们就会无所适从,浪费时间,丧失主体,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媒介素养对当代大学生来说,是“现代大学生的一项基本素质”,他们认为,当代青年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与提升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具备正确的使用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对并媒介信息作出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还必须能够利用媒介有效的传播和运用信息的能力,从而达到学习知识,获取信息,多层面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参与社会社会。[13]这是媒介素养最为简要的阐释,我们以手机为例,可以更好的说明媒介素养的培育与提升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意义。手机,对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媒介工具的属性,不仅仅可以使用的器物,同时也成为人的媒介延伸的工具。在今天,我们通过手机,更多的生活在线上,生活在一个个网络联系起来的赛博空间,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拟的。线上支付,网上购物,在线娱乐,热点追踪,网络跟风,抖音,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等,媒介文化带给我们的虚拟体验,是前所未有的。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身体的延伸”,事实上,远远不止,媒介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延伸,同时人的情感,情绪和生命体验,也都被媒体向内心延伸,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左右了,这对于心理防线还不成熟的青年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与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五、青年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养与提升路径
提升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的认识能力。当代部分青年大学生“缺乏对现行主流文化的认同感”是当前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突出难点。一些青年大学生对媒介文化缺乏基本的认识,对网络媒介中出现的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色、丑、怪、俗等现象,持无所谓的态度,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断力。这几年在一些高校校园流行的“跟风”“躺平”“无脑”“摆烂”“追星”“游戏人生”等观念,都说明部分青年大学生面对如潮水般的网络负面信息和针对青少年开发的典型的媒介产品—游戏,他们并没有构筑好道德和文化上的认知心理防线,美丑善恶的界限还比较模糊,对传统美德和主流文化的认同感,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据调查,超过80%的青年大学生使用手机学生就是为了聊天,打游戏,看直播视频,特别是一些学生沉溺游戏和视频,不能自拔。事实上,现代人虽然在技能上熟练掌握了各种传播媒介,却未必在心智上理性地掌控了它们,人与媒介之间形成一种“异态的关系”——现代社会的“媒介异化”。媒介异化是在媒介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媒介过分依赖、沉溺、轻信和盲从的状态,是人对媒介的一种误用,具体反映在“媒介技术异化”“媒介权力异化”“媒介偶像崇拜”“信息崇拜”等多个方面,从而成为媒介时代信息的迷失者,要走出媒介崇拜的误区,走出媒介与人的异化迷失状态,必须提高媒介素养,掌握理性的、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能力。[14]我们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开设媒介素养或者媒介批评的课程,同时,还可以通过演讲与口才训练,辩论赛等活动,让学生对一些网络热点开展辩论赛,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对一些网络负面效应开展调查,得出结论,主要让学生看到媒介信息背后的真正原因,培养其正确使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充分利用媒介,获取知识,提高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从而提升媒介素养的价值判断力。
摆脱媒介依赖症,成为当代青年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和提升的重点和难点路径。今天,全球化思潮不仅仅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媒介技术及其传播日益迅速更新的时代,信息和媒介文化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地球村”已经名副其实。互联网作为最为迅捷的新型媒介,将传统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融合、吸纳和重新塑造,形成了“环境即媒介”,这与传统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不同,媒介不断深入和深度参与生产、消费和生活的诸多领域,并借助强大的技术功能,实现它的社会功能,改变了人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从而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比如一部智能手机,连着无数个APP,一个微信APP 就可以完成手机充值、生活缴费、城市服务,医疗健康等,其中微信城市服务就可以实现社保缴纳、交通违法查询、加油充电、城市热力图、医疗、办证、政务综合、便民服务、民政公益等等,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人们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媒介及其移动设备(手机),人们更多的生活在一种“媒介环境”中,形成无法自拔的“媒介依赖症”。同时,技术和媒介也把我们带进了“风险社会”。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新技术展现出来的技术现代化“威胁的全球性(人类、动物和植物)以及他们的现代起因”,给社会带来了“风险和危险”,提醒人们警惕科学技术巨大的负面效应。[15]媒介化社会最显著的风险就是技术神话带来的大数据,使得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都毫无藏身之处。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购物品种、消费习惯、行踪、人脸识别、甚至个人嗜好,都被大数据所记录,甚至可能被传播。有学者指出,大数据库不仅能能提供每个人的“精准化信息”,但同时还将“个体赤裸裸的暴露在技术面前”,侵犯个人隐私,这就是“媒介技术的悖论”,这大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人类将永久置于媒介化社会的技术风险之中”。[16]对当代青年大学生来说,一方面要积极拥抱互联网、理性认识现代科技带来的社会进步,开拓创新,获取知识和信息,一方面也要警惕和抵御媒介化社会带来媒介依赖症、风险和异化,扬长避短,超越媒介化生存环境,多回到现实生活,回到自然世界,感受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