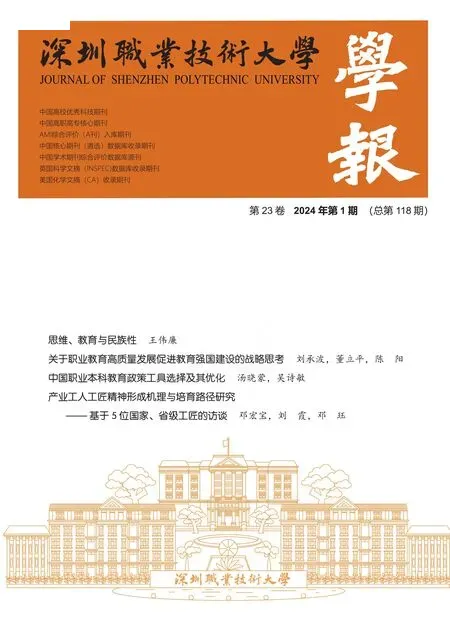思维、教育与民族性
王伟廉
(汕头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广东 汕头 515063)
从科学角度看,思维作为研究领域或学科,与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情报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很多学科都有关系。当然,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思维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这一关系的粗略考察,笔者发现,无论从教育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教育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的角度,都明确地指向了这样一个待解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不是与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的不足或缺陷有关?又或者:我们的教育现状是否又是造成进一步的系统性的思维缺欠的原因?这个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民国时期,这个问题就已经被一些国内学者注意到了。比如一些著名学者就说过这样的一些话:“国人思维讲究如何应该,西方人思维讲究如何可能”“国人思维讲求情理,西人思维讲求论理(即逻辑)”“整体思维是国人思维特点,分析思维是西人思维特点”……。西方人也有这方面类似论述,例如,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出者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就说过:我们正处在把对自发自组织现象进行描述的中国传统与重分析的西方传统结合起来的时代(大意)。而在当代,中外教育界强调学生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一译“审辩式思维”或“审辩思维”)能力的培养似乎已成共识,国内时不时就有文章批评国内研究者写论文不会论证、博士生招生面试回答不出“特别想要研究怎样的问题”、社会科学学者论文缺乏逻辑性……。这些都说明,我们的思维的确存在问题。而这个问题究竟情况如何,笔者不是专门研究思维的,因此,只能通过教育活动中的一些现象和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研究,以及和大学同事曾经做过的一些对思维进行的研究和改革实践,来揭示这些问题的症结、特点以及程度,并探求解决它们的一些思路。
一、思维与教育关系扫描
思维培养的重要性,似乎不用费笔墨来论证。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并非都达到一定的高度,就连笔者也曾认识不足。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个典型实例来做个简要的说明。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张首晟生前在斯坦福大学开设过一门很特别的课程,叫做《2012 信封的背后》。该课程假设地球毁灭之前,诺亚方舟上只允许携带一对动物和一个信封,让你在信封上极其简要地写下对重建地球文明最重要的知识。张教授给出的答案包括数学中的欧式几何、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等八条知识,而这八条,被很多学者认为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有学者称其为“哲科思维”或“一思维”。可见,思维应该是教育中最值得培养的内容。
笔者还发现,在世界教育改革的历史上,比较重大且涉及面广的改革案例,其起因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对思维的新认识有关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先说国外。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针对传统教育而发起的教育改革。杜威的这次改革中有很多主张都基于他对儿童思维的研究,例如“思维起于疑难”,就是他的“做中学”主张的心理学基础。
又如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学课程改革,作为改革的心理学基础而提出了“发现学习”的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所依据的心理学理论中,占据改革重要地位的就是“探究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目标的设立。
再说国内。
中国当下的教育改革,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很多教育界和学术界人士,就开始特别关注“批判思维”的培养。在不少高等学校,无论从学校层面还是各院系各专业培养方案中,甚至在单门课程教学大纲中,都可以看到“培养学生批判思维能力”或“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目标表述。这些都说明,一些重要的思维能力,是教育活动无法回避的目标,也或许是教育理论界以及相当部分的普通人群的共识。
这里有一个笔者亲历的案例,表明并不是所有关于培养学生批判思维能力的见解都来自有一定阅历和比较年长的“有识之士”的共识,而是有不少来自普通教师和行政管理干部以及大学生自己的见解。汕头大学曾就全校层面培养目标做过一次广泛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中排列出了一张可能作为高等学校整体培养目标的备选目标清单,请本校学生、校外专家、校内教师以及一些行政部门领导干部等不同群体按重要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序。问卷收集上来并经过统计处理后的结果显示,重要性排在第一位的,即认为学校层面最重要的培养目标,竟是“培养学生有效思维(effective thinking)能力”。
汕头大学之所以搞了这次问卷调查,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之前针对大学教师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培养目标就是“有效思维”。看到此消息后,笔者查阅了一些美国教育文献,对“有效思维”的解释不多。有一份教育文献解释说,这个概念与“批判思维”“逻辑思维”等概念在内涵上没有太大区别,经常混用。也有国外学者的著作名称就叫做《有效思维》[1]。就我自己的粗浅理解,有效思维和批判思维都属于逻辑思维,在此基础上,批判思维更关注对思维本身的反思和对思维对象的质疑态度;有效思维包括了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的所有关注点,强调思维的科学品质和效果。笼统地看,三个概念都注重思维的逻辑、有效和科学,所以我们这里暂且把这三个概念作为同一个概念来讨论。言归正传,我们也是为了解一下中国学界对思维能力的看重程度而组织了上面所说的问卷调查,没想到调查结果在“最重要”的培养目标上如此一致,说明对有效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二、作为教育改革基础的思维研究
国外和国内对思维的研究情况不同。
国内对“有效思维”或“批判思维”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在对这种思维能力的详细的组成部分的研究方面,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研究成果。国外则有不少研究。笔者看到的最粗糙的分类是把“有效思维”分成这样五个部分:(1)对争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2)做出推论和提出结论;(3)明确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4)进行归纳的能力;(5)对各种可能的解释进行概括。这五个部分的思维能力,笔者曾把它作为高校新入职教师的培训内容。其中曾撰文谈到的一点是关于归纳思维的一些评论,大意是说,国人在演绎思维方面还是比较强的,而归纳思维相当弱。这一观点,最初是从与中国科学院林群院士的一次谈话中得知的。关于那次谈话涉及的内容,后来纳入《不愿丢失的教育感悟》,连载于《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18年各期。这里把其中我与林群院士的谈话写成的文字,简要摘录如下:
“我一次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林群院士谈到大学的数学课程改革问题。林院士说他在河北大学数学系正在进行一项改革,缘由是看到美国大学的数学课本比中国的薄,但好东西却在这薄本里。原因是美国的数学课本是用归纳思维①这里说的“归纳思维”是指由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的科学归纳法,不是有学者指称的中国古代《易经》中所说的归纳法。后者被包括杨振宁教授在内的很多科学家认为是阻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思维方式。编制的,而我国大学的数学课本是用演绎思维编制的……”。
“我不敢保证我所转述的林院士的话准确无误,但可以保证关于两种课本是由两种思维来编写的那些话,是不会有误差的,因为我那时特别关注教学改革中的师资培训问题。所以,我还追问到,教师是否适应?记得很清楚的是,林院士说出了另一句话。大意就是,因为我们的教师也都是被演绎思维培养起来的,所以适应美国课本的确是个挑战。”
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尽管那时已经读过一些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对归纳法的批评,对这一问题有过一些思考。此外,有学者认为,从思维品质上看,归纳思维属于第一层楼,演绎思维则属于第二层楼……但科学发现需要归纳思维这一点,却是当代众多学者非常重视的,甚至比演绎思维更加重视。这一点从上面引述的对有效思维的五种分类中就可以看出来。关于这些问题,不是本文讨论重点,这里暂且搁置。
批判思维在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中被分解出很多细目,根据这些细目,人们可以开发思维量表用来判断思维方式的缺陷所在,从而有针对性地推进有效思维培养的教育进程。可惜据我们了解,我国在我任职汕头大学时还没有这种量表。而美国当年的情况,经了解,也只是某些学科领域里开发出了一些量表。听一位了解美国情况的同行说,针对一些学科领域的批判思维量表倒是开发出来一些,比如针对英语专业就开发有这样的量表,但不分系科的总体的思维量表国外好像也没有。(很久以后才得知,美国在1992 年就已经开发出了思维量表, 叫做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简称CCTDI。但现在仍不清楚这一量表是否是一种所有学科学生都适用的,还是像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只是针对某类学科的学生的。)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开发。这项工作首先就必须有心理学提供的批判思维的具体细目,而前面所说的五种细目的分类显然不够用。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研究团队里有一位心理学教授,平时就与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心理学家有联系,正好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我们这位教授就立即写信给这位心理学家寻求帮助。更幸运的是,这位心理学家正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长话短说,不久后我们就得到了把“有效思维”或“批判思维”划分为大约200 条细目的研究成果,经过大家的努力开发出了A、B 两套量表,并经当时中山大学心理学教授进行的科学检验,其中一套量表通过了科学检验,随后开始依次对学校一、二、三年级学生和汕头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二、高三年级学生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高中阶段已形成了有效思维的一些能力,尽管分数并不是很高。但问题在于,到大学三年级结束时(四年级没有测),有效思维水平对比高中三年级的平均水平,似乎没有什么提高。这一结果让我们很不解,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思维量表是不是存在信度和效度上的问题。可这套量表是已经经过了科学检验的呀?!这种情况使我们的测试兴致被泼了一盆冷水,后来因一些骨干的退休和调动,这一研究活动没有进行下去,也是因为对我们自己开发的思维量表的科学性抱有怀疑。事情说来也巧,我退休以后,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爆料,美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批判思维水平比起中学生,并没有明显进展。我已记不得是在哪里看到的这篇文章,但当看到这篇文章时的那种感觉至今还会浮现出来。这虽然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但一直在我心里存放着。这里有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是,即使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与美国的研究结果都表明,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批判思维都是“进展不大”,但两种“进展不大”对应的“起跑线”是否一样或接近,亦即在高中毕业时,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在批判思维能力上是基本持平还是有明显差别?这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因为知道了这一点,对于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教育改革的着力点的确定是非常关键的。
三、学校的思维培养
思维的研究并非易事,而思维的培养就更不容易了。但无论如何,心理学上的任何关于思维研究的成果,都应及时转变为教育的实践。唯有如此,我们培养能力的教育才能逐步前行而不至于停滞甚至倒退。
关于各级各类学校思维培养的实践,中小学和大学第一线的老师们比我们教育研究者更有发言权。但就笔者的了解,就思维能力培养而言,我们的实践,无论哪一级哪一类学校,基本都处于“粗放式”的状态中,有针对性又有科学性的思维培养,少之又少。如果把这些现象做一个归因研究,恐怕在相当程度上会触碰到现行教育实践的整体上的弊端,或者说会触碰一些“系统性矛盾”,因而改动起来会涉及方方面面,而且即使自上而下下决心改,也在短期内难以见到成效,很可能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努力才能见到大面积的明显效果。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么说,根据在哪里?我们这里仅举一例。
就拿归纳思维的培养来说,前面所举的林群院士在大学数学系搞的改革就很说明问题,因为我们的高校数学教师本身就是他们的老师在演绎思维的氛围里培养起来的。这种笔者称为“教育惯性”的现象,就是一种系统性问题。没有大面积、持久的改革,很难获得根本扭转。这种“教育惯性”倒不是我们国家的“专利”,而恐怕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在一篇讨论高等教育的文章中,一位美国学者就调侃过美国高校的这种现象。他给大学教授下了一个“定义”来描述这种代代相传的“教育惯性”:所谓教授,就是按照他们的教授教授给他们的方式来教授。(注:句子译文中后两个“教授”是动词)而中国的这种“惯性”还有一个颇具特色的“增强剂”。最近看到一篇著名学者的文章,说我们的教育体制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选拔体制。至少从小学开始,各级学校就用各种考试的成绩来挑选或者说是筛选“英才”。这还不算,还加上社会上或者学校与社会共谋的各种竞赛成绩来给选拔提供“助力”。至于这种选拔体制从何而来,是从科举制度沿袭而来还是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教育特色,那是历史学家或教育史家研究的课题。我这里要说的是,考试与竞赛这种选拔方式一旦成为了一种系统性的教育实践,它的结果就一定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甚至极为重要的教育目标。
回到我们的主题,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中的层层选拔要保持“公平”,就必须严格用标准化考试或必须使用标准答案来评判或评价。因此,凡是没有标准答案或答案难以评价对错和水平的东西,一定不会拿出来考。这样的一种教育体制,就至少会在很多学习内容的思维方式上只青睐演绎思维而忽视甚至排斥归纳思维。因为我们都知道,演绎思维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走向,即用一定的已有理论或共识来解决或说明特定情况下的具体问题。而我们的绝大部分学科,都可以使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考试,因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可以得到一种“确定性的”结果。在选拔考试中,就表现为考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或者答案是要遵循某些明确的评判标准的。而归纳思维,是从特殊到一般,是要学生把一系列特殊现象归纳成某种科学判断或原理。而这种归纳,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难免就会出现不同的判断或提炼出不同原理。因此,无法用这样的思维训练方式来出题目选拔优秀者。道理很简单,它没有办法给出标准答案。然而,这种归纳思维能力的获得被认为是科学发现和原始创新必备的条件。诚然,我们有些教师因学科特点,会在无意中培养了学生的归纳思维(例如在数学教学中)。但有意识地遵循科学原理培养学生归纳思维的教育实践,乐观说也如凤毛麟角。笔者曾多次在给一些大学的教师做教育改革报告时询问过是否有教师有意识地培养了学生的归纳思维,结果是,在若干年的很多场报告中询问听报告的老师,竟没有一个大学老师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国外大学的情况如何?前面所举美国大学数学教材一例已经做了部分的说明。国外中小学的情况我不是了解得很充分,不过我在拙作《课程研究领域的探索》[2]里引用过美国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关于人类发展史的教材《Man: a Course of Study》(直译为《人:一个学程》),其中的教学方式就是向学生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如“动物有没有家庭?”“人类的婴儿需要成年人呵护很多年才能独立生活,而动物的幼崽为什么在出生不久就可以独立生存?”……。然后让学生搜集并阅读相关资料,最后让学生自己归纳出:人类从原始人变为后来的直立人,需要哪些必要条件;人类与动物有什么主要异同等。这门学程或课程就是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归纳思维的。显然,这样的教育,如果评价学生是否达到了目标,绝不可能使用标准答案来评价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训练比用标准答案考试,对学生的发展潜力的挖掘至少是同等重要,而对于创新,可能要比纯粹的把标准答案告诉学生让学生记住,要有价值得多。退一万步说,即使归纳思维一无是处,波普尔自己在批评归纳思维的同时所提倡的、他所定义的“批判思维”,其中最看重的是用某种已经认识到的“可证伪”的证据对已有理论进行质疑,而这在考试中同样无法出考题进行测试。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思维能力,以“标准答案”来考学生几乎不可能。比如我们都知道,想象力对于创新思维极为重要。实际上,想象力也可以认为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创新思维的一种。而我们的选拔考试,无法对想象力设定标准答案。所以像想象力、灵感、好奇心、情感等重要的心理过程,在选拔体制的教育系统中,就必然会被长久地忽视。而这些心理过程中属于“情意侧面”的部分,按照我国心理学家潘菽的观点,相对于“认知侧面”,它们在人的发展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我们一些主张教育人文化的学者,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要让学生发展“成人”。而如果缺失了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心理过程的培育,“成人”即使不成为一句空话,至少也是难以企及的事情。这或许就是笔者所说的“解决此问题的钥匙或许就藏在人文与科学的交界处”的又一例证[3]。
很明显,教育领域忽视重要思维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必然忽视与这些思维能力一同起作用的人的心理过程中情意侧面的发展,而鉴于这样的教育本身已经或正在影响着我们后代的全面发展,长久下去,就会改变我们的民族性和文化基因。而这些民族性和新的文化中的价值观反过来又影响我们的教育。这不是危言耸听,“比较教育”学科就有一个学派叫做因素分析学派,这一学派是对该学科影响深远并一直受到重视的学派。他们有一句经典的话:“学校外的事情的影响比学校内的事情更重要。”这一派就是从各国的民族性来看待该国的教育体系特点,例如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等。这些“校外的事情”都会对该国教育产生重要且持久的影响。而重要思维能力的缺失和因此而形成的思维缺陷,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民族性。这些学术上的观点是否具备真理性,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关注思维欠缺并及时弥补,总归是具有正当理由的。
最后还想强调的是,思维的多样、丰满与平衡,并不能带来利益或世俗的收益。尤其重要的是,它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有些珍贵的思维能力和与之配套的心理侧面很难测量和评价。这些思维能力与人的心理的情意侧面遥相呼应或互为补充。这方面的教育改革是一件涉及面很广又很艰巨的任务,但越拖延改变起来就越困难,要花费的时间也越多。这一步越早迈出越好。让我们借用毛泽东的一段诗词来结束本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①见毛泽东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作于70 岁时的1963 年1 月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