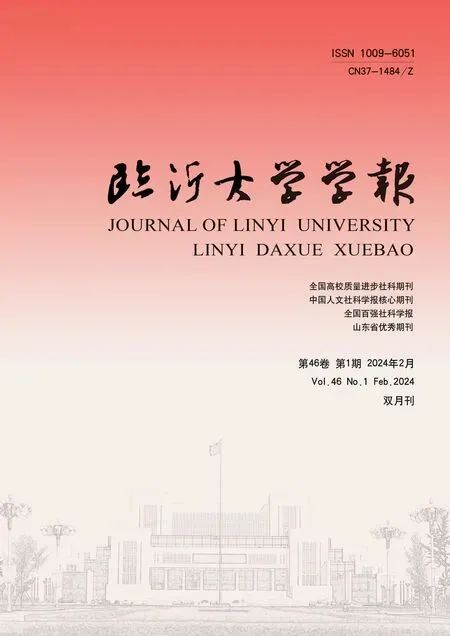隐微处的罗生门图
——《骗子:他的假面舞会》中的共同体书写
唐 文
(临沂大学 国际生物资源应用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引言
19 世纪上半期,美国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这是美国作家探索个人身份特征、建构美国文化认同的关键时期。①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是19 世纪美国文学界以文明志的代表。 自1846 年的《泰比》到1857 年的《骗子:他的假面舞会》(The Confidence-Man:His Masquerade)(以下简称《骗子》),麦尔维尔创作了九部小说,文学写作逐渐由以取悦读者为中心目的,转移到了表达自我、建构文化共同体的重心上。 在麦尔维尔看来,原创性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准则,“宁可因原创而失败”也不愿“因模仿而成功”。[1]247《骗子》正是这样一部独具原创性的小说,麦尔维尔对这部小说寄予厚望,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以至于在《骗子》之后,他放弃了小说创作。现在看来,《骗子》可以被看作是麦尔维尔在小说创作领域中的天鹅之歌:“具有自传色彩,同时也是对作者意识形态的总结。 ”[2]1
一、隐微视域与传奇书写
在霍桑的帮助下,麦尔维尔与伦敦梅塞尔、朗文等出版公司签约并于1857 年出版了小说《骗子》。该小说于同年4 月1 日与读者见面,此后3 个月才卖出了343 册,而到第二年的6 月总共卖出409 册。[2]14出版公司血本无归,麦尔维尔更是灰心至极。
与对麦尔维尔之前小说大加赞誉的态度不同,美国学界面对《骗子》的出版十分冷漠。按照美国学者福斯特(Elizabeth Sophie Foster)的话来说,《骗子》“遭遇了一片死寂”[2]18。 美国学者休·海瑟林顿(Hugh H.Hetherington)指出,“麦尔维尔是一位天才……《骗子》讲述了一个地道的美国故事”,这部小说“每个人都会买,其中有些人也会读,但很少人能够懂”。[3]384即使到了20 世纪20—30 年代的“麦尔维尔复兴”(Melville Revival),《骗子》仍被束之高阁,相关评论也大多对其持否定的态度。美国学者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认为,小说“假面舞会”的含义模糊,文本充斥着“作者个人的失败体验”[4]144;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则认为,小说是“未老先衰的艺术产物”[5]179。 20 世纪40 年代,福斯特的博士毕业论文专门研究了《骗子》的缘起和意义,论文伊始就指出:“《骗子》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并不重要。”[2]Preface:i更有甚者,美国学者塞缪尔·蔡斯·凯尔(Samuel Chase Coale)在谈到美国传奇文体时提出,“等到了《骗子》的时候,(麦尔维尔的)小说就已经死亡了”[6]33。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也有肯定的声音。 论者罗伯特·福赛斯(Robert Forsythe)认为,《骗子》是麦尔维尔继《麦迪》(Mardi)、《白鲸》(Moby Dick)和《皮埃尔》(Pierre)之后最好的一部小说[7]92;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提出,《骗子》是“仅次于《白鲸》的小说……骗子这一角色是美国文学中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8]185;而罗伯特·米德勒(Robert Milder)则认定小说“是集讽刺和自我表达为一体的经典作品”[9]440。 如果说国外学界对《骗子》漠然视之,大多数人对其持否定的态度,那么国内学者更是将其自动过滤,极少论及这部小说。 国内学者郝运慧等的文章《“信仰”的幻灭——解读赫尔曼·麦尔维尔的〈骗子的化装表演〉》,开门见山便指出小说“是麦尔维尔的小说作品中被长久遗忘的一部”[10]。
总而言之,学界对《骗子》一书的评论褒贬不一,虽然绝大多数的论者对其持否定的态度,但也有学者指出了可圈可点之处。如何去解读这种褒贬不一,以及作者最初对小说的期待,一个比较合理的解读是,作者使用了隐微写作手法,在表面故事背后隐含了与审美、文学和社会等相关的多层意味。
隐微写作(esoteric writing)是17—18 世纪欧陆作家主要的创作方式之一。所谓“隐微”,与“显白”(exoteric)相对,意指在表面文本之后暗含深意。 美国学者亚瑟·M.梅尔泽(Arthur M.Melzer)在专著《字里行间的哲学:被遗忘的隐微写作史》(Philosophy between the Lines:The Lost History of Esoteric Writing)中如此界定“隐微写作”:
(隐微)是利用内在的难点、深奥性或者特定的聚焦,让大多数人不明白文本意义的某种内涵——这一点与量子力学是相似的。 严格来讲,在哲学阐释语境中,因其是隐含的、秘密的,所以隐微指的是难以理解的东西。[11]1
从梅尔泽定义中可以看出,所谓的“隐微”创作,看似讲述A 实则是在谈论B,而且大多数人并不明了B 的内涵。自柏拉图时代到18 世纪,隐微写作一直被经典作家奉为圭臬,“少数人读懂”成为作品高品质的重要标准。隐微作者利用“难点”和“聚焦”进行书写,用创作来揣摩并把握真理,具有一定的反理性特点。 随着18 世纪理性启蒙时代的到来,作家将清晰理性置于隐晦感性之上,隐微书写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福斯特谈到,“麦尔维尔写了一本书, 想要讲述的主要内容并不是表层显而易见的故事,其真正的主旨藏在层层符号和反讽之后,其中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2]199。 1850 年前后,麦尔维尔开始接触莎士比亚戏剧,尤其对其悲剧作品做了深入研究,与此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主义作品。在经历了《麦迪》等显白书写后,麦尔维尔开始尝试隐微创作,而隐微视域正好解释了学界对小说褒贬不一的反应。霍桑曾经讲过,“他(麦尔维尔)不肯轻易投入信仰的怀抱中,但这种无信仰的状态又令他备受煎熬。他太诚实也太勇敢,宁肯在这种痛苦中挣扎也不愿意随意放任自我”[12]135。对麦尔维尔来说,文学创作是其终身追求的信仰,文学书写则是其缓释生存之重的方式。 从《泰比》《欧姆》(Omoo)中对读者反映的绝对关注,到《马迪》《白鲸》中对生存秩序的主动思考,从《白鲸》前半部分的轻幽默到《公鸡喔喔啼》(“Cock-A-Doodle-Doo! ”)中的讽刺书写,麦尔维尔不断探索着维系生命之源的信仰书写,而这些对文学审美的思考,在《骗子》中以隐微方式得以巧妙地表达。
整体看来,小说在故事层面可以弗兰克·古德曼(Frank Goodman)的出现为标志分成前后两部分,但在框架上则可以分为讲述行骗情节的部分和有关元小说创作的部分。 小说共有40 章,前23 章描写了“信仰号”形形色色的骗局,讲述了灰衣人、草帽人、代理人、草药医生等骗子行骗的故事;从第24 章开始,终极大骗子弗兰克登场,成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在与骗子查理斯·阿诺德·诺贝尔周旋、与马克·温塞姆和爱格伯特交锋后,弗兰克成功骗取了理发师的信任,并在故事结束时将船舱中的老人引向黑暗。 在框架结构上,除了行骗情节,作者分别在第14 章、第33 章和第44 章中论及文学创作。 有关文学创作的讨论被均匀地分布在文本之中,让作品带上了鲜明的“元小说”特点。 第14 章就前一章商人的怪异举动展开讨论,“起先看起来存在悖论, 但之后作者却可以通过高超的创作技巧自圆其说”[13]75,小说人物性格只有多变才符合现实。 第33 章再次提到前两章中人物行为表现与性格设定的不符,并进一步提出,读者“在小说中所找寻的,不仅是愉快的阅读体验,更是现实生活背后的真理”[13]190,即作品既要符合又要超越现实。在第44 章中,针对弗兰克形象的塑造,麦尔维尔谈到了原创的重要性,把神话创世纪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将原创作者比作新宗教的创始人,从而将文学创作上升为一种信仰。
从小说结构看,行骗故事贯穿始终,而穿插在文本中三个有关作者创作思路的章节,看起来则让故事稍显松散。 但如果从隐微视域去逆向审视,整本小说实际都是对这三章谈及的创作思路的实践和反思,即这三章正是作者着意强调突出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将故事性放置在第一位,那么这具有元小说叙事的三章很明显跑题了,对故事的整体性起到了破坏作用;但如果将这具有“破坏性”的三章放在核心位置,即麦尔维尔旨在从故事隐微视角展开对文学创作的思考,那么作品的整体布局就显得合理了。在这三章中,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讨论最为重要。 第14 章提出,通过作者之手一切矛盾都会得以解决,而所谓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作者精心杜撰出来的。 第33 章进一步提出,“小说具有宗教的特点:它应该呈现一个他者世界,但是我们却感觉与之紧密相连”[13]190,这实际指出了小说的传奇本色。第44 章提到了原创性的问题,“就算是仅仅创作一个原型人物,作者也需要极好的运气”[13]247,更将小说创作与《圣经·创世纪》联系起来,颇有“文章天然成,妙手偶得之”的意味。 如果将这三章联系起来,就可以明确地看到作者在小说中所隐微表达的创作理念:建构在现实基础上的传奇体裁与杜绝模仿的原创人物塑造。 总而言之,小说文本所讲述的故事仅是表达文学创作理念的平台而已。尽管一直在标榜“现实”,但在麦尔维尔看来,超越现实的原创才更为关键。 麦尔维尔有关原创理念的执着,正呼应了霍桑对传奇(Romance)的偏爱。
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序言中,霍桑谈到了小说和传奇的区别,认为前者“旨在达到细节上的逼真,不仅叙述有可能发生的事件,还要描写普通人潜在的行为可能”;而后者虽然“漠视人心对真理的渴求”,却“可以呈现隐藏在故事图景中的真理,并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作者选择(该主题)的意愿和创作初衷”。[12]Preface:viii发源于古老的欧陆文明、发展于荒芜的美洲大陆的美国文化认同建构,在传统和革新之间艰难行进。从美国梦的视角审视,最初追寻宗教自由的梦想深处纠缠着物质欲望,灵魂和物质的相反相成正是确立美国精神的基础。 也正因如此,美国学者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才提出,美国作者的想象中充满了“疏离、矛盾和混乱”,而美国传奇小说之所以在美洲大陆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正是因为传奇作家“了解并接受了这种乖讹”。[14]2-6正因如此,霍桑认为传奇是最适合美国的文学表达形式,作为霍桑主要拥趸的麦尔维尔对此也是认同的,麦尔维尔正是基于对建构文化认同的思考才将作家原创性推至前台。 在 《霍桑和他的青苔》(“Hawthorne and His Mosses”)中,麦尔维尔提出,“宁可因原创而失败”也不要“因模仿而成功”。[1]247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提出,国家认同包含历史空间(historic territory)、法律政治共同体(legal-political community)、法制平等(legal-political equality)以及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common culture and ideology)四个方面。[15]1519 世纪中期是美国认同建构的关键时期,很多作家在创作中都为建立“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献计献策,麦尔维尔也身在其中。有关现实和原创的创作理念的提出,是麦尔维尔探寻美国作家身份、建构美国文化认同而做的努力。在《霍桑和他的青苔》中,麦尔维尔讲到了原创性之于美国文学的重要性:“我们不需要美国的戈尔史密斯;不,我们不需要美国的弥尔顿……我们不应不加辨别地歌颂外国作家,而应该适时地认可值得赞颂的本土作家……让我们勇敢地摒弃一切模仿。 ”[1]248从隐微视域下审视,这种对原创性的偏执根源于作者对建构美国文化认同的自觉意识,体现了麦尔维尔对于“什么是美国文学”“如何创作美国文学”等问题的深度思考。 这种文化自觉,还体现在《骗子》一书的有关“骗子”形象的塑造和共同体书写上。
二、骗子背后的共同体书写
小说第14 章中指出,即使文本细节与现实不符,作家也可以生花妙笔地让故事读起来真实可信。正因如此,作家创作和骗子行骗确有相通之处,环环相套骗局的故事表层和宣讲创作理念的隐微书写并行线索在“骗”字上得到了统一。 从施众和受众的关系上来看,让读者相信虚构内容是创作的重要目的,因而在不掺杂道德伦理的符号意义上,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正对应着骗子和受骗者的关系。此外,与骗局性质相同,文学创作也建构在文本内容和现实生活分离的基础之上。 骗子编织谎言并想方设法让对方就范,这正对应着作者绞尽脑汁让读者接受文本的努力。 美国学者苏珊·库尔曼(Susan Kuhlmann)提出,“利用修辞术来建构幻觉”,在这一点上“骗局”和“艺术”是相同的。[16]13
19 世纪中期,美洲西进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初的康涅狄格州人、哈德逊河流域的居民、特拉华州人等沿着东部的内陆河北上,之后向西翻越了阿巴拉契亚山脉和阿利根尼山脉,最终到达了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来自不同地域的逐梦者聚集于此,密西西比河流域热闹起来,逐渐融合为集中体现19 世纪中期美国精神的地域。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中讲到,“19 世纪中期,密西西比河流域运行的仍然是绝对意义上的经济民主体制,是美国性真正的故乡,也是最靠近美国梦的地方”[17]148。 以驯养为特征的文明西行,与荒野秩序进行了冲撞:“西部边疆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文明是如何冲撞和改变荒野的。”[18]52冲撞之下、秩序未建构之前,为“从无到有”的行骗行为提供了良机,这也是骗子横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重要原因。 小说于1857年4 月1 日愚人节正式与读者见面,而故事开始时间亦是4 月1 日。 “愚人节”的设定凸显了“欺骗”的主题。 小说中,密西西比河上的信仰号(Fidele)从圣路易斯市出发,往南开往新奥尔良市,甲板上人头攒动,轮船在不同港口吞吐着乘客。 骗子在故事中以黑人瘸子乞丐、聋哑人、草帽人、灰衣人、股权人、草药医生、代理人以及弗兰克·古德曼八种不同形象出现,精心设定了一场场令人叹服的骗局。在美国19 世纪西进运动的背景之上,这些骗局亦带上了梦想者逐梦的色彩。
在西进的行程中,追梦者离开故土不断前行,希望在“山巅之城”重建自我。模糊旧身份而展示新自我,追梦与欺骗在模糊历史这一点上是相似的。除此之外,库尔曼还将骗子看做是19 世纪重要的边疆开拓者:“绝顶聪明、左右逢源、流浪汉身份、多变与热情,还有始终想要过得更好的欲望。 ”[16]12在小说前23 章中,弗兰克扮成7 个形象,均在赢得信任后骗走对方钱财。第3 章,黑人为了自证身份拿出一张列有8 名证人的名单,为后续故事中骗子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一场场精彩的骗局,名单上的人物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行骗是这些骗子形象赋予自身生存意义的方式,亦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前半部分,灰衣人、股权人和草药医生行骗的故事所占篇幅最多。 打着为孤寡院筹钱的旗号,灰衣人轻易从牧师、金纽扣绅士和寡妇那里骗取了钱财;股权人骗得大学生、商人、船舱里的老人等对象的信任,劝说对方买下黑流炭公司的假债权;草药医生将假药兜售给了瘸腿士兵和船舱里的老人,等等。如果将信仰号视为符号意义上的共同体,那么骗子同样是船上的梦想者,行骗亦带上了梦想的崇高。除了勾连行骗与美国梦之间的呼应关系,麦尔维尔还通过骗子形象中民粹和精英的双重特性审视了美国文化认同的建构。
进入19 世纪,建构美国认同,尤其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被提上日程。一方面,与欧陆儒雅传统一脉相承的美国白人主流价值观(WASP)信奉清教思想与贵族传统,带有精英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源于平等的美国梦鼓励民粹精神,而这种精神已经渗入了整个民族的灵魂机理。 精英和民粹之争在19 世纪上半期美国总统之争中得以具象化。 1824 年的总统竞选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之间展开,亚当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主张以华盛顿为中心开展全面的教育和科技改革,是典型的精英派代表;而杰克逊则倡导自由经济和实用主义,是民粹主义者的代言人。总统之争体现了民主思想和官僚意识、民粹思想和精英主义之间的龃龉,暗含了美国认同在民粹和精英之间的矛盾挣扎。 两人势均力敌,1824 年,亚当斯胜出;而1829 年,实干家杰克逊当选了美国总统。骗子是社会边缘人与独居者,本身具有精英分子的特点;而骗子行骗则是民粹和精英对抗的另一种形式。正如库尔曼所讲,“(骗子奉行)绝对的个人主义,或是欺骗他人②或是被别人逐出,他总是自愿游荡在共同体之外”[16]42。
小说第3 章中,作者提到了一起阿肯萨斯审判案。该案中,民众因不服审判结果而使用暴力将被告救出,结果发现被告确实罪大恶极,于是大家又一起绞死了被告。 麦尔维尔总结:“一个人被朋友们绞死了,绞刑架一幕确实具有警示意义。 ”[13]19小说中该场景细致地呈现了暴徒行径,民粹精神的负面因素亦被挖掘出来。 自然主义的笔吻点明了麦尔维尔精英作家的身份,字里行间满溢着他对暴力民粹的恐惧心理。 在第24 章中,弗兰克讲道:“生命就是一场化装晚宴;我们必须要参与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在情感上准备好,随时扮演傻子的角色。”[13]141在这里,麦尔维尔借助弗兰克的口表达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显而易见,弗兰克的话是对莎士比亚“生命是一个大舞台,而每个人都是演员”的演绎,但相比较莎士比亚的版本,弗兰克的“化装晚宴”多了骗子这一角色。可以看出,麦尔维尔预设了精英和民粹的对立,更把自己放置到精英群体之中。 一方面,麦尔维尔认为骗子属于具有精英特质的群体;而另一方面,为了在民粹大潮中生存下来,精英分子往往需要隐瞒自己的身份而扮演骗子的角色。 这样看来,在骗子这一角色之中,精英思想和民粹精神得到了有效融合,可看作是在隐喻层面上对美国文化认同的审视和思考。
三、信仰危机与文化共同体
在以霍桑为代表的19 世纪传奇作家看来,与现实主义的小说不同,传奇因其奇幻因素能够在想象和现实之间达到平衡。 “奇异事件可能发生,从象征或者意念上具有可信度,而不是现实意义上。”[14]13英语文学中的“传奇”(Romance),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盎格鲁诺曼时期,像是《嘉文和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这样的传奇作品,故事情节都包含了超自然元素,而且往往着意宣讲某种思想品质。 霍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具有美国特质的传奇文学,并坚信传奇才是最适合美国文学创作的体裁。 霍桑创作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Seven Gable)、《福谷传奇》(Blithedale Romance)和《云石牧神》(The Marble Faun)等四部传奇小说,是对现实和虚幻结合的传奇体裁的最好阐释。 麦尔维尔深受霍桑文学创作观的影响,将现实主义与超自然元素结合在一起,通过写作传奇体裁作品探讨个人文学创作特点,构思民族文学的认同特质。与霍桑写作“罪与罚”主题的传奇作品不同,麦尔维尔将小说背景设置为航行于大西洋之上的船只。 乍看来,《骗子》的故事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无论是黑人瘸子乞丐、草帽人、代理人等骗子,还是商人、牧师、老人等受骗者,包括行骗中双方谈论到的与慈善、信任、超验等相关的社会思潮和哲学理论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但在平静的现实主义湖面下,涌动着充满了神话元素、寓言特质和符号意象的暗流,其中,故事中的基督信仰隐线,是通过传奇书写建构共同体的典范。
小说隐微指出了弗兰克与撒旦的人物对等关系。 第36 章中,弗兰克和马克·温塞姆谈到了蛇的意象,并声称这种“美丽生物”是温顺的。之后,小说甚至描述了弗兰克“化蛇”的情景:“一边说着,他似乎应声而动——就像一些最真诚的描述者那样——他无意识地扭动身体,头顶盘旋而上,直到他自己也变成了蛇。”[13]195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故事中,撒旦化身为蛇,花言巧语诱骗夏娃吃了禁果:“诱惑者巧舌如簧,他编织的谎言/通过花言巧语击中了夏娃的心田。 ”[19]210小说中的弗兰克是披着慈善外衣的终极大骗子,而其行骗手法即靠“巧舌如簧”骗取对方信任,而这也是麦尔维尔描写弗兰克化蛇的原因。此外,弗兰克骗取理发师信任的章节,还呼应了《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中撒旦诱惑耶稣的场景。
第43 章中,弗兰克与理发师克里姆打招呼:“上帝保佑你,理发师! ”[13]232此时的克里姆正打盹,懵懂之间还以为碰到了鬼魂(spiritual manifestation),这里的鬼魂,其实暗指隐藏在弗兰克身上的撒旦意象。弗兰克巧妙利用“概不赊账”的牌子与克里姆签订协议,“须完全信任所有的人,特别是陌生人”[13]242,而弗兰克则会承担其因信任而导致的任何损失。为了让克里姆相信自己,弗兰克还决意拿出50 美元做保险金,但最终因身上没零钱而作罢。就这样,在弗兰克灿若莲花的巧舌下,克里姆心甘情愿地上了当,概不赊账的克里姆被弗兰克彻底改变了。在弗兰克离开之后,他才意识到,不仅签了一纸废约,而且应收的理发费也泡汤了。这正是弗兰克的高明之处:将骗术建构在对方情感认可的基础上。 如果弥尔顿(John Milton)“在无意识间站到了撒旦的阵营中”[19]39, 那么麦尔维尔则是有意通过隐微圣经故事指出:所谓“信仰”不过是“欺骗”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这样,就从本体论意义上对传统宗教和文化信仰进行了釜底抽薪的解构,这种离心力在小说最后得到了加强。
最后一章开头写道,“在客舱的中间、天花板吊着一个日光灯”[13]247,微暗模糊之中还有一座角坛(a horned altar),上面有一个穿着长袍、头顶光环的人像。很明显,这里的人像即上帝,而角坛的意象则明确了小说文本与圣经之间的互文性。微弱的灯光和模糊的圣像,暗示了基督信仰在19 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式微。 本章主要受骗者是一位形似先知西蒙的苍然老叟:“看到并赞美了信仰之主后,安静地离开了。 ”[13]248《骗子》中的“西蒙”同样是骗术的牺牲品,在推销员男孩的诱骗下,他购买了毫无用处的旅行锁和钱袋。 老叟的愚昧和易信,构成了对基督信仰的解构力量。在离开船舱之前,老人四处寻找救生圈,却没发觉自己正坐在一个救生圈上。 可以拯救生命的救生圈,被错用为板凳;可以用来厘清生命秩序的信仰,却成为弗兰克行骗的手法, 这个细节揭示出信仰式微的源起正因为信仰者本身的愚昧和固执。 小说结束前,弗兰克熄灭了本来就微弱的灯光,指引着老人走向了黑暗,意为信仰的彻底终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所谓的共同体并不是实体存在,而是“因想象而被赋予内在固定的却有限的神圣主权”[20]6。简言之,“想象”是认同建构和稳固的关键所在。处于文化认同建构关键期,以霍桑、麦尔维尔等为代表的美国作家发挥文学想象的作用,梳理美国共同体的内涵构成。根据学者桑塔亚纳的解读,对欧陆儒雅传统的继承批判是建构美国文化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在 《美国哲学中的儒雅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 in American Philosophy)中,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借建筑风格的隐喻指出了美国特性的双重内涵:“美国精神(American Will)生活在摩天大楼,美国心灵(American Mind)居住在殖民者的宅邸,前者是美国男性气质主导的世界,而后者(至少大部分)是美国女性气质的天堂。一个积极向上、富有攻击性,而另一个则信奉儒雅传统。”[21]40桑塔亚纳认可被称为“美国精神”的儒雅传统,认为其是构建美国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桑塔亚纳所谓的“文雅传统”,主要指的是传播到美洲大陆的欧洲特别是英国传统贵族文化,即狭义上的传统清教道德禁律和广义上的传统贵族文化,而《骗子》正是针对两者进行了大肆解构,正如印度教里的梵天,必须以毁坏旧世界为前提才能创建新世界。美国建构文化共同体的前提,即抵制儒雅传统,解构以正统清教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 在撼动了信仰根基之后,如何建构新的、能够取而代之的文化精神和认同内涵?这既是麦尔维尔深度思考并以隐微文本传达给读者的关键问题,也是解读小说中弗兰克身份复杂性的关键。 在读者眼中,弗兰克是慈善家,亦是终极骗子,是上帝之光熄灭后取而代之的撒旦,亦是柏拉图出洞又入洞的圣贤哲人。在文章《论作伪和掩饰》(“Of simulation and Dissimulation”)中,培根将骗子分为“作伪者”和“掩饰者”两种,前者是“肯定的”而后者是“否定的”,即“作伪者总是创作与自我不符的身份”,而掩饰者“故意不动声色地抹杀痕迹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22]27小说前半部分出现的七个骗子属于前者,通过掩盖真相而行骗,后半部分的主角弗兰克则通过创造来行骗。弗兰克具有创造性的行骗方式,正是解读其身份矛盾性的关键。 如果熄灭上帝之光意味着对基督的颠覆,那么获取被欺骗者的信仰则将自己重构为“上帝”。先“破”后“立”的信仰更迭,隐喻了麦尔维尔对于共同体建构的多方思考,而弗兰克身份的晦涩和模糊性,也暗含了作者对认同走向的困惑。
在新的共同体语境中建构文化认同,背离儒雅传统,却迷失在民粹和精英之间的平衡中;颠覆基督信仰,却陷落于骗子精心编织的罗网中。 小说表面讲的是骗子行骗的故事,隐微视角展示了作者借“骗”来审视文化认同和共同体建构的创作主旨,既指出了建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困惑。总而言之,《骗子》是麦尔维尔从文化认同出发思索美国社会走向的文学表达,精彩的骗局编织成一幅共同体建构的罗生门图。
注释:
①F.O.马西森(F.O.Matthiessen)在《美国文艺复兴:埃摩森和惠特曼的艺术与表达》(American Renaissance: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中,将19 世纪30 年代到60 年代的时段称为“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
②库尔曼用到了英文词组“take in”和“drive out”标识骗子和共同体的关系,“take in”是双关语,既有“纳入”的意思,也有“欺骗”的涵义。
——评《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