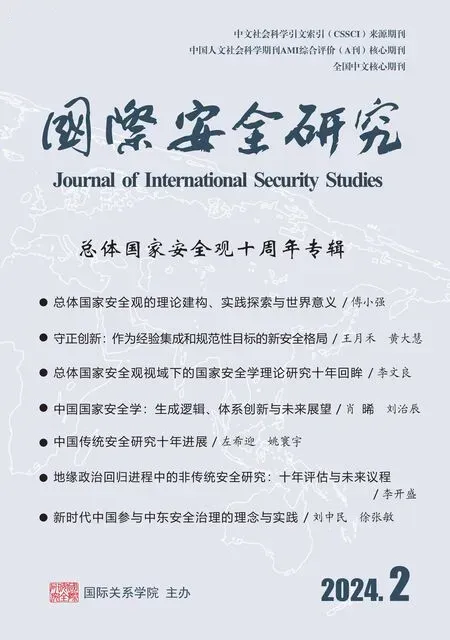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进展∗
左希迎 姚寰宇
【内容提要】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中国的传统安全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从研究议题看,中国的传统安全研究主要聚焦地区冲突,领土争端,联盟政治与伙伴关系,核安全、太空战略与网络安全,安全秩序等重要议题。在理论研究上,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方面都有大的提升。总的来看,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过去十年研究水平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学者发展了一些安全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方法、人才梯队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上,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取得了进步。不过,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目前理论创新仍落后于中国的外交实践,难以满足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面临学科碎片化和产出泡沫化的问题。展望未来,中国传统安全研究需紧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重视对中国经验的提炼和总结,通过基础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撑。
国际安全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最核心的研究领域之一,大致可以分为传统安全研究(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与非传统安全研究(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两类。当代传统安全研究兴起于冷战期间,聚焦于国家间的军事和国防问题,如战争、领土争端、武力使用、结盟、威慑和裁军等议题,将国家视为主要的安全行为体,并通过运用不同的军事手段和安全战略来维护或提升国家安全。传统安全研究与现实主义理论高度相关,强调国家的中心性、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权力政治,关注国际安全秩序的变革。相比之下,非传统安全研究扩展了安全研究的视野,关注除传统军事和国防外的其他议题,包括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非传统安全研究认为安全主体不仅限于国家,还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行为体。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较为多元,涵盖了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哥本哈根学派等理论流派。①有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相关论述参见:Paul D. Williams, ed., Security Studies: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13; Joseph S. Nye, Jr.,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1988;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91; David A.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1995; 余潇枫、王江丽:《非传统安全维护的“边界”、“语境”与“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11 期;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涌现了无数关于战争与冲突以及安全与秩序的论著,诞生了大量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带领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安全理念,积累了丰富的安全思想和实践经验。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统安全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关系学科不断发展,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逐渐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新时代以来,中国传统安全研究进入黄金时期。2014 年4 月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安全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之间的界限,将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相结合,将传统安全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统筹到国家安全的视野下,既突破了传统安全研究过度强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局限,又补足了非传统安全研究对国家安全重视不足的短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在思想和理论上为中国传统安全研究指明了方向。过去十年,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多变,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凸显,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为传统安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那么,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主要关注哪些议题?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主要有哪些理论流派?这些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不足?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又该如何发展?本文将通过回顾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年来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取得的成就并分析存在的不足,从而为中国未来的传统安全研究提供借鉴。
一 传统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
过去十年,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与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变迁息息相关。尤其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与中国外部环境变化形成了共振效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地区安全危机频发,这些现实问题为中国传统安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事实和研究案例。中国近十年传统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基本回应了中国的重大现实关切。
(一)地区冲突
二战以来,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对大国战争的恐惧使得全面战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有限战争逐渐成为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形式。从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冷战结束后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再到当下的俄乌冲突,大国对这些地区冲突的介入也对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过去十年,中国学术界对地区冲突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研究大国介入地区冲突的行为模式。牛军研究了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中“联盟”与局部战争之间的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①牛军:《“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6 期。对于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驱动因素、手段和模式选择,以及美国实施军事干涉的理念基础,中国学术界也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②刘丰主编:《美国军事干涉与国际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有学者对美国战略精英在地区冲突中如何评估外部威胁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美国政治精英在战争决策时夸大威胁以及战争过程中威胁流散的内在机理,解释了美国输掉反恐战争的内在逻辑。①左希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版。俄乌冲突爆发后,不少学者更是集中探讨了该冲突爆发的原因、美俄互动的模式及其战略影响;②冯玉军:《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外交评论》2022 年第6 期;左希迎:《美国威慑战略与俄乌冲突》,《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5 期;曾向红、陈明霞:《俄乌冲突前的外交谈判与信息测试》,《国际政治科学》2023 年第1 期。针对西方对中国的质疑,达巍撰文指出,中国反对“大国寻求独占影响力范围”的想法,但认为应该尊重国家合法的安全关切。③Da Wei, “Security Concerns are Reasonable, Spheres of Influence are No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5, No. 2, 2022.
第二,讨论代理人战争的实质和效果。地区冲突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形态,即代理人战争。过去十年,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文少彪提出,代理人战争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双向博弈会影响代理人战争的效果和进程。在内战中,当内外双方都存在利益需求时,内战往往演变为代理人战争。④文少彪:《控制与自主: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版,第166-173 页。陈翔则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多次以不同借口、不同手段发起代理人战争,其根本目标在于进行霸权护持。⑤陈翔:《内战为何演化为代理人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1 期;陈翔:《霸权护持与美国的代理人战略》,《当代亚太》2020 年第1 期。然而,代理人战略并非大国完美的“白手套”,当代理人战争无法达到目的时,大国往往需要直接介入地区冲突。
第三,关注族群冲突与内战的深层原因。二战以后,国家间冲突的频率大幅下降,族群冲突和内战成为冲突的主要形态。唐世平、熊易寒和李辉提出,石油并非引起族群冲突的深层原因,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才是导致族群冲突的关键。⑥Shiping Tang, Yihan Xiong and Hui Li,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Security Studies, Vol. 26, No. 3, 2017.苏若林系统研究了统治者发动战争以转移国内视线的原因、时机和方式,她认为国内危机烈度会影响决策者是否挑起战争来维持统治以及选择何种对手发动战争,决策者不同的过往经历和特质也是诱发地区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⑦苏若林:《国内危机烈度与冲突对象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8 期;苏若林:《内外冲突关联的实力维度与冲突对象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11 期;Ruolin Su, “Wars of Choice: Leaders, Rebellion Legacy, and Domestic Unres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4, 2021。
(二)领土争端
领土争端是中国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安全议题。过去十年,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中印领土争端不断出现,这些争端本身以及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行为模式成为传统安全研究的重点。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学术界高度关注美国南海政策及其影响。周琪指出,南海问题的不断复杂与恶化,与美国的南海政策从“观察”转为“干预”、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队有着直接关系。①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6 期。胡波认为,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加速发展,美国逐渐将大国战略竞争视为其面临的最大海上挑战,开始实施从“由海向陆”到“重返制海”的海上战略转型。②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5期;胡波:《美军海上战略转型:“由海向陆”到“重返制海”》,《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第5 期。在南海地区,美国采取叙事战争、议题联系、民事介入、自由航行、前沿存在和军事联盟等六类“灰色地带”策略与中国进行海上安全竞争。③陈永:《精准修正主义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 期。美国还试图通过在避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运用综合手段进行“成本加强”,增加中国的战略成本。④赵明昊:《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制衡的政策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1 期。
在钓鱼岛问题上,学术界重点讨论了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的反制措施。黄大慧等学者详细分析了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批驳了日本政府的错误主张。⑤黄大慧等:《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借助大众动员、资源汲取与投送、制度整合等手段,在钓鱼岛争端中取得了一定的战略优势。⑥左希迎:《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外交评论》2014 年第2 期。节大磊从前景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在日本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之后,最初中国处于损失区间,因此中国通过加强海空巡逻、暂停危机管理机制,表现出高度的风险接受态度;当中国逐渐掌握有利态势、开始认为自己处于收益区间时,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行为转向风险规避,开始减少巡逻和恢复有关危机管理机制的谈判。⑦Dalei Jie, “From ‘Shelving Sovereignty’ to ‘Regularized Patrol’?: Prospect Theory and Sino-Japanese Islands Dispute (2012–1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23, No. 2, 2023.
在中印领土争端上,学术界主要关注中印在2017 年洞朗对峙和2020 年拉达克对峙中的战略行为。谢超研究了印度对中国的“惩罚性威慑”及其效果,他认为尽管莫迪政府多次失败,印度国内对危机的不同看法促使其在失败后更积极地挑起新的对峙。①谢超:《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8 期。叶海林研究了中印在边界争端中如何判断对手的自我认知,他认为国家应准确判断次要对手的自我认知和关系认知,避免因信号释放失当造成政策目标与手段不匹配的消极后果。②叶海林:《自我认知、关系认知与策略互动——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博弈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11 期。
(三)联盟政治与伙伴关系
联盟政治与伙伴关系是传统安全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议题。过去十年,美国持续推动其全球联盟体系转型,中国也不断发展自身的伙伴关系。中美两国各自的行为与彼此互动极大地塑造了全球安全环境,因此中国学者对美国的联盟体系、中国的伙伴关系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首先,研究联盟形成、转型与瓦解的过程。一是关注美国构建新联盟的努力。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试图加强盟伴体系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上的作用。③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6 期。尤其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升级,反映了美国重构同盟关系的理念。④樊吉社:《美英澳三国新防务合作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11 期。二是聚焦美国分化其他联盟体系的努力。凌胜利通过研究冷战期间美国的联盟实践,指出美国基于联盟重组、联盟解除、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等多重目标,采取楔子战略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从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⑤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年版,第33 页。
其次,分析美国联盟管理的逻辑。有学者认为,美国的联盟管理服务于其霸权护持的目标,一般通过利益协调式管理、制度规则式管理和霸权主导式管理三个模式展开,以安抚和施压相结合的策略约束盟友,以减少其对美国安全利益的损害。⑥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外交评论》2014 年第6 期,第95 页;节大磊:《约束盟国的逻辑与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3 期。周方银比较了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不同联盟管理策略及其影响。⑦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2 期。左希迎认为,美国在战略收缩的态势下将面临没有能力兑现盟友骤然增长的战略承诺需求的“承诺难题”,需要在联盟的成本与所面临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为此美国实施双重再保证战略,以维持联盟威慑的可靠性。①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当代亚太》2015 年第3 期;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保证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9 期。
再次,考察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阎学通认为,中国选择伙伴关系战略而非结盟,原因在于联盟维护生存和推广意识形态的价值下降,从经济成本考虑,结盟被视为包袱。②阎学通:《反思为何结盟战略不受大国青睐》,《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3 期。对于伙伴关系战略的价值,门洪华认为,它既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③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2 期。孙学峰等人提出,建立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伙伴国类型是影响中国伙伴关系升级的核心因素。其中,中国与支点国家或结点国家的伙伴关系更可能实现升级,原因在于推进与支点或结点伙伴国的政治及安全合作有助于中国缓解崛起困境。④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2 期。陈志瑞和吴琳指出,新时期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构建正呈现出多边主义转向,中国将区域作为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主层次,以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区域性大国和组织作为包容性治理平台的生力军,视共建“命运共同体”和提供“和平公共产品”为落实全球合作倡议的议程载体,推动多边主义守正创新。⑤陈志瑞、吴琳:《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多边主义转向》,《外交评论》2023 年第4 期。
(四)核安全、太空安全与网络安全
核安全和太空安全也是传统安全研究的重点领域。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核安全、太空安全和网络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阐述中国核政策的基本逻辑。中国在核战略上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和逻辑,学术界系统阐述和研究了中国核战略思想。⑥李彬、赵通主编:《理解中国核思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樊吉社认为,中国的核政策整体比较稳定,但是也可能适当调整核政策,以谨慎务实地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核裁军进程停滞、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发展及新兴技术影响。⑦樊吉社:《中国核政策的基本逻辑与前景》,《外交评论》2018 年第5 期。也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①胡高辰:《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2 期。吴日强认为,尽管中美战略稳定性意味着双方都没有动机率先发动核打击,但是一旦中美陷入常规冲突,冲突仍然可能在无意中升级到核层次,因此有必要建立自我约束机制。②吴日强:《不对称核力量结构战略稳定性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22 年版,第127-214页;Wu Riqiang, “Assessing China-U.S. Inadvertent Nuclear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3, 2022。
二是分析美国核战略的历史演变。江天骄在回顾了美国核战略理论、历史和现实后指出,以实战威慑和延伸威慑构成的绝对自由核战略才是长期指导美国核政策实践的根本。③江天骄:《美国实战威慑核战略:理论、历史与现实》,《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2 期。在延伸威慑方面,美国冷战后的延伸威慑从以核保护伞为核心转变为核保护伞与导弹防御并重的模式,它加强了美国联盟体系的凝聚力,但是美国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成本。④程志寰、李彬:《导弹防御与美国延伸威慑政策》,《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6 期。由于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确保机制不同,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有所差异,导致盟友之间出现不同的核扩散行为。⑤江天骄:《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外交评论》2020 年第1 期。
三是研究当前有核国家的核战略。在宏观上,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了全部拥核国家的核战略。⑥张沱生主编:《核战略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在微观上,中国学者在过去十年聚焦朝鲜核问题。樊吉社认为,朝鲜核武器已经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⑦樊吉社:《朝核问题重估:僵局的根源与影响》,《外交评论》2016 年第4 期。也有学者对朝鲜的行为逻辑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朝鲜通过虚张声势的行为成功跨越核门槛,以及美国和朝鲜在互动中的威逼战略。⑧左希迎:《核时代的虚张声势行为——以朝鲜在第四次核试验后的行为为例》,《外交评论》2017 年第6 期;吴日强:《朝美双向威逼与朝核危机的出路》,《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2 期。
四是探究太空安全、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安全等问题。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关注核技术与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的结合及其对威慑战略产生的影响;⑨徐能武、黄长云:《太空威慑:美国战略威慑体系调整与全球战略稳定性》,《外交评论》2014 年第5 期;蒋家敏、石斌:《网络威慑与霸权重塑:美国网络威慑战略的演化及动因探析》,《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4 期。另一方面,重视研究新技术对军事安全领域的影响。在太空安全上,学术界高度关注美国“星链”的军事化,尤其是关注其对俄乌冲突和未来战争的影响。①张煌、杜雁芸:《“星链”军事化发展及其对全球战略稳定性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5 期;余南平、严佳杰:《国际和国家安全视角下的美国“星链”计划及其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5 期。在网络安全上,当前网络空间处在稳定与不稳定之间的脆弱稳定状态,原因在于大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操弄网络空间公共产品;因此西方大国应认识到维护网络空间的完整性和互联互通性的重要性,塑造网络空间的稳定性。②Lu Chuanying, “Forging Stability in Cyberspace,” Survival, Vol. 62, No. 2, 2020; 江天骄:《全球网络空间的脆弱稳定状态及其成因》,《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2 期。张耀和许开轶提出了网络冲突的攻防关系模型,并指出“攻防制衡”模式所具有的低烈度特征,使其成为当前国际网络冲突攻防互动的常态。③张耀、许开轶:《攻防制衡与国际网络冲突》,《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3 期。
(五)安全秩序
过去十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安全秩序与地区安全秩序面临变革,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首先,阐释全球安全秩序变革。早在2016 年袁鹏就指出,世界正在经历近四百年来第四次历史巨变,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④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中信出版社2016 年版。有学者提出,有效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有助于更为进步的世界秩序的构建。⑤陈志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6 期;刘雪莲、姚璐:《国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6 期。对于全球安全秩序变革的动力,西方理论界往往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然而,中国的崛起并不能从“修正—现状”的二分法进行分析。⑥温尧:《理解中国崛起:走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迷思》,《外交评论》2017 年第5 期。为解决全球安全赤字,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苏长和认为,中国提出这一倡议的目的是克服联合国集体安全模式的不足,避免排他性安全结盟体系的危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拓展安全架构的范畴。⑦苏长和:《全球安全架构设计的理论思考》,《国家安全研究》2022 年第5 期。
其次,研究海洋安全秩序演变。21 世纪以来,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正在改变海上格局态势,朝着海上多极的趋势发展。⑧胡波:《从霸权更替到“多极制衡”——16 世纪以来的海上格局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2 期。其中,关键的历史动力就是中国海权的崛起。胡波认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应包含三大目标体系,分别是拥有地区性海上力量、成为国际海洋政治大国、成为世界海洋经济强国,这将对国际海洋安全秩序产生深远影响。①胡波:《2049 年的中国海上权力:海洋强国崛起之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年版;胡波:《中国海上兴起与国际海洋安全秩序——有限多极格局下的新型大国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11 期。张文木指出,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需要发展海权,而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西方海权。②张文木:《论中国海权》(第三版),海洋出版社2014 年版。此外,海军战略是海洋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吴征宇认为,中国“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的结合,意味着中国全球利益不断扩大与不对称的海权途径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也标志着中国将在未来发展马汉式蓝水海军和一系列海外基地的基础网络。③Zhengyu Wu, “Towards Naval Normalcy: ‘Open Seas Protection’ and Sino-US Maritime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4, 2019.
再次,关注东亚安全秩序调整。唐世平通过博弈论分析指出,域外大国对于地区主义的演化至关重要。④Shiping Tang, “Regionalism in the Shadow of Extraregional Great Powers: A Gam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3,2021.东亚最重要的域外大国显然是美国,因此中国学术界聚焦美国战略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的影响。⑤达巍:《全球再平衡: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再思考》,《外交评论》2014 年第2期;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当代亚太》2014 年第4 期。针对学术界认为东亚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分立的现象,有学者提出,东亚地区秩序并非单纯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而是通过经济和安全配置的巧妙耦合形成了具有灵活性的地区结构。⑥Feng Liu and Ruonan Liu,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rder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An Economy-Security Nexus Approach,”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6, 2019.然而,由于地区内部复杂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以及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东亚地区始终难以形成稳定的安全架构。⑦Dong Wang and Friso M.S. Stevens, “Why Is There No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Assessing the Strategic Impediments to a Stable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4, No. 4, 2021.对此,王俊生认为东亚安全架构走向中美“双领导体制”将是可能的方向。⑧王俊生:《大变局时代东北亚区域安全理论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83-230 页。此外,对于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秩序,魏玲认为东盟之所以能够推动东盟中心的制度化,根本原因在于它维持了“关系平衡”,将地区大国纳入东盟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对关系的主动管理和调节,实现各种关系亲疏均衡和关系体系环境的最优。⑨魏玲:《关系平衡、东盟中心与地区秩序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7 期。
二 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理论流派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传统安全研究并不从属于特定理论流派。21 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在国际安全研究上的理论创新趋缓,中国学术界却出现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传统安全的理论研究主要聚集在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两个方面。
(一)宏观理论
从宏观理论上看,中国传统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国学者从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出发,对现实主义理论本身和国家安全战略两个部分进行了研究。
首先,在现实主义范式内,中国学术界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拓展了现实主义范式的理论范畴。阎学通将现实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王道思想结合,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道义现实主义遵循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但是更加重视国家领导人的道义关注对决策的影响。阎学通指出,虽然国家利益是国家行动的主要驱动力,但在国际关系中,道德和伦理同样重要。这意味着,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国家不仅要考虑实际利益,也要考虑行为的道义正当性。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成功超越霸权国、实现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强于主导国的政治领导力。①阎学通:《大国领导力》,李佩芝译,中信出版社2020 年版。宋伟提出了“位置现实主义”理论,位置现实主义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分为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两大类,并将大国分成了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四类。这一理论认为,国家首先应该准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然后确定合理的位置性目标,这样才能制定理性的外交政策。国家在寻求提升国际秩序地位时,需要遵循实力原则与审慎原则:实力原则意味着需要谋求力所能及的秩序地位目标;审慎原则意味着不过分热衷权力位置以及对规则位置的改变保持谨慎。②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唐世平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和界定,并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两个概念。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通过蓄意损害他国来追求自我安全,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则并不会刻意损害他国来追求自我安全。①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林民旺、刘丰、尹继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唐世平还借鉴生物演化的逻辑,指出从公元前8000 年至今,世界已经从伊甸园世界,经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至今天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②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 年到未来》,董杰旻、朱鸣译,中信出版社2017 年版。
其次,中国学术界还从现实主义的路径来考察国家的安全战略问题。安全战略决定国家如何有效地使用威胁和军事力量,更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稳定,影响着战争与和平的转圜。③Paul D. Williams, ed., Secur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3, pp. 2-3.中国学者结合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对大国战略竞争和战略透支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一,从体系结构的角度,对大国战略竞争进行理论探索。过去十年,战略竞争重新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内容,④门洪华、李次园:《国际关系中的大国竞争:一项战略研究议程》,《当代亚太》2021年第6 期。中国学术界对中美战略互动进行了理论分析,解释了中国的崛起与对外战略变化所带来的安全影响。中国崛起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和巩固其霸权地位,遏制或削弱后发国家。⑤唐永胜、李冬伟:《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12 期。吴心伯提出,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未来中美两国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⑥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5 期。阎学通认为,中国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有助于塑造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外部环境。⑦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国际政治科学》2014 年第 4 期;Yan Xuetong,“Becoming Strong: The New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100, No. 4, 2021。也有学者对中国在应对美国“印太战略”和在南海争端中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和解读。⑧Liu Feng, “The Recalibration of Chinese Assertiveness: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Zhou Fangyin, “Between Assertiveness and Self-Restraint: Understanding Chin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4, 2016.第二,关注国家的战略透支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引发了中国学者关于战略透支问题的辩论。时殷弘指出,中国推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多项战略经济和战略军事政策,存在战略透支的风险。①时殷弘:《“一带一路”:祈愿审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7 期;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外交评论》2015年第6 期。这种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什么是战略透支、中国是否会战略透支的热议。为此《战略决策研究》杂志组织了专题讨论,阎学通、周方银、高程和刘丰等学者对战略透支的学术定义、战略透支与战略冒进的关系,以及如何进行战略平衡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②参见《战略决策研究》2017 年第3 期的讨论。也有学者做了进一步研究,并认为止损失败对战略透支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③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2 期。
(二)中层理论
相比宏观理论,中国学者在传统安全的中层理论成果产出方面则更加活跃。宏观理论关注体系变动、战略问题,中层理论更聚焦于探讨国家在不同安全背景下的行为逻辑与互动模式。
第一,探讨武力使用、威慑和对冲行为。首先,有学者研究了武力使用的逻辑与作用。学者们讨论了美国及其盟友对外军事干预的行为逻辑,美国如何退出非对称战争等议题。④王立新:《世界领导地位的荣耀和负担:信誉焦虑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2 期;左希迎:《威胁流散与美国退出非对称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12 期;魏冰:《美国北约盟友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的行为选择》,《欧洲研究》2021 年第3 期。就武力使用的效果而言,研究者大多认为,从其他崛起大国的经验教训来看,使用武力往往弊大于利,无益于崛起国实现自身目标。⑤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6 年第4 期;Liu Feng,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Alignment, and China’s Role in the Regional Order Transition,”The Pacific Review, Vol. 36, No. 2, 2023。其次,有学者研究了中美战略威慑的行为模式,对美国的“一体化威慑”,以及美国威慑战略过于注重威胁而减少了安抚进行了系统研究。⑥Zuo Xiying, “Unbalanced Deterrence: Coercive Threat, Reassurance and the US-China Rivalry in Taiwan Strait,”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4, No. 4, 2021; 左希迎:《美国对华常规威慑战略的调整》,《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5 期;陈曦、葛腾飞:《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论析》,《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5 期。最后,有学者研究了中小国家的对冲行为。查雯认为,这种战略选择不仅取决于国际体系压力,也取决于国内政治和决策者自身执政地位。⑦查雯:《大国竞争升级下对冲战略的瓦解与延续——以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的对华政策为例》,《外交评论》2021 年第4 期。孙德刚等提出,安全伙伴和经济伙伴越是错位,中东国家就越有可能选择对冲政策。①孙德刚、李典典:《俄乌冲突与中东安全伙伴的异化》,《国际政治科学》2023 年第1 期。
第二,关注中美冲突管控和危机管理。在冲突管控上,祁昊天认为,大国对实力转移强度和对军事转型进攻优势的认知会影响冲突管控。②祁昊天:《规则执行与冲突管控——美国航行自由行动解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 年第1 期;祁昊天:《大国隐性军事竞争与中美冲突管控》,《外交评论》2021 年第4 期。李开盛提出,中美两国的冲突管控还受到第三方的影响。③李开盛:《第三方与大国东亚冲突管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在危机管理上,如何管理中美海空危机成为学术热点议题。关于中美海上安全合作,朱锋认为相互尊重是前提,行为自律是关键,规则的制定应紧跟问题变化。④朱锋:《中美海上安全合作:原则与路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 年第1 期。胡波则提出,有效的中美海上危机管理必须在战略、规则和机制三大方面相互适应和妥协。⑤胡波:《中美海上危机管理面临的困境与改善路径》,《美国研究》2021 年第5 期。
第三,关注安全困境问题。在安全困境的生成方面,唐世平批驳了学界关于安全困境的定义,提出了安全困境的主要特征,其中无政府状态、双方均无恶性意图以及一些权力的积聚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必要条件,且安全困境并非战争的主要原因。⑥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林民旺、刘丰、尹继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25-136 页。在安全困境的缓解方面,尹继武认为,缓解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克服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通过战略沟通增强国家意图传递的可信性与正确认知,这有助于实现命运共同体以及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关系。⑦尹继武:《国际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一项理论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1 期。秦立志认为,战略不确定性带来的安全困境难以消除,不过可以通过威胁预期进行调节。⑧秦立志:《战略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的生成机制》,《国际政治科学》2023 年第2 期。
第四,关注国家的安全认知与承诺问题。国际政治心理学为传统安全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更加关注国家和领导人的安全认知与承诺等问题。通过关注国家和领导人的心理和行为,国际政治心理学有助于发现传统安全研究的新问题,同时也挑战和丰富了安全研究的传统框架。有学者分析了安全认知问题,尤其是领导人如何判断对手。岳圣淞从图式视角出发,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华政策一直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但是不同领导人对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不同,他们看待事件、人物和行动时会根据自身理解来选择具体策略。①岳圣淞:《图式演绎、叙事重构与冷战后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4 期。有学者研究了安全战略中的承诺问题,尤其是威慑中承诺的可信性问题。杨原提出,核威慑理论中确保摧毁原则忽略了承诺可信度的重要作用,以及核武器数量与承诺可信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认为确保摧毁不是核威慑唯一有效的手段或必要条件,核武器数量少于确保摧毁水平也可能实施有效核威慑。②杨原:《超越“确保摧毁”:核武器数量、承诺可信度与核威慑原理》,《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5 期。
三 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进展及不足
过去十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下,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研究水平、研究方法、人才梯队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然,也不能忽视学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总结过去十年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推动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进展
1. 研究水平不断提升
第一,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论文质量不断提升。不管是理论类抑或政策类研究,学术论文大多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试图解答理论谜题(puzzle)或经验困惑,解答中国面临的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而非单纯进行描述性研究。过去十年,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中国的部分现实安全关切。传统安全理论的发展与国家的现实关怀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是一个交互影响的过程。一方面,现实政治环境和国家安全需求推动着理论发展;另一方面,理论创新又可以帮助国家更好地理解自身所处的安全环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实际的政策制定,影响国家的行为模式。在此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自我调整的生态系统。十年间,无论是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还是理论进展,都积极回应了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安全问题(如台海问题、威慑问题等),呈现出现实发展推动理论进步,理论研究回应现实关切的正反馈效应。
第二,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研究。在经历了对西方国际安全理论的引介和消化之后,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开始聚焦中国与世界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自主研究。其一,发展出了一些原创性的传统安全理论,诸如道义现实主义、位置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相关的宏观理论,以及依托关系理论、社会演化理论、国际政治心理学等理论发展出的传统安全议题的中层和微观理论。这些理论建树推动了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发展,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二,重视对中国传统安全思想的挖掘和经验总结,拓展了传统安全研究的范畴。有学者总结了“仁”与战争正义性、“礼”与传统东亚稳定、“统”与大国兴衰和体系变迁的关系,①陈康令:《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潘忠岐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也有学者对古代中国国家安全理念与战略思想、战争和结盟经验进行提炼和中西对比研究。②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时殷弘:《从帝国复兴到华夏野蛮——对〈后汉书〉的政治/战略解读》,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周方银、李源晋:《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为例》,《当代亚太》2014 年第4 期;刘伟:《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国际安全研究》2019 年第5 期;孟维瞻:《古代中原王朝统一与崛起时期的联盟安全经验与启示》,《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6 期;蒙克、董琦圆:《“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春秋等级制下会盟的兴衰》,《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8 期。
第三,国际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一是不少学者在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③笔者统计了中国学者过去十年发表在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Security Studi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rvival, The Pacific Revie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等代表性国际期刊上传统安全论文的数量,2014—2018年五年间年均发文量约10 篇,2019—2023 年五年间年均发文量约16 篇。二是社会演化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和关系理论的相关著作在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④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print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唐世平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SA)2015 年年度最佳著作奖。三是国际话语权有了极大的提升。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国际政治杂志》(TheChineseJournalof InternationalPolitics)跻身SSCI 一区,成为国际知名的国际关系类研究期刊。2023 年12 月,唐世平还当选国际研究协会副主席。
第四,进一步译介了国外经典和前沿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方编译所译丛”和“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继续翻译和引介了大量传统安全研究的著作。近十年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战略研究丛书”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译丛”聚焦国际安全研究相关议题,翻译了不少新作。这些译作拓展了中国学术界的国际视野,丰富了读者对于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理解,也提升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水平。①任晓:《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商务印书馆2022 年版,第359 页。
2. 研究方法不断精进
第一,对定性研究方法的掌握更加深入。研究者熟练掌握了基本的定性研究方法,注重研究设计的科学性,通过“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半负面案例比较法、正负案例对比等方法进行案例研究,同时重视对案例因果机制的考察。②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12 期。中国学者还知晓定性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有学者深入讨论了定性研究中选择性偏差问题及其识别、类型化与研究设计、理论化与整合性的案例选择策略等问题。③刘丰:《类型化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设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8 期;刘丰:《定性比较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1 期;游宇、陈超:《一切为了理论——理论化与整合性的案例选择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12 期。
第二,对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更加广泛。过去十年,越来越多受到严格方法论训练的中国学者使用定量方法对武装冲突、冲突调停、联盟和安全合作网络等传统安全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Xun Pang, Lida Liu and Stephanie Ma, “China’s Network Strategy for Seeking Great Power Statu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 No. 1, 2017; Yiyi Chen, “Why Appoint a Weak Mediator? A Strategic Choice to Reduce Uncertainty i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2, No. 3, 2019;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Once and Future Peacemakers: Continuity of Third-Party Involvement in Civil War Peace Processes,”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8, No. 2, 2021;陈冲、胡竞天:《空间依赖与武装冲突预测》,《国际政治科学》2022 年第2 期;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2 期。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意识到定量研究的边界。庞珣指出,定量方法具有透明度高、可重演性和明确程序化的优势,但不适用于探索规范性理论或寻找历史的真相,因此定量方法的使用必须注意其功能的边界。⑤庞珣:《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1 期。在定量方法普及的同时,传统安全的研究者也意识到,要根据具体研究问题来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
第三,对新研究方法的尝试更加普遍。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探索大数据、机器学习、实验、田野调查等方法在传统安全研究中的应用。①陈冲:《武装冲突与妇女赋权——基于两项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4 期;陈然、于朔:《支持还是反对军事冲突?——日本与邻国争端中民意的调查实验分析》,《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5 期;卢凌宇:《政治学田野调查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1 期;汪段泳、赵裴:《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公民安全风险调查——以刚果(金)为例》,《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5 年第1 辑。董青岭提出用大数据态势感知重塑国际冲突预测的模型与路径,并提出机器学习的冲突预测范式。②董青岭:《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复杂社会的政治分析》,时事出版社2018 年版;董青岭:《大数据安全态势感知与冲突预测》,《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6 期。然而,尽管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研究方法非常前沿,但是不少学者也指出它们在冲突预测等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③刘辰辉、唐世平:《机器学习在冲突预测方面的局限——基于对暴力预警系统的再检验与讨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12 期。
3. 研究队伍不断强化
第一,老中青人才梯队不断优化。过去十年,老一辈学者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不仅进行理论创新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成果,还积极提供学术公共产品、奖掖后学。在此背景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快速成长起来,成为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坚力量。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训练更加专业和科学,并且相当一部分在海外一流名校取得学位。这种学术背景让中青年学者在研究议题上更前沿国际,研究方法更多元科学,从而推动了传统安全研究的发展。④祁怀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北大复旦人大清华国关青年教师的发展现状与思考》,《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3 年第1 辑。
第二,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来,传统安全研究迎来巨大历史机遇。2018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设立国家安全一级学科。2020 年12 月,“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正式设立,传统安全研究的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完善。此外,安全研究专门类教材不断修订、不断推陈出新,例如王帆和卢静主编的《国际安全概论》、李少军和李开盛等撰写的《国际安全新论》以及陈拯编写的《国际安全导论》等。⑤王帆、卢静主编:《国际安全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李少军、李开盛等:《国际安全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陈拯编著:《国际安全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 年版。
第三,学术期刊建设不断进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学术期刊更加重视传统安全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专门开设“国际安全”“安全研究”“国际安全理论”“国家安全学”等栏目,十年间发稿近百篇,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国际安全研究》以“加强战略思维、审视国际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为宗旨,十年间专注于安全研究各类议题,发表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进步。《国际展望》《太平洋学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等期刊的转型与蜕变,以及《国家安全研究》《国家安全论坛》等专注于国家安全的新期刊出现,都为传统安全研究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保障。
(二)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过去十年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在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上仍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在基础理论上的创新能力仍然不强。其一,公允来讲,21世纪以来全球安全研究的大理论创新都趋于停滞,中国也不例外。大理论的“终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冷战期间已经发展出较为完备的大理论,对当前反复出现的一些国际关系事实仍有解释力。然而,大理论发展的停滞并不意味着理论整体的停滞,传统安全研究理论的增长点从宏观理论转向了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①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宋伟:《兴盛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已终结的大理论研究》,《教学与研究》2019 年第10 期。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传统安全研究的新议题带入已有的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如何通过研究中国自身的特殊性重新推动理论创新与发展。同时,值得引起警惕的现象是,老一辈学者致力于理论创新,但是中青年学者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在急剧下降,多聚焦于议题导向的研究。其二,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创新与中国外交实践有着较大差距。中国传统安全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理论与现实“共振”,但这种共振更多是对现实发展对理论研究的单向引导,理论对现实的影响则相对有限,难以满足中国外交的实践需求,也落后于中国政府提出的思想、理论和倡议。其三,传统安全研究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仍然有着较大距离。过去十年,百年大变局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为学术界提供了巨大的学术机遇,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学术界提供了深厚的学术理念,中国的外交实践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素材,但是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并未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成果,对中国立场和中国方案的支撑也远远不够。
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学科发展仍需进一步提升。其一,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传统安全研究横跨政治学、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三个一级学科,在学科建制上更加碎片化。由于各学科缺乏统一的研究议程和研究共识,都试图在传统安全研究中掌握更大话语权,这无疑增加了研究重叠和资源浪费,强化了各学科之间的沟通藩篱,加大了理论创新难度,限制了传统安全研究发展的空间。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内涵是研究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安全问题,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综合性、交叉性核心支撑学科。①《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网站,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这要求中国学者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既要熟悉西方传统安全理论和实践,还要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学理论。同时,中国的传统安全议题的研究者要打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研究在研究取向上的分歧,采取更加综合和多元的视角来审视安全问题,尽快补齐在学术研究和人才上的不足。其二,当前传统安全研究成果量有余而质不足。传统安全研究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深度研究,但过度聚焦热点议题往往伴随着无效、同质化的研究大量产出,这导致研究的泡沫化,其中能够沉淀下来并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成果相对有限。对热点问题追逐,还会导致难以形成长期有效的研究议程,从而使重大理论创新受限。其三,过于依赖西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过去十年,尽管中国传统安全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引介和消化吸收比较系统,但是在理论创新上还没有完全脱离西方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了提高理论创新能力,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致力于构建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四 传统安全研究的发展方向
过去十年,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中国传统安全研究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未来十年将是理论创新的关键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安全研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共振将给理论创新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总体而言,未来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聚焦重大战略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 页。传统安全研究也应遵循这一要求。首先,回答中国崛起带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崛起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学术界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我们需要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走和平道路、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美如何找到正确相处之道等重大课题,从而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其次,深入研究大国竞争和大国冲突问题。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重新回归,大国竞争空前激烈,中美关系也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中美两国如何作出正确历史选择,如何共同有效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这将关系到两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福祉。再次,关注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问题。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塑造了国家的行为模式和互动模式,形成了传统安全研究的“新边疆”。对此,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可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注重对新技术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二)重视中外经验总结
传统安全研究应该重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全实践的经验总结。学术界不仅要对1949 年以来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不结盟政策等重要安全理念进行总结,还要进一步提炼新时代以来中国丰富的安全实践。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复兴处于关键时期,中国的安全实践重要而独特。诸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却遭受美国前所未有的遏制、围堵、打压,中国在安全赤字的世界里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这些社会事实都为传统安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学术界要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安全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美国的传统安全研究和安全实践为其维护霸权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导。然而,当下美国的传统安全研究出现了理论与实际脱节、过度经济理性化和技术化、对历史重视不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有限、过度意识形态化等痼疾。②于铁军:《霸权的护持: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2 年第5 期。可以说,美国传统安全研究曾经的辉煌见证了美国曾经的辉煌,当下美国传统安全研究的困境展示了美国当下的困境。中国学术界应总结美国传统安全研究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走美国的老路。
(三)坚持基础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也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撑。未来中国学者坚持理论创新宜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思想体现,是百年来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不断自我总结、修正、完善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国家安全思想的系统集成。①袁鹏:《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7 期,第2 页。发展中国特色的传统安全理论,必须加强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把握和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研究者从系统思维角度重新认识和分析安全问题,相比西方传统安全理论视角下由威胁或能力所界定的安全,中国学者可以探索以风险界定的综合安全,重新讨论传统安全概念和思维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②代表性的研究参见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7 期;唐士其、庞珣:《综合安全论:风险的反向界定和政治逻辑》,《国际政治研究》2022 年第6 期;祁昊天:《国家安全系统理论刍议》,《国际政治研究》2023 年第1 期。二是重视对中国传统安全思想的研究总结。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为传统安全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智慧源泉。一方面,学术界应继续加强对中国古代安全概念和思想的挖掘,通过中华经典概念和理论弥补西方理论的不足,解构西方的逻辑陷阱;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安全思想文化和历史的总结不能脱离现实问题,需坚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为中国古代议题的研究注入灵魂,而非为了研究而研究。三是积极推进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创新不应该是拿来主义,也不能画地为牢而孤芳自赏,而是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传统安全思想和西方安全理论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与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对话,用西方听得懂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话语阐释中国的思想和理论,发出中国声音。
(四)使用科学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安全研究应该积极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推动传统安全研究成为“有用之学”。一方面,科学研究方法可以提升传统安全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也是保证学术质量、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其一,中国传统安全研究要在学生培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等多个层面夯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使用和推广。其二,以研究方法服务研究问题为根本,超越定量和定性之争,坚持合适有用方法论使用原则。其三,积极使用社会实验、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新研究方法,以推进传统安全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强调实践、重视调查研究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到中国和世界的安全实践中,避免走美国传统安全研究的老路——成了一门“精致而无用”的学问。美国学者迈克尔·德施(Michael C.Desch)指出,当前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对政策的影响减弱,主要原因是研究越来越重视狭义的科学严谨性,忽视了政策相关性,走向了知识上的死胡同和政策上的溃败。①Michael C. Desch, 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8-19.这给中国传统安全研究的启示是,要注重研究大问题和真问题,走出书斋并重视田野调查研究、实地考察、访谈等研究方法的应用,做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问。
结 语
过去十年,中国传统安全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研究水平不断提升,研究方法不断精进,研究队伍不断强化。然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时代背景亟需理论创新,亟需构建传统安全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对于中国传统安全研究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面向未来,中国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高水平的传统安全研究创新成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保驾护航。历史上,英国的战略研究与美国的安全研究为英国和美国的崛起与称霸提供了理论知识上的支撑。现在,这一历史重任交到了中国学者手中。中国学者能否实现理论创新,能否踏踏实实做好“有用之学”,能否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连结起来并提供思想支撑,事关中国国家安全之稳固、大国崛起之成败、人类之和平与发展。未来大国之争不仅仅是国力之争,还是理论创新能力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安全研究的水平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