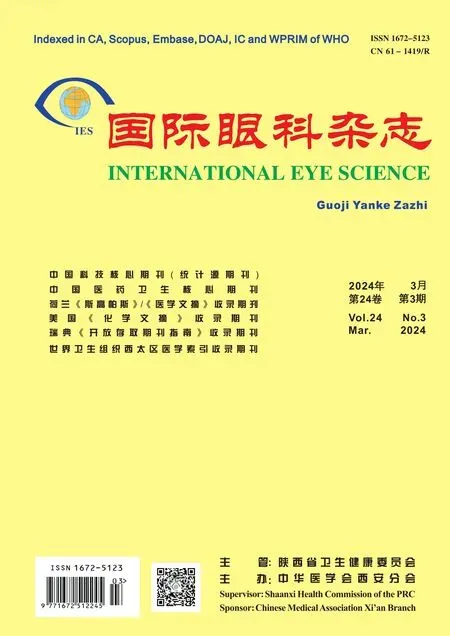近视与调节功能的相关性研究现状
王正静,赵 粟,2,谷 浩,2,蒋 浩,2,龙秋蓉,2,陈芷璿,谢 婧,3
0 引言
近视正在成为全球流行病,特别是东亚地区近视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升,60 a前,10%-20%的中国人近视,但现在,中国的青少年和青年人近视率高达90%。比半个世纪前的发病率高出1倍[1]。有学者指出,中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持续性上升[2-3],在未来可能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4]。近视通常伴随着调节功能的异常,而调节功能异常易导致视疲劳,出现眼胀、眼痛、眼干及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等全身症状,严重者会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并出现焦虑、烦躁及其他官能症状[5],这些症状严重干扰了近视患者的视觉及生活质量,同时调节功能障碍与近视的发生及发展存在一定关系,因此,近视患者的调节功能情况及调节功能与近视的相关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1 近视的机制与病因
当调节处于放松状态时,平行光线经眼球屈光系统后聚焦在视网膜前,这种屈光状态称为近视,通常是眼球的前后轴过长所致,但也可能是由于角膜或(和)晶状体曲率过大造成[6]。在近视病因中,遗传因素对近视起着重要的作用[7-8],而环境风险因素也不容忽视,环境风险因素包括教育、城市化和近距离工作[9-10]。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会引起调节痉挛和睫状肌痉挛,造成“近距离工作的短暂性近视”,而近距离工作的短暂性近视与永久性近视存在一定的联系[11],近视患者的短暂性近视衰退时间比正视者长,这与近视患者睫状肌向前增厚、后部变薄的形态学变化有一定关系[12]。Mountjoy等[13]研究表明教育中暴露的年限越久会导致近视患病率升高,增加教育时间可能会无意中增加近视的患病率,而明亮的室外光线可能会刺激多巴胺的释放,抑制眼睛的生长,户外活动可以减少儿童近视[14]。既往研究指出环境因素可能与基因相互作用而增加近视的风险[9]。关于视网膜对眼睛生长的作用,Flitcroft[15]研究表明中央凹外视网膜与中央凹视网膜在控制眼睛生长方面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最近有研究也指出中央凹外视网膜屈光度与眼的调节功能作为内在因素,近距离的工作环境作为外在因素,两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促使青少年近视进展[16]。
近视通常是眼球的前后轴过长所致,至于什么原因会导致眼轴增长呢?有学者指出调节滞后或调节量不足会导致视网膜上的远视散焦,如长期不干预,时间长了可能会促使眼轴增长,从而刺激儿童期近视的发生[17]。但也有学者从动物实验中得出不同的意见,调节能力不足导致的调节滞后不能引起雏鸡眼睛的生长变化,不会导致近视[18]。上述研究表明,近视和调节能力的关系仍存在争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2 近视眼形态与调节
调节是通过睫状肌的收缩和晶状体的弹性改变共同协同使物体在视网膜清晰成像的过程[19-20]。有研究指出近视患者的睫状肌更厚[21-22],且近视度数越大睫状肌越厚[21],睫状肌增厚会导致其收缩反应较差,从而导致调节反应减少、调节滞后增大[22],调节滞后又会导致视网膜远视离焦[23],如长期不干预会使眼球轴向增长,可以从睫状肌增厚这个角度解释近视儿童的调节功能不足及眼轴增长[17];而晶状体厚度随着调节程度的增加不断增大[24-25],但与远视眼相比,在同等调节程度下,近视眼的晶状体厚度小于远视眼[25],这可能是因为近视眼睫状肌较厚,睫状肌收缩反应较差,悬韧带松弛不够所致。
调节过程会引起眼球轴向伸长,这种轴向的伸长是可以恢复的,但近视患者从调节引起的轴向伸长中恢复所需的时间更长,在长时间的近距离任务后,近视患者比非近视者表现出更大的轴向伸长趋势,调节伴随着脉络膜变薄,有助于轴向长度的变化[26-27];睫状肌收缩的力量减少了眼球赤道部巩膜的周长,并导致眼球的轴向伸长[28],在调节过程中,脉络膜变薄以及赤道部巩膜周长减少是眼球轴向伸长的原因,眼球在调节过程中轴向伸长是否有其他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近视与调节功能
3.1近视与调节滞后调节反应量小于调节刺激量即调节滞后。对于先出现调节滞后还是先出现近视,有专家提出调节滞后时,物像将成像在视网膜之后,为了更好地呈像,眼轴向后适应性增长,形成轴性近视。龚胜等[29]研究发现,无论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在近距离(25 cm)的调节滞后量均大于正视者,提示近视患者的调节滞后量大于正视者,但该研究是基于横断面的研究,难以说明调节滞后与近视的因果关系。Mutti等[30]研究发现调节滞后增加发生在近视发病1 a或更长时间之后,而不是在近视发生之前或期间,该研究还发现正视儿童和近视儿童的调节滞后差异仅在近视发生后出现,故认为调节滞后量增加可能是近视的结果。但Gwiazda等[31]通过在近视发生之前增加调节滞后量,发现调节滞后会产生远视视网膜散焦从而导致近视[32],认为调节滞后是近视的原因。分析由于实验方法不同导致上述研究结论不同。
关于进展性近视调节滞后量的研究中,Koomson等[33]将150例加纳近视学龄儿童随机分为配镜完全矫正组和不完全矫正组,发现两组儿童初始调节滞后的平均值与24 mo后测得的平均调节滞后值无显著差异,且近视的变化量与两组戴镜前后的调节滞后量也没有显著关系,故认为在进展性近视儿童中,调节滞后与近视进展速度之间没有关系。此外,Lan等[34]对轻度和进展性近视儿童进行了为期1 a的纵向研究,重复测量屈光度数和眼部一般生物学参数(眼轴长度、玻璃体腔深度)并进行分析,发现调节滞后量与近视进展之间没有明显相关性,推测调节滞后与近视进展无关[35],Lan等[34]认为通过减少近视滞后量阻止近视进展没有临床意义。近年研究发现,在负透镜引导的高度调节需求下,成人进展性近视的调节滞后量大于正视者和稳定性近视患者[36],同样也发现,发展性近视儿童的调节调节滞后量高于正视儿童[37]。李静姣等[38]对7-12岁进展性近视儿童随访观察1 a发现,近视增长较快者的调节滞后量较高,且近视度数增长越快调节滞后量越大,表明调节滞后可能是近视发展的重要因素。Koomson等[33]研究结果可能与种族、依从性等有关,而Lan等[34]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研究时间较短或调节滞后量不够大,不足以表现出眼生物学的变化。
3.2近视与调节幅度调节幅度指调节远点和调节近点之间的距离,以屈光度的形式表示,主要反映睫状肌收缩、晶状体变凸等眼部结构的最大变化程度。Fong[39]对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696例1 148眼进行调节幅度的测量,发现近视患者的调节幅度较低,调节幅度较低的眼睛在近距离工作时使用更多的调节储备,推测近视可能是眼睛调节幅度降低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适应现象。然而,有研究将青年受试者分为正视组与近视组进行调节幅度的测试,再将近视组分为低、中、高度近视测量调节幅度,发现近视组的调节幅度大于正视组,且高度近视患者的调节幅度最大,其次是中度近视、低度近视患者,推测随着近视度数的增加,调节幅度值越大,即调节幅度与近视程度呈正相关,并认为高调节幅度可能是引发近视的原因之一[40-42]。Fong[39]研究中未提及调节幅度的测量方法,可能是测量方法不同及受试者存在基础疾病的原因,导致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
关于儿童进展性近视的研究中,陈云云等[43]随访21例进展性近视儿童,发现在儿童近视进展过程中,调节功能保持相对稳定,推测调节幅度与近视进展无相关性。既往研究表明,20岁之前调节幅度保持相对稳定,20-50岁下降速度最快[44],调节幅度随年龄增长而下降[45-46],分析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晶状体的弹性减退以及睫状肌功能减退,从而导致调节幅度下降,而青年人和儿童的晶状体弹性及睫状肌功能尚可,调节幅度可保持相对稳定,且进展性近视多见于儿童和青少年。
3.3近视与调节灵敏度调节灵敏度是指在两个不同水平的调节刺激下所做出调节的反应速度,反映了眼睛控制调节状态(松弛-紧张-松弛)的能力。Allen等[47]研究指出调节灵敏度是区分是否为稳定型近视的一个关键调节参数,同时调节灵敏度降低与近视进展的加快有关,并提出调节灵敏度可以独立预测近视进展。李静姣等[38]发现近视进展较快的儿童双眼调节灵敏度较近视进展较慢的儿童差,近视度数增长越快调节灵敏度越差,但单眼调节灵敏度无明显差异。Chen等[35]研究在远距离(3.3 m)下,每间隔6 mo以上对近视儿童进行单眼调节灵敏度测试,发现近视进展与单眼调节幅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推测单眼调节灵敏度与近视进展无明显关系,而双眼调节灵敏度与近视进展速度存在负相关,说明可能是双眼调节和集合功能的紊乱导致近视的发展。
与正视者相比,近视患者在远距离下测得的单眼调节灵敏度明显较低,但在近距离下测得的单眼调节灵敏度无明显差异[48-49],单眼远近距离调节灵敏度的不同结果可能是由于近视患者对远处模糊物像不敏感,不能造成有效的调节刺激[50],以致于调节灵敏度下降。陈云云等[37]研究发现,进展性近视儿童的单眼远距离(4.5 m)调节灵敏度与正视眼无差异,该研究采用的是手动翻转翻转拍测量方法,而多数研究采用半自动或全自动测量方式,不同测量方法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同,且既往研究认为调节灵敏度的手动测量与全自动测量结果存在一定差异[51]。
4 近视与AC/A
产生调节的同时会引起双眼的集合,调节越大,集合越大,调节和集合是一个联动过程,两者存在协同关系。注视有限距离目标时,伴随调节出现的集合成分,即为调节性集合。调节性集合与每单位调节的比值,称为反应比值(AC/A比值),反映了调节与集合之间的关系,近视会因调节集合功能紊乱而导致AC/A比值异常。Mutti等[52]研究发现,与正视儿童相比,近视儿童AC/A比值偏高,高AC/A比值增加反映了晶状体和睫状肌的状态异常,且AC/A比值在近视发生前就已经升高,近视发病当年达高峰,发病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因此可以预测近视的发生。Zhou等[53]将8-18岁轻度和中度近视儿童青少年分为两组,一组进行为期6 mo以上的框架眼镜矫正,一组未进行矫正,发现未矫正组AC/A比值高于矫正组,且AC/A比值随着未矫正近视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近视发展越快的儿童AC/A比值越高,提示眼调节功能与调节集合可能出现了紊乱[38],当调节功能不足时,优先动用调节集合功能,以确保近目标在视网膜黄斑区成像;AC/A比值异常与调节滞后存在一定关系,影响近视的发展,同时可以预测近视的发生,AC/A比值异常是近视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
5 总结与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教育的普及,近视患病率逐年升高,但近视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在既往研究中遗传是近视发生的公认因素[7-8],另有研究指出环境因素可能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而增加近视发生的风险[9]。但针对近视患病率增加的原因,最近有研究发现遗传因素不能作为千禧一代(1982-2000年出生者)近视患病率增加的主要原因,反而与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很大,表型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遗传进化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由此可以推测近视患病率增加似乎与环境因素有关[54],现在多以近距离工作为主,眼持续处于调节紧张状态,眼内、外肌对眼产生的压力使眼轴增长,导致近视的发生发展。
目前关于调节功能障碍与近视的相关性存在一定的争议,针对近视与调节滞后的相关性,由于研究方法及人群的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有研究表明调节滞后会导致近视的发生[17],也有研究发现调节滞后不会导致近视的发生[18],对于近视进展的影响方面也尚无明确定论[55]。针对近视与调节幅度的相关性,有研究指出近视患者视近物时具有较强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有着高调节,而视远物时需要动用一部分的放松调节,以至于近视患者的调节幅度偏高[41],多数研究表明调节幅度与近视度数具有相关性[40-42],但与近视进展无相关性,调节幅度与年龄显著相关,随着年龄的增加调节幅度减小[45-46]。针对近视与调节灵敏度的相关性,由于近视患者对模糊的图像不敏感,不能有效动用调节功能,并且近视患者容易产生视疲劳,不易调节放松,调节灵敏度降低,在远距离下测得的调节灵敏度明显较正视者低,而在近距离下测得的调节灵敏度无明显差异[48-50]。针对近视与AC/A比值的相关性,有研究指出近视患者AC/A比值较正视者高,近视调节能力降低和调节集合量增大,以致调节集合功能紊乱导致AC/A比值异常,调节功能与集合功能的紊乱导致近视进展[38,53]。
如何抑制眼睛轴向过度增长及如何干预近视的发展一直是眼科医生及科研工作者面临的难题,目前针对近视的矫正手段有激光手术、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等,光学矫正包括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等。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是视力恢复迅速、高效的近视矫治方法,术后部分患者的调节功能后期可以进一步改善[56-57]。调节过程会引起眼轴增长,若长期处于调节紧张状态,可能会导致近视进展,尤其是近视患者,视疲劳严重,近视进展快,理论上对近视患者进行调节放松,减少自身动用的调节,可以减缓因过度调节引起的近视进展。对近视儿童进行针对性的调节功能训练和用眼干预措施,可改善调节功能,缓解视疲劳,减缓近视进展,恢复双眼视觉功能[58-59],防止近视度数的加深和高度近视的发生,降低一系列病理性近视并发症的发病率。调节功能训练是否可以完善成一种治疗手段?调节功能障碍与成人的近视进展是否存在一定关系?成年近视患者进行调节功能训练是否同样可以减缓近视的进展?调节功能与近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而研究近视眼的调节功能有助于了解近视的发生、发展过程及机制,为近视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