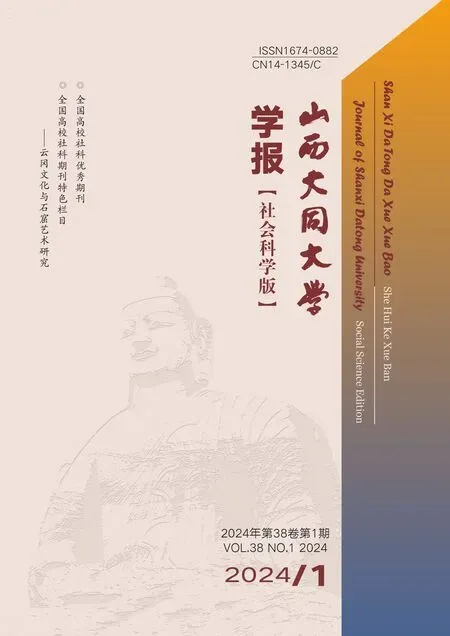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陈千里
(鞍山师范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5)
20 世纪初,符号学家索绪尔和皮尔士分别提出自己的符号学基础思想,现代符号学由此诞生。然而两位符号学大师的研究模式和系统却是截然不同的。初期由于当时结构主义的繁荣,索绪尔的符号体系更为显赫。然而,随着20 世纪70-80 年代结构主义的崛起,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在后续的结构主义框架下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逐步取代了索绪尔的模型,成为了现代符号学的基础核心。
一、中国符号学溯源
中国关于符号研究可追溯回先秦时代,[1]早在2500 年前的先秦时期,公孙龙就在《名实论中》提出了“物、实、位、正”等概念,强调作为符号的名与指称对象的一一对应关系,荀子的“正名论”则深入探讨了“名”与“实”之间的联系。在《易经》中,“易卦”则展现了符号化的特点。战国时期尹文子的符号决定论和符号功能说、先秦惠子的历物论、春秋思想家邓析的辩论、老庄的无名无为、墨家的逻辑学以及北宋文学家谢绛的“指”解释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此外,在《礼记·大学》《尔雅·释言》《广雅·释言》以及先秦诸子的名言中,都有关于符号相关议题的深入探讨。
胡以鲁先生于1912年编写的《国语学草创》是中国近代对符号研究的起点。[2]在这篇文章中,他深入探讨了关于语言符号的观点、符号的任意性以及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等相关的语言符号议题;在1923 年,乐嗣炳先生发布了一本名为《语言学大意》的书籍,其中阐述了语言结构是由“内在的意义和外在的符号”组成的,这与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学的观点有着极高的相似性;中国近现代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赵元任先生,在1926 年发表的《符号学大纲》一文中,不仅提出了建立普通符号学的必要性,还系统地构建了符号学研究的框架。赵元任先生对于普通符号学的核心观念和结构的阐述,实际上比皮尔士先生早了好几年。赵元任在1968年的著作《语言和符号系统》中,再一次对自己的符号学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拓展,并将这些观点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汉语的符号和信号通信领域。到1973年为止,赵元任撰写了一篇名为《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的文章,其中主要探讨了汉语中符号学的各种理论和实际应用。虽然赵元任在符号学领域的研究相对于语言学和哲学来说,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但他的符号学研究探索是独立于索绪尔、皮尔士等西方符号学的先驱的。实际上,他对汉语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符号学”最初的话语源头。[3]
二、现代中国符号学研究发展历程
我国符号学成规模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研究起点高,[4]善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中国学术界,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宽松氛围中,从一起步就尽情地吸收、消化和利用外国符号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中极为丰富的符号内含和博大精深的符号诠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迄今为止,在符号学的多个研究领域,我国研究已经紧跟国际研究的发展趋势,回望过去,总结得失,在未来的道路上稳步健康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回顾我国符号学五十余年的研究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大致划分成三个主要的阶段[5]:
(一)起步阶段(1981—1986):“西方学派”主导时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人几乎无人系统地研究符号学,符号学的名称也只是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文学和哲学的翻译文献中。[6]1981 年,李幼蒸撰写了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符号学的文章——《关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辨析》。自1982 年起,他曾多次访问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知名高等学府,与各国符号学研究学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982 年,施拉姆访华,曾带来一部由其弟子余也鲁译述的著作《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1983 年,金克木在《读书》杂志的第5 期发表了题为《谈符号学》的文章,在其中,他首次采用了印象主义的漫谈手法,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该学科进行了深入的解读。[7]在1985年,高名凯完成了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翻译工作,而张晓云则翻译了池上嘉彦的《符号学入门》。在符号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为了更深入了解到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及进展,我国符号学学者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参加各项国际符号学学术会议。他们详细介绍并评论了西方符号学家们提出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包括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皮尔士的三位一体符号观和符号分类思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艾柯的符号代码理论和生产力论,以及洛特曼的符号双模式系统和符号域思想。这些研究工作为中国符号学后续的进步奠定了关键的基石。
(二)平稳发展阶段(1987—1993):中西方学派融合时期 这个阶段我国符号学界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继续学习、引介和评述西方符号学的研究成果,除了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外,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艾柯的符号代码理论和生产力论、洛特曼的符号双模式系统与符号域思想也逐步被引入。1988 年,李幼蒸先生翻译并出版了法国巴尔特的著作《符号学原理》,而徐恒醇先生作为一名高级访问学者,前往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进行学术研修。在返回国内之后,他在1992年完成了《广义符号学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这本书的编译工作,并在其中向国内的符号学研究者展示了以美学家本泽为首的德国斯图加特符号学派的核心理念。
第二,开始探索中国文化和西方符号学结合的研究模式,并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挖掘出来。在这个阶段一批试图形成中国学者自己的“符号”见解体系的论文和专著频频发表,《从八卦符号系统看〈易经〉的思维模式》(1988)、《传统文化典籍的符号学特征与典籍阐释》(1993)、《六经注我:经学的解释学转向》(1993),这些论文都尝试用全新的视域——符号学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并尝试通过符号学的观点对其进行新的阐释。
在这个阶段,我国不少符号学研究人员开始为了建立中国符号学体系而努力,如肖峰的《试论以符号为直线起点的认识》(《哲学研究》1988 年第6 期),章仕荣的《符号的理解和解释》(《哲学动态》1989 年第8期),都属这种努力的范围。
第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8 年1 月成功地组织了第一次符号学专题研讨会,邀请京津地区符号学及相关领域的一些学者专家参加。会后中国哲学研究会和中国逻辑学会分别成立符号学研究组织。这场会议意味着我国的学术领域已经正式步入了符号学的研究和组织时期。
(三)全面展开阶段(1994 年至今):“中国化”符号学体系建立时期 1994 年后,符号学的研究进程显著提升,展开了全面的探索。符号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在各个学科领域得到广泛展开。表现为:
第一,除了深入研究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理论继续进行之外,研究者们还重视探索和研究在其他领域符号学理论的延伸,如传播符号学、翻译符号学、广告符号学、社会符号学和艺术符号学等。
李幼蒸编写的《理论符号学导论》的目的是为了突破西方符号学的传统思维,全方位地展示符号学在全球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此项研究在广泛的领域内为我国的符号学体系带来了飞速的进步。2004年,黄新华和陈宗明联合主编了由我国符号学界的八位著名学者共同完成的《符号学导论》。在这本书中,他们试图将索绪尔和皮尔士这两位现代符号学的主要创始人的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符号学学科。到了2011 年,丁尔苏教授在他的新世纪符号学论文集《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对迪利的现代符号学领域进行了修订,将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排除在外,从而推动了符号学在国内的进一步研究。同年,赵毅衡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基于对各种学说的综合总结,其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强调符号接收与文化约束功能的符号学研究体系。这本书主要研究了符号在接收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是如何限制符号的。
在我国,语言学一直是符号学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中国学者取得最多成果的领域。[8]2005 年,教育部指定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为研究生用书,同时期,丁尔苏的《语言的符号性》(2000),介绍索绪尔理论的消极影响、寻找新的符号模式、建立以词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2000)和《现代语言符号学》(2013),对西方符号学大师的语言符号学思想进行详细阐释的同时,还对语言符号学的众多核心要素进行集中的探讨,提升了语言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林信华出版了《社会符号学》,通过西方对符号系统的理解,尝试观察中国符号系统的特征,并由此延伸东西方在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差异,冯钢于的著作《艺术符号学》从更深刻的层次、更前瞻性的视域出发,对当代符号学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整理。该书拓展了艺术符号学的内涵表达和外延展,突破了传统的文化视野限制,将艺术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在最近的几年中,四川大学出版社连续推出了多部关于中国符号学的系列书籍,其中包括《广义叙述学》《社会文化符号学》《先秦符号思想研究》《电影符号学》《图像符号学》《广告符号学》《新闻符号学》《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武侠文化符号学》以及《20 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等。这系列丛书为国内的学术领域呈现了我国符号学领域近些年在多个方向上的深入研究成果。
第二,把符号学理论大众化,为国人普遍了解和应用,也一直是我国符号学界的学者们努力不懈奋斗的目标之一。1988 年12 月,李先焜与陈宗明开始在期刊《思维与智慧》上连载《符号学通俗讲座》,1992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王红旗的《生活中的神秘符号》,使大众初步认识到符号学可以与广泛的日常生活相联系。李伯聪老师2000年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高科技时代的符号世界》把我们周围如火如荼的数字革命和符号学联系起来,帮助大众理解符号学的深刻内涵。陈丽卿在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职场仪礼:你的成功符号学》一书中对大众很有启发:符号学其实就在身边。2015 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毅衡《趣味符号学》,这是中国第一本面向没有符号学知识读者的符号学普及读物,2019春季四川大学首次以慕课的形式把《意义生活:符号学导论》送上了网络,让更多人体会到符号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中,也渗透到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只是我们一直不自觉而已。慕课形式也为更多的大学生、社会人员了解和学习符号学提供了方便有效的平台。
第三,通过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献中的符号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尝试用符号学理论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李光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分析汉语文字学中的符号学和儒家正学说中的符号学角原理,发表了《中国——一个具有丰富的符号学传统的国家》的论文,1990 年代中期,由苟志效、沈永有、袁铎共同编著的《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纲要》,是第一本尝试从符号学的视角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分析解读的编著。祝东从1980年代起,就着手中国古代符号的研究,数十年来,坚持不懈,从中国古代易学、诸子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唐宋佛学以及阳明心学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挖掘其表意机制与伦理思想,终于在2021年完成了在他的专著《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符号学思想史传统,为促进中国符号学发展、中外学术思想对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5 年,龚鹏程在他的作品《文化符号学导论》中,将中国的哲学、文学、语言学和史学中的专业术语与中国文化的理念相结合。他还参考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符号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介绍。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文化符号学》中,他将文化视为一种生成性的符号叠加过程。在叶舒宪及其团队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这本书中,他们融合了文化符号学的多重编码理论和文化文本的时序与共时性特点,将文化解读为一种创造性的符号叠加过程。上面提到的研究成果仅仅是对中国符号学思想的部分展示,我们在未来应该更加积极地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并努力将这些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
民俗学与符号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高乐田、邓长青从民俗符号的形态、意义、应用分析入手,把民俗现象看作符号现象,将符号学方法引入民俗学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9]白丽梅提出了用符号学方法揭示鲜活生动的民俗现象所固有的结构原则,[10]乌丙安以民俗符号的构成为出发点,关注言语系统和非言语系统中的民俗符号的两个重要视角。[11]他结构性地分析了与听觉,视觉等感觉系统相关的声音、特色装饰、神话形象、民族服饰、民俗图腾、色彩及实物象征的所指与含义,并初步建构起当代民俗符号学底层框架。刘东霞以山西民间布艺为例,从符号学的视角,挖掘民间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为民间艺术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12]总之,民俗学与符号学研究相结合成就斐然,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困境与展望
五十年过去了,中国符号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具体表现在:
第一,论著只在博士论文中见到的多,年轻的学者为评职称或迎合单位的评估,只撰写论文,而放弃专著的论述。
第二,国外有符号学专业刊物40余家,我国只有四家,国内符号学的专业刊物太少,大部分符号学的交流活动,不得不集中到网络上。
第三,文化研究被视为符号学的主要应用领域,但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固定学科体系中,符号学常常面临着没有明确归属的窘境。在诸如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比较文学、外语翻译以及广告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有限。
第四,中国符号学界盲目跟从,做西方学术“批判的表演者”。
第五,近些年来,符号学成为了多个学科讨论的焦点,与之相关的学术文章数量之多犹如海洋。尽管如此,至今关于符号学的确切定义、研究领域、研究手段以及学科的界限仍然存在争议,尚未达成共识。
相对来说可喜的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高度符号化,目前,许多研究中国符号学的学者不仅认识到“中国符号学”作为一个独立且普遍的符号学体系的重要性,而且还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化发展,促进中西社会人文学术传统的有效交流,从而稳步推进中国符号学的建设。纵观国内外符号学发展历史,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有中国风格的符号学新派,一个带动世界文化健康发展的符号大国,一定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