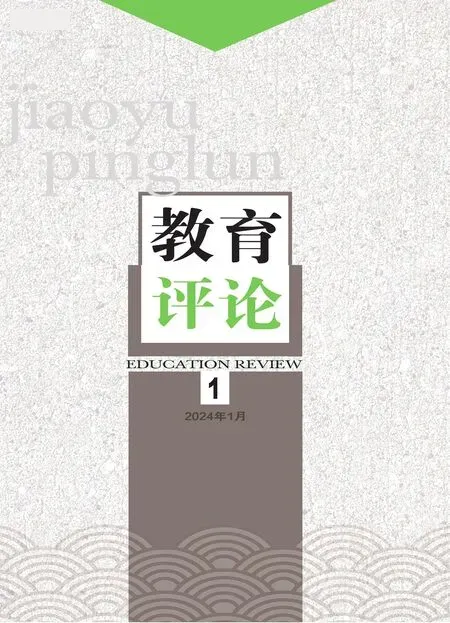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及当代启示
●黄传球
“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原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开展的各类思想政治工作的总称,源自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自觉。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正式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后,“思想政治教育”指代的是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同民族和国家共有的一种教育现象。这种教育现象指“人类社会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所开展的思想教育活动,或者是以思想教育的形式所实现的政治”[1]。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称谓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称谓的不同并不能否认其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利益与意志的重要手段,其核心价值指向培养服从帝王统治并能为帝王统治服务的人。围绕这一教育目标,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均提出了极富操作性和吸引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这也成为各个历史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主要构成要素,形成一定的结构关系。若以历史整体的视域视之,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虽然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稳定性特征,但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在政权更迭、经济发展、社会形态演变、思想观念转化等动因之下发生一定结构变迁。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历史的整体性回溯,探寻其发生变迁的动力之源,进而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合理建构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与基本遵循。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历史回溯
按照社会形态以及历代王朝之间的承继关系,可以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先秦、秦汉、隋唐、魏晋南北朝、宋元以及明清(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等六个历史时段。每一时段(也可将之理解为某种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成要素不尽相同,根据要素内蕴的属性可以将它们归纳为观念(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知识(主要指儒家经学)以及规范性内容(主要指封建礼教和封建纲常)等三种不同的类型。在具体实践环节中,出于统治者施行统治的实际需要,观念、知识以及规范性内容在不同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的地位会有所不同。因此,根据观念、知识以及规范性内容要素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的层次地位和主次关系,可以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观念性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内容的历史时段
观念性内容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础构成,也是历代王朝建政之初尤为重视和优先开展的教育内容之一。就观念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具体构成要素而言,其主要蕴涵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两个方面,普遍存在并贯穿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段。尤其是在先秦时期,鉴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客观限制,观念性内容成为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主导内容,这也成为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最鲜明的结构特征之一。
在实践操作层面,观念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通过阐释“天人关系”来规范和约束世俗世界中的“人人关系”,以实现“倚天治人”的教育目的。鉴于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天性局限,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交往实践方式始终处于较为原始落后的状态,在人类无法克服的各类自然灾害和疾病面前,神灵护佑和封建迷信成为人们意识领域最重要的精神图腾和心灵寄托。正因为这样,夏、商与西周统治者无不将“天人关系”“宗教教义”作为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构成要素,甚至于假借“天神”“鬼灵”之名来论证和维护自身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期实现对世俗社会的有效治理。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认知水平和社会交往能力均得到较大的发展。这也造成春秋、战国时期之后,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盛世。先人们对外部世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观念性认知逐渐升华为知识化、系统化的理论知识。系统化理论知识的产生,尤其是各家《经典》的渐次出现,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知识性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内容的历史时段
知识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成和发展于先秦后期,以儒家经典文献的出现为重要标志。知识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经典文献作为蓝本依托,并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为主要传播载体不断推动和实现伦理政治化或政治伦理化的教育目标,最终推动政治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历经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之后,中国古代社会亟待恢复相对稳定的社会运行状态,这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全新的发展要求。就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成要素而言,法家之刑法思想、道家之黄老思想,均短暂出现于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之中。但伴随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儒家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优越性作用逐渐突显出来,并逐渐成为封建王朝维护社会稳定与自身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待到汉武王朝时期,更是通过“罢黜百家”使儒家思想彻底形化为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思想内容,并一直延续至我国之后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段。
秦汉之后,隋唐两朝逐步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之巅,经学教育内容更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牢牢占据了主导性地位。总体而言,以知识性内容为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出现,同当时封建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们交往方式、范围的不断拓展,法家的“无情”、道家的“无为”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协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利益关系时既显单一更显无效。之于先秦儒家而言,其是在充分汲取天人观念和礼仪教育等合理内核基础之上而生发形成,将“有情”“有为”作为思想的真谛所在,自觉承担起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社会发展的双重使命。所谓“有情”要求统治者广施“仁政”,顺天安民;“有为”要求被统治阶级主动接受儒家经学思想教育,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觉承担起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君主统治的主体使命。发展至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终于在儒家“顺天承命、经学致用”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价值与行动上的双向统一,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基本实现了与国家教育的天然合体。但是,伴随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衰落以及王朝专制统治力的渐进性削弱,知识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无法独自肩负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使命。正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社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决定力量”[2]。在封建社会式微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必然会产生新的变迁。
(三)规范性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内容的历史时段
规范性内容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体系中主要是通过阐释天理与私欲之间的关系,亦即主体心、行之间的关系,规范和引导世俗世界中人人(君臣、君民、臣民等)之间的关系,其核心价值主张是尊天理以灭人欲。从中国封建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看,在进入宋元以后,其整体呈现出式微和持续衰落的发展趋势,封建专制统治面临的挑战和所需应对的危机日益增多,传统观念和知识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已无法满足封建统治的切实需要,宋明理学作为此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新产物便应运而生。总体观之,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最为精致、完备的儒学理论体系,对后期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至深至巨。理学作为传统道德神学的承继与发展,在宋元之后逐渐演化成为论证封建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依循。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其以儒家学说作为内容中心,兼容并蓄佛、道两家的理论精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存在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并逐步将之演变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理学的纲常教育思想亦顺其自然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成为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最高准则。虽然这一时期依然存有经学教育,但其教育内容与先秦时期相比也发生了较大的改观,历经宋、明儒学达人的全新阐释,其已彻底沦为封建纲常教育的载体和辅助工具,丧失了原先应有的知识价值属性。规范性内容占主导性地位的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出现,不仅是统治阶级试图通过硬性行为规范来实现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客观反映,也是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衰落与式微的重要印证。
上文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整体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只是一种概略性的宏观历史描绘,仅仅是按照观念、知识以及规范性内容在不同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层次中的地位和主次关系而进行的区划与归类。虽然在某一时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会与其整体历史发展趋势产生冲突与背离,但在新朝统治逐渐稳定后,这一矛盾便会得到消解而重回正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均是由多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观念、知识、规范均蕴含其中,而其结构的变化更多源自于不同要素层次和地位的改变,并非非此即彼式的全面取代,结构调整和变迁的目的是突显其某种功能,以便更好地适应和维护特定时期统治阶级施行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的动因探源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历史变迁是一个多因素相互交织、彼此作用的复杂过程,也存在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耦合的内在逻辑。但是,无论原因为何,政权更迭、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转变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发生变迁的主要动力之源。
(一)政权更迭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
马克思将政治视为是阶级社会的特殊产物,是由阶级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是以政权为核心的阶级关系和人民内部关系的反映。回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演变之路,政权的更迭(或曰王朝的替代)均是其无法回避的动因之一,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内蕴政治属性的客观使然。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国家(或者是朝代)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均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属性,正所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无论先秦时期的夏、商与周,还是先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概览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主要要素构成,无不印刻着浓郁的阶级烙印。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4]鉴于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呈现出来的依附性以及工具性特征,政权更迭更是成为其内容结构演变的最重要外部动因之一。即使是先秦后,在儒家思想占据绝对思想统领的封建历史时代,政权更替也往往会催生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仅改变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还使之相继在观念、知识与规范性内容主导的结构之间发生转换。
(二)经济发展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
经济发展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在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自然的维度来看。伴随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逐渐脱离原始、愚昧的窠臼,其理论性、系统性和知识性逐步提升。如,先秦以前,统治阶级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会假借天神的名义阐释和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无论是夏朝统治者对“家天下”正当性、合理性的宣扬,还是商、周两朝对自身统治权合法性的论证皆是如此。秦汉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社会和自身的认知更加全面。因此,传统具有浓郁宗教性质的、以观念性内容为主要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以知识性内容为主要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随之也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迁,这成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从社会的维度来看。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催生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无论是奴隶制经济形态的产生,还是后来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出现,每一个获取统治权的阶级总会在各自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大力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观念。因而,儒家思想之所以能牢牢占据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引领的地位,概因先秦儒家的思想主张及后代学者的不断改良,顺应了封建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二者相互因应,融于一体。
(三)社会形态转型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
社会形态变化是一项宏大的社会课题,不仅表现为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也隐含着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在某些特殊时期发生的阶段性量变。就传统中国社会而言,其曾历经两次较为明显的社会形态变化过程。其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在历史上大致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秦王朝的建立宣告社会形态转换的最终完成。其二,发生于清朝晚期,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性事件,中国由传统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第一次社会形态的转变,揭开了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帷幕;第二次社会形态的转变促使中国与封建社会形态渐行渐远,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孜孜努力之下,成功穿越“拉夫丁峡谷”,顺利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之路。对存续于阶级社会各个历史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然会伴随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变化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5]这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主流文化转变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6]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不难看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内容深受该统治阶级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即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主流文化一旦发生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结构也必然发生变迁。如,在汉朝建立之初,承秦制而建的汉王朝,在主流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主要遵循和崇尚道家学派的“无为”思想,其宣扬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主张也深受道家学派的影响。但是,为了顺应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至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之下,更加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儒家思想成功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并形化为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并一直延续至清朝晚期,虽然也曾在宋明时期受到理学和心学发展的冲击,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改变。由此观之,主流文化转变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带来的影响更为持久和深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警醒我们,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只有找到继承与发展的黄金节点,才能持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优化、发展。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的当代启示
探究和梳理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的历史变迁,其目的既是为了找寻内含于古代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之间的通约性所在,也是为了通过积极反思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向好发展。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研究具有如下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坚持时代性发展
“一切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7]一种理论要想在一个国家受到广泛的接受,必然需要在最大限度上满足这个国家的时代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需要主动适应其他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运行方式,还要在适应中主动超越积极作为,成为社会思想的引领力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伴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的时代适应性趋向。就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面对的最大时代课题,就是如何积极回应新时代对社会发展新目标的设定以及如何解决新矛盾,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时代呼唤。思想政治教育在建构内容体系时决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这一时代选项,否则思想政治教育便会脱离时代发展的土壤而彻底沦为空泛之想。因此,在合理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性内容、主导性内容与发展性内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紧密结合新时代的时代蕴涵,推进和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时代性发展,以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是一个科学的实践过程,要坚持科学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建立以来,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其科学性的探讨从未间断。总结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基本理论体系层面,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知识性、系统性、真理性、学术性方面仍处于建构阶段,提升空间巨大;二是在实践应用层面,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多以经验操作为主,对规律的积淀和提纳深度不够,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与预期差距较大。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源于其本身的科学化水平。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是一个系统过程,既要有科学的理论基础、方式方法与制度设计,更要有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成,只有内容科学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列宁曾经指出:“如果认为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内容是真实的。”[8]由此可见,科学的本质既是对真理的孜孜以求和对客观事实的严格遵循,也是对人类先进知识和文明成果的承继学习与积极吸纳。因此,要“严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的科学性原则,协同推进科学的理论基础、科学知识支撑、以及科学的组织实施”[9],进而全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建构的科学化水平。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整体性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10]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整体性特征指内容体系中各组成部分之间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作为其他部分的联系而存在。观念与知识之间、观念与行为规范之间、知识与行为规范之间均存在内在的关联,使结构内部的构成要素在相互联结和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在分析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时一定要拥有整体性的视野,只有形成整体性的认知,才能更好地阐释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形成最大的教育合力和最理想的实际效果。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理清基础性内容、主导性内容和外围性内容的要素构成,更要将三者视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整体构成,针对不同的教育群体和教育对象要做到有的放矢,分类推进,这样才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整体性发展。
(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当中。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主要内容也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趋向,甚至于出现碎片化的演化风险。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中永葆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心”与“使命”,显然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无法绕开的一个现实课题。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会遭受多重因素的制约,但归根结底离不开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精神的坚守。正如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精神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核和灵魂,既是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基础性、普遍性以及稳定性精神特质的深层认知,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实运行的基本逻辑遵循。”[11]因此,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过程中需要始终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具体言之,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建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服务精神,既要服务于人的精神成长的主观需求,更要服务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精神充分体现了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内在统一,其内容体系的建构是个体与国家、社会需要之间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不可偏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守好基本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才能不偏不倚,才能有效兼顾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利益,才能在实践当中找准自身的社会定位,才能肩负起应有的教育使命,才能真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发展。
综上而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探究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变迁的价值旨趣意在以古鉴今,在承继、批判和古今对照中探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其系统建构的科学化理路,以期更好地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