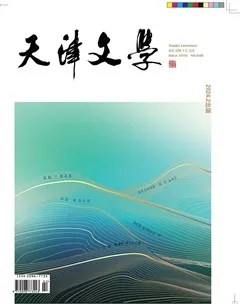春风有信
梅花消息
下了车,沿着小径走一段路,又循溪流,一路听春鸟枝上轻啼,溪水哗然。日光照在树上,散在发梢上,又洒落溪水上,蹦蹦跳跳的。
早年来过梅花沟,零星散落些人家。屋外一片空地,捆扎好的木柴堆放墙角,山里人家日脚闲在,早起扫尘,生火做饭,再劳作一整天,月上东山时枕风而眠。
说是梅花沟,其实更像梅园、梅林。清早,人从屋内推门出来,抬眼到处是梅树,漫山清白,一树一树自远而近,真是看不过来。一些长势好的枝桠直攀屋顶,花瓣就搭在滴水檐上,人伏在窗格里,便闻得到一缕一缕的冷香。若有一阵风过更有意思,花枝频频招手,花瓣微微点头,像好客的主人。花容风意,山岚设色,别有一番趣味。人在花间独立,恍惚也是一株青衫客。造物有意,苒苒物华,让人惊叹之余又莫名生惆怅。
少年时总幻想有一座大观园那样的院子,园子里曲径旁遍植各色梅树,待到梅花香消玉殒,凋零萎落,我们几个怀春少女,就像黛玉一样,肩扛花锄,提着香囊,忧忧戚戚的,也来一场月下葬花,祭奠我们悄然流逝的青春。然而我们毕竟没有那样的院子,我少年时生活的黑土地也不见一树树清雅之物。
有时很不服气,梅花是寒客,我故乡是全国最寒冷之地,梅花为何不肯落脚呢,唯一可解的是,这黑土地太粗糙,养不得高标清香之物。
我第一次见到梅花,是在一本画册上,那时,父亲有几位爱丹青的好友,常聚在一起。有一次他从朋友处回来,夹着一本略有些残破的薄薄画册。翻开就见一树树繁密的枝丫梅朵,占满整个画页,扑人脸面,也许当时并未被梅花吸引,觉得梅花总该是疏疏落落冷冷清清的,那样的繁枝,让人觉得他画错了。多年后回想起来,那大约是金农梅花,一树繁花颠倒开。金农表面是热切的,也曾进京求取功名,然而骨子里,却是一副冷落的孤傲,最终不肯折腰向人,仰他人鼻息,甘心以布衣雄世。是以他的梅花,虽繁花如簇,底下却是金石般的清冷傲骨,冷冷落落,像一个久居深山的绝粒人。
我真正爱上梅花是来京后。那时居所靠近翠微山下永定河畔,依山临水,地气自然是好的,春天站在楼上,推窗可见一山野桃,白白粉粉,活色招摇,庆幸自己选对了居所。顺山路西行,可至八大处、植物园、卧佛寺、樱桃沟,第一次见到绿萼梅就在卧佛寺外。
那时,刚走出象牙塔,尚留一身书生意气,对于人世间的蝇营之人与事,总以一双白眼相对,以为世间干净之人莫过于我,众人皆浊,唯我独清。这一腔冰雪肝胆,无人与共,难免就成了踽踽独行之身。见到绿萼梅那一刻,内心好一阵玄惑,世间真有如此清淡雅致之物啊,白色花瓣,淡绿色花蕊,晶莹灵秀,清白相守,觉得如此空灵之花绝非人间物,它是造物主不小心遗落人间的珍珠。又觉得这绿萼梅是为我存在的,至少是为与我一样干净清澈的人存在的。
如今染世已久,最初那个清高不尘的人也渐渐和光同尘了吧。试问世间人,谁敢毫无愧色自比梅花呢。“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孀娥槛外梅。”为了能与梅花相近,我在旧居楼下西侧辟了一块地,种了两株梅树,一株绿萼梅,一株红梅。心思也简单,一是喜欢,一是希望自己守住初心,无论世事如何沧桑变幻,永远如梅花一样,清宁自守,清气无边。梅不负人,那几年,每到春节前后,红梅总是先放蕊,它像个老人,老命也知春,格外珍惜不多的几日,尽全力盛放。老树新枝,红蕊点点,在万木冻得萧瑟灰颓之中,红梅报春,添了喜上眉梢的祥和气氛。每年年三十早晨,我都会拿着一根钩子,到西边墙角梅树下,仔细挑选,择不大不小的一枝,要枝子姿态好看,花蕾多的,小心拗折下来,红梅枝子比较脆,极易折,回屋插在事先备好的梅瓶里,整个屋子忽然就亮堂了。
绿萼梅总是开得迟些,仿佛一直在蓄积力量,为了更加清幽香远,它像个贞静的女子,淡淡的,不喜欢抛头露面,静静地来,悄悄地去。但它清清白白与世无争的模样,真让人看不够,就像世间难得一遇的清澈之人,你喜爱却不敢轻易靠近。
后来我迁居,两株梅树,留在了旧居,每到冬末,还要去看上一看,在梅花边流连一阵子,嗅一嗅那冷香,洗一洗一年来累积的疲累与俗气。即便跌倒,也要倒在樱花上的日本俳句女诗人千代尼,有一短诗:“梅花香中,食白饭,足矣此世。”也道出了我等清淡又满足的心声。
生在南方的友人有福气,家门前一条水流,水边红梅、黄梅、白梅、腊梅争相竞放,每日上下班都从梅林中过,渐渐地也染了一身梅花清逸之气,人真成了梅花客。出行受限时,梅花也被栅栏围住,她每次路过水边,只能遥遥张望,一日终于忍不住,趁无人见,越过木栅栏,跑到梅林里,足足待了一个时辰,看够了,嗅足了,携一身冷香,踏着夕阳落日孤独归去。世间爱梅人总是孤独的。
宝钗吃的冷香丸,也与梅花相关。春天白牡丹,夏天白荷花,秋天白芙蓉,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待凑齐了水露霜雪,应是梅花放蕊时节,封旧瓷坛埋在花根底下,那花树自然也是冷幽四溢的梅花了。
向来以“稻香老农”为泥人、俗人,不能诗不能文,自幼也只读过《列女传》《女经》,又斋号老农,颇有台上泥塑味道,其实不然。李纨实则是个优雅慧心之人,俗人断乎不能为海棠诗社掌坛人。李纨寓意结子,是要“其叶蓁蓁”“宜尔子孙”的,“诗礼簪缨之族”未来“诗书继世长”,要靠她,俗不得。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宝玉又落第挨罚。李纨道:“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来插瓶。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如今罚你去折一枝来。”众人都道,这罚得又雅又有趣。且妙玉处必宝玉去了才求得来,李纨心知肚明,曹公不说破,属“夜雨瞒人润花法”。李纨是有梅花心思的,她的清冷玲珑,不外现而已。
我自己画梅,自何时始?也忘记了。古来画梅人太多,而人品与梅品、画品最恰当的要数梅花道人吴镇,他一生高标自清,饿死不卖画。那首《调寄》诗,算是他自况:“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几到头,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回拜相,两度封侯,采菊篱边,种瓜圃内,都只到邙山一土丘。”高洁又通透。清末江峰青为吴镇祠题写过楹联:“君身自有仙骨,几生修到梅花”,每每读到此,都会默然,进而惭愧。
见过人描绘的一幅旧画:“一间茅屋,一位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题目为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这是多好的岁朝清供图啊。
许是今年年景好,刚过春节,房山区上方山的古腊梅开了,淡黄的花,幽远的香。红墙的映衬下,花朵就像一盏盏鹅黄色的小灯,挂满枝头。与友人信步来到松蓬庵院内,房屋西北角的两丛古蜡梅,有三百五十岁了,名为“九英黄”,正尽全力绽放。据传乾隆年间,知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查礼得知上方山腊梅盛开,特意寻幽至此。当来到松蓬庵院那株绽放的蜡梅前,正有瑞雪纷纷而至,尽兴观花,乐而忘返,遂速绘多幅蜡梅清供图。
我附近花市街巷总有卖梅人,择长短疏密成束,既自然粗放又雅致,一路走,一路吆喝,一路留香,我喜欢看这样的情景,尤其日落时,又美好又惆怅。暮色降临,楼上听见卖花声,推窗叫住了,懒得移步下楼,花绳坠下,拴一大束黄灿灿香气上来,也能闻上好几日的冷香。
古人有个待花泡酒的美法,叫作“悬花熏酒”。我试过,白纱花囊盛满新鲜蜡梅,悬在秋天新酿的青梅酒上方一寸,让蜡梅香气熏染至酒酿中去。但以我们这一颗俗心,怎样学古人,也不像了。
再过几日待梅花凋谢,老干清枝陡然生出苍凉气息,赏梅人也跟着沉寂。四时物象,皆为寂寥,人心也仿佛空无一物,却又期待着皎洁圆满。
日暮苍山远,立春好些天了,梅将落尽,山上桃花在望。时光错落迁徙,西风流年暗度,又一个春天就要来了。
春风有信
立春那天我在园子里闲逛,像个无所事事的游魂。北方回春缓慢,风刚刚摘去刺骨的手套,草木枯落还未有新消息,天色亦灰暗模糊。园子里多水杉,高大的身影灰零零的,枝干硬挺光秃,不见芽苞。土地下的虫儿们,许是在挣扎着翻身,努力想睁开眼睛,预备苏醒,就像我此刻的内心,挣扎而疲惫。一年终了,除却一身疲惫,老去一岁的年华,似乎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
冬阳姣好,街巷张结着红彩灯,春节前的热闹,浮沉里也有喜气飞扬,而这一切仿佛都与我无关。我只有一具身躯在这个世间游走,灵魂早已出窍。门前人们来来往往,不住搬运。此时的我看着他们,觉得很可笑,一袋子一袋子的米面,一桶一桶的油,整箱子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海鲜,不停运回家,仿佛一天要吃掉一年的食物,年就一天,而余下的三百六十四天,才叫度日如年吧。
晚间照例要读几页书,证明自己还活着,读到茶月令,字里行间有隐隐春气。南方二月,风已柔软,身体有松动的意思。春气萌发,荠菜正肥,田间地头已有人挖荠菜。漫山春茶遮遮掩掩在云雾中。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南北相隔数千里,他们在春,我在冬末。
春风它没有脚啊,跑得却那样迅疾。节后才几日,天还未明,朦胧里听得雀儿稀微的鸣声。声音远远的,时断时续,几乎像没有。再听,那细细的泠泠声,既真切又虚幻。起床推窗,鸟鸣婉转,在清晨的空气里似带着水汽,春天的清晨是湿润的。这婉转清脆的鸟鸣,能带给我回春的心情吗?
金、木、水、火、土、风六位之中,风、木同位,在东。一岁之中历经了大寒、立春、雨水、惊蛰,在春分前,人间的第一缕春风也即东风就来了。所谓春分,其实是风之分也。传说中的风神名叫巽二郎,八卦之一的巽卦,乃为风为木,巽地方位东南,乃吉利之地。是以东风一起,万木铮铮欣欣,枯萎一个冬天的草木自此露头向荣。东南风又称“清明风、景风”,春风有信,人间春和景明,绿满大地,大吉利也。被东风轻抚,心情也渐渐向吉回暖。
早晚已见草色一星一点自地下挤出,顶着新梳洗过的绿发。篱前青瓦人家,女人在河畔提水,岸上白鹅悠悠踱步。山腰几株山桃花树,跳出星星点点粉白枝花,今年山桃放花格外早,预示冬天像一场大梦一样过去了。山桃最早放花,我第一次知道,它有淡淡的香气,但要在无风处才闻得到。林间有白鸟飞过,停在湖畔,又缓缓掠过水面,高飞低落,再隐没林丛中,像那些远去人的背影。春色如此烂漫,悲伤的人,也该给内心填一点春色吧。
我承认自己是忧郁的,生而如此吧,不合群不随大流,不会讨好不善结交。骨子里那点不值钱的清高,即使年纪一把仍然敝帚自珍,骨骼硬得像后山那一树不屈的野山桃,自开自落,不妒不羡。春女秋士,春思秋悲,思谁呢?“挑兮挞兮,在城阙兮”的恋人,挥手自辞去山长水远的家山故园。我少小离家,行踪如萍,故园是心头的胎记,抹也抹不去。每到春来,总是风起故园之思,那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该醒了吧,我少年嬉戏游乐的河流也该解冻了,被棉衣束缚了一冬的人们,也该走出屋舍,方杖溪山,我那白发苍苍的父母,又老去一岁,而我还在千里之外,如一片随风远去的树叶,飘飘不能归去。
春天日落更增惆怅,想出门寻一点欢喜。走出庭院,天边霞光铺洒,照亮半边天,半山花树。想寻一处吃酒,这乍暖还寒的暮晚适宜饮酒,抵消一点料峭微寒。天黑时起了风,看见有人在水边玩耍,有人燃烟火,烟花在空中散去,烟花无情思,天空一望无尽,像这不休的岁月。
己亥三月十二日的雨
夜半抑或黎明,春雨悄然湿窗棂。清早,有人出门看花,旋又折回取伞,方知夜里有雨了。透过窗子看,地面黑湿湿的,却看不见一滴雨,想来第一场春雨,终究是不好意思倾盆地下,大抵类似于“细雨湿衣看不见,五更桐叶最佳音”。夜里,雨是别有风致的吧,滴滴答答,与窗外草叶呢喃了一夜方歇。这样的春雨大约也可涤荡些微看不见的尘埃。
一场春雨,庭前玉兰新绽,待玉兰落尽,后山桃花就次第开了,时序催花,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童年习俗,第一场春雨,用雨水洗头发,以示新年气象蓬勃。也有淘气的孩子,仰起脖子伸舌头接雨水。那时对雨水心存敬畏,是为天水,天所恩赐,要格外敬待,能喝到雨水仿佛得了天赐宝物,如今谁还敢喝雨水呢?离开家乡后,不再用雨水洗发了。今早洗发,长发又去稍许,像人情,一天薄似一天。发秃齿摇是每个人的未来,不必急。
一夜春雨,连檐下鸟雀也喜悦起来,一早啾啾报新晴。园子里,青枝上,一望清凌凌的碧色,春韭、野芹、水葱、莴笋,水洗一样的葱绿,争挤着撞人眼皮。朝阳尚远在山门外,发梢就有细风拂过,风中夹着雨湿气息。
春雨如恩照,雨湿天气,不必外出,闲在屋子里喝茶、读书写字。尘事扰人,我本是个不管俗务的人,人与人的关系更令人头疼,总觉得那些你来我往的戚戚之事,浪费生命。有一段时间了,躲在山里做些静心之事,哪管山外尘土飞扬,名来利往。王维的诗句说到我心坎上:“年来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此诗,有春雨的清新干净,也像我此时喝茶的心情,有可心茶自然好,若没有,粗茶也可过咽喉,喝茶不过喝的是一段安静时光,一点散淡心情,至于哪种茶也不打紧,喝下去也就去了。但有璞玉可相食,不求良玉过咽喉。人生规则限制何其多,能有这一刻的自在随意,哪里还挑拣呢?随手播放《普庵咒》,古琴曲中此曲有梵音意味,多了几分空灵,俗事、俗物在心的人,难得空灵,心中、眼中都填得满满的,希望这山中春雨能洗我一身尘俗。
早饭后,雨又淅沥了半个上午,拐着一个中午。心像被雨水浇灌过,有了一丝蓬勃气象。午饭在檐下吃,偶有几丝细雨飘进白瓷碗,觉得碗里要生出禾苗。山居的人,不怕雨,亲近雨,是老杜的“春夜喜雨”。“午后雨住,飞鸿落照,相将归去,何人无事,宴坐空山”,这也有点矫情了,春雨就有这样的功能吧,让俗人也多了一点诗情画意。“夜雨剪春韭”,虽不为写雨,却是春雨里最好的诗,一生沉郁忧国的诗人,这句诗却明丽得像邻家小女。伟大的诗人,重锤之后必有轻音。一夜春雨,一畦春韭,容易让人忘却,一朝作别,世事茫茫的无奈吧。
雨后夜晚开着窗,灯下读书,这些时日一直在读东坡,看到朝云墓六如亭对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虽是东坡意,而格调颇低,未必是东坡手笔,许是后人撰。清人也有不平句:“一骨何难共北归,东坡心事太深微。”这也是我的心事,我慕东坡久,唯此一事,不能平。东坡最终仍是将朝云孤零零留于岭南。自东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以朝云的冰雪心性,如露如电的佛心,自然不会嗔怪东坡。从前以为,东坡酸腐,稼轩输于典雅,唯张孝祥,一阙冰雪词,干净爽朗到极致。古今男人气概,东坡、稼轩皆不及。他最好的诗句“肝胆皆冰雪,表里俱澄澈”,多像初春的山雨,纯粹干净。
书里夹樱花书签,三角形镂空樱花,樱花亦虚亦实,镂空形制好,通透的视觉效果,字迹亦隐约若现,美人如花隔云端般朦胧。这枚书签,自何人手里流转而来?匠人?烧制工?锻造工?我非第一个拥有它的人,也绝非最后一个。他日,又会流到谁人手里,我亦不能知晓了。
早春山里的雨还是凉,需穿夹衣,寒雨入骨,听得见骨骼哐当作响,岁齿渐长,骨骼也来添惆怅,好在还有雨后闲情聊以慰藉。
朱自清先生也是爱雨的,他在《外东消夏录》中“成都诗”部分写道,“在这样细雨的路上缓缓地走着,呼吸着清新润泽的空气,叫人闲到心里,骨头里。若是在庭院中踱着,时而看见一些落花,静静地飘在微尘里,贴在软地上,那更闲得没有影儿。”
世间种种,哪里好得过一个“闲”字呢,“闲看落花”“闲庭信步”“大知闲闲”。世间事,哪一件不是闲事?世间事,又哪一件是闲事?春天的雨,是给闲事、闲人做注脚的。雨是闲物,落花是闲情,空气中灰尘也是闲的,天澹云闲。
闲吃茶
饮酒生豪气,也生浊气,更易生悲凉。“惟记去岁与王子立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春日酒后最怕读到这样的句子,寂寂生惆怅。
一个人静静治愈这春日惆怅,有时吃几盏茶,多是独自饮。午后睡醒,阳光穿过帘帷,温暖地照着墙壁,照着地面,也轻轻掠过案头瓶花,青白小雏菊玉面书生相,院子里有零星落叶。这样的日子,总想起旧词,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起床净手,绾发。开火煮滚沸的水,清洗茶具。一柄提梁壶,合盖子浸泡,几只小杯一字排开,一杯一杯斟到好处,断续着喝,也不急,凉、热、浓、淡也不管,清淡自在,并不觉得孤独。
茶不大讲究,世间好茶也不求,大红袍、金骏眉、小青柑也都吃。旧时喜欢从铺面买回各色花茶——茉莉、玫瑰、栀子,紫罗兰紧抱着的花苞,遇滚水,花瓣在杯底渐渐舒展,溢出淡淡花香气,佐以小食,温一出旧戏,闲度半日也是好的。
倒喜欢茶具,几年来藏了一些,有时盛茶,有时只是赏看。玉杯,银碗,玛瑙盏,最好玩的是一只竹杯。有年去蜀地,请人用青城山竹子,整根扣了两只杯子带回来。送人一只,自己留一只,一直舍不得用。层层包裹好,偶尔念起,一层一层打开,细细嗅一嗅,似尚存一丝若有若无的青竹气息。得了那一只竹杯子的人,多年后变作“隔浦人家”,遥不相识了。同在世间,任青史几度春秋,凭四时物象起落,只是不见。
我送人礼物有个习惯,必是自己珍爱之物送人,才是尽心之举。是以,喜欢的东西,往往在别处,自己却常常两手空空了。
有文字说,喝汾酒当用玉杯,“玉碗盛来琥珀光”。白酒,为增芳冽之气,需用犀角杯,酒香醇美无比。葡萄酒,自然用夜光杯。高粱酒是古之酒,须用青铜酒爵,始有古意。至于米酒,其味虽美,失之于甘,略显淡薄,当用大斗饮之,方显气概。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南宋勉强可用,但已有衰败气象,至于元瓷,则不免粗俗。吃茶也如此,普洱茶用紫砂杯,绿茶用透明上佳玻璃杯,红茶用白瓷杯,白茶且用酒红玛瑙杯。
讲究真是多,我吃茶随性得很,惟取手边有的,尽一时之兴吧。吃茶饮酒不过都是兴趣,若有趣味相投之人共饮,足可醉煞江南千万山。
问小孩子喜欢喝哪类茶,她总是先问名字,告诉她,白茶称白头霜,红茶作点绛唇,绿茶叫烟波翠。我猜得出她会以白头霜为老人,会喜欢烟波翠,觉得自己还太小,要待长大才饮点绛唇。她本喜欢白色,春色葳蕤时节,从园子里回来,牵着衣襟问,你见了吗?路左侧一株梨花开了,好清白呀,可以泡梨花茶吗?
她曾好奇地问过,为何这个叫杏花,那一株就叫梨花呢?我答不出花名的缘由,只知道,惟望她如春天的花朵,拂面不寒,一生“古木短篷”,不问凡俗事,自在悠游度一生。
杏花开时,她也活跃起来。有模有样随我读诗文,读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便跑去拿出竹笛吹奏起来。笛声有几分杏花的疏落清淡,也有春天草木的新鲜气息,就像她稚气明媚的脸庞。
又是早春,暮色来得迟,茶饮到淡了又淡,晚霞渐渐爬上天际,窗外风天一色。时光如逝水,老去又新生,都是陡然间的事。再过些时日,可以山中待月,花下坐饮茶,清风一塌值千金了。只是,春天日暮无端生出一缕淡淡的惆怅,不知为哪般。
韩玉,女,作品见于《散文》《山花》《雨花》《湖南文学》《滇池》《四川文学》《红豆》《飞天》《山西文学》《人民日报》等。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