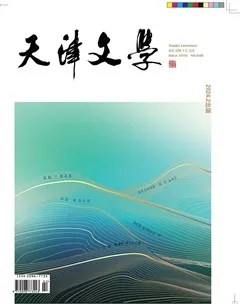呼唤
上官李军
一
一种来自大山的声音在血管里澎湃。从县城出发骑行五十里,就要进山了,我向雪前岭方向爬去。盘山越岭,阒寂无人,越往上越清新幽静,我此时正行进在三十多年前曾多少次行走的路上。又三十多里后到达了雪前岭——几个乡的交通交汇点,一个令我倍感亲切的地方。
沿着原李圪塔乡(已撤)的公路向下,我知道第一个村是阳坡。那年,我十四岁,大雪纷飞,我从父亲教书的山里步行六十多里回村,走在阳坡与雪前岭这段坡陡弯大的公路上。天地一白,道路莫辨,寂无一人一鸟,我独自走在冰天雪地里。我缓慢地骑着回味着,仿佛回到了那个大雪飘飞的年月。
过了阳坡,再往下就是口河村。九岁上第一次跟爸爸进山,到他教书的松甲庄,到口河时已是下午,忽降大雨,不得不在口河停留。山势高峻,大雨迷蒙,笼罩山岭。高山就耸立在窗前,伸手可及。还是孩子的我第一次对山感到惊奇。
到了口河,我越来越激动,就要打听松甲了,我感到些微的恐惧,怕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忐忑地向村边的一个男子打听,路往哪走,他指给了我。还好,心终于落下来,我魂牵梦萦的松甲终究没有被一阵风卷走。
终于在山坡上看到了一个小庄,高低错落,似有十几户人家。把车停在路边,我走进一个院子。屋门前坐着一个上年纪的妇人和一个中年妇女,她们惊奇地注视着我。我问,这是前松甲?她们说是,你是干什么的?我告诉她们爸爸当年在此教过书,叫上官誉(父亲已病逝二十多年),我是他的儿子,九岁时来这里住过。那个年老的略一思索,说,是记得你爸在这里教过书。噢,你是上老师的儿子,来这里干什么?我说趁“五一”假期来这里看一看。
我沒有忘记一直牵挂的一个人——一位妇人。我说,记得有一个常常闹“阴火”(胃痉挛)的中年妇人,要是到现在,她也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她们想了半天,不很肯定地说,不知说的是不是她,她早已不在了。
有一天下午,我在前松甲,一个常闹“阴火”的妇人正发病,捂着肚子,她穿着贫穷,脸色铁青不时呻吟,听到旁边的人说许又是“阴火”了,快去放放,别教老了就放不出来了。我在一旁为她暗暗焦急担心。一会儿她找人放了,好些了,还向人说,再迟点就过了那边了。我听了多么恐惧。那个下午的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常常在脑海里泛起。自那之后她让我牵挂:她后来生活怎样了?在不在人世?在这茫茫的世界上,闹“阴火”的妇人,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孩子关心过你,曾为你惊恐担忧过吗?
我又问她们庄上的情况,学校的情况。学校还在,还在原来的地方,只有四个学生。庄上这会儿只剩下十几口人,原来有一百多口人,都迁往山外了,后松甲也只剩下一二十口人,剩下了几个年老的人。她们告诉我,这条路往上不远就是松甲学校,从学校就能看到不远的山上的后松甲庄。
出来在村边,又遇见一个放羊老汉,我同他攀谈。提起父亲,他立刻来劲和惊奇,显出一副故人久别重逢的热情。他告诉我那个只剩石头围墙的就是当年的学校。
他请我到他家里。他对我父亲印象很深。我看出他为故人的后代能重新寻访至此而感慨、激动。也许当年他同父亲交往的那一段生活后来几十年不曾翻阅,早已遗失在岁月深处,今天我的突然寻访,令他又想起父亲和旧事——他年轻时的一段生活,怎能不心生感慨?我告诉他,父母早已过世。物是人非,故人的后代早已成人且已中年,猛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怎会不动心!
我又向他询问我记得的一些人。随着老汉的介绍,当年那些人和事又浮现眼前。
他向我诉说庄里的情况。人都迁出去了,只剩下几个老年人。为什么?女的长大了就到城里寻点事干不回来了,男的娶不下媳妇,娃们又念书不便。他家很脏,可能是因为他要照顾门口坐着的偏瘫的老伴。他拿出两个菜包让我吃,我推辞,他又忙拿了两袋方便面要给我做饭吃,我再三拒绝。也许对山里人来说,方便面是唯一干净的能拿出来招待城里人的饭食。我知道他们的方便面都是用粮食同货郎换的。我既不忍心为他制造麻烦,又为拒绝了他的情意而内心不安。我们互相问候了解了各自的家人、生活。我起身告别,他一再感叹我大老远来没有吃饭显得愧疚不安。我说我还要来。也许他认为我是客套话,但我确实发自内心。我一定还要来。
他把我送到庄前。
不一刻就望见了学校,这令我日思夜想的地方终于出现在眼前,像久久离别的亲人,我急切地要捧起他的面庞细细地端详,看她的容颜是否改变。它在一个山坡上,前后松甲之间。在一个只剩四面石墙的石屋边,有一个三间瓦房的小院,我想这就是松甲小学了。我怀着激动而神圣的心情逡巡徘徊。原来面朝山前的教室,现在成了面朝侧面,当年的教室只剩四堵墙,门上架着篱笆。久久高仰低徊,我觉得山势地形依稀如当年,葱郁的青山依旧,前方的山坡还是傍晚爸爸归来时的情景,而当年那一片玉米地却形迹难寻。
那时我九岁。也许是为了减轻家中的口粮负担或是觉得我到爸爸那里能吃饱饭,家里就让我随父到山里住一段。
大约傍晚时分,我和爸爸摸黑到了松甲。松甲小学孤零零地坐落在相隔四五里的两个庄子中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幢三间大的地盆房——用石块砌墙和石板铺盖房顶的小平房。山里全是地盆房。分里外间,外间是教室,里边是爸爸的居室。学校高山环抱,林木蓊郁,山石荦确,还有绿油油的庄稼地。出了房子斜对面是一片玉米地,穿过地中小路约二十多米是学校的厕所。之间往返走过的那一片玉米地给我留下清晰而美好的印象,像一片绝世的仙境。记忆里始终闪现的是这一景象:清新的山风吹拂,油亮的玉米叶子轻轻晃动,衬映着干净淡蓝的天空,一个敏感内向的孩子身着一身阴丹蓝布衣裳,独自走在地中的小路上……
住在爸爸这里基本能吃个饱,不为挨饿忧愁又有新的同伴,因此非常快乐。
爸爸常常到公社的中心学校集训,就不得不把我安置在前松甲或后松甲人家,到天黑或半夜回来才引着我走着漆黑的山路回家。有时他有事下山,留我在家里。每到黄昏时他还没有回来,我就走到前方百米的山坡前向下山的小路上张望,盼望爸爸能突然出现在山路上。
我探头向院里望去。教室的门开着,像是有人。我慢步走进院子,到教室门口看见里面有学生和一位中年男子。男子也发现了我,走出来。他约有四十几岁,高个子。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向他作了介绍。他听见父亲的名字,立即说,认得,认得。他说他是阳坡人,三年前小学老师走后,没人愿来此教书,他就向乡教委说,真不行他来。现在只剩四个学生了。他说,这里简直与世隔绝,不比当年你父亲在此时有二十来个学生,前后庄几百口人,现在只剩下几户人家,甚是荒凉。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大部分晚上回家,早上来。我说,为什么每晚要回去?晚上没事干,又没电视,一个人孤寂得害怕。我父亲当年不是也一直是一个人?那有所不同,那时,前后莊人多,晚上时不时有前后庄互相串门的经过,而现在一到晚上,几乎人影绝迹。
虽然如此,我想象得到当年父亲也是承受了多少艰难,需要多大的忍耐精神!他说,学校早就说要撤,今年终于下了文,六月份撤掉。这是口河村办小学,但是学校一年的微薄开支,村里也管不起,不是不管,确实没钱。我只好从自己的工资里往外拿,比如煤火和一些学杂费。
他把我让进屋里,让我看看小娃们。外面是两间教室,里面是他的居室。外面有一个大炉子,生着火,做饭用。他进去就一步抬腿跨上炉子,坐在小木凳上,四双小眼睛稚气而好奇地打量着我。两个女娃两个男娃。他说,就现在还有两个学生的家已经迁往山外,不久就要走了。我说,剩下的两个学生怎么办?不知道,反正像这样子肯定坚持不下去。我想,幸好,我终于在撤掉之前赶来了!多么迟到的寻访!
他告诉我,去年省剧院的几个人到历山旅游,回来时经过这里,看到山里的学校是这样子,同情又惊奇,给小娃们和学校留了影,回去后还真把照片寄来了。说着,他到里间拿出照片递给我看。
我感到了山里小学和师生的寒酸与艰辛。简陋的教室,桌椅七歪八斜,令人心生怜悯。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质朴无华的美。
我几次就要对他说,你今晚不要回去了,我同你做伴。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在这所荒寂无声的小屋里,黑夜如漆,我们缓缓地谈论着小学的从前、现在和山里的故事。当身旁这个一生一直在山里教学的人熟睡后,我独自感受着这荒凉静谧的山里之夜,感受当年睡在这所小学的感觉……但我终究没有说出。
我准备下山,他把我送到小院外,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松甲小学,向山下奔去。
二
那一条绕向山后的小路,怎似曾相识?哦,是到东沟的路。爸爸当年教书的又一个山庄。我又激动起来。已是下午,天气阴沉,冷风夹着雨点。
我缓缓行进在小路上,努力寻找当年的感觉。转过山就看见了东沟庄,清晰地记得小学校。穿过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寻到了学校的房子前,但是没有了门前喷涌的清泉,屋里已非学校而是住成了人家。一个年老的妇人坐在门外的石墙边。我说明了来历和来意,她说知道我父亲和母亲。她说学校记不清哪一年撤的,只知己好多年了。
我上高中是在山的那边,属横河乡,和父亲这里只隔一道大山。翻山越岭,其间有十七八里。我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徒步跋涉到父亲这里。也是三间房子,爸爸一个人同时代着一至四年级的课。学校在一个小岗子上,依陡坡而建,搭有一架石桥,与庄里人相通。最妙的是门前石桥边有一泓深褐的山泉,清冽甘甜,喷珠溅玉,声音清亮悦耳。爸爸做饭用水就直接到池里舀,那情形别提有多么惬意了。我最爱到池边双手伸进清澈的水里,掬一捧清凉的泉水。
星期日下午我就要返回学校,在爸爸处停留的时间真短,多么珍贵、幸福!我抓紧享受着这短暂的时刻。每次到来,一向对儿子们淡漠的爸爸这时也对我十分亲切,常常问我:“军,给你做点什么好饭?”他总是做那时最好的饭,如烙饼待我,此时我感到爸爸亲切慈爱多了。
有时我孤身一人在里屋,静静地感受,淡淡地思索。方桌上放着学校的钟表,指针下方是一公鸡啄米的动画,不停地啄着。我长时间一个人静静地聆听钟表铿锵有力如青春步伐般的滴答之声,我不知不觉走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我觉得在这优雅静谧的山庄小学的小屋里,是一个孤独遥远而又深邃宽广的世界,是少年梦幻的世界。
在上学的两年中,东沟小学是我的又一个家和圣地。我多次独自跋涉在峰峦沟壑间,每次打算要到爸爸那里,我心中就怦怦直跳,按捺不住幸福和激动。
我问妇人,有一年来这里时,恍惚记得父母亲不在这里住,是另外的房子。她说,是,那时他们住在那里的一间房子,不跟学校在一起。说着用手指向前面。我按她的指点,寻到了那间房子。是了,这就是那个给我留下美好回忆的房子。房子依旧,小而低矮,但是房门紧锁,好多年已无人居住。我左右逡巡端详着它,我多么想能再进去看一看啊!我在此是怎样度过了一星期的幸福而美好的时光啊!我脱离了繁重压抑的生活和家务劳动,远离纷争、歧视,得到了极大的母爱,无忧无虑,真正享受了一个少年的生活。
那时我上初中,有一次,省里的为人民服务医疗队为村人免费检查时,检查说妈妈有不治之症,怎么办?哥哥同妈妈合计,最后决定让不堪劳累重压的妈妈到父亲处养病。走时只说住个把月就回来,但结果是去了一年,家里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哥哥起早贪黑在生产队劳动,家务活全搁在了我的身上,好几次我实在承受不住繁重和劳累,止不住哭着要妈妈。某一天,我终于一个人坐上大班车进山里去寻找妈妈。见到了妈妈,已经快一年没见了。我和妈妈都怀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我看到妈妈的身体和心情都比在家里强多了,没有了往日整天阴郁着脸不说一句话的样子。她快乐开怀,话也多了也和蔼了,问长问短说这说那。温馨和煦整日充溢着这个简陋的家。
我回到了亲密无间的母子的小世界。在短短几天里,我充分享受着温暖甜蜜的母爱,压抑了很久的孤独和苦痛的心得到了释放和慰藉。环境秀美、清新简朴的山庄和简陋临时的家温暖复苏着这颗心。妈妈尽量倾其所有给我做好吃的,无微不至地体贴和关怀我,母子间推心置腹。妈妈给我讲山庄里的人和事,她来这里的一切,同庄里人上山或到邻庄的经历。妈妈同庄上的几个中年妇女们很要好,特别是同一个叫“丑女”的性情开朗的胖妇女要好,同她你来我往出入上山,去过好多地方,见识了好多树木、草药、山货。她同庄上几乎所有的人关系都不错,而他们也都对她很好,不仅看得起她,而且很尊重敬佩她,她在这里获得了从前未有的尊严和骄傲。
每天晚上总有三四个庄上的人来到我们这个小天地谈天说地。
我在爸爸的柜子里发现了一摞一摞的彩色儿歌图画书。我看着看着跌进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童话世界。小学和中学都几乎没有见到过什么彩色读物。彩图配着儿歌是那么美好,活泼上口,画面鲜艳,内容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农业机械化的。封面是一个男孩和女孩倚在窗前,拿着画笔和纸。有一幅是一个宽阔的坡形的街道伸向里面,色彩缤纷,四周是彩色的楼房,街道上只有一个穿着半袖衫短裤的儿童向着画面深处走去。多么纯净美好啊!这些儿歌和图画为我营造了一个个幻美的天地。我无忧无虑,整日沉浸遨游在彩色童话的世界里。当我偶尔把目光移向室内时,居室及其一切都是绮麗的图画。黄昏降临到静谧的小屋,妈妈坐在炕沿上静静地做着针线,如一幅近晚的肖像画。这同明亮温馨的环境是多么吻合和谐啊!
当年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令我怀念而激动。这间小屋是我神圣生活的见证,经过几十年的沧桑岁月,还依然完好地立在那里。它是否把那个多思善感的忧郁少年和怀伤柔弱的母亲的身影存留其间完好如初呢?
我正沉湎在往事的回忆里时,一个脸庞白胖而近老年的妇人走过来,问我,我一一说了,她很惊奇。从她的表情和言语中,看出她同父母熟悉和亲近,不无感情地一再提到和感叹母亲。
我向她打听我曾记得的一些人,她说都过世了。我又问她一个长得高大俊秀、相貌出众的年轻妇人。她想了想说,你说的是不是丑赛?一听名字我想起来了,她同母亲关系很好,常来往,常听母亲说起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纯洁的人。也许是她的标致美丽吸引了我。我问她的下落,妇人告诉我她男人有病早死,她后来又嫁到了山外。
对丑赛印象最清晰的是这样一个画面:在依山而建的高低错落的石砌的房子和道路中间,她高高而美丽地挺立着,笑盈盈地看着我,询问着我……
我在周围徘徊的当儿,不知妇人几时就到附近的小卖部买了两袋方便面,要给我煮。她对故人的后代真是青眼有加。这时天又下起雨来,我担心雨下大,再三辞谢了她,便离开了东沟。
三
冥冥中有一种东西在呼唤,要我寻访父亲曾经在这片山水里停留过的所有地方,沿着他的足迹。愿望是那样的强烈和执着,就如同我曾经在这些地方生活过一般,虽然与父亲的感情并不深厚。这是否是冥冥中血缘在起作用?是否是一种说不清的父辈独有的精神穿越了生死、距离、时间,多年后在我身上涌发出来?小时曾隐约听见家人谈到“西哄哄”“人参埌”“白寺沟”“贾山”这些地名,父亲一定在这些地方留下过印迹。我入住的农家房东告诉我确有这些村庄,但人口也已迁走不少。
窗子刚显灰白,我就醒了。雨还是那样不知疲倦地下着,相伴了我一夜,看来不会马上停歇,骑车不行那就徒步出行吧。
吃了早饭,我要冒雨出行,房东家人感到惊讶和不解,说白寺沟离此有三十多里地,偏僻冷清已没有几户人家,到那里有什么可看的?
山路泥滑,朝雨潇潇。到了西哄哄村已有十点多,在村头河谷边一座小桥旁,问了路,到白寺沟还有七八里,一直顺河上就到了。
雨雾霏霏,一幅雨天山景。哗哗的水声在这无人的深谷格外响亮动听——一个异常清幽的世界。河中的石头五彩交辉,清流浅潭清澈见底,像无数个不同的五彩池。愈走愈山高沟深,仰望山顶,浓雾绕拂,好似身在国画的意境里。
我边走边思索着父亲当年一个人常往来于这条路上,是怎样的情形,怎样的感受。那时从公社所在地开始——两天一趟的班车只通到公社所在地——就要翻山越岭跋涉三十多里崎岖的山路才能到他教书的村庄。那样的艰难困苦,那样的孤独冷寂,他是如何忍受过来的?他二十出头就成了一名教师,听母亲说,他那时本来能分配在离家近的山外,但山区教师短缺,他主动要求进山。母亲劝说,他说,那么多山里娃总得有人带吧。决然拎起简单的行李落户山区,在本县最偏远的离家八九十里的李圪塔乡扎根了三十年,二分之一强的山庄留下他从教的轨迹。这令我想到了蒲松龄的大半生远离家乡教书。父亲一生都在这样的环境里打熬、消磨,一年顶多回三四次家,直到在工作岗位上得肝病去世。母亲在世时总说父亲是一个苦命人。其间也有多次机会出来,但他本人没有积极意愿。仿佛他已经适应了大山,爱上了大山,爱上了诚厚纯朴的山民和山娃子们。所以我和哥哥小时总与他生疏,也不怎么爱他,更不理解他。现在踩着父亲的足迹,站在他工作和生活过的土地上,在与知情人的谈论中,才深深了解和理解了他,才真正领会了父辈们在那个特殊时代和环境下的品质和精神——勤苦、奉献、坚毅,淡于享乐!这岂是很多讲求享受、娱乐的人所能理解的?而正是他们这样的吃苦耐劳、不重名利的坚守才让后代的我们汲取了更有价值的养料,也承继了他们的某些品质。想到此我感慨万千,不善言语、不显山露水的父亲的形象在这大山深处清晰起来,鲜活起来了,也像沉厚、坚实、伟岸的大山在我心中耸立起来了!我竭力把此时的自己想象成当年的父亲,身穿洗得发白的蓝制服,高大简朴的身形正走在这条山路上。
终于隐隐地看见了房子。走到跟前,原来是一所已破败有年的孤零矮小的屋子。当中一个三间,两头各一间耳房,门窗全无,里面空荡荡的,早已无人居住。一种直感使我不禁猜想这是否就是白寺沟小学,父亲当年生活的地方。
再向前走不远,就看见了村庄,这大概就是白寺沟庄了。庄在山坡上。我走进去,许久不见人影,面前的房子似乎都空寂无人居住,抬头瞭望,在辽远处的房顶上有人影。我寻来,看到有三四个人正在收拾房顶。他们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明了来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说,好像有上官誉这么个人,我从部队回来不长,他就调走了。正在房顶上干活的一个精干老头开口道,这人在这里教过书。他说,你刚进村时那一所房子就是学校,原是一座庙,你父亲那时就在那里,学校已撤掉多年了。这是前庄,往后上是后庄,我是后庄人,你到后庄,我一会儿就回去,就在我家吃饭。他又说,前庄只剩下眼前这三四口人。
闲扯几句后,我便向后庄走去。正走着,听到后头有力而疾快的脚步声,我回转身,原来正是刚才那个老头快步跟来,他可能放下活计赶我而来。我停下稍等,同他并肩而行。我们边走边聊。他跟我说着庄上的一些事情。后庄属垣曲县,他是垣曲人而非阳城人,再往上还有沁水县的几个小庄,这会儿都没人了。原来小学校里同时住着三个县的学生。庄上的人几乎迁完了。他的子女都迁出山外,一年也不常回来。我说,如此你们这些老人的生活怎么办?谁来照顾?他说,就这样了,活一天算一天,能动的时候自己顾自己,不能动了死了算了。我心底感到一种悲凉,为仅留的这些老人生出同情和怜悯。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心态是怎样的,有无生活的希望。
我告诉他我的来历和状况后,他也一样不胜感慨。我看见河对面的房子,他说那就是后庄。我跟着他涉河往村里进。村子建在河岸边的陡坡上,高高低低,庄间的石头路曲里拐弯儿,陡峭逼仄。走到一个矮小的房前,他掏出钥匙打开门,把我让在地上一个小凳上。屋里凌乱也有些脏。他捅开封着的火说要给我做饭。我谢绝。说着进来几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老头告诉他们我是上老师的后人,专门来这里看看。他们一样的惊奇,他们都还记得父亲,询问我的状况。他们情不能自已地怀旧,谈论在父亲前后谁谁来过,谁走后谁又来了,数算着共来过多少个老师,哪个老师走后撤的学校等等。他们在数念着山村的历史、小学校的历史。我静静地听着,仿佛看到了山庄几十年的情景、小学校那时的繁荣景象。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说再往沟上头走走看看。老头说,这院那一个屋里还有一个患病的老汉,他同你父亲当年是好朋友,经常来往,你进去看一看。而我略作犹豫没有进去,说我一会儿再过来。他一再让我返过来吃饭。
我向河谷下走去,又几次瞭望浏览庄子的全貌,然后就涉水返程。才离开庄子,便生出一种懊悔。为什么没有按照老人的建议进去看一看那个患病的老人?他一下看到我——几十年前故人的后人赫然站在他的面前,一定无比惊异。我的到来能勾起他对那个年代一些美好的往事和记忆,而这些往事也许随着父亲的长久离去之后,在他几十年的生命里久被尘封不曾冒出过翻动过。而今我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久闭的门,一簇火重又燃起了他年轻时的生命,使他能在回忆里幸福地生活一回沐浴一次。同时我一定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更具体的父亲的情况,这不正是我期望的吗?也许我与他的失之交臂,造成了世界上两个生命之间本应有的一些美好东西的丧失,永远不可挽回和呈现了。我即便于公元某年某日来,那个同父亲交好的老人也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返回还能挽回,返回还是离去,我几次犹豫徘徊,但我已走上了村外的路,最后还是离去了。
几天里,孜孜寻访的这些山村,让我亲历了那原味原汁的乡愁,受到莫大的触动,对乡村振兴和留住乡愁获得了更深切的感受,并触发了纷纭的思考。这些不愿意离开也不愿抛弃世代之根的山民们,在城市化、现代化的今天,该如何去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幸福的矛盾状况?山村小学是否应该全部撤掉让孩子们背井离乡去上寄宿学校?该如何让社会要素资源包括教育、人才、文化等向这些山乡倾斜,以保留并发展华夏几千年的乡愁文化和文明?这些看来是多么重要的现实!这也证明了乡村振兴之国策恰当其时且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意义。
当我走出庄外,到了来时第一个见到的那所独屋时,我要好好再看看它。我走上屋前的场地,荒草萋萋从石板缝里长出,这是教室的小院。我走到窗口往里观看,屋里堆积着尘土,墙皮斑驳剥落。渐渐地,我看到了娃们的笑脸,下课后在门外空地里玩闹嬉戏,上学时一个个从同一个方向走来。我看到小小的耳房内搭着床铺,生着炉火。当一天放学后,父亲不知怎样度过一个恐惧孤寂的夜晚,伴着他的只有黑魆魆的山野和哗啦哗啦奔腾的河水。我久久盘桓,竭力呈现当年的情景,寻觅父亲的身影。但一个个地名还在大山深处呼唤我,我还要抓紧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