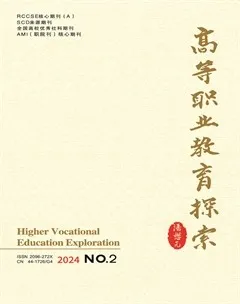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研究
康诚轩,李保忠,陈新忠

摘要:统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是发挥人才引领驱动作用的必经之路,也是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内在要求。目前两类高等教育协同创新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仍存在适应功能尚未完全实现、目标达成功能发挥相对滞后、整合功能释放效能偏低、潜在模式维持功能触发负面效应的问题。为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需满足社会需求来增强适应、培养全面人才来夯实目标、建立协同机制来强化整合、营造文化环境来加强维持,不断加快二者协同创新的步伐。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普通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普职协调;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0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的提出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随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加快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的呼声日益高涨。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各类优秀人才的涌现有赖于不同类型教育的共同优质发展。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要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引领和保障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普职协同创新发展,也呼应了构建人才强国和教育强国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我国现有研究多是从整体视角分析普职融通的意义和实现路径,对国外普职融通的经验次之,选取普、职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系统阐述两类高等教育协同创新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关于普职融通的价值意蕴剖析。有学者研究认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间的沟通和融合对教育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具有重要影响[1]。普职融通还有利于尊重差异,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实现教育公平[2]。二是关于普职融通的实现路径探索。有學者研究认为,普职融通需从完善职教高考和升学制度和强化课程融通、逆向转学、学分互认等方面加强横纵融通[3]。推进普职融通还要注重普职之间的实质平等,在普职融合过程中寻找二者的“中间道路”[4]。此外,可通过建设国家模块化课程库,创设新版综合高中,建立普、职教师“跨校走教”机制,完善升学考试制度等路径促进普职横向融通[5]。三是关于普职融通的国外经验借鉴。有学者在对英国T Level行动计划的研究基础上,认为引导雇主参与育人环节、基于项目式学习培养人才以及兼顾学生就业与升学等方式能够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通[6]。有学者对德国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通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教育决策者的宏观引导、国家资格框架等相关制度建设、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合作、高质量的科研支持是助推融通的主要因素[7]。还有学者通过研究英国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举措,提出要建立一体化的教育资格框架、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与质量、以延后分流实现学生多元化培养,逐步探索普职融通的“合轨制”高中体系[8]。
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是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其研究有助于厘清普、职高等教育的发展优势与定位,优化高校的组织建设与管理,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和资源的整合利用,推动相关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进而实现二者协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以最大程度发挥各自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促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目前,由于普、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一,在协同创新进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有鉴于此,分析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现状、问题及解决路径,强化协同创新的高质、高效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重大实践价值。
二、结构功能主义内涵及其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研究的意义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将社会系统视作由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结构相互耦合、相互作用的整体,来探讨社会系统中结构是如何与功能联结进而维护系统稳定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结构中行为有机体、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四大行动系统分别对应适应功能(A)、目标达成功能(G)、整合功能(I)以及潜在功能或说是模式维持功能(L),即著名的AGIL图式”。适应功能是指系统必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并使环境适应其需要;目标达成功能是指系统需要不断调整来实现其目标;整合功能是指系统要将各构成要素协调统一起来,通过合作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是指系统应提供、保持和更新个体的动机,并塑造稳定的价值观使行动按一定的规范和秩序进行。[9]各子系统通过不断地分化与整合,发挥着各自的功能,维护了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均衡。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加强系统与功能间的有效互动,尤其注重共同价值、制度和行动在系统运行中的作用,其分析范式可以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研究提供相对“中立”且系统全面的研究框架。实现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需要摒弃二者发展轨道孤立、办学活动分离的观念,将其视作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系统来统筹协调,重新设定协同创新目标、制定规范和塑造文化,为高等教育普职之间的有效衔接和有机耦合提供功能支持,促进二者的有序运转与融合发展。有鉴于此,本文借助帕森斯的“AGIL”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四个主要功能作简要分析。“AGIL”分析框架下,高等教育只有适应性强、目标一致、功能互补、文化共育,才能促进普职协同创新的实现。
(一)适应功能:经济社会发展诉求的呼应
帕森斯认为,“系统必须适应它的环境,以及调整环境以适应它的需求,系统必须应对外部的环境危机和偶变”,如此才能发挥适应功能。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都会受到一定的技术、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并要与之相适应,高等教育也不例外。面对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高等教育必须在遵循自身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及时进行相应的教育改革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诉求,提高教育在传承、变革和创新中的张力。为提高对教育系统外部环境要求的适应能力与内化能力,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是必要之举。
普、职高等教育对应的载体分别是普通高等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因此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不仅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两类院校履行各自职能进程中需要明确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加速迭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更加注重人才的复合性和创新性,这对高校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统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举措应运而生。加快高等教育普职间的联结与耦合,这有利于弥补两类教育孤立发展的缺陷,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适应性。
(二)目标达成功能:多元化人才的培养
在目标达成功能方面,帕森斯认为是“系统定义并达成其主要目标的需要。系统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持续生存,还包括它自身的成长和扩张”[10]。特定的社会系统共有这些一般性目标,同时还有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目标。育人是高等教育最核心的目标,所提供的教育应重视学生个性的发展,尽可能满足学生的多元化需求。培养多元化人才,是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目标达成功能的内在要求,也是二者目标一致的具体表现。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的自主选择和自由发展,满足学生不同的教育需求,还有利于构建“融合贯通、多元包容”的培养体系,加快协同创新进程。
如今,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加剧,宽口径、厚基础的全面发展人才更为社会所青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帮助学生成长成才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等教育的育人目标不能仅局限于按各自传统培养单一的专业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而要树立多元化人才培养理念,促进学生科学素养、人文素养、专业技能、道德品质、创新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并根据学生特点进行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以此来培养多元化人才。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正是在遵循教育外适、内适和个适规律[11]及“以学生为中心”基础上,达成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体现。
(三)整合功能:双向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
帕森斯认为,“整合功能是指经由整合,系统试图对各个构成部分的关系进行调节,还包括对其他三种功能必备项(AGL)之间关系的管理”。要发挥高等教育的整合功能,就必须统筹普、职间的协同创新。从本质上来讲,是对各类创新要素的汇聚与整合,通过调整和优化高校育人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大学的育人目标[12]。
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是一个大系统、大生态、大规划,需要实现二者发展需求与条件间的耦合与对接,各自功能的互动与互补。对协同创新谁来统筹、如何统筹、要实现何种程度的协同等问题要进行深入思考,否则会在整合过程中缺少规划,无所适从,进而严重制约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实现。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程度基本上在于各自教育体系、模式和资源的有机结合,既包含建构协调融合的主体间关系,还涉及多维度、多层次的联结制度和多重教育功能的整合。
因此,完善高等教育普职双向协同机制,特别是在师资、课程和资源等方面開展全方位合作,进行功能互补,才能实现外部协同、内部共生、各美其美的教育生态,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整合功能。可见,统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不仅需要两类教育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还要与对方的制度相耦合,进行功能互补,形成系统合力,实现教学育人资源的整合配置,如此方能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四)潜在模式维持功能:独特价值文化的塑造
帕森斯认为,“价值是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主要基点”“价值模式会对系统所在情景中表现出的基本取向起决定性作用”[13]。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指系统供给、维持和更新那些创造和保持个体积极性之文化模式的需求。可见,结构功能主义并未仅仅关注系统结构及互动机制等表层因素,还注重价值、文化、观念等深层因素对社会系统产生的作用。统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文化共育,塑造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和职业认可与尊重的文化,发挥潜在模式维持功能,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不仅是一种基于政策引导而产生的教育发展新态势,还是一种基于价值文化影响而触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升级。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不只是两类高等教育间的简单结合,更是一种独特价值文化的存在。
高等教育在普职协同创新过程中所积淀的文化底蕴和孕育的文化精神,成为不同于以往两类教育分离发展的显著性内因。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功能,本质在于它不仅是促进普、职融通的平台,也是实现因材施教、满足多元教育需求的有益渠道,是学生按照自身兴趣和潜能自由充分发展的重要前提。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所形成的文化是二者协同创新系统的核心所在,既体现了普、职高等教育从二元孤立到融合互促发展的历史积淀,也体现了统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因此,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要真正发挥其联结优势,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就必须共育文化,更新价值观念,创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品牌项目,组织多形式的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活动,营造浓郁的科学与技术相互平等的文化氛围,以提升普、职高等教育共同的影响力和各自的吸引力。
三、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但直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才提出要将职业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置于同等地位,强调“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这一变化,不仅影响制度体系和教育活动的改变,还涉及人才培养理念和教育价值观的转变,需要进行综合性改革。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检视现有高等教育的普职协同创新现状,还存在适应性不强、目标不一致、功能未互补、文化积淀不深等问题,系统功能尚未有效发挥。
(一)适应功能尚未完全实现
教育是培养人才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途径,而市场对高校培养人才的反馈则是教育质量的试金石。社会对高校培养人才的正向反馈与评价,有助于高校提升美誉与社会声誉,获取更多支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培养符合市场用人标准、满足社会需求的优质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社会的加速变迁和科学技术的迭代升级,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才的复合性和创新性受到了重视。
然而,当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不契合,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结构与社会要求不匹配的现象层出不穷,对外界环境变化和要求的适应性不强,使得普职协同创新系统的适应功能尚未完全实现。普通高等教育发展时间相对较长,有一定的教学和科研底蕴,也有较好的生源。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普通高校培养的人才一定会被社会认可和接纳。部分毕业生虽饱读诗书,但却缺乏社会所需的必备技能,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只能“纸上谈兵”,从而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職业高等教育发展时间短、水平相对较低,生源素质较差,培养的技能人才因综合素养较低而导致在市场上总体就业竞争力不强。同时,职业院校还会由于未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优化实践训练环节,致使所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错位。
此外,人才培养结构扭曲程度较高,这与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程度不足的现状密切相关。当前就业市场悄然进入了学历受宠、名校崇拜的阶段,接受本科教育已不足以在就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与直接工作相比,更多高校毕业生希望毕业后继续深造。为提高自身学历或拥有名校光环,学生升学意愿日趋强烈,纷纷加入“考研大军”,考研竞争逐渐白热化,这随时可能会陷入“恶性内卷”的漩涡,也极大地影响着人才培养结构的合理化。市场上经常呈现“有岗位无人应聘”或“岗位少扎堆应聘”的矛盾现象,这也是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尚不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的重要体现。
(二)目标达成功能发挥相对滞后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教育发展正由“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是在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全面发展的条件下,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加速,生产生活新形态新方式的变革加深,急需更多高质量的应用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满足更多年轻人多样化学习需求的任务更加突出”。
作为目标达成功能的内在要求,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要通过提供多元教育、满足多重教育需求、培养全面发展但又各有所长的人才等方面来发挥应有功能。然而,当前高等教育没有制定较为合理一致的普职协同创新目标,使得目标达成功能的发挥相对滞后。一方面,人才培养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在个体层面,对于事关个体成才和成人的教育,我们既无法周密计划,也无法严格控制,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无法展现学生的个性化特长。但当前作为普、职高等教育载体的高校,已成为一个类似于工厂的机构,正在大规模、标准化、高效率地培养人才,使得学校的职能从致力于“让人成为人”转变为更快地让人成为“有用的人”[14],人才培养千篇一律的现象较为普遍。
另一方面,从成长成才规律来看,高校需要促进个体实现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但是普通高等教育大都侧重于科研创新能力提升,职业高等教育则注重实践应用能力的提高,现有的目标要求和培养侧重已将学生的能力分化[15]。这严重淡漠了学生成长的多元教育需求,撕裂了学生成长的全面性,固化了学生的发展方向,使得学生一入学便被贴上“学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标签。可见,多元化人才的供给缺口有待补齐,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亟需推进。
(三)整合功能释放效能偏低
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实现有赖于良好制度设计基础上的功能互补以及各类创新要素的汇聚、整合与共享。当前高等教育在普职整合进程中并未取得理想成效,两类教育协同运行存在诸多阻碍,其中最重要的成因就是制度问题。统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进程中,“路径依赖”现象层出不穷,对已有制度的依赖使得高等教育普职功能互动与互补难以真正实现。与此同时,新的制度体系设计不完善,高等教育普职协同运行机制不健全,缺少相关配套发展制度,难以实现协调发展。
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一体化环境与平台有待优化,保障结构融通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力量的发挥,有赖于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不断完善各项制度来促使系统功能的有效实现。尽管《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2022年5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都提出了“促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然而相关政策还停留在倡导层面。由于缺乏具体细则,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不强,普职融通无法真正落地。目前二者依旧沿着学术与职业的路径孤立运行,分别管理、各立门户,教育活动分离,流转融通制度不健全,联结协调制度不完备,限制了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影响力。
二是统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缺乏支持性制度环境,校级协同机制尚未建立,功能互补尚未实现,资源整合还未发挥作用,高等教育普职独立建设、各自为政的局面还未打破。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无论是在人力,还是物力,亦或是财力等方面都不占据优势,诸如师资队伍水平较低,资金投入不足等,使得职业教育发展经常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总体而言,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体系的功能互补和制度建设任务迫在眉睫。
(四)潜在模式维持功能触发负面效应
作为稳定的价值观念,文化在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模式维持功能,也成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系统内部维系良好秩序的内在机制。文化是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系统得以传承和持续的核心,也是两类教育提高自身内涵和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新指向标,其有效组织和有序运行离不开各方权力的支持、学校组织的调整以及制度体系的规范,但其深层次功能的发挥则主要依靠包括价值、理念在内的文化内因。统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既离不开二者之间联结融通的框架设计和外部环境的营造,更离不开共育文化积淀的功效。
目前,共育的文化底蕴还不深厚,在文化精神层面还未形成实质性内涵,致使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不仅缺乏特有的文化内核作为价值支撑,还受到了现有文化产生的负面效应的波及。一方面,社会大众对高等职业院校和技能人才的认同度较低,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良好氛围有待形成。相较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始终“低人一等”。不仅家长、学生更倾向于普通高校,企业也更青睐于普通高校培养的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高等教育普职间的差距,阻碍了二者的协同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观念代代相传,虽然错误,但却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人们用以处理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或认知结构。在感知、理解、审鉴和评估社会世界的过程中,人们被赋予了一系列内图式。正是通过这些图式,人们才能创造出他们的实践,并对它们加以审鉴和评估”[16]。惯习难以改变,也正如人们的传统观念难以撼动。因此,在缺乏平等文化的社会环境中,要使人们对普、职高等教育一视同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问题的解决路径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将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视为一个社会系统,它涵盖了系统运转的目标、流程、模式和效用等功能要素。要解决当前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问题,需满足社会需求来增强适应、培养多元人才来夯实目标、建立协同机制来强化整合、营造文化环境来加强维持,不断加快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步伐。
(一)增强适应,满足社会需求
只有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适时进行改革与调整,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才能增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系统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促进系统各结构的有序运转和功能的正常发挥。
首先,普通高等教育要发挥基础研究的优势,在厚理的基础上拓工,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新教育生态。一要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结构设置。对于市场上供大于求的专业,应调整招生名额,以免学生扎推热门专业,造成学生结业难、企业招人难的局面。而对于市场上急缺人才的专业,应实施扩招政策,并根据行业需求设置人才培养标准,提高培养质量,真正发挥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二要抓住国家实施“双一流”战略的机遇,立足学校特色,发挥学校优势,通过构建一流师资队伍、加强跨学科交流合作、调整学校发展战略等举措,建设一流学科,跻身一流大学,提高学校的实力和知名度。
其次,高等职业教育要拓宽发展空间,完善管理体制,增强吸引力,激发办学活力。应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办学,促进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精准对接。通过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采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将合格的毕业生直接输入企业,还可以明确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在课程教学方面,要推行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教学改革。一是要以具体的工作任务或要求来引导学生学习与实践,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以职业行为为导向,强化学生的职业理念,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17]。
再次,基于高等教育普职各自特色发展的基础,整合资源,调整布局。以结构融通打造教育发展新格局,搭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立交桥,推动多轨并行、交错互动、融汇共生。通过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等方式,完善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建设各类教育和产业企业密切合作的新生态,从而以两种教育类型高质量的协同创新助力面向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的培养。
(二)夯实目标,培养多元人才
高等教育只有以达成培养多元化人才的目标为基石,普职协同创新才能深入进行,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达成目标方面,究其本质,主要是明确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哈佛大学前校长劳威尔认为,“自由教育的最佳目标是培养知之甚广而在某一方面又知之甚深的人”[18]。这表明大学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1998年,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委员会在《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中提出,“研究型大学应通过一种综合教育”“造就出一种特殊的人才。这样的人将是下一个世纪科学、技术、学术、政治领域富于创造性的领袖”[19]。这进一步指出普通高等教育应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各行各业的拔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那么职业高等教育,则应在“通才”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和本领,促使其成为知识型技能人才。
鉴于此,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学生的多元教育需求,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使学生“就业有能力,升学有基础”,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要实现此目标,亟需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
一要满足人的多元需求,注重个体间的差异化培养。宽厚的科学基础、自由的兴趣发展是学生健康成长和取得突出成绩的重要因素。要发揮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优势,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来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通力合作来根除传统高等教育“流程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痼疾,避免陷入大规模、标准化人才培养的误区。
二要解构传统高等教育普职教学资源分别建设、彼此独立的旧格局,不再用固化的培养方式强制要求学生按照某种类型学习知识与发展技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指出,对于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高校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等。鉴于此,可以通过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促进各自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渗透和互相学习。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帮助学生发现自我兴趣、优势和潜力,从而培养一技之长。
(三)强化整合,建立协同机制
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实现,不仅需要有良好的协同理念,还有赖于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两类教育的资源配置、联结融通和机制运行提供有效的组织规范,以弥合冲突、凝聚合力。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应以人才培养为出发点,注重功能互补,强化整合,改革与完善现有制度体系,建立协同机制,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化的机制保障。
首先,要建立政策协同机制。我国政府应通过科学统筹和整体设计,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提供政策支持保障,明晰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目标定位、发展规划和实现途径,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系统进行规范,保障协同创新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一是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明确普职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对资源配置进行调控,使各方面工作的开展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要通过各种政策赋能,改变职业高等教育的公众认知和弱势局面,使之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可等值、可对比、可沟通、可衔接,促成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丰富生态[20]。以高技能人才为例,可以进行包括学徒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首席技师、科技技师等在内的制度设计[21],从而构建与普通高等教育对等的晋升体系。普、职高等教育只有势均力敌,才能真正形成联结融通、互学互鉴、协同创新的良好局面。
其次,要建立校际协同机制。在世界日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的趋势下,命运联结、资源共享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普职双向沟通,如定期的学术交流、联合研究项目、师生互访等方式,促进学术和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整合。一是完善学校组织机构设置,构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常态化机制,加强协同力度,保障合作质量,赋予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促进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紧密融合。二是加强高等普职教育资源的整合共享,提高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可以通过教学生产共时、技术资源共享、课程体系共构、课程学分互认、专业队伍共建、高校企业共育等路径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进行功能互补,不断加强两类教育的紧密联结[22]。
(四)加强维持,营造文化环境
默顿认为,“文化是由某一群体或社会主导其行为的社会成员们共有的组织化的规范价值”[23]。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会慢慢地将文化在人们的意识里扎根并影响他们的思考、感觉和行动。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文化环境是实现模式维持功能的重要保障。加强文化建设与内涵积淀,是推进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内在动力的核心环节,也是提升系统模式维持功能的关键所在。教育是提升全民素质的有效途径,社会成员是教育发展最广泛的受益主体之一。作为最庞大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社会成员不仅是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更是二者良性发展的监督者。随着人民对美好物质生活和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向往,社会成员对教育在类型、质量上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充分利用社会成员力量发展教育,就成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机制与路径选择。
首先,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使学生在文化环境的浸润中提高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的价值认同,并能依据自身兴趣与特长选择适宜的教育类型。
其次,企业要提高促进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责任意识,消除学历歧视,尊重人才,不唯学历论人才,而应把应聘人员的才干作为岗位胜任力的判断标准,为不同教育类型的高校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再次,社会要营造对各种职业同等认可与尊崇的文化环境。德意志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提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职业的不同只是劳动分工的不同[24]。黑格尔有言,“存在即合理”。因此,社会上的任何职业都有其存在价值,职业类型不同只是由于社会分工有别,职业本身是平等的。社会成员要一视同仁地看待和对待每一种职业,共同建设职业平等的社会文化,如此方能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接纳力,助力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发展。
最后,应发挥媒体舆论作用,构建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话语体系。可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开辟文化建设阵地,结合社会热点宣传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重要性与价值意义,推送具有价值引导作用的案例报道,并及时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技术攻关等信息,以网络为桥梁,将普职协同创新文化与学生情感倾向相耦合,从而使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理念在学生群体中扎根生长。
五、结论
统筹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亦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时代命题,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内在要求。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下,高等教育只有当适应性强、目标一致、功能互补、文化共育这四方面的功能共同发挥作用时,普职协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然而,普、职高等教育目前存在适应性不强、目标不一致、功能未互补、文化积淀不深等问题,系统功能尚未有效发挥。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需从增强适应,满足社会需求,培养多元人才,建立协同机制等多方面做出努力,进而促进高等教育普职协同创新的有序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玉静.新发展格局下的职普融通:价值与内涵[J].职业技术教育,2021(10):1.
[2]郝云亮.新職业教育法背景下普职融通的必要性、现实意义和实现路径[J].当代职业教育,2022(3):4-7.
[3]肖纲领,熊亮州.普职协调发展的价值意蕴、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2(22):13-17.
[4]丁关东,问清泓.从“分流”走向“融通”:职普协调发展的路径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2(19):48-54.
[5]李欣泽,匡瑛.“双通制”背景下高中阶段职普横向融通的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3):12-18.
[6]吴雪萍,陈浊,吕乐瑶.普职融通视域下英国T Level行动计划探究[J].比较教育学报,2023(1):17-32.
[7]孙进,郭荣梅.双向贯通交叉结合趋同融合——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融通的三种模式[J].中国高教研究,2022(2):76-82.
[8]吕杰昕,陈晨.高中阶段如何协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英国普职融通的经验与启示[J].比较教育学报,2022(4):29-41.
[9]喬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M].刘拥华,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60-61.
[10]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M].刘进,林午,李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7-18.
[11]陈新忠,董泽芳.高等教育规律“三分法”探析[J].江苏高教,2008(2):20-22.
[12]刘学燕.大学书院制改革的困境反思与路径优化——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22(4):119-127.
[13]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8.
[14]王建华.高等教育中优绩主义为什么会失败[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1-12.
[15]陈新忠,康诚轩.从招考分育到自由分流: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重构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4):61-67.
[16]罗布·斯通斯.核心社会学思想家:第3版[M].姚伟,李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315-318.
[17]宋正富.校企合作视角下德国“双元制”教育及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借鉴[J].中国高等教育,2018(23):61-62.
[18]BENTINCK-SMITH W.The Harvard book.350 anniversary edition[M].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22-23.
[19]刘宝存.国际视野下的研究型大学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141.
[20]张强.职普融通不应变成“单向输出”[EB/OL].(2022-12-02).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615650679215878.
[21]余晓.多地争揽技术人才,释放积极信号[EB/OL].(2022-10-1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044160679862172&wfr=spider&for=pc.
[22]梁克东,成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逻辑、特征与行动方略[J].教育与职业,2019(13):9-16.
[23]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M].刘拥华,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72.
[2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04-205.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KANG Cheng-xuan1, LI Bao-zhong2, CHEN Xin-zhong1
(1.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Coordinat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s a necessary way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talents, and is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strengthening talent support in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although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shown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incomplete realization of the adaptive function, the relatively lagging performance of the goal achievement function, the low release efficiency of the integration function,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triggered by the potential mode maintenance fun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eet social needs to enhance adaptation,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talents to consolidate goals, establish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integration, create a cultural environment to strengthen maintenance, and constantly accelerate the pa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the two.
Key words: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ordination of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