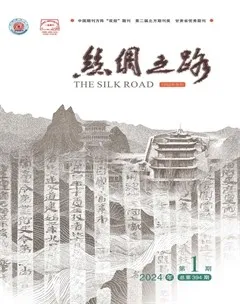戊己校尉命名与匈奴习俗关系考
崔广庆 杨航
[摘要] 关于戊己校尉的命名,古今学者的诠释大多立足于五行理论,也就是其衍生出的“居中说” “压胜说”和“寄治说”,但是这些诠释更多地是源自对颜师古注释《汉书》的个人解读,并且也不尽完善。本文结合匈奴长期控制西域的历史实情,认为匈奴的文化习俗对西域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匈奴社会“居中”的习俗在西域地区影响较大。西汉政府在经营西域之际,以“因其故俗”的管理模式,继承了匈奴社会的“居中”文化,而戊己校尉的命名就是这种文化继承的体现。
[关键词] 戊己校尉;命名;匈奴习俗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1-0027-07
一、五行理论诠释下的戊己校尉命名及其矛盾
关于戊己校尉的命名缘由,当今学者如余太山、林剑鸣、高荣、赵贞等人主要从“居中说”“压胜说”和“寄治说”三种理论予以诠释①。但是这三种诠释的最初源头均是从《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对“戊己校尉”的注解引申而出:
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1]738
其中“居中说”认为由于戊己校尉处在西域之中而抚诸国,他和天干的戊己一样都居于中间位置,所以借用戊己而命名。而“寄治说”则是认为如同天干中的戊己一样没有正位而附属其他天干,汉政府设置的戊己校尉也没有固定的治所,因其相同的状况而得名。“压胜说”的由来则是在《后汉书·西域传》总叙里唐章怀太子李贤等人关于戊己校尉的注释,他引用东汉应劲《汉官仪》一段话说:
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2]2910
对此清人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又进步一解释为:
西域在西为金,匈奴在北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3]
据此可知“压胜说”之依据为利用戊己在五行中属于“土”的属性而压制北方属于“水”的匈奴。虽然颜师古的注解中没有明确指明“压胜”思想,但是不难发现后世学者“压胜说”的理论来源依旧是颜师古注解中十天干生克的关系。
虽然由五行理论延伸的这三种诠释都能够自圆其说,但其缺陷依旧比较明显。首先“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这个表述是不恰当的,按《汉书·西域传》:
至元帝时, 复置戊己校尉, 屯田车师前王庭。[1]3874
这说明当时的“戊己校尉”并非“无常居”而是有固定的治所。其次,关于戊己校尉的作用,颜师古注言“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很明显他夸大了戊己校尉的作用。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言:“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而当时戊己校尉却是“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1]738,不仅设置的时间比西域都护晚,而且职級也比西域都护低。所以无论从设置时间的早晚,还是官职的大小来分析,西域都护均在戊己校尉之上,真正能够“抚诸国”的也只能是西域都护而不是戊己校尉。
综上可见,如果不能脱离颜师古所倡导的“五行”思维模式,从多角度考察和分析戊己校尉的得名显然是难以实现的。故而针对这种现象贾丛江先生也认为“这种秉持一义、不计其余的思维模式,背离了探求其真实名义的正确轨道”[4] 。所以,为了更为全面地诠释戊己校尉的得名,笔者认为应当摆脱“五行理论”的束缚而另辟蹊径。考虑到匈奴长期控制西域,为此笔者在此探索从匈奴习俗的角度对戊己校尉的命名做出新的诠释②。
二、“日上戊己”与匈奴的“居中”习俗
《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在介绍匈奴社会文化之际,都提到匈奴有“日上戊己”的习俗。对此解释,古今学者多是以择吉而论,如清人钱大昭就认为是“以戊己日为吉也”[5]。该依据主要是匈奴在戊日有祭祀天神的传统,按《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言“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2]2944。能够在一年中多次的戊日祭祀天神,显然这个时间是较为吉利的日期。但是为何匈奴社会会认为戊日是吉利的日期而选择“日上戊己”,笔者认为戊己既然是十天干的中间数字,所以他很有可能与匈奴的“居中”习俗有关。
在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代表的原始资料中匈奴的“居中”习俗体现得特别明显,如单于龙庭之位置居中③、对月中的尊崇④、重要的活动也放在一年之中间的五月份⑤。尤其是中间数字“五”,因其居中更是颇受匈奴的喜爱。如打仗的时候将军队划分为五个方阵并且单于在中央方阵⑥,此外匈奴最重要的诸侯王被称为“十角”,但是考虑到匈奴职官是左右对称,所以“十角”也仅仅是五个重要职官而已⑦。另外,匈奴单于在与汉帝的交往中所馈赠的礼物也是基于“五”而准备,如孝文帝四年,匈奴单于因为右贤王事件而赠送汉朝的礼物是“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駟”[6]2896而凑成五数。故而结合匈奴对中间数字“五”的偏爱,也就不难理解,发生在汉宣帝五凤元年为何是五位匈奴单于争夺正统。另外,按照汉朝的制度,匈奴朝贺一般是200人的队伍,但是在汉哀帝的时候匈奴贵族为了向汉哀帝表达尊崇特意上书请求“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1]3817。在此将人数由原先的200人提升到500人应该也是基于数字“五”在匈奴社会习俗中所喻意的吉祥含义。
另外,如果仔细分析《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日上戊己”这句话,其仅仅提到在“戊日”祭祀天神,而没有谈到“己日”有何特殊活动。对于这个问题,当今史学大家如吕思勉、杨树达等人在诠释“日上戊己”的时候也是仅仅引用“戊日祭天神”这句话,依旧没有诠释在此为何出现“尚己日”的原因。⑧对此,笔者认为这属于节日的代指,因为古人的重要节日活动一般都很少在一天之内完成。匈奴虽然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祭祀天神,但是由于活动状况盛大,有很多诸侯王来自遥远的地方,可以推测这种活动至少会持续到戊日的第二天己日。这种节日的代指事例可以参考唐朝的三元节,按顾炎武《日知录》卷3所引《册府元龟》载唐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
道家三元,诚有科诫。朕尝精意祷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兹……自今以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7]
再如《旧唐书·武宗本纪》也言:“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月不禁。”[8]也就是说在唐代三元的节日虽然是每个月的十五日,但实际情况却是十五日的前后一共三天之久。所以据此推测匈奴“戊日”开始的祭祀活动很有可能是持续到“己日”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匈奴的祭祀活动不仅仅是两天,而是“每月五、六、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匈奴以为吉日也”[9]。考虑到匈奴的“居中”习俗,以及匈奴人“相信战争的胜负受日月盈亏圆缺影响的观念”[10],在此笔者还是比较倾向于十五、十六这样的日期,而不是每个月都举行三次繁琐的祭祀活动。
总之,在匈奴社会中,无论是战争、祭祀、职官的设置还是王位的争夺,都隐含着“居中”这样的社会习俗。而十天干中的“戊己”又恰恰在其中间,考虑到匈奴社会习俗的特点,故而笔者认为将“日上戊己”视为是一种匈奴“居中”习俗的表现是比较合理的。
三、戊己校尉与“因其故俗”的文化承袭
在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因其故俗”“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因其俗而治”⑨这样的策略往往成为古代中原王朝管理西域的主要模式,故而综合当地的民情和习俗,也往往成为中原王朝在西域设置职官的一种文化特点,如唐代在西域设置的羁縻州,明代敕封哈密民族首领为忠顺王,清代在南疆推行的伯克制度等。前文笔者已经考述在匈奴社会中存在着“居中”的生活习俗,并且这种习俗的影响涉及祭祀、职官设置、分封、军事等诸多方面。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匈奴的“居中”习俗不仅流行于匈奴社会,而且在广袤的西域之地也很有可能普遍被遵循。因为在西汉政府设置都护控制西域之前,很多匈奴的习俗其实已经是西域诸国的“土俗”了,汉政府为了标榜与匈奴残暴统治的差异,除了将“僮仆都尉”更改为“西域都护”,还标榜“因其故俗”的治理模式来宣扬自己的仁义和德威,而戊己校尉的设置便是这种政策之下的产物。
(一)西域诸国对匈奴风俗的接纳
按《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76年写信给汉文帝,在信中夸赞自己“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6]2896。据此可视为“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为匈奴阻隔,西域尽为匈奴掌治”[11]。除了常规的接纳西域诸国质子之外⑩,为了有效地管理该区域,匈奴的日逐王还“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3872。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之后随着其控下的僮仆都尉逐渐瓦解,匈奴势力才基本上退出西域。
正是由于长期受匈奴的控制和文化渗透,原先本是与匈奴“异俗”?輥?輯?訛的西域诸国,在文化习俗方面也逐渐与匈奴趋同。如《汉书·西域传传》就记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1]3890 。另外,在《汉书·西域传》中还记载着与大月氏同俗(等同与匈奴同俗)的诸多小国:康居国“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1]3892,奄蔡国“与康居同俗”[1]3893,大宛国“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1]3894。再如西汉之际的乌孙是西域的一个大国,按《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他长期“故服匈奴”且“与匈奴同俗”[1]3901,而葱岭地区的一些国家如休循国、捐毒国、尉头国等国的习俗也多与乌孙一致,“民俗衣服类乌孙”[1]3897“衣服类乌孙”[1]3898成为描述他们习俗的常用语。
此外,由于长期受匈奴的控制和文化习俗渗透,西域诸国在政治制度方面也逐渐吸纳了匈奴的一些习俗,这些特点在西域诸国职官的设置和特殊数字“五”的流行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汉书·匈奴传》所言:“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1]3751据此可知匈奴职官的设置多以左右对称为特点。而《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各国的职官也多是左右对称,如疏勒国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1]3898,温宿国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译长各二人”[1]3910,龟兹国也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1]3911。再如乌孙国国王昆莫的婚姻也是“以(细君)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1]3903。如前文所考证,匈奴有“居中”習俗,故而在诸多制度文化中对中间数字“五”特别尊崇,而西域诸国受此影响也对数字五也有特别的喜爱之意。如大月氏征服大夏之后便在大夏国设“(凡)五翕侯,皆属大月氏”[1]3891;而羁事匈奴之康居国也设置有五个小王作为臣属之地[1]3894。
总之,在匈奴控制西域的百余年中,匈奴文化逐渐被西域诸国接纳,一些匈奴的习俗如“居中”等也逐渐成为西域诸国的习俗。在此背景之下中原王朝也逐渐有了一种“西域本属匈奴”的共识?輥?輰?訛,这一方面是基于匈奴对西域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估计也是基于现实中西域诸国与匈奴习俗文化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
(二)西汉政府对匈奴习俗的认知与利用
随着西汉与匈奴的交流交融不断推进,汉王朝对西域的了解和认知也在不断地加深,政府机构中“习知胡事”?輥?輱?訛的官员群体在不断地扩大,故而在处理西域的事务中他们肯定会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些官员除了提供军事、物产、交通、气候、水文等方面的情报之外,还会结合当地的生活习惯提出相关的建议供决策层参考。
如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昆邪王降汉,而汉政府对其安置则是分置为五个属国:“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1]176设置五个属国除了分离匈奴势力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匈奴有“居中”习俗,对数字“五”有迷恋。
再如,依据《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所言:“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12]中原王朝往往以“六军”出征以象征军队之威武,故而在早期的对匈奴战争中多以“六军”出征。如《汉书·武帝本纪》在元朔五年(前124)和元朔六年(前123)皆是“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1]171-172,以讨匈奴。但是随着汉王朝对匈奴习俗的了解,在以后的讨伐战争中也开始用“五军”以威慑匈奴。如《汉书·西域传》所载宣帝本始三年(前71) ,解忧公主和乌孙昆弥请求汉发兵击匈奴,结果“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而没有采取传统的“六军”。更为巧合的时候,乌孙昆弥为配合汉军作战“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1]3894,其军队也是以“五”为单元。
(三)戊己校尉的设置与匈奴的密切关联
首先,戊己校尉驻地在历史时期是匈奴控制新疆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1]3874车师前王庭在今吐鲁番一带,自匈奴控制西域以后,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一直都是匈奴重点经营的地方,如匈奴呼衍王和伊蠡王的驻牧地就分布在吐鲁番一带[13],除此之外匈奴日逐王所设置的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3872。其主要活动范围也在吐鲁番周边不远的环博斯腾湖一带。[14]52总之,戊己校尉的驻地在历史时期是匈奴重点经营的区域,经过百余年的控制,这一地区在习俗文化上是不可避免地被“匈奴化”。
其次,戊己校尉的设置除了显示与匈奴旧地设置的僮仆都尉的差异之外,也有着遵循当地社会习俗的“仁德”体现。西汉政府所设置之官职如“西域都护”之“护”就有保护、领护的含义,而匈奴管理西域的职官“僮仆都尉”,则明显带有匈奴人压迫西域诸国的政治色彩。并且这一称谓还是出自汉文的意译,很显然这种翻译明显带有贬损匈奴形象的意图,也就是说汉政府在介绍匈奴职官的时候“不排除其中有汉人否定和攻击匈奴西域活动的可能”[14]49。而戊己校尉这一职官的设置,如果从政治色彩上面考虑一定是和西域都护府一样带有保护或者尊重西域习俗的含义,而这层含义如果用中原地区流行的五行学说给予西域人民以诠释,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如果从尊重西域的习俗方面考虑,戊己校尉的称谓则有着强烈的政治寓意。因为这一地区长期受到匈奴的控制,他们的习俗更多地融合了匈奴的习俗,而匈奴则是以“居中”为尊贵,以“尚戊己”为吉利,这样“戊己校尉”体现的是“居中”的习俗内涵,反映的是尊重当地的习俗,这显然相较于以压迫为寓意的“僮仆都尉”更为得人心。
四、結语
由于匈奴长期控制西域,匈奴的习俗也逐渐渗透到西域诸国文化之中成为他们文化习俗的一部分,故而西域的文化又有着鲜明的匈奴文化色彩。而汉王朝在开拓边疆的进程中,为了巩固既有成果,设置政治喻意鲜明的职官和“因其故俗”的政治管理模式成为常用策略。戊己校尉的设置正是这一政治策略的体现,他继承了匈奴以及当地居民生活中的“居中”习俗,融合了西域文化特色。也正是由于他的名称融合了匈奴和西域诸国的文化习俗,不但对于稳定汉政府在当地的统治,而且在客观上对于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以及对大一统王朝的维护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 释]
①关于这三个理论的具体诠释,详见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1948年版,第185页;劳干:《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庆祝胡迪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53年版,第485-497页;余太山:《两汉西域戊己校尉考》,《史林》,1994年第1期;林剑鸣:《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高容:《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西域研究》,2000第2期;赵贞:《汉代戊己校尉阐释》,《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侯灿:《汉晋时期的西域戊己校尉》,《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
②学术界已经有些学者意识到戊己校尉的命名与匈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陈直先生言:“戊己校尉作为管理西域的一种官职,他的设立不应该仅仅考虑中原地区的官职命名原则,也应该考虑到他的西域地域属性以及其中的匈奴文化因素。”(见《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页)再如张碧波、董国尧两位学者也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中认为“元帝时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这是汉人从匈奴习俗而取名”。虽然这些学者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出他们之间的关联,但是却缺乏详细的考证,让人引以为憾。
③按《史记·匈奴列传》匈奴一共立有左右“二十四长”,其中左方的王将居住在东方,右方的王将则居住在西方,而单于之王庭则位于中间,也就是汉王朝的代郡、云中郡之北。
④《史记·匈奴列传》言匈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92页)。据此可知匈奴重要的活动尤其是战争都是在每月的中旬月盛之际。
⑤《史记·匈奴列传》:“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第2892页)这三次大的集会又以五月份最为重要,而五月即一年之中(古人称五月为“天中”,如明代田汝诚《西湖游览志余》所言“端午为天中节”,就是认为五月五日太阳行至中天,达到最高点,午时尤然,故谓之“天中节”)。
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围困汉高祖的时候“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第2894页),若加上匈奴单于的方阵则恰好是五个方阵。
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在论述窦宪、耿夔追击匈奴的战果之际写道:“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00页)《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言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第2944页) 。
⑧杨树达:《汉书窥管》,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45页;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58页。
⑨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浑邪王降汉之后,汉王朝“因其故俗”为属国(第2934页), 于此《资治通鉴》中也写道:“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599页)再如清人稽璜在《皇朝通典》 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延袤万余里,各设三品至七品伯克管理回务,皆因其俗而治之。”(浙江书局,光绪八年影印本,卷73)
⑩按《汉书·西域传》楼兰国“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877页);康居国“东羁事匈奴”(第3892页);又《汉书·匈奴传》:“乌禅幕者,本乌苏、康居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第3790页)再如《汉书·西域传》宣帝时,车师降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第3922页)。并且这项举措发生在汉哀帝建平二年,当时匈奴已经对汉称臣之际,而车师迫于匈奴的威力依旧向其派遣质子。
11《汉书·西域传》言:“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第3872页)
12《汉书·陈汤传》:“(陈汤)与延寿谋曰……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第3010頁)
13《史记·韩长孺列传》:“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第2861页)《史记·匈奴传》汉武帝时候有“王乌,北地人,习胡俗”(第2931页)。《史记·佞幸列传》也记载:“上(武帝)即位,欲事伐匈奴,而(韩)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第3194页)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清)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M].清道光九年张琦刻本.
[4]贾丛江.西汉戊己校尉的名和实[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04):37.
[5](清)钱大昭.汉书辩疑.青铜熨斗斋丛书[Z].清刻本.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清)顾炎武.日知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1308.
[8](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99.
[9]田澍,李清凌.西北史研究(第三辑2)[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423.
[10]胡小鹏,张嵘,张荣.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27.
[11]邵台新.汉代对西域的经营[M].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5:44.
[12](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2237.
[13]林幹.匈奴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39-40.
[14]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M].北京:中国社科科学出版社,2019.
——探访酿名斋郭勇孝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