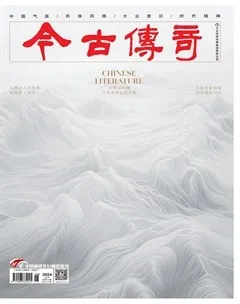范仲淹在邓州
阳春
在来邓州之前,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好奇:这该是一个怎样神奇的地方啊?让范仲淹对它流连忘返、依依不舍,并且在这里写下了震烁古今的名篇《岳阳楼记》!
我的好奇,跟随着我一起来到了邓州。短短两天的行程里,伴随着当地文化学者的讲解,白天一步步实地参观了重修的花洲书院,晚间在夜市摊点上感受着当地淳朴的烟火气息,我此前的种种好奇仿佛也得到了答案。
范仲淹无疑是中华历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人,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曾经称赞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有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能文能武号称无所不能的“全才”,竟然还是一个“刺头”和“杠精”呢?充斥在他前半生里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不和解”!
我能想象得到范仲淹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心路历程。
他拥有的是一个“稀碎”的童年:两岁跟随寡母改嫁到朱氏,得名朱说。待他懂事后,朱家子弟直言,你不是我们朱家的后代,不配享受我们的钱财。范仲淹听完后默然离开继父的家,居住在寺庙里苦读,期待有一天能金榜题名。
那个时候,在寺庙里每天只喝一碗稀粥的范仲淹,作为寒门学子的榜样,亲力亲为地为后世读书人创造了一个成语——断齑画粥;那个时候,面对唯有读书才能改变自身命运的范仲淹,期待“东华门唱名”那一天的到来,以求改姓归宗、迎母侍养;那个时候的范仲淹,就像一棵被大风吹到悬崖峭壁上的小树苗,有可能存活,但是几乎不可能成长为栋梁之材。我甚至能想象得到,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范仲淹,没有心理扭曲、行事偏激,已经算是侥幸了。
事实上,这种环境下的副作用还是很突出的。那就是成年之后特别是科举高中后的范仲淹一直以“怼人”的模式存在于朝廷之中。章献太后刘娥执掌朝政的时候,范仲淹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结果是范仲淹被贬。刘娥去世,仁宗执政后,将范仲淹召回。让仁宗想不到的是,范仲淹这个“自己人”,返京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怼自己”:仁宗要废黜郭皇后,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竟是范仲淹。没办法,范仲淹继续被贬。
好在,三年后返回开封担任京兆尹的范仲淹这次怼的对象不再是皇帝仁宗了,而是一人之下的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进献百官图,直指吕夷简任人唯私。好吧,范仲淹,您继续被贬。
为此,好友梅尧臣写诗劝他不要当个啄木鸟,他写《灵乌赋》答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就是范仲淹的个性。当然了,有本事的人不会永远沉默。当大宋与西夏边境战事爆发后,范仲淹再一次被仁宗征召,经略陕西。当西线战事逐渐平静下来之后,范仲淹终于迎来了仕途上的最高光——返京担任枢密院副使,后拜参知政事,这是副相的职位。
然而,这既是范仲淹仕途的巅峰时刻,也是他彻底走向落幕的开始。担任副相的范仲淹这次“怼”的对象不再是临朝执政的太后、仁宗和宰相,而是整个执政体系——他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庆历新政。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一年的时间,庆历新政失败,改革人物纷纷被贬斥出京。也就在这个时候,范仲淹想起了邓州,把这个地方当作了自己舔伤休养的蛰伏之地。
庆历五年正月,五十七岁的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后,向宋仁宗上《陈乞邓州状》求解边任,“伏望圣慈恕臣之无功,察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访良医,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邓之间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
范仲淹向往邓州的理由很充分:我的肺病一到了秋冬就发作,希望您让我去邓州附近寻医疗养。
邓州,北宋的京辅之地,也是一代名医张仲景的故乡。按照医术代代相传的习俗,去名医的家乡寻找治病良方肯定是个不错的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邓州“六山障列,七水环流,舟车会通,地称陆海”,本身就是一个适宜病人疗养的好地方。
就这样,拖着带病之身,范仲淹于庆历五年十月十四日,带着体弱的长子范纯祐从陕西邠州南下,赴任邓州。
这一刻,是范仲淹的幸运。这一刻,是邓州的幸运。这一刻,是滕子京和岳阳楼的幸运。这一刻,更是范仲淹之后中華民族千千万万读书人的幸运。
知邓州的第二年也即庆历六年六月十五日,范仲淹收到了至交滕子京的书信,滕子京在信中请求老友为他新修的岳阳楼写一篇记文。担心范仲淹拒绝,滕子京在信中言辞恳切,并且带上了“感情绑架”的句子,“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甚至害怕范仲淹找理由推辞,他还妥帖地附上了《洞庭秋晚图》供其参照。
滕子京不愧是范仲淹的至交,他深知此时的范仲淹也许有些心灰意冷,更不想在诗词歌赋上鼓捣些是非风云。毕竟,此时的范仲淹已经五十八岁了。多次贬谪的宦海沉浮,加上肺病缠身,已经让这个当年的“刺头”少了许多棱角。这从他近些年在西北戍边的诗词里可见一斑:无论是《渔家傲·秋思》里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还是《苏幕遮·碧云天》里的“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都可以看出此时的范仲淹不再有少年的蓬勃朝气,而更像一个思念故乡的垂垂老者。
那么,范仲淹的故乡又是哪里呢?是他的祖籍陕西邠州?是父亲生活的江苏吴县?是继父朱氏生活的山东长山?或者是青少年读书时候的河南商丘?都不是。这一刻,范仲淹真的是把寄身的邓州当作了自己的家乡。
在邓州,范仲淹把昔日供达官贵人游玩的百花洲景区改造成花洲书院,以知州的身份,公务之余亲自授课讲学。在邓州,范仲淹在原配去世多年后,还迎娶了新婚妻子,并且诞下了第四个儿子范纯粹。一切的一切,都表明此刻的范仲淹似乎有醉心传道授业、享受天伦之乐、寄情山水之间的退休状态。
那么,不给滕子京写关于岳阳楼的记文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事实是,范仲淹真的没有给滕子京写这篇记文。至少是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范仲淹没有去动笔。
也许,范仲淹真的是倦了前半生的贬谪流离,也厌了庙堂上的唇枪舌剑、边塞上的刀光剑影。假设没有三个月后的那场惊雷,假设没有被惊雷震醒后的胸怀激荡,假设没有激荡后的奋笔疾书,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么丰满的范仲淹了。
也许岳阳楼在国人心目中的美名要直接腰斩一半。
也许邓州就会变得平淡无奇,只是范仲淹贬谪路上众多地名中不起眼的一个,而不是现在伴随在范仲淹身边最璀璨夺目的那一颗明星。
如果说苏轼一生功业尽在“黄州惠州儋州”,而范仲淹一个“邓州”就足以媲美。
好在,没有出现假设。那场惊雷在三个月后的九月十五日还是降临了,伴随而来的还有那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那一出现就震动北宋文坛的《岳阳楼记》,那让此后数百年间所有读书人慷慨激昂的《岳阳楼记》,那让今天所有中学生必须背诵的《岳阳楼记》,就这样在邓州花洲书院诞生了。
果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还是那个“自带光芒不畏权贵”的“愣头青”,还是《宋史》记载中那个“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刺头”。
当然,和此前自己那些锋芒毕露的谏言不同,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虽然去掉了尖刺,却依旧内蕴犀利,仿佛红彤彤的铁块经过淬火后变成了坚韧的精钢。
或许邓州,就是让范仲淹淬去火气的那潭冷水。
三十多年后,苏东坡写下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词句。
邓州,即是范仲淹的“吾乡”。
(责任编辑 丁怡1596371626@qq.com)
也许,范仲淹真的是倦了前半生的贬谪流离,也厌了庙堂上的唇枪舌剑、边塞上的刀光剑影。假设没有三个月后的那场惊雷,假设没有被惊雷震醒后的胸怀激荡,假设没有激荡后的奋笔疾书,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么丰满的范仲淹了。
- 今古传奇·当代文学的其它文章
- 失踪的父亲
- 访谈
- 天山,苍茫的不只是明月
- 去天山
- 天山行
- 日常生活的审美反思与吟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