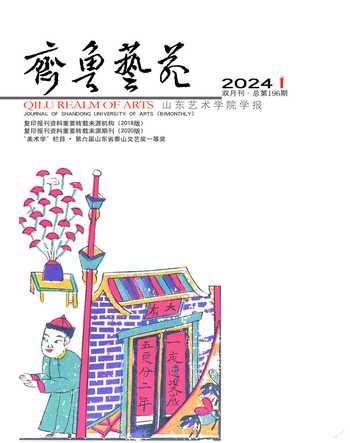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传承创新研究论纲
摘 要:遵循“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整理、挖掘、阐发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中的丰富内涵,分析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文艺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价值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对于新时代文艺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文艺价值的视角看,当前文艺作品尚存在着价值尺度失范的现象;创作者层面,一些文艺创作者卷入功名利禄的追逐;理念层面,未能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当代的文艺价值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末、90年代初较为繁盛,已有成果从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哲学基础、结构特点、理论体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已有成果梳理的较多,系统研究、研究的体系性与深度尚嫌不足;与新的时代结合,立足于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进行现代传承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多见。中国传统文论中有丰富的文艺价值创造思想,富含积极入世、勇于探取社会人生的艺术献身精神,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当前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有重要借鉴作用,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本位观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文艺良知与责任的文艺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质兼美”的精品意识。同时,要在研究中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与其他民族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236(2024)01-0004-07
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实现文艺的繁荣发展,是文艺理论研究者面对的时代命题。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在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历史时刻,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希望、发出号召:“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1]
对照这些“希望”,当下中国文艺发展、文艺研究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文艺价值思想尤其值得关注。文艺作品是一个民族精神特质、文明水平的集中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对社会进步有着强大的引领作用。文艺价值研究,涉及到文艺意义的阐发、文艺理想的设立、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重要问题,在文艺研究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2]这是对文艺价值的高度概括和充分强调。时代发展,推进价值观念变革。新时代的文艺繁荣,要在“高原”的基础上多出“高峰”,亟需建构新时代的文艺价值体系。新文艺价值体系的建构,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里面内含的是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传承创新。遵循“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整理、挖掘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的丰富内涵,分析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文艺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艺价值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对于新时代文艺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当下中国文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走出了文化贫瘠,几亿人欣赏几种文艺作品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近些年来,文艺作品的数量与日俱增,每年单单是长篇小说的出版产量便已达几千部之多,海量的网络文艺作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可堪称世界上第一文艺大国。同时,毋庸讳言,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有些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3]这些问题,目前依然或多或少的存在。
文艺界的这些现象,与文艺价值问题息息相关。主要表现为:
其一,作品层面,存在着价值尺度失范的现象。一些作品渲染血腥、暴力和下半身叙事,强调人性的阴暗面,鼓吹阴谋论,炫富斗狠、编织消费主义神话,以强化肮脏丑陋博取眼球,裸文化、暴力文化、偷文化、鬼神文化、泛娱乐文化、不良语言文化、炫文化、星文化、门文化、洋文化、假文化、丑文化、贱文化等内容时有出现。
其二,创作者层面,一些文艺创作者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诱惑,卷入功名利禄的追逐,成为“见书不见人,见人不见书”的空头文艺者,没有时间和精力深深扎根生活,不了解人民大众的疾苦和悲欢,不了解社会的发展变化,不能深入思考、认真阅读、艰辛书写,未能沉下心来反复打磨、精于创造。
其三,理念层面,未能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一些作品中,“人民”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文艺成了市场的奴隶,混淆了低俗与通俗、欲望与希望。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渗入文艺,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一些文艺工作者。
以上问题虽是在部分作品中存在,但危害严重,值得警惕。
二、包括文艺价值问题在内的中国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价值”是经济学上一个特定的范畴,在一般意义上泛指物质或现象对人和社会的用途、作用或意义。自人类从动物界独立出来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逐渐形成了诸种对象性的主客体关系,人对自然、社会、自身进行评价,价值便开始出现。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哲学具有“价值论”的特色。“我國自古以来的哲学传统,习惯于以‘天、地、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以构建种种关于社会、国家的伦理政治体系为目标来进行理论思考。作为这一传统证据的是:历来在各家学说中,最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往往是诸如‘道德‘仁义‘善恶‘美丑‘贵贱‘吉凶‘祸福等这类价值范畴,而不是欧洲哲学中最常见的‘存在‘实体‘理性‘经验‘知识‘真理等存在论和知识论范畴。也就是说,与欧洲的哲学传统相比,中国哲学更具有以一种以价值哲学为主要线索的传统。”[4](P1)虽然价值论在19世纪下半叶才初步确立,但价值论的思想古已有之;价值论哲学诞生于西方,但价值论方面的思想、论述中西皆有。
文艺活动是一种具有强烈审美性的审美活动,与价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在许多文论家、文艺家看来,文艺活动就是一种价值活动,而不是认识活动或其他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据主流,讲求经世致用,在这一思想看来,文艺是育人的重要方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经过文艺化育的合格的“大人”“士”,才能承担起安邦治国的大任,于是有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有了汉代的“美刺”说。汉代的王充所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是这一传统极好的注脚。
中国当代的文艺价值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较为繁盛。除在文艺理论史、美学史、相关领域的资料,汇编汇聚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外,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数部文艺价值研究的著作,其中以敏泽、党圣元的《文学价值论》最具代表性。该书对中西各个历史时期文学价值观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梳理,而且对中西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价值思想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论在史料的开拓还是意义的判定上,都多有新的发现和建树,尤其是十分注意把握和开掘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思想精华,对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价值论思想、建设文学价值理论只能取材于西方的虚无主义观点,不啻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已有成果从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哲学基础、结构特点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李西建《中国古代文艺功能观的文化学分析》(1989),从文化学的角度立论,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艺观一开始就与政治目的相结合,构成了一条融合文艺诸功能、使其为历代统治服务的发展主线,并认为这与中华民族“政治—心理”模式、“伦理—心理”模式、“实用—心理”模式密切相关。(参见:李西建.中国古代文艺功能观的文化学分析[J].人文杂志,1989,(1)。)谭帆的《试析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价值观念》(1991)提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具有“功利性”“宣泄性”“享乐性”三种价值观念,并从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艺价值观念具有“功利性”逐步与“宣泄性”融合、“享乐性”向“娱乐性”转移两个发展趋势。(参见:谭帆.试析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价值观念[J].文艺理论研究,1991,(4)。)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艺价值结构的基本类型及其解释框架》(2010),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的并列型价值结构、等级型价值结构、层深型价值结构、有机型价值结构、主次型价值结构等,并提出其解释框架主要有二元对立解释框架、生态式解释框架及体、相、用解释框架,是对中国文艺价值思想的研究深入。(参见: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艺价值结构的基本类型及其解释框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黄海澄的《艺术价值论》(1993)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探讨建立在传统认识论哲学基础上的文艺学的危机,将价值论作为文艺学新的哲学基础。颜翔林的《论价值与艺术价值的逻辑关系》(1994)、《艺术与时间:对艺术价值的美学怀疑论》(1994)则是从怀疑论的角度将文艺价值界定为在一定时间维度的受民族性制约的主观伦理判断和情感倾向对于文艺的评价。曲本陆的《文学价值结构及其功能系统》(1994)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命题入手,提出了“中介”这一范畴,认为文学活动及其价值结构统一的“中介”是审美。杨曾宪的《文化审美价值距离与“难能为美”》(1997)从价值学角度探讨美的本质和规律,探讨审美价值。
已有研究取得多方面的进展,为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尚存在如下不足:其一,对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梳理得多,系统研究、深入研究的成果还较为少见;其二,已有成果多集中在20世纪末,与新的时代结合,立足于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进行现代传承创新,尤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谭好哲的《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的思想谱系与理论积淀》(2021),是近年来研究文艺价值思想的一篇力作。这篇文章虽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问题,但文章提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思想在理论逻辑上认同并持续强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文艺本质观,在文艺价值源泉的理论追索中建构起了文艺与时代生活之间的辩证反映关系,在文艺价值的主体归属上把人民需要作为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才成为了指引中国现代文艺走向进步、服务人民的思想火炬与灯塔,这一认识为中国文艺价值思想传承创新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借鉴。
三、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中汲取丰富营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根本特征。人类文明在发轫之初,世界各个地域就显示出不同的文明特色。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世俗性、人文性、伦理性、和谐性为基本特征的文化体系。梁启超曾说道:“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6](P2-3)在全球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维系民族共同生命的最根本力量。在此意义上,民族的生命力和文化的生命力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的发展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强盛总是以文化为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虽历经磨难,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贡献巨大。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影响巨大。朝鲜半岛古有“小中华”之称。日本也是“东亚汉文化圈”的成员国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日本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7](P215)除了东亚地区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南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重要影响。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到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当今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蕴含着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丰厚滋养。以儒学为例,儒家文化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表述,不只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宝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化共同体及其历史发展,有着深切的文化认知与实践,同样蕴含着大量丰富的共同理念与价值旨归。
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资源丰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艺价值思想体系最为完整,影响最为深远。孔子主张以礼乐的方式建立一个“仁爱”的社会,认为文艺具有独特的审美认识、审美教化之用,可助力国家长治久安,可助人修身养性。兴、观、群、怨,可看作儒家提出的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开山纲领”,主张文艺作品通过艺术所描绘的形象,使人联想到一种事理和人的精神品质,从而产生一种鼓舞人的意志的力量;书写民众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考见政教之得失;传达充满情感色彩的“仁”道,把人们“结为一体”的;揭露当政者非“仁”之处,以刺上政。“美刺”说,与“兴观群怨”说本质上一致,但更突出了文艺的政治效用,强调文艺要服务于治国安邦的需要,也加强突出了“刺上政”的价值,“泄导人情”“补察时政”。要发挥好文学的怨刺功能,必须把握好分寸,“发乎情,止乎礼义”,“怨而不怒”。儒家思想主张文艺家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艺要具有“劝善惩恶”的价值,“论功颂德”,是为了导人为“善”;“刺过讥失”,是为了“使闻之者足戒”。“劝善惩恶”说原出于儒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吸收了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并与之相融合,影响广泛。兴、观、群、怨说和美刺说、劝善惩恶说,从不同角度突显了文艺的价值,与西方注重个人情感不同,更侧重于政治伦理性。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文艺的衡文标准,除“文质彬彬”等被人熟知的观念外,“老”“清雕琢”“高致”是非常独特的观念。中国文论中有着丰富的文艺价值创造的思想,其中,“胆”讲求“智”和“勇”的结合,体现出积极入世、勇于探取社会人生的艺术献身精神,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四、以中华美学精神为核心推进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传承创新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8]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基铸魂,文艺才能高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华美学特质,将人民当作文艺表现的主体和服务对象,将爱国主义当作主旋律,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当前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有重要借鉴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给予了许多新的阐释,特别是提出了“中华美学精神”概念,强化了中国优秀文艺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作用。习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9]的優秀作品。讲话所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再一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底色、根基与取向,指引当下的文艺理论建设要充满中国的文化元素和理论色彩,杜绝用西方标准来剪裁和衡量我国文艺和文艺作品,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切实落到实处。讲话中还涉及了诸如“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质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美的发现”“美的创造”“美学精神”等许多美学范畴和词汇,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表述增加了美学光泽,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
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本位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10]。这一论断脱胎于经典的“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增加了“人民的”和“艺术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触及批评的立场性判断,又关涉批评的专业性强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内涵和意蕴的丰富。这一观点比之于传统文艺理论只谈“内容”和“形式”的观点,也明显地推进了一步。此外,讲话还提出“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11]。这句话同马克思说过的“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讲话把“够不够资格”的角度,变成了“审美”鉴赏的角度,把“判断者”变成了“鉴赏家”和“评判者”,而且把人民放在了文艺作品鉴赏、评判主体的位置上,具有了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由人本学立场到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确认的转变,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人民的丰富实践和现实生活“感同身受”,在真正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培养对人民的感情,不沉缅于个人内心的“杯水风波”,牢记人民的冷暖,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于创作的笔端,坚持发现美、创造美,赞美奋斗人生,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文艺良知与责任的文艺观。讲话批判过度文化消费主义,强调文艺创作的良知与责任,主张文艺作品在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时,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消费主义主张,文艺创作以获取市场利益为目的,以大众的娱乐需要为价值导向,文艺的经济价值追求超过甚至取代文艺价值追求,文化产品的娱乐功能超过乃至排斥审美功能、精神教化功能。文化消费主义有两大特征:重视文艺产品的娱乐性,主张文艺产品的机械式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批评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12]恰是文化消费主义在当前文艺活动中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益,孔子把文艺的社会效能概括为兴、观、群、怨四个字,通过文艺可以“观风俗之盛衰”“考见政治之得失”,文章期于用世,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中国传统文论格外强调文艺的修身作用,孔子曾把“修身”分为三个阶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使初学者懂得好善与厌恶之情,乐则可以调和、沟通人与人之间、对立阶级之间感情,使人情感上得到升华,走向成熟。汉人班固《汉书·礼乐志》中有:“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唐人白居易则在《与元九书》中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宋代的李觏在《上宋舍人书》中把文艺化的功能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窃谓文之于化人也深矣。虽五声八音,或雅或郑,纳诸听闻,而沦入心窍,不是过也。尝试从事于简策间:其读虚无之书,则心颓然而厌于世;观军阵之法,则心奋起而轻其生;味纵横之说,则思诡谲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学,则憙苛刻而泥廉隅;诵隐遁之说,则意先驰于水石;咏宫体之辞,则志不出于奁匣:文见于外,心动乎内,百变而百从之矣。”儒家讲求诗言志、文以载道、劝善惩恶,道家讲求心斋坐忘、澄怀味象,都是以文艺社会效益的强调。同样,马克思主义对过度的文化主义也持批判态度。马克思指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產不同……资本主义生产就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批判了标准化、程序化的文艺生产抛弃了艺术性,被彻底世俗化、均质化、商业化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要创作“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的好的文艺作品。[1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艺创作不考虑作品的经济效益不可能也不现实。但在过度消费主义有抬头趋势的今天,作家要有更强的定力,严肃认真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把审美理想放在核心位置,以高尚的道德情操赢得读者的尊重。要认清并处理好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珍惜而非滥用创作自由,在承担应有的责任基础上来谈论创作自由。要认真探究、真正掌握文艺传播的市场规律,使优秀作品能够受读者欢迎,赢得市场。
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质兼美”的精品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创作者要创作出文艺精品,提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14]的艺术标准。“文质兼美”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文艺命题。孔子曾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后来,孔子将这一标准逐渐从对人物的品评演化为对文艺作品的评论。《论语·述而》篇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之好在于“尽善矣,又尽美也。”他批评《武》乐则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善的东西要成为审美对象,还必须在艺术形式上具有审美价值,否则便不能称其为文艺作品。东汉王充“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清代王夫之说“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晚清刘熙载 “凡物之文见乎外者,无不以质有其内也”的说法都与此一脉相承。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未来戏剧的理想,即“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期盼的也是“文质兼美”的艺术作品,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文艺精品能够具有强大的动人力量,源于其深刻思想内涵与优秀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作家要坚持高标准的艺术追求,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强调的,把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动活泼”“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相结合,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
五、深化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传承创新研究应该科学处理几对关系
一是科学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范畴。传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式”概念,更是指与现在相关、汇入当下并对现实产生意义和价值的“有生命的”过去。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文艺价值思想传承创新研究,助力文艺发展繁荣,应着重注意:其一,加强甄别、去粗取精。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既不能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其不加甄别地照单全收,从而困于“文化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编织的文化囚笼;也不能以“全盘否定”的眼光对其毫无保留地弃如敝履,从而裹进“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搅起的文化旋涡,将优秀文化成果和价值理念从传统文化中甄别遴选出来,并根据当代文艺发展需求,使之转化提升为适应新时代的新内容与新形式。其二,搜集整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价值论色彩,中国文艺价值思想资深丰富,但目前还散见在文论史、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中,未能有效汇聚,更未能形成体系,需下功夫整理挖掘。其三,开阔视野,充分利用。要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与价值,就必须让传统“活”起来,让其焕发新的生机。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研究,不但要面向时代,还要面向世界,汲取其他民族相关优秀文化的营养。充分利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推进相关资料的搜集、保护、发展。
二是科学处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原始基因、核心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当代文艺发展相协调。创造性转化是以服务现实为旨归,按照时代需要、当代标准改造传统文化的功能、价值和目标,与现代社会接轨、与人民需求合拍,实现传统文化在核心理念、实质内容和表达形式等方面的现代转型,达到为今天所用、为今人所用、为现实所用的目的。创新性发展则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以现代化和现实需要为原则,提炼出融入现代社会形态的新内容,在现实条件下致力于文化提升和思想超越,并在充分尊重传统特长和思维优势的基础上求解当今时代问题的文化方案。要以文艺发展实践需要为研究导向。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转化与创新并非某些范畴或精神的抽象归纳,也不是传统典籍的引用言说,而是将其思想精华融入当下文艺实践中来,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文艺发展提供借鉴。
三是科学处理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与其他民族文艺思想的关系。文化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其中超越时代与国别、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又要剔除其落后于时代的糟粕,还要增进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互鉴。同时,坚决反对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毫无原则地厚今薄古、闭门自守的夜郎自大。不忘本来,始终坚守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民族主体性。吸收外来,广泛借鉴世界多元优秀文化成果。面向未来,建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价值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文艺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國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3][8][9][10][11][12][13][1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5-10-15)[2023-05-06].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15/c1024-27698943.html.
[4]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5]新华社.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3-06-02)[2023-08-15].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4316.htm.
[6]梁启超.儒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7][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杜 娟)
收稿日期:2023-09-02
作者简介:孙书文,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学。
项目来源: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传承创新研究”(18BA016)的阶段性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24.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