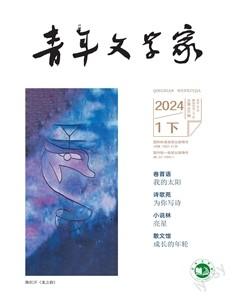论清代彝族诗人余家驹对陶渊明田园诗的接受
杨卓 钱昊东
清代彝族诗人余家驹对陶渊明的田园诗的创作接受,源于他对自然生活的向往和对陶渊明的钦服。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内容多描写平淡的田园风光,或记录朴实的农村生活。诗中隐逸的心境和生活的情趣,高洁的人格和美好的意愿,一直为后世文人所尊崇和學习。余家驹归隐后的田园生活与陶渊明有着极大相似之处,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创作基础。他的田园诗除了对陶渊明诗风的接受外,还流露出文人士子独有的美学思想和精神追求,具有独特的诗学审美价值和重要的研究价值。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在归隐后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其内容多以农家生活为主,或写农家的平淡祥和,或描田园的优美静谧,或赞农人的淳朴率真,或抒精神的自由不羁。余家驹祖上七代世居贵州毕节大屯,他科考取得贡生身份之后再无心仕途,回家侍奉母亲颐养天年。他自幼深受汉文化熏陶,儒家的士子情怀和孝悌人伦深入其心。他对历史文化名人如数家珍,尤以陶渊明对其影响最为深远。余家驹归家之后耕读度日,寻亲访友之余,以读书、吟诗、饮酒作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目前,黄瑜华先生校注出版的《时园诗草》一共收录了他384首诗,有近60首描写田园风光和记录田园生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思想造就了余家驹“于功名富贵,听其自然,莫习奔竞”(《云山雾雨黔中气,亦道亦佛亦文章—余家驹诗歌初探》)的文人清高,也造就了他别具一格的田园诗风—平淡中流露出唯美,唯美中透出深沉,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研习他的田园诗,了解他的文人精神,有助于我们认识清代黔西北地区的文人风貌。
一、田园精神的接受
余家驹的田园诗上承陶渊明,也受晋代以来的诸家影响,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田园诗多为描写黔西北田园景观和风土人情,囊括了他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认识,蕴含了文人独特的审美体验,也寄予了他至情至性的人格特征。他笔下的山林清泉和农事生活,平淡中夹杂几分清奇,高雅中不离人间烟火。诗歌语言平淡自然,风格质朴不假雕饰。其田园诗写物、记事、抒怀不滞于物,情感热烈却又张弛有度,无论从文人精神上,还是从取材技法上,明显有着对陶渊明诗学接受的痕迹。
余家驹世居黔西北,虽地处西南边陲,但是在家学的深远影响下,深爱汉文化的他,自幼熟读经、史、子、集。中原的传统文化和文人精神深入其心,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播下了种子。他归隐林泉居家耕读,除了“孝必躬亲”侍奉母亲的原因外,也源于他不受世俗和官场束缚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多是受自陶渊明以来的隐逸思想所影响。他在《甘隐篇》中就表达了自己甘于归隐,不趋名逐利的隐逸情怀:“世人趋名利,所学在干禄。及至登仕途,患得失荣辱。时刻撄其心,戚戚复碌碌。喜怒不自由,行止受人束。赵孟贵贱之,祸福同转烛。所以托沉冥,于焉在空谷。如鱼求深渊,如鸟择高木。饱道全天真,清新寡嗜欲。尚友古之人,悠然靡不足。”诗人先说世人争名夺利,一生所学皆是“干禄”;次说贪图功名之人不自由,后将《孟子·告子上》中“赵孟”之贵与杜甫《佳人》诗“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中的“转烛”作比,得出富贵不可长久,世事变幻莫测的总结;再把“鱼求深渊”“鸟择高木”和“抱道”“天真”对比,得出清心寡欲才是自己的追求;最后自况“尚友古人”庄子、陶渊明之辈,比之“悠然不足”。可见余家驹的归隐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看透世事变幻莫测的本质之后,知道富贵不可久,不如归隐后的自娱自乐来得逍遥自在。
余家驹乐于田园,不仅是天性的回归,还在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同样也是诗人向往的精神家园。纵观余家驹的一生,不仅没有他出仕的任何文字记录,诗歌里也没有流露出他渴望仕途的意愿,他骨子里流淌着士人“隐逸精神”的血液。他在《桃林》一诗中尽享隐逸之乐,在深山桃林里甚至到了“忘我”“无我”的境界。其诗曰:“闲赏兴自高,步入深山处。山深无居人,十里桃花树。花落舞缤纷,清风悠扬度。红堆三尺深,迷却来时路。”此诗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意象。诗人兴致所临,独步深山。清静无人的深处,有十里桃花。清风过处,落英缤纷,红堆三尺。诗人浑然不觉,迷失其中,忘却归路,在清风落红中怡然自乐,浑然忘我。“红堆三尺深,迷却来时路”于平淡之处见精神,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之味。
此外,古代文人受“酒”文化的影响颇深,陶渊明更是爱酒如命。他流传于世的二十首《饮酒》诗,自然地揭示了生命深层的本真状态,体现了独特的生命领悟和审美境界。余家驹颇有古人饮酒之风,再加上天性不羁,饮酒也是他田园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他的《饮酒》诗写自己饮酒如同战斗,可以消愁解忧,且诗酒相酌,吟风弄月间纵横捭阖,这何尝不是他对生命的一种领悟?其诗曰:“劲酒如劲兵,一战愁城破。操此全胜威,锐气那能挫。花园诗催战,贾勇纵横过。凯歌入醉乡,风月争来贺。功成封华胥,倒偃酒旗卧。”在余家驹看来,饮酒如同战破“愁城”,“锐气”侧露,“凯歌入醉”后想象“风月争贺”,倒地醉卧在酒家。这不是狂饮烂醉,是一种对“酒”的理解和升华,是自己性格洒脱不羁的真情流露。敢于把自己醉后的情形描摹出来,敢于挑战世俗之见,刘伶当楼,渊明接踵,太白继武……余家驹亦是真性情者。诗人的田园,还有他相处融洽的父老乡亲。例如,《村中请新酒》一诗描写了村人农闲的七月,左邻右舍来请新酒,诗人与他们举酒共话丰年,乐在其中忘记了自己年老。诗人“刚逢西舍来牵袂,又被东邻去举觞”的情状与陶渊明“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归去来兮辞》)如出一辙。
二、田园生活的接受
余家驹歌颂田园,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安贫乐道的情怀。陶渊明把田园当作生活和精神上的归宿,他的诗歌充满了乡土气息。对于余家驹而言,家园的日常生活同样是乐土,他笔下的家园生活,看似平淡清寒,却又在平淡中透着富足,在清苦中品出诗意的唯美。只有热爱生活的人,只有安贫乐道的诗者,才会写出如此诗意的作品。生活是个大染缸,那些冗繁复杂的世俗礼节,那些明争暗斗的名缰利锁,只有内心期待生活本质和回归生命本真的人,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和体悟到生命的真谛。余家驹在《家园》一诗中抒发了自己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他随性欢喜的个性特征也流露无遗。他写幽居自家小园,独处怡然自得。“欲饮尽其兴,不饮亦自由。客坐亦不遣,客去亦不留。俗情尽捐去,人逸事事幽。欲问我何名,我名逍遥游。”诗人安贫乐道,不滞于外物,不限于外情,内心宁静自然,颇有老庄的“清静无为”与“逍遥”的意趣,更深得陶渊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的洒脱自在。
余家驹对田园的歌颂,还在于他的无欲无求。如果陶渊明归隐田园时的心情显得很决绝,那么余家驹的归隐时的内心就属于波澜不惊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余家驹虽取得贡生身份,却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他对功名富贵的淡漠,对田园的热爱,在他的《园中二首》诗中,可见一斑:“娇鸟啼呼客,文鱼出听诗。闲将一斗酒,坐向好花枝。花香浓似酒,风气暖于绵。未饮心先醉,风来我欲眠。”诗歌描写了诗人在家园中的生活情趣。娇莺“呼客”,文鱼“听诗”,诗人闲坐赏花,吟诗饮酒,好不惬意。清风带着花香,诗人如饮佳酿,似软绵抚身,不觉沉沉睡去。诗人在家居生活中享受清幽宁静,怡然自得,颇有陶渊明“物我两忘”之境。余家驹看透世事无常,了悟人生,一切随心可喜,不拘于世情变化。再如,《时园》中的“孤云有意间归岫,明月多情自入门”之句,当得陶渊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之意,甚有过之。
三、田园诗学的接受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高洁的隐逸精神,到汉朝末期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形诸文字将其表现出来的很少。自张衡的《归田赋》问世以来,隐逸、田园生活开始进入文人的写作视野。东晋的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祖师,作品影响至今。余家驹与陶渊明相隔千年有余,却在精神上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诗学交流和对话。他的田园诗保留了陶渊明大量的写作素材和写作技法,在当时的黔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对白描手法的接受。余家驹的田园诗崇尚陶渊明的古朴自然,文字修辞不假雕饰,如充满乡村气息的《村女》:“相邀女伴踏春阳,布服麻裙淡薄妆。行到陇头人意倦,散金满地菜花黄。沾来花露湿衣裳,故向东风坐曝阳。一个游蜂挥不去,裙边衣角嗅余香。”诗人不去修饰“村女”的体态,却用白描的手法将“村女”融入环境。诗歌描绘了农家女子相伴出游,她们身着布裙麻服在春光中嬉戏的场景。即便花露打湿了衣裳,她们也毫不在意,只是坐在春阳之下晒干,裙角沾染的菜花香气惹得蜜蜂也来轻嗅,甚至挥之不去。寥寥数语写出农家女子的生活情态,充满了别样的诗情画意。此诗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情趣相偕却辞体大异,既有春日时节淳朴自然的乡村女儿风情,也有人、花相映,物我两忘的艺术构思,颇有陶渊明诗的“语言朴实率真,笔调疏淡,风韵深厚”(廖仲安《陶渊明》)。
余家驹另一类反映农林牧渔的田园诗,描写手法与陶渊明更为接近,均来自他真实的隐逸生活,如《樵二首》写道:“等闲误入洞中天,砍得灵根荷两肩。一曲清歌摇曳去,通身缭绕尽云烟。崎岖一径入烟萝,摇曳余音岭外歌。落叶纷纷人不见,深山幽谷白云多。”此诗前一首平铺直叙写樵夫入山打柴,山歌隨落叶摇曳,通身云烟缭绕,浑似从仙境走来;后一首写山路崎岖,樵夫一路高歌浑然忘却生活艰辛,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与山中落叶、白云为伴,飘逸之情悠然自得。再如,《耕二首》其二写道:“子规啼破万山烟,人在东阡又北阡。正是一年农事急,微风细雨插秧天。”该诗写出农人耕种时节在子规声催中忘却“微风细雨”,忙于“插秧”等农事。“急”字道出农忙,却又表现出诗人与农人乐在其中,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情趣。
其次,对“平淡、自然”诗风的接受。余家驹世居黔西北,耕读传家,与当地农人来往甚密。他对当地的自然、风俗了解甚深,其诗中语言蕴含地域特色,平淡自然。他的诗歌语言无须雕饰,将俚俗与雅致熔于一炉,平淡中见真情,如《催耕鸟》一诗写道:“鸟使催耕作,殷勤春日中。深山三月雨,乔木五更风。物性随时化,禽言与俗通。须知天帝意,所急是农功。”诗人不再单纯吟咏“催耕鸟”,而是借“催耕鸟”形象地表达出农人暮春三月耕种的忙碌,“禽言”与“俗世”相通,“催耕鸟”也暗暗为农人着急。诗歌语言朴实自然,情感真挚热烈。可见余家驹若无真实的田园生活经历则无法传达出农人生活的具体状况。
最后,对“比兴寄托”和“情景交融”的接受。余家驹的田园诗不是大白话的生活叙事,也不是照葫芦画瓢般的风物拓印,而是蕴含了诗人深刻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他“师古而不拘泥于古”,每一首诗,都是他生活画面的神韵再现,是他匠心独运的艺术成果,如《初冬闲居》写道:“岁晚殊无事,偏于木石亲。秋霜能艳物,冬日最宜人。活火煎茶馥,新泉灌酒醅。鸿儒吾不慕,来往有乡民。”诗人写岁末年头,与木石更亲。秋霜下的万物倍加艳丽,冬日暖阳最适宜闲居。这正是农人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冬天没有了农耕的劳苦,故而才有了“闲居”一说。然诗人不仅仅是农人,他的闲居生活与农人不同,“活火煎茶”和“灌泉醅酒”乃诗人之日常,但他不羡慕“鸿儒”,而乐于与“乡民”相交。可见余家驹并非自视清高的文人士子,而是“与民同乐”的“布衣诗人”。本诗虽语言平直,感情直露,同样彰显了诗人高大伟岸的形象,寄托了诗人“众生平等”的意识,其精神境界不亚于古之贤者。整首诗的艺术价值也达到了审美的和谐统一。
总之,余家驹的田园诗,从田园精神到田园生活,再到田园诗学上,都体现出他对陶渊明的田园诗的有所接受。他热爱自然,崇尚老庄思想,不仅清其表里,而且随性欢喜。他归隐田园是本心使然。他的性格宁静淡定,生活平凡从容,心灵自然随性。余家驹纯洁高雅的情操,恬淡豁达的个性,平等待人的人格,与民同乐的态度,造就了他诗风飘逸出尘、不染世俗,可谓平凡中见伟大,自然中见真情。他的田园诗没有刻意而为之,遣词造句没有雕琢,如同深山璞玉,是清代地域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本文系2023年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清代黔西北诗人余家驹诗歌研究”(项目编号:YCX2305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