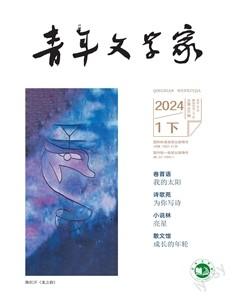论原型视野下小说与散文中的植物意象
李瑞雪 杨泽林 范丽

植物与人类生活联系紧密,它既为人类提供了安身之所,也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和药材,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文学作品中,植物也一直贯穿其中,形成了内涵丰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意象,用以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本文将以原型理论为依托,对小说和散文中出现的植物意象进行深刻阐述。
关于“意象”,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理解。《周易·系辞上》中提到了“意”与“象”的关系:“圣人立象以盡意。”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象”理解为客观物象,“意”则是作家对“象”投射的主观情意,那么意象就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的结合,也就是在作品中作家赋予客观物象的细腻情感和丰富内涵。但是,如果将“意象”这一概念放置于原型理论的视角下来看待,意象所包含的情意就并非作家个人所赋予的,而是远古文明和一代又一代记忆的体现。
一、原型视野下的意象
原型理论作为一种文艺批评理论方法,是通过对原始意象的追溯,找到一条踏上寻找远古文明的道路。这一批评方法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指导人类审视精神来源,以及提升人的审美及思维品质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原型”一词最早由裴洛提出,指人身上体现出的上帝形象;之后荣格在柏拉图“理式”和康德“构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不断地研究,提出了原型概念,并将之引入文学领域。荣格认为,人为赋予某些事物和现象的意义都包含了历史的范畴,它不仅仅是人类主观赋予的,它更多是融入了原始社会和远古文明记忆的。继承荣格原型理论并将之发展为“文学意象”的是弗莱。从传统认知上来看,意象完全是某一特定主体赋予事物的特殊意义,但当弗莱站在荣格的原型思维下,重新审视文学意象后,认为意象不仅可以包容而且可以贯穿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以及发展背景,每一个原型都有一个对应的象征意义。根据荣格和弗莱的观点,原型批评理论视野下的意象就不仅仅是作者赋予客观物象的个人情意了,此时客观物象被赋予的主观情意是沿袭了原始先民流传下来的一代又一代记忆,是远古文明的体现。
由此可见,在原型理论的视野下,每一个意象都是我们祖先在历史上悲欢离合的历史碎片,它承载了远古人类的悲欢离合,将远古文明的记忆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而与意象对应的每一个原型,就像为承接意象之水流而凿出的一道又一道河床,从此人类一代代的记忆之流得以奔腾不息。
二、植物意象的原型追溯
在文学作品中,植物经常出现,构成了内涵丰富的植物意象。追溯文学作品中植物意象的源头,便是森林这一意象。森林与人类早期的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广袤的森林为人类早期提供了食物来源,同时成为人类居住、生活,以及祭祀活动开展的场所,是远古时期人类的栖息之所和精神家园。由于生活上对森林的依赖,加之早期认知的局限,人类便将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认定为某种神秘的力量所赐予决定的,便根据人的形态描绘自己心中树神的模样,认为这种力量正是源于树神。例如,希腊樵夫们就崇拜着名为得律阿德斯的木神。人类这一时期的树神形象都是以人的形态出现,恰恰证明了早期人类与森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方文化中,狄安娜神庙旁长有一棵大树,任何人不得折其枝干,只有外来逃亡之人才可折下其枝干并同祭司决斗,如果决斗成功便意味着其可成为新的森林之王,这就是保卫金枝的风俗。保卫金枝的风俗一方面表明了远古时期森林的神圣,另一方面也向后人展示了远古时期形成的树木崇拜。在中国文化中,也有属于自己的“金枝”—社树。“社”从示从土,即地之主也。傅道彬在其《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中指出,远古时期的“社”表明其祭祀对象为木,“木”即“社”的主人。祭木的风俗从著作当中也可以找到依据,如《论语》中可以看到夏商周时期的祭木,《墨子》中也提到“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这一时期的人类通过祭木来祈求得到庇佑。所以综合来看,无论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在早期赋予了森林非同一般的意义,中西方所反映出的树木崇拜其实都是人类早期依赖树木而生的体现,是对自己生活居所的依赖,更是对自身精神家园的依恋,是生命和意识的象征。所以,将原型理论下的森林与文学作品中的森林意象结合起来,以森林意象为代表的植物意象也就蕴含了家园和生命的象征意义。
三、散文对植物原型的延续
通常我们会习惯性地将意象与诗词这一文体相关联,通过诗词中出现的意象分析诗歌内容,对诗歌进行鉴赏,进而体味通过意象组合而营造出来的意境,体会诗歌之美,感受文化之魅力。但将意象与散文、小说等文体结合起来去分析则显得陌生。其实,在原型理论视野下运用意象解读文学作品,不仅作用于诗歌这一文体,对于其他文体,尤其是小说、散文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将原型视野下的森林置于文学作品之中,以森林为代表的植物意象蕴含了强烈的家园和生命意识,将这一原型分析思路引入散文的分析鉴赏之中,对于散文的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植物蕴含的生命和家园意识,在哲思散文的分析和鉴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下文将以冯至先生的散文《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是一篇哲思散文。冯至先生在散文开始提到“人口稀少的地带,我们走入任何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总觉得他们是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这一片森林之中出现了多种植物,如“彩菌”“鼠麹草”“尤加利树”,冯至笔下的这些植物,就像是一位位见证者与聆听者,它们默默地在这一片土地上长大,延续自己生命的同时,也见证了此处的兴衰。雨后五彩的菌子,在点染此刻山林的同时,也曾为那片消逝了的山村带去了颜色,为冯至先生提供了写作思考的动力,也同样为曾经山村的儿童提供了幻想的可能。那小小的鼠麹草,“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它只是默默陪伴着村女,“在山腰里一言不语地负担着一切”,它以一个小生命的形象承担着一个大宇宙,当横来的命运迫使它离去,它不留下任何夸耀后人的事迹。由此看出,冯至先生笔下的鼠麹草是那样的安静、纯洁、弱小,但就是这安静又弱小的品质,向读者传递出了它那一份坚韧的生命力,它就像一位倾听者,没有任何语言和行动,却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这一份力量恰恰就是生命个体表现出生命意识的象征。尤加利树对于这一片山村来说属于外来物,但这棵在短时间内茂盛生长的外来物,也是对于植物意象原型的生命意识和家园概念的体现。正是森林中这些植物的存在,使得冯至先生有了对于生命个体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思考,才有了两三年来山林中的一草一木给他生命带来的滋养,才有了山林的一切带给曾经山村居民的思考,才有了山林中的一切带给一代代读者的思考。
除了《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再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为例,来看这种生命意识的具体体现。《我与地坛》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在描写那一座废弃的古园时,着重突出了“祭坛四周的老柏树”“到处的野草荒藤”和“满园子的草木”,这几种植物本应该同这古园一般苍老幽静,缺乏生机,但在史铁生眼中,这古园的老柏树愈加苍幽,野草荒藤自在坦荡,草木竞相生长,甚至弄出窸窸窣窣的响动,表现出的是另一番景象:自由、生机。史铁生在文中提到了他会在园子里专心致志地思考关于“死”的事情,当他意识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时,他看到了生存的本质,即“怎么活的问题”。所以,越发苍幽的老柏树,自由坦荡的野草、荒藤,以及竞相生长的草木其实也引导了史铁生对“怎样活”这个问题的思考。对于身体残疾的史铁生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如此荒芜几乎是被人遗忘的园子,就如同身体残疾、意志颓废的自己,但这座园子是怎样“活”的呢?园子中的草木给出了答案—即使处于城市喧嚣的边缘,即使被遗忘,即使苍老、荒芜,园子中的一草一木却尽显生命的张力,他们在顽强、热烈生长的同时,还如同智者一般,饱含着情感和意蕴静静伫立在园中。看到这些植物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坚韧,看到这些植物在逆境中的静默坚持,史铁生也逐渐体会到自己的生命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呈现。与冯至一样,史铁生也是通过这些植物获得了思考和启发。在史铁生眼中,一片叶子的掉落也是以摇曳的身姿归属大地,整座古园甚至会因为这一片歌舞着掉落的叶子而“播散”熨帖。
由上分析可知,原型视野下散文中的植物意象蕴含了更多的哲思意味,体现出的多是生命、时间,以及家园意识。通过对这些植物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思想精髓,更好地体味散文之情。
四、小说对植物原型的延伸
相比散文中的植物意象,原型視野下小说中的植物意象则将这种生命和家园的意识投射到了人的情感思绪上,再加之文体的不同,小说中的植物意象更多是为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来服务的。所以,理解小说当中出现的意象更有利于把握小说情节的发展,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人物心理、分析人物形象。
原型视野下小说中的植物意象通常与人物性格、品质、命运相联系。例如,在《红楼梦》中,从故事的开始来看,林黛玉本是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神瑛侍者时常浇灌它,使得它延长岁月,这里化用娥皇、女英的故事暗示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恨纠葛。再如,在《世说新语》中,谢太傅对子侄说长辈只想他们品质高洁时,车骑将军回答谢太傅“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这里以芝兰玉树比喻弟子的形象:容貌美好、德才兼备。同样,在《世说新语》中,以植物来喻示人的生命状态:“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这里就以蒲柳和松柏两种植物比喻人的生存状态是否康健。可以看到,小说中将植物原型的生命意识凝聚到了人的精神品质意识的层面上。另外,现代小说中也有以植物暗示人物形象的例子。曹文轩极其喜爱葵花这种植物,在其作品《青铜葵花》中,女主人公就以“葵花”命名。当葵花的爸爸沉浸在葵花地中,表现了主要人物的心理状态如阳光之下的葵花一般温暖;但是当爸爸遭遇意外之时,女主人公葵花再去地里所看到的是葵花低垂之景,昔日充满阳光的葵花地已然不再,眼前尽是灰暗低迷,其实这里就通过葵花的状态,侧面体现出人物的心理变化。
小说中的植物意象除了可以映衬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心理变化历程,象征人物品格,还可以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大家熟知的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中女主人公翠翠的名字就源于她身处湘西的一座小山城,此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也正因如此的自然环境,她因此得名“翠翠”。小说中反复出现竹子意象,但是小说中不同位置的竹子有着不同的作用:小说开头出现的竹子是为了引出主人公,映衬小说主要人物的形象;小说后半部分出现的竹子则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天保和傩送对翠翠的爱意并不是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传递表达的,而是通过竹林中的歌声推进了故事的发展。另外,《边城》中所表达的对于山水自然的向往和追求也正是在以“竹”为背景的自然环境中实现的。沈从文正是通过植物意象营造出来的清新唯美的环境,向读者展现出天人交融之美。就沈从文的作品来说,不光《边城》通过植物意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映衬人物形象,在《阿黑小史》中也以“蕨菜”这一植物意象反映阿黑和五明之间的爱情。这两部作品中的植物意象都象征着爱情这一情感意识,并以这一线索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综上所述,原型视野下的植物意象所蕴含的家园与生命意识,在散文和小说中都可以体现出来:在散文中,尤其是哲思散文中,作家透过植物引发了对生命、时间和家园等问题的思考,意味深远;小说中则将这种原始的生命意识和家园意识凝聚到了人的情感和品质上,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主旨。所以,在原型视野下分析小说和散文中的植物意象,对于我们了解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系2023年度张家口市“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原型视野下的高中语文植物意象教学”(项目编号:23310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