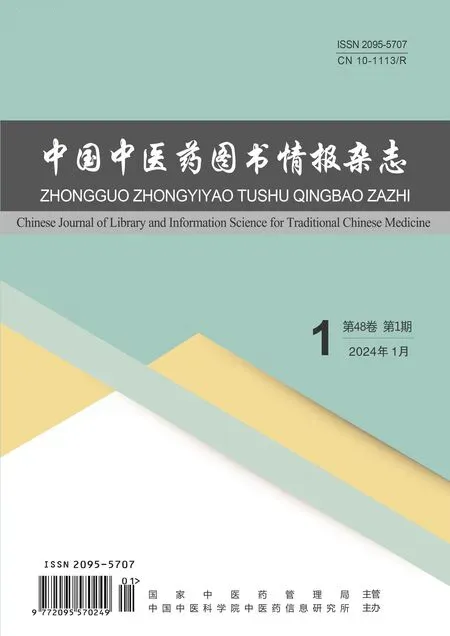心房颤动伴抑郁中西医治疗研究进展
白一岑 ,宫丽鸿
1.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110847;2.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 沈阳 110032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常见危害包括脑卒中及血栓栓塞、心力衰竭、心肌梗死、认知功能下降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AF的患病率和死亡风险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抑郁以心境低落、兴趣减退、失眠、精力疲乏等情感活动减退为主要临床特征。AF引起的心悸、头晕、乏力等并发症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从而引起一系列负性情绪变化,其中以抑郁最为多见。调查显示,伴抑郁的AF患者占AF患者总体的33%[1],而具有抑郁型人格的患者生活质量会更差[2]。AF会引起抑郁的发生,抑郁症状又会导致AF的发生率增加[3]。因此,临床上需关注对AF伴抑郁患者的评估,在治疗上予以重视。本研究对近年中西医治疗AF伴抑郁的研究进行综述,为AF伴抑郁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1 中医研究进展
1.1 中医对心房颤动的认识
AF常以患者自觉心跳不安,甚则难以自主为主症,临床表现符合中医学“心悸”范畴。引起心悸的原因有体虚劳倦、内伤七情、感受外邪、药食不当等。病机为气、血、阴、阳亏损,心神失养,心神不安,亦可因痰、饮、火、瘀阻滞心脉,扰乱心神。朱丹溪论治心悸,从“痰”“虚”两端出发,证属本虚标实。《诊家枢要》有“促脉之故……十之二三,或因气滞,或因血凝”,认为是由于气虚血瘀而引发心悸。李用粹则将心悸的病因病机总结为8个要素,分别为气虚、血虚、气郁、郁痰、痰结、停饮、阴火、肝胆心虚。陈士铎指出五脏皆可致悸,病机有肝郁化火、肺气不降、心肾不交、脾胃不足、血热扰心。强调首重五脏关系,次辨寒热气血[4]。于白莉认为,心悸病因有实有虚,重点考虑因虚而悸。心气不足,宗气外泄,正气虚动而心悸[5]。丁书文认为,心悸病之根本在于气虚,瘀阻心脉为其主要病机,热毒是主要的病理环节,证属虚实夹杂[6]。
1.2 中医对抑郁的认识
抑郁临床表现为心情抑郁、焦躁不安、胸部满闷、或易怒易哭,咽中如有异物梗阻等,与中医“梅核气”“脏躁”“百合病”等情志病的症状相似,故中医学将其纳入“郁证”范畴。郁证多因郁怒、忧思、恐惧等七情内伤,以致肝失疏泄、脾失健运、心神失养。基本病理因素为气、血、痰、火、食、湿,基本病机为气机郁滞,脏腑功能失调。《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提出土郁、木郁、金郁、火郁、水郁五气之郁,认为五脏气机运行失常是郁证的病理实质。《丹溪心法·六郁》中提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生诸病多生于郁”。《杂病源流犀烛·诸郁源流》曰:“诸郁,脏气病也。”其源本于思虑过深,更兼有脏气弱,故六郁之病生焉。明确提出“脏气弱”为郁证之内因,为虚实夹杂证候。董洪飞等[7]指出“凡郁病必先气病”,气郁贯穿郁病的整个过程。司国民认为,郁证致病首伤气分,久及精血,强调调畅情志气机,以“肝病治肾”“肾病治肝”“肝肾同治”的法则论治[8]。王萌等[9]认为,情志活动与脾密切相关,从脾论治,提出行气化痰、通阳利水、健脾安神、和中缓急治法。
1.3 从中医角度探讨心房颤动与抑郁的联系
心悸病位在心,与肝、脾关系密切。情志不舒,肝郁气滞,郁而化火,耗伤心血,心神涣散引发心悸。郁证病位在肝,与心、脾相关。情志不畅,心失所养,神失所藏致脏腑气血阴阳失调,发为郁证。可见,AF伴抑郁与心、肝、脾三脏关系紧密,三脏正常运转、相互协调,共同维系着全身气血津液的输布与运行,而脏腑功能失调使二者互为因果。心悸久之则气血阴阳亏损,心失所养,而心主神明,神思紊乱,出现抑郁。“凡病无不起于郁”(《类证治裁》),郁证致肝气郁结,脾失健运,脏腑气血失调,心神失养,而作心悸。七情所伤是两者共有病因,且皆属于心功能失调。气血失宣,脉道不利,精气亏损,神明失守。韩安邦[10]分析34例房颤伴抑郁患者的中医证候分布特点,结果发现此类患者证候分布以气虚、阴虚、气滞、血热、痰浊为主,主要病机为本虚标实。证型的分布特点以心脾两虚、心血瘀阻、阴虚火旺为主。
1.4 中医治疗研究进展
AF与抑郁虽然临床表现不同,病因病机确有相似之处。在把握病因病机的基础上根据中医“异病同治”理念,抓住主要联系,辨证施治。
1.4.1 中药汤剂
中医在治疗AF伴抑郁方面有独特优势。王有鹏认为,现代人久食肥甘厚味易形成湿热体质,久则伤阳,心阳虚衰,气血失调。故以调和营卫、疏畅气机、疏利三焦之法分消走泄,以祛瘀为本,达到治疗心悸的目的,自拟柴桂温胆汤,疗效显著[11]。蒋健强调溯本求源,认为心气虚、心血虚为心悸伴郁证的发病基础。气血不足,神气失守,心失所养引发心悸。故以调整五脏气血阴阳为治疗大法,针对心气虚患者以养心汤加味,对于心脾两虚心悸合并郁证者常用归脾汤、寿脾煎、七福饮等加减,对于痰热内扰患者治以辛开苦降,兼以化痰,常用黄连温胆汤、柴胡桂枝龙骨牡蛎汤及安神定志丸加减。在减轻患者症状的同时,养心安神,提高生活质量[12]。程丑夫针对心胆气虚、风阳上扰证患者治以解郁定志丸(安神定志丸加柴胡、白芍)以达疏肝解郁、安神宁心之效,从而防止心悸发生、改善预后[13]。康法宝等[14]认为,此病因心悸日久,肝气郁结久而生瘀,心脉失养。故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定悸安神为法,以四逆散为基础,自拟舒郁定悸汤应用于气滞血瘀证持续性AF伴抑郁患者,可有效缓解心悸症状,改善抑郁情绪。
1.4.2 中成药
中药颗粒剂对AF伴抑郁患者的治疗也取得了较好疗效。罗康华等[15]研究发现,老年阵发性房颤伴抑郁证(气阴两虚证)患者单独应用稳心颗粒在恢复窦性心律方面优于单独使用胺碘酮。胡海玲等[16]认为,心悸加重后常伴有恐惧感,致患者情志不畅,肝郁气滞,郁而化火,扰动心神发为郁证。故以疏肝理气、解郁安神为治则,应用解郁颗粒治疗永久性房颤伴抑郁状态患者。
1.4.3 针刺疗法
针刺疗法为AF伴抑郁患者提供了非药物治疗的新方法。针刺治疗与药物治疗相比安全性较高,通过辨证循经取穴原则治疗心律失常的有效率达60%~90%[17],以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为主,常用腧穴有内关、神门、心俞、大陵等,根据中医辨证论治、随证配穴治疗原则,以扶正为主,兼以驱邪[18]。
2 西医研究进展
2.1 现代医学认识
AF伴抑郁状态与“双心医学”概念相符。双心医学指在患者躯体治疗的基础上,对于伴有心理障碍者进行评估并采取适当的心理干预治疗。AF的发生发展受心理-生物-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在治疗AF方面不能单一考虑生物医学模式,而应当重视疾病的心理因素[19]。“双心医学”强调“身心同治”,认为心血管疾病与精神心理因素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影响。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可以改善AF伴抑郁的程度,有利于预后[20]。
2.2 抑郁症状评估
心血管疾病心理障碍识别难度较高,因抑郁状态常表现身体症状并非相应的精神症状,一些抑郁患者的症状如心悸等与AF症状类似,当心血管疾病与抑郁同时发生时,易诊断为心血管疾病而忽略了共病者抑郁的诊断。
临床可使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或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抑郁评分。HAMD可根据评分反映病情的严重程度,适用于临床,有一定的客观性、全面性。SDS量表用于评估一周内患者抑郁的主观感受及症状轻重,评分越高,抑郁状态越重,由于大部分抑郁患者通常会采取否定态度,故该表检出率不高。
2.3 心房颤动治疗
《2020 ESC心房颤动诊断与管理指南》指出CCABC的整体管理路径[21]。其中CC指对AF诊断及特征化评估,包括评估卒中风险、AF症状严重程度、AF负荷及AF的基质特征(4S体系)。ABC管理路径中,A为抗凝预防卒中;B为根据患者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方式(如抗心律失常药物、电复律、导管消融)以控制心室率,改善症状;C为优化心血管及合并疾病,如针对危险因素与患者生活方式的管理等。
2.3.1 心房颤动伴抑郁的药物治疗
对于AF伴抑郁需在治疗AF的基础上配合采取抗抑郁治疗,应优先选择安全性较高的药物,且在治疗期间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调整药物用量。作为一种新型抗抑郁药物,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在临床中使用广泛,其具有高效性、依从性好、不良反应较小等优点。在临床上常用的此类药品包括: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西酞普兰等,其中盐酸帕罗西汀可降低阵发性房颤的发生率。帕罗西汀相较于传统三环类、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类抗抑郁药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及更小的不良反应,耐受性更好,且可有效控制AF患者的发生频率,减轻抑郁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氟哌噻吨美利曲辛亦适用于AF伴抑郁患者,该药已被广泛用于临床治疗之中,不良反应小且耐受性好。需要注意的是,此类药物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如血压升高、胃肠道反应、心率加快、惊厥等。一项Meta分析显示,第一、二代抗抑郁药物可引起代谢综合征,增加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2]。
2.3.2 认知干预疗法
针对AF伴抑郁患者,单一的药物治疗尚有不足。临床上应从生理、心理、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施行有效的干预调节,认知行为疗法近年来在临床上使用频率较高且疗效显著。一方面,针对不同病情的患者采用个体化的心理治疗方案,通过认知和行为的一些理论及技术方法改变个体认知和非适应性行为,鼓励患者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应对疾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改善不良的情绪和行为;另一方面,使患者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预后等方面有充分的认知,消除患者的恐惧心理。
3 小结
AF人群基数大,伴抑郁患者预后较差。中医治疗优势明显、途径多样、个体化程度高,根据不同辨证分型施以不同治法,在中医经典方剂的基础上加减化裁、灵活运用。针对长期服用抗心律失常及抗凝西药可能出现加重患者负面情绪的问题,应发挥中医因势利导的治疗优势,同时深入中药药理研究,对于AF伴抑郁患者应依据不同阶段拟定有针对性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达到中西医优势互补,协同增效。此外,在积极有效地规范治疗基础上,加强对患者心理、行为、精神层面的认知干预,对治疗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