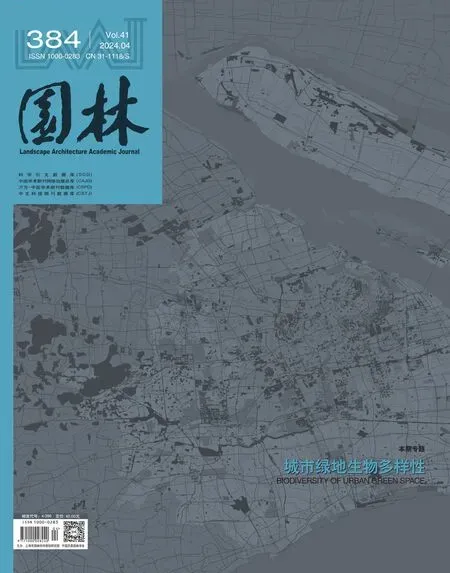明清古籍及诗画中的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分析
贾 虎 董青云 吴 瑾 沈 琳 李秉玲 张亚利
(1.上海地产三林滨江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上海 200120;2.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3.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上海 201403;4.上海上园苗木有限公司,上海 201103)
茶花作为中国的十大传统名花和世界著名花卉,在中国有着近两千年的栽培和应用历史,其在中国的古籍、诗词与绘画中留下了诸多的科学和艺术记忆。在前人对唐宋诗画中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古籍及诗画中茶花的发展脉络,为更好地探索茶花未来的创新性应用及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从搜集检索到的明清时期描写茶花的古籍、275诗首词曲赋以及部分绘画作品来看,明清时期的茶花品种多达百余种,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园林应用的植物素材;在园林具体应用方面,茶花在私家园林及寺庙园林中应用频次更高、形式更为丰富,并出现了茶花专类园的雏形;在配植植物方面,茶花与梅花、水仙、竹子的配植依然盛行,并逐渐发展出茶花与玉兰、牡丹、柏树等植物的配置模式。
明清时期;茶花;诗词;绘画;园林
茶花作为中国传统名花,历来被文人墨客所青睐,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科学记录。自唐代宰相李德裕(787–850年)《平泉山居草木记》中“贞桐山茗”的记载开始,唐宋期间关于茶花的129首诗词以及若干绘画作品对茶花称谓、品种以及园林景观应用都有了充分的展示[1];进入明清时期,茶花及其园林应用有了更多史料记载和科学发展,无论是在茶花品种方面,还是在其应用及开发等方面。文章在前人对唐宋诗画中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初探的基础上,通过梳理明清时期古籍、诗画等古文献的记载,进一步总结归纳茶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脉络,为更好地探索茶花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1 明清时期的茶花品种
1.1 古籍中的茶花品种
明代是茶花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清朝在此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两个阶段茶花新品种不断涌现。截至1912年,茶花品种记载共131种,其中明代记载的山茶花新品种27个,清代记载的茶花新品种87个[2]。
明朝时期开始出现专门研究茶花的著作。王象晋(1561–1653年)的《群芳谱》[3]中记述了包括宋代已有记载的‘鹤顶茶’(云南,托桂型)、‘磐口茶’、‘月丹’、‘玉茗’,并把‘千叶茶’细分为‘千叶红’和‘千叶白’(今‘雪塔’);同时记载了有芳香的‘串珠茶’(粉红色,芳香[4])、“亦有黄者”的黄色茶花等新增品种。吴彦匡(1628–1644年)的《花史》记述了‘笔管茶’、‘水红茶’、‘玉鳞茶’、‘五魁茶’(今‘五色芙蓉’)等品种[5]。在明代,关于云南山茶的记载极大丰富,《云南志》记载:“茶花奇甲天下,明晋安谢肇淛谓其品七十有二,赵壁作谱近百种。”[6]冯时可的《滇中茶花记》记载滇山茶至今仍有应用的‘九心十八瓣’(今‘狮子头’)[7]。发展至清代,朴静子和李祖望各自编撰的《茶花谱》、陈淏子的《花镜》,以及《温州府志》、《永嘉府志》等古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品种,包括不少至今仍在栽培的名贵品种,如‘十八学士’、‘醉杨妃’、‘抓破脸’、‘小桃红’等。朴静子的《茶花谱》记录茶花品种44个、李祖望的《茶花谱》记录山茶花品种48个,这是继明代以来记载茶花更加丰富的重要文献。此外,1930年,方树梅先生总结整合前人古文献著成《滇南茶花小志》三卷,记载了云南山茶花的传统代表性品种72种,并广泛收集明清两代相关诗词歌赋163首,这是研究古云南山茶品种的极为珍贵的文献[8]。但由于同名异物或者同物异名、品种描述信息不足等情况的存在,很难确定具体的品种数量及品种名。
明清时期,茶花品种除了数量的增加,还有了新的发展。主要包括:(1)清代芽变品种增多,如‘十八学士’等;(2)花型、花色更加丰富,出现了紫色的‘紫重楼’、复色的‘五魁茶’等;(3)芳香品种增加了王象晋在《群芳谱》中描述的‘焦萼白宝珠’、‘串珠茶’,夏旦在《药圃同春》中记载的‘白钱茶’(“夏月用山茶移接。花极可爱,清香”)[9],品种的不断增多为茶花的园林应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植物材料。
1.2 诗词中的茶花品种
通过山茶、玉茗、海榴、耐冬等茶花别名及明清时期茶花品种名等作为关键词搜集检索到明清时期描写茶花的诗词曲赋275首。入诗较多的茶花品种有宝珠茶(约18首)、玉茗茶(约11首)、杨妃茶(约8首)、‘鹤顶茶’(7首)、‘宫粉’(6首)等。其中‘玉茗’和‘鹤顶茶’是唐宋诗词中已有记载的品种。玉茗(花)在唐宋时期约有9首诗词对其进行了描述[1]。
除了品种之外,诗词中关于茶花的形态特征、栽培养护也有丰富且形象的描述。清弘历的《题钱维城四季花卉册其四十山茶》中的“玉茗名因叶类茶”点出了其命名的缘由。清蒋士铨的《杂感 其十五》“千朵玉茗花,开时若晴雪”描述了玉茗洁白如雪的花色;明代诗人张新的《宝珠茶》“胭脂染就绛裙,虎珀妆成赤玉盘”,用胭脂、绛、赤等字描写其红色,以“裙”和“玉盘”比喻其形状和质地。清宋荦的《玉茗花》“灌溉每同檐卜惜,阴森还借海榴遮”描写了玉茗的灌溉及需要遮阴的生态习性。此外,弘历的《春景花卉 其二山茶》“弗以香称以色誇,近疑火齐远疑霞。菜榴焦萼奚堪比,知是滇南鹤顶茶”和清刘秉恬《寄题惠风堂茶花》“尘世山茶非一种,品题高出数滇中。一枝占尽人间艳,千朵飞来鹤顶红”,均介绍了品种‘鹤顶红’,认为产自滇中的‘鹤顶红’品质上佳。
1.3 绘画中的茶花品种
进入明清时期,除了文人画、院体画两种主要的艺术特征外,写意画迅速发展,尤其是清代,为写意花鸟画最为发达的时期,这也为从绘画中鉴别茶花品种带来了困难,因此,本文重点对工笔画进行分析。在明清时期,出现诸多与茶花有关的绘画,如明代吕纪的《先春四喜图》《雪梅集禽图》、王维烈的《双喜图》、朱竺的《梅茶山雀图》、邵宝的《梅花山茶图》、孙克弘的《百花图》、林良的《山茶白羽图》,以及清代邹一桂的《白梅山茶图》、蒋延锡的《岁朝图》、罗聘的《花卉图》。
茶花以红色为主,有白、粉、黄、二色山茶,从绘画中出现茶花的花色、花型等形态特征,并结合古籍、诗词中关于品种的出现频率,绘画中出现的品种主要集中在常见的‘鹤顶茶’、‘宝珠茶’、‘杨妃茶’、‘玉茗(花)’等品种。如孙克弘的《百花图》以‘大红宝珠’山茶之富丽灿烂与白梅之清新秀美和谐构图,一并装点着万籁俱静的严冬季节(图1);林良的《山茶白羽图》山野一隅伫立着一双神态俊逸的雌、雄白雉,石后山茶树枝叶疏落有致,纷纷开着粉红色的花朵。罗聘的《花卉图》以一株粉红茶花为主体,衬以玲珑的山石和腊梅(图2),推测应用的是当时栽培较为广泛的‘杨妃茶’。

图1 百花图局部(明·孙克弘,收藏于故宫博物院)Fig. 1 Part of the Baihua Tu (Ming Dynasty, SUN Kehong, in the Palace Museum)

图2 花卉图(清·罗聘,收藏于上海博物馆)Fig. 2 Huahui Tu (Qing Dynasty, LUO Pin, in Shanghai Museum)
2 明清时期的茶花园林应用分析
茶花作为重要的观赏花卉,其花色“由浅红以至深红,无一不备。其浅也,如粉如脂,如美人之腮,如酒客之面。其深也,如砂如火,如猩猩之血,如鹤顶之珠”(清李渔《闲情偶寄》),株形“拔地孤根耸十丈,威仪特整东风前”(明李东阳《山茶花》),花期“一十四春风,一百五寒食。自开雪中花,至今好颜色”(清朱彝尊《松霭山房六咏·其二山茶院(辛巳)》),寿命“宜寿如《山木》,经霜似女贞”(明邓漾《茶花百咏·其一》)等特征在诸多诗词中均有表述。此外,茶花还具有饱满的人文品格,邓漾将其誉为十德花,称赞其“虽具富贵姿,而非妖冶容”。明杨慎的《山茶花》写道与茶花相比“海边珠树无颜色”,传说中的玉树琼枝也相形见绌。沈周在《红山茶》题画诗中赞扬红山茶“愿希葵藿倾忠胆,岂是争妍富贵家”,赋予其忠肝义胆的节操。段崎的“岂徒丹砂红,千古英雄血”则为山茶增添了英雄主义色彩。因此不论帝王官宦、平民百姓还是文人僧侣都对茶花偏爱有加,茶花在园林景观等用途中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丰富。
2.1 茶花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2.1.1 应用空间
明清时期种植茶花之风在私家庭院及寺院依然十分盛行,至今仍有众多的珍贵古树茶花得以保留。
(1)庭院应用。苏州拙政园的‘宝珠’山茶久负盛名,清吴梅村有诗赞曰“艳如天孙织云锦,赪如姹女烧丹砂。吐如珊瑚缀火齐,眏如螮蝀凌朝霞”,描绘了拙政园的宝珠山茶最盛时,灿如云霞、照红殿宇的动人场景。杨慎的《渔家傲》“正月滇南春色早,山茶树齐齐开了。艳李妖桃都压倒。妆点好,园林处处红岛”,足见园林中茶花之多,色彩之浓。清陈维崧的《喜迁莺·咏滇茶》“春园里,较琪花玉茗,娇姿更别”则提及江南私家庭院内种植滇山茶、玉茗茶的景观。清吴照的《白山茶歌》也写道:“我家旧铺有此花,不与红紫争丽华。”《广群芳谱》中的“余得一株长七、八尺,舁归植澹园中,作屋幕于隆冬,春时拆去,蘂多輙摘,仅留二、三,花更大”提到了山茶在园林应用时的养护管理。
(2)寺庙应用。山茶花花轮形似佛教中代表宇宙精神的曼陀罗,在古时广泛种植于寺庙园林中。在云南紫溪山茶花园有一株元朝东林寺僧以野生山茶为砧嫁接而成的古山茶,此山茶先开红花“紫溪茶”,后开白花“童子面”,明末清初的画僧释普荷作《山茶花》咏此树,“冷艳争春喜烂然,山茶按谱甲于滇。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个天”[10],将茶花茂盛开放的姿态写得热烈奔放。清林则徐的《万寿山看茶花》“定光寺里珊枝老,可惜今年花不早。菊瓣群夸太极宫,还输万寿庵中好”“梵行寺里端明咏”则提到了昆明的万寿寺、定光寺红山茶,太极宫菊瓣(恨天高),扬州梵行寺的宝珠山茶,可见当时茶花广泛种植于寺庙宫观内外。陈维崧《宴清都·咏杨妃山茶》“几朵僧房吐。东风里,胭脂浅淡偷注。空王斋院,艳阳天气,红香盈树。邻娃漫斗轻盈,尽玉茗、明妆缟素。总输伊,睡足春酥,脸潮分外娇嫭”描写了一株种植在寺庙内的杨妃山茶,密叶藏花,红香盈树,分外妖娆。《崂山志》记载山东崂山太清宫“初无耐冬花,三丰自海岛携出一本,植于庭前,虽隆冬严雪,叶色愈翠。正月即花,蕃艳可爱,龄近二百年,柯干大小如初”,至今此树犹存[11]。
随着茶花品种的丰富,茶花专类园初具雏形。顾养谦在《滇云纪胜书》描述:“西园有楼名‘簇锦’,茶花四面簇之,凡数十树,树可二丈。花簇其下,数以万计,紫者、朱者、红者、红白兼者。”[12]清光绪年间,拙政园主人张履谦以山茶花为主题修建十八曼陀罗花馆,栽种数株名贵茶花“十八学士”,《拙政园志稿》记载:“此地原栽名种山茶十八株,有东方亮、洋白、渥丹、西施舌等名种,早春开花似锦。”[13]
2.1.2 应用形式
唐宋时期,茶花从宫廷到私家庭院都有种植,明清时期园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观赏茶花之风盛行,茶花在庭院绿化中的运用更为广泛。明清时期茶花的园林景观应用形式在原有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
(1)配植植物方面。唐宋时期茶花与梅花、水仙、竹子的配植依然盛行,同时也逐渐发展出其他的配植植物。诗词中的记叙多为纪实,描述了明清园林中茶花与其他植物相搭配,营造出色彩、季相、气味富于变化的园林景观;绘画作品中关于茶花与其他植物的配置,是否纪实无从考证,画家可能更多从画面构图、色彩搭配及赋予作品吉祥寓意等方面考虑,将茶花与其他植物、山石、禽鸟等相结合。在明清诗词中,“迎晓香残宫粉腻。悄和梅边风味。韶华并占冬春”(清吴茝《清平乐禁体·山茶》)、“窗窗堆满梅花雪,衬出山茶一树红”(清张英《忆秦园山茶》)、“山茶水仙春满堂,梅花如雪凝清香”(明徐庸《题画》)、“宫粉凝脂竹外栽”(元末明初徐贲《春暮见山茶有感》)、“山茶花开雪初霁,竹光满眼摇寒翠”(明胡俨《雉鸡图》)等描绘了山茶与梅、水仙、竹子等组成的植物景观。明清时期的绘画也常把茶花与这些植物相组合来表达不同的寓意。朱竺的《梅茶山雀图》、吕纪的《梅茶雉雀图》、邹一桂的《白梅山茶图》(图3)中,红茶花与白梅相互映衬,共同表达傲霜斗雪、不畏严寒的精神;明张宏的《仿陆治茶花水仙轴》(图4)、清钱维城的《梅茶水仙图》、清樊圻的《岁寒三友图轴》则用山茶水仙组合展示纤尘不染、典则俊雅的氛围。在丰富配植植物方面,《长物志》中写道山茶“多以配玉兰,以其花同时,而红白灿烂”[14]。《归园田居记》也记载,明代崇祯年间苏州的归园田居内“每年春月,山茶如火,玉兰如雪”,可见园主已经有意识地利用山茶“如火”的花色,与玉兰配植,营造富有色彩、对比强烈的庭院植物景观[15]。清代袁越的《随园图说》“由台东出回廊,且折且下,玉兰、海榴,环列于右,万石鳞缀,杂植牡丹、兰蕙、朱樱、红蕉,拱抱于左”,“海榴”即为山茶。留园第二任园主刘恕在留园内广泛种植茶花等花木,更著有《茶花说》[16],留园内的“古木交柯”就是以山茶、古柏两树交柯连理,红绿相衬成景。

图3 白梅山茶图(清·邹一桂,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Fig. 3 White plum and camellia (Qing Dynasty, ZOU Yigui, in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2)配置小品方面。明代郑元勋影园内的曲廊小庭院种植着黄、白、大红宝珠山茶,与庭前奇石互为搭配,营造“石骨棱棱古,茶花澹澹香”的庭院景观。苏州耦园内拥有两棵同龄同种的古茶花‘杨妃茶’,园主沈氏夫妇将其种植在全园最具亮点的黄石假山上,名山和茶花相得益彰。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写道:“得此花一二本,可抵群花数十本,仅取盆中小树,植于怪石之旁。”在种植形式上,茶花在园林常采用对植和散植(丛植)的种植方式。如宋荦《玉茗花》“双树连蜷傍槛斜,园丁唤作白山茶”描述了两株白山茶斜倚栏杆相对而生的场景。明吴宽《山行十五首·其十五 观海云院连理山茶》“两株并植东轩前,密叶如屏遮几席”也描述了两株山茶对植的景观。清张英的《小园阴雨浃旬》中“屋角数丛湘浦竹,堂围四座岭南花”则描写了丛植的4株山茶花与翠竹相伴而生的景象。
2.2 茶花盆栽与插花
南宋时期茶花盆景开始出现,明清时期,随着茶花品种的进一步丰富,茶花盆栽的应用也更加普遍。《大理府志》记录明朝初期大理苍山感通寺高僧将云南山茶盆景进贡给太祖,沿途“马嘶花放”,太祖视为祥兆,龙颜大悦[2]。清初查慎行的《西湖棹歌词十首·其四》记载:“(却收)亭台到处罗列盆景宝珠山茶尤多。”清沈复的《浮生六记》记载:“至南雄,见人家墙顶多列盆花,叶如冬青,花如牡丹,有大红、粉白、粉红三种,盖山茶花也。”[17]
此外,明代插花艺术开始流行,袁宏道的《瓶史》中对茶花插花艺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茶花在插花材料中的地位。其称“黄白茶韵胜其姿”,突出了黄山茶和白山茶在插花时的搭配运用[18]。清朱昆田《题雪中山茶画扇》中写道:“凌冬百卉尽飘零,开处常愁素雪停。最好温黁乳炉畔,一枝红插砚头瓶。”陈维崧作茶花词《醉乡春·咏茶花》“瓶里玉花先逗”。明陈洪绶的《麻姑献寿图》,画中两位女仙一主一仆,女仆怀抱的花瓶中插有山茶和梅(图5)。此外,茶花还常与松枝、梅、百合、水仙、天竹等一起作为插花材料,搭配柿子、如意等寓意生机勃勃,百事如意。明清以祥瑞为主题的岁朝图描绘的就是这样的图景(图6)。

图6 岁朝图轴(明·陈洪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Fig. 6 Year-old painting scroll (Ming Dynasty, CHEN Hongshou, in the Palace Museum)
3 结语与展望
在茶花近两千年的栽培历史中,人们不断积累经验与知识,茶花在中国的古籍、诗词与绘画中留下了诸多的科学和艺术记忆。不同朝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背景及发展为茶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支撑。茶花从唐宋时期,到明清时期,无论是品种的数量、多样性,还是其应用都有了新的传承与发展。明代时茶花文化继续保持鼎盛;清初、中期茶花文化进入大发展时期,清末茶花的发展逐渐缓慢,但主体旋律仍不断向前[18]。明清时期随着园艺水平的提升,茶花品种大幅增多,这一时期所记录的茶花新品种占中国古代茶花品种的87%,更是出现了流传至今的珍稀茶花品种。茶花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也更为成熟多样,从地栽、盆栽,再发展到瓶供,使观赏茶花不再受室外自然环境的局限。
发展至今,茶花品种极大丰富,出现了四季开花品种群、束花茶花品种群、抗寒茶花品种群等可以满足不同时间和空间开花需求、不同审美需求的茶花品种,从而为茶花的应用区域、应用形式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在此过程中,优秀的中国传统品种、鲜明的人文品格、经典的应用方式等都需要在发展中传承,同时,茶花在园林景观应用中,除了满足人们达观赏需求之外,其色彩、香味以及组合空间如何能够带给人更多的价值也是未来值得探讨和实践的方向。
注:本文诗词主要搜索自古诗文网App,绘画作品来自中华珍宝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