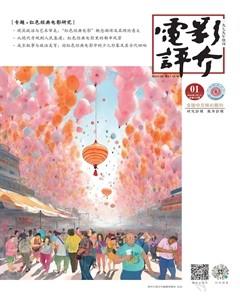《梦华录》:古装偶像剧的宋韵文化想象与女性意识表达
童晓康 范志忠



电视剧《梦华录》(杨阳,2022)兼具高热度话题与现象级传播,使久伏低迷的古装偶像剧创作重焕生机。作为本土语境下内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与影视剧类型,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关于“古装偶像剧”的精准定义。就创作类型而言,古装偶像剧可被视为融合古装元素的偶像剧,题材囊括青春爱情、仙侠玄幻、宫斗权谋、悬疑穿越等诸多类别;在具体的创作路径上,古装偶像剧承袭了偶像剧浪漫主义的叙事风格与古裝剧东方美学的视觉奇观,充分发挥“古装”与“偶像”两个要素的造梦属性,致力于在历史秩序外建构起瑰丽的东方世界。于是,网络游戏、小说戏剧成为孕育古装偶像剧影视改编的天然土壤,衍生出《仙剑奇侠传》(李国立/吴锦源/梁胜权/麦贯之,2005)、《步步惊心》(李国立,2011)、《花千骨》(林玉芬/高林豹/梁胜权,2015)等“网生代”①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古装偶像剧凭借精美的服化道设置、浪漫细腻的情感叙事与“大IP+流量演员”的生产模式,一度成为电视剧市场中热门紧俏的类型;与此同时,部分古装偶像剧对历史故意扭曲、千篇一律的创作程式与消费主义的娱乐化倾向也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与抵触情绪,使古装偶像剧的创新创制陷入窘境。
古装偶像剧经过多年发展,经历了以王侯将相、后宫佳人、上神仙女、江湖侠客为核心人物创作阶段,逐步跳脱出传统言情、宫斗与权谋的套路窠臼,为了避免“戏说”历史的悬浮,古装偶像剧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造梦机制,即通过丰盈的文化想象精雕细琢地展现历史风貌。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张开宙,2018)、《鹤唳华亭》(杨文军,2019)、《长安十二时辰》(曹盾,2019)、《清平乐》(张开宙,2020)为代表的一批古装新剧,以细腻的视听影像还原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建筑空间、服饰器物、风俗礼仪等日常生活细节,构建了现代人关于古代世界浪漫瑰丽的东方美学想象空间。
《梦华录》根据关汉卿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改编,在主题上“取意”于原文本中女性互助意识,将“弱女子”对不公命运的反抗升级为“独立女性”对阶层平等的追寻;在内容创作上“变通”,故事情节中移植了原作中赵盼儿智斗周舍营救宋引章的桥段,并在皇城司史顾千帆的牵引下开辟出市井生活与权谋斗争交织的新篇章,涉入更为复杂、纠葛的叙事格局之中。《梦华录》延续古装偶像剧男女情感叙事的同时,没有落于英雄救美的俗套剧情,顾千帆的“朝堂戏”和赵盼儿的“救风尘”,交替上演,时而交汇,凸显出男女情感关系间的平等和尊重;在视听影像艺术建构中,《梦华录》重现北宋时期的节物风流与人情和美,试图在真实的历史细节和市民生活中间,借由对历史的诗化叙述,以寻求历史与现代价值的契合点,传递更加符合当下文化语境的价值观念。
一、江湖、市井、朝堂:宋代生活图景的空间建构
《梦华录》精准把握宋朝时代特点与美学气质,通过对茶坊、酒楼、街市、书院等多维叙事空间的构建,复现江湖士人风雅与市井烟火气息兼具的北宋生活图景,巧借宋代人文景观搭建出与现代社会平行的精神时空,折射出现代人心中的乌托邦。在此基础上,《梦华录》试图颠覆传统影像的历史想象与对女性话语的遗忘,为剧集注入空间转向的深层动力,在真实与虚幻交织并置的权力场域中呈现朝堂内外的党争权斗与女性群体的命运纠葛,“异托邦”的空间形态在乌托邦镜像空间的映衬下被建构[1],建筑空间在市井与朝堂之间交叠往复,在增加叙事张力的同时,也使得传奇女性的现代内核趋于饱满。
(一)江湖社会作为情感载体
“江湖”本是单纯的地理学概念,狭义上可理解为江与湖的交汇处,又泛指江河湖泊、溪流池沼,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与社会语义。“江湖”既可以是士大夫、文人的隐逸之所,同时又指涉民间社会生活中由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所组成的特殊社会空间形态。
《梦华录》对江湖空间与江湖社会的影像呈现同时包含了以上三层含义,从地理位置来看,北宋代北周,定都开封,称为“东京”,沟通南北的水陆交通与“天下之枢”的优越地势推动了北宋商贸经济的繁荣,剧中的钱塘县令郑青田私开海禁并杀人灭口之事,便可窥见宋朝海外贸易的巨利。航运交通贸易带动经济发展,都市中的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构成了两宋特定的江湖社会。[2]《梦华录》正构建了一个茶坊酒楼林立,娱乐设施遍及,街市贸易繁华的城市空间,为三位女性开启“北漂”创业模式铺陈道路。从半遮面茶坊到永安楼酒肆,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的竞争对手或联合抵制半遮面的经营,或抄袭永安楼的食饮,或拒绝合作,她们的创业经历有如行走江湖、历经千帆,成为无数现代创业者辛酸奋斗史的真实写照。
从烟波钱塘的小桥流水到繁华东京的水乡码头,舟楫成为剧中人物行动的主要方式,“江湖”便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载体。当赵盼儿出场划着竹筏从水面悠悠而来,隐于江湖的赵氏茶坊被人知晓,成为文人墨客点茶品茗的闲逸之所;当赵盼儿救助顾千帆同乘商船前往东京,船舱的甲板成为见证两人消除误解、相识相知、互生情愫的起始点;当赵盼儿与顾千帆各自跨越障碍、在爱情与理性中寻找自我的真实状态,便有了卧船相拥、伫立相吻。至此,《梦华录》以大篇幅的涉水镜头完成人物情感的书写与江湖气质的浸润。
(二)市井叙事丰盈文化想象
《梦华录》将古装偶像剧的叙述视点从皇宫朝堂、世外秘境的凝固空间中抽离,以赵盼儿经营茶坊酒楼的视角将宋人插花、焚香、品茶、挂画的雅然逸致在剧情中徐徐铺陈开来,构建起富有人间烟火气息的民间生态景观。剧集通过《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描摹,直观呈现出北宋商贸繁荣的市井空间:茶楼酒肆林立、夜市灯火不绝,游商行于街头巷尾,艺伎献唱勾栏瓦肆。在此基础上,《梦华录》试图以平民化、生活化、轻量化的市井叙事完成宋韵文化的书写,开辟了三位女性携手创立“半遮面”茶楼的事业线,并采用轻喜剧的叙事格调,以赵盼儿经营茶铺、酒楼为核心事件,通过设置纨绔无度、呆萌可爱的十二行头池衙内,迂腐迟钝、憨厚沉闷的落魄进士杜长风,机灵圆滑、诙谐幽默的贴身跟班陈廉等角色,在市民角色的日常中重现宋朝市井烟火气息。
若将灯火通明的河面、鳞次栉比的夜市、熙熙攘攘的人群视为宋代都城繁华盛景的初步建构,那么《梦华录》对风雅宋韵的极致想象则在“花月宴”中走向高潮。永安楼外烟花璀璨、河灯绚丽,永安楼内西施舌脍、江瑶清羹、四鳃美鲈、莲花毕罗等佳肴美馔引得宾客心神荡漾,宋引章巧手奏乐,歌伎轻拢慢捻,舞伎衣袂飘飘,“花月宴”幻画为真,以歌舞为载体复现唐朝名画《簪花仕女图》《捣练图》中端庄柔美、风韵卓绝的唐朝仕女形象,散发出古典风韵,引得文人雅士满堂喝彩。
《梦华录》对宋朝市井风俗的细节呈现极为考究,从轩榭廊舫、亭台楼阁的构建到家具器物、点茶工艺的还原,力图再现一部影像版的《东京梦华录》。剧集以“碾茶、热盏、击拂、水痕”一系列点茶流程,还原中国传统非遗手艺“茶百戏”的韵味;同时将清隽典雅的宋瓷、舶自南洋的火珊瑚发簪、琵琶“风月”等器物作为载体,融入茶道、饮食、音律、服饰等宋朝文化符号,拓展文化想象力的边界。
(三)朝堂权谋建构异质空间
“异质空间”(heterotopia)的概念由福柯于在巴黎发表的演讲《关于异类空间》中提出。福柯认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3]也就是说,这个另类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背离的空间。《梦华录》通过对江湖、市井的空间建构,以诗意的視听影像呈现宋代社会与市民生活,成为现代人理想中的乌托邦,时而又将观众的目光从宋韵景观中抽离,转向风云诡谲的权谋斗争。“朝堂”作为与市井江湖相对的异质空间,成为真实与虚幻交叠往复的权力场域。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4],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维系着宋朝政治的基本格局。宋韵尚风骨、生清流,涌现出王安石、范仲淹等流芳百世的名臣;在权斗与党争的背后,亦有秦桧、蔡京等权倾朝野的奸相当道。“清”与“浊”泾渭分明,又相互映衬、彼此交锋,构成宋朝政治改革与新旧党争的历史轨迹。在《梦华录》构筑的权力空间中,齐牧、高观察为代表的士大夫以清流自许,他们对“借鬼神晋身的能臣”“欺上瞒下的五鬼之辈”嗤之以鼻。但是清未必清,“清流领袖”齐牧对顾千帆的苦心栽培,不过是使其成为牵制萧钦言的一枚棋子,为了打倒政敌,他精心策划帽妖案,不惜以无辜百姓的鲜血促成传言。作为依靠暴力稽查、审案皇城司使,“活阎罗”顾千帆褪去了仁义礼智信的光环,却深掩着一颗清流为志的赤诚之心,为此他放弃进士及第的光明前途,甘为皇帝私人的鹰犬爪牙,只为成为“清流的暗桩”。不论是夜宴图的真伪查存,还是清浊两党的权力交锋,《梦华录》呈现争议与倒转真实,在故事文本对宋朝安定繁荣社会的定向视野外,拾起历史中真实存在的权谋碎片,构建起一个清浊难辨的朝堂空间。
二、创伤、焦虑、治愈:人物自我构建的价值共振
《梦华录》以“创伤”的复现揭露人物过往经历与内心隐痛、以身份认同焦虑的泛存透视女性角色面对无常命运的纠结与抉择,最终以成长的“治愈”完成现代价值书写。一方面,创作者没有回避角色背负的时代局限性,通过赋予角色曲折与复杂的成长路径,对现实社会进行映射和反思;另一方面,人物弧光的展现还承载着观众对于角色塑造的期许与对影视剧价值共振的要求。
(一)创伤:成长中隐痛的复现
“创伤”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刺破或撕裂的皮肤”。现代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开辟了创伤的新维度,即“心理创伤”。“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高强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5]
《梦华录》以“创伤”叙事见证人物成长,剧中主人公大多都经历了从逃避创伤、接受创伤、治愈创伤的成长历程。赵盼儿的“创伤”源自因“父罪”被无辜牵连,昔日的乐籍身份成为赵盼儿心头挥之不去的隐痛,也教会她在逆境中洞察世情保护自己;顾千帆的“创伤”源自幼年被父亲萧钦言抛弃,于是他选择用割裂关系来救赎自己;宋引章在“创伤”中试图通过依附他人的力量来完成脱籍,却一再遭受欺骗与背叛。孙三娘的“创伤”源自丈夫儿子的抛弃,于是投河自尽成为她了却伤痛的方式。葛招娣的创伤源自父母,平日以男装示人是她对原生家庭的逃离。
“创伤记忆难以用言辞叙述,也缺乏前后脉络,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受和影像方式储存起来。”[6]《梦华录》多次通过梦境、闪回、延宕等叙事手法在创伤潜伏、复现与爆发的线性叙事基础上,制造了创伤影像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顾千帆深陷童年被父亲抛弃的阴影中,以至于其在重伤昏迷时噩梦缠身,梦境中浮现父亲萧钦言不顾哭喊与挽留而决绝离去的身影。赵盼儿虽已脱籍从良,但童年沦落伎乐营的经历却成为心中无法消除的伤痕,创伤记忆总是以片断式的闪回缠绕着受创主体。在萧相寿宴之上,宋引章以琵琶为剑,凉州曲节奏慷慨激昂,有金戈铁马之势,惊艳四座,同时也唤起了宋引章内心深处对周舍施暴无力反抗的悲惨回忆。
(二)焦虑:身份认同感的缺失
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7]《梦华录》以“创伤”叙事揭示了不同角色的身世困境与成长隐痛,伴随着深刻的“焦虑”,折射出人物面对命运抉择时的纠结心境与自我身份建构的曲折历程。
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将焦虑定义为:“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他存在的根本。其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8]在《梦华录》中,家世身份化作隐蔽性的焦虑,潜伏在人物关系与行动中,当角色间的个体价值不一致、产生交锋时,内生的焦虑则外化为冲突,逼迫人物做出价值决断。
赵盼儿介怀自己曾落为“贱籍”,不管是对待顾千帆的情感,还是生意场上竞争对手的挑衅,她都保持理性与克制,但在“斗茶”这一情节中,事关半遮面茶坊的存亡,面对胡掌柜等人的挑衅和谩骂,赵盼儿必须要在自我价值与他者价值之间做出选择与确证,于是在茶艺交锋中,赵盼儿不再隐瞒过往,不再因曾处“贱籍”而自卑,而是将舞蹈与茶艺融合,打开心中桎梏。
与之形成反差的则是急于摆脱乐籍身份的宋引章,身为江南琵琶名手,宋引章在进入东京后成为教坊司琵琶色教头,得到了前宰相的赏识与题字,可是世人对乐籍女子的轻视鄙夷始终成为宋引章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宋引章的自我价值在于通过提升其所热衷的琵琶曲艺来追求崇高的艺术境界,可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宋引章误把世俗的价值判断视为其实现自我的根本途径,所以才会陷入了外部世界与自我价值的矛盾中,面临着自我被他者异化的焦虑,于是宋引章才会不顾赵盼儿的劝阻,选择相信周舍帮助自己脱籍的谎言,也正是在多次遇人不淑后,宋引章终于开始清醒,意识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
(三)治愈:清水涤尘式的洗礼
水在西方宗教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基督教中的洗礼仪式是入教者必须领受的第一件“圣事”。约瑟夫·坎贝尔认为“洗礼”象征着人的“第二次诞生”,水不仅可以洗净身上的尘土也可以洗涤心灵的执念,本身具有拯救、再生的意味。[9]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被赋予了相近的内涵。《管子·水地》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诸生之宗室也。”意为水是生命的起源。在不同地区的文明中,水崇拜是一种植根于农业社会生活土壤中的自然宗教。[10]诞生礼俗中的洗三、送水礼等,水都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功能,能够祛灾消难,带来祥瑞。“清水洗尘”也成为人们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成长模式。
《梦华录》中同样潜藏着“清水洗尘”式的人物成长逻辑,“水”也便成为见證人物成长,完成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意象。顾千帆“活阎罗”的外表下埋藏着清流之志,但他长期置身于清流与后党清浊难辨的权谋混斗中,面对铜镜里审讯犯人沾染鲜血的自己,顾千帆开始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错位与质疑,更甚难逃梦魇的纠缠。他者作为自我之镜,参与了顾千帆自我认同的身份重建。赵盼儿以“国之鹰犬,民之爪牙”作为回应,帮助顾千帆建构起自我认同。于是他高举水盆肆意浇淋身体,在洗尽沾染污秽的同时,也借清水进一步洗涤内心的杂念,继续支撑自己的清流信念。
孙三娘被休后选择投河来了结生命,正巧被坐商船去东京的赵盼儿和顾千帆遇见施救。过去依附于丈夫儿子,庸碌终日的她已经死去,要为自己而活的孙三娘重获新生。此外,类似的情节也在她儿子身上发生,傅子方被推下水中浸润后方才醒悟过来,主动找到母亲孙三娘道歉并尊重母亲再婚的选择。宋引章同样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识破沈如琢的诡计完成逃离,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清醒个体。《梦华录》中人物身份认同的转变,洗涤过往经历的污垢都是以水为载体得以实现的。
三、自立、共济、救世:现代女性意识的进阶表达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女人是他者”的命题,“在男人身上,人的价值和生命价值在他那里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女人的独立成功却和她的女性气质相矛盾,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体,成为他者”[11]。《梦华录》在解构女性在社会象征秩序中的被支配地位时,试图通过唤醒“他者”困境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打破桎梏,在事业生活中追求经济独立,在亲密关系中追求势均力敌,寻找属于女性的精神家园。《梦华录》中的女性成长经历了从“他救”到“自救”,再到“救天下”等三个阶段,显示出现代女性意识的苏醒过程。
(一)自立:女性主体对他者身份的解构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12]在传统男权社会文化里,女性在男性的注视中丧失了自我,沦为第二性的“他者”(次要的、依附的、非主体的)。《梦华录》没有规避古代女性特殊处境中的“他者”身份,而通过女性个体的成长完成对“他者”的解构。
《梦华录》呈现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爱情中依附地位的捆绑:赵盼儿经营茶楼等待欧阳旭中举迎娶自己;孙三娘希望儿子能够为自己挣得凤冠霞帔;宋引章曾因身在乐籍而自卑,想依靠他人脱籍。当三位女性角色遭受爱情与事业的变故后,逐渐意识到“女子贵在自立”,才能执掌人生、方得始终。
于是,从被救到自救,《梦华录》开启了女性觉醒的成长历程,剧集中的女性开始成为自主自觉的行动者。面对欧阳旭的负幸薄情,赵盼儿不委身苟求,果断与其分道扬镳;面对顾千帆的真诚深情,她不丢失理智,在反复的试探与确证中完成情感倾注。孙三娘凭借精湛的厨艺立足东京城,由“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转变为不被儿子左右自己人生的独立女性,是对女性身份中“母亲”身份清醒的表态,“靠自己挣得凤冠霞帔”则成为孙三娘完成自我价值确证的追寻。完成“脱籍”是宋引章的夙愿,懵懂的她先后寄托于周舍、欧阳旭、沈如琢;当理想破灭,成长的阵痛促成了宋引章的觉醒,她独自应对沈如琢设下的圈套,不再介怀乐籍身份,最终独当一面撑起永安楼的大小事务,领悟了“风骨”的真正含义。
(二)共济:女性情谊对价值表达的丰盈
伴随着女性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欢乐颂》(孔笙/简川訸,2016)、《逆流而上的你》(潘越,2019)、《流金岁月》(沈严,2020)等一批彰显现代女性气质的女性群像剧应运而生,女性情谊的书写成为影视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女性互助的价值表达同样被承袭至古装剧集的创作中。
《梦华录》没有偏执于描绘女性友谊的紧密和深刻,而是以友情的拉扯与成长阵痛的纠缠堆叠出细腻的层次感,显示出女性友谊的复杂与坚韧。宋引章曾不顾赵盼儿劝阻执意要嫁给周舍,又在对顾千帆的感情认知中发生错位,两度与姐妹反目决裂,最终在识破沈如琢的阴谋后幡然醒悟,理解赵盼儿的良苦用心,开启联手打拼事业模式。葛招娣每日混迹于江湖,讹诈茶坊不得被赵盼儿识破,赵盼儿非但没有责怨葛招娣,而是在了解她的身世遭遇后,选择招收葛招娣为半遮面跑堂,又帮助其成为永安楼的股东,赶走贪婪无赖的母亲,逐步解开葛招娣的心结。赵盼儿与高慧,本是情敌,相识后结为好友,并互相在对方受困和落难时伸出援手;张好好与宋引章,都是伶人,没有竞争没有“相轻”,反而惺惺相惜。《梦华录》舍弃了女性倾轧的情节,转而呈现女性群像的辛酸成长与互助关爱,温情细腻的叙事格调不失为古装剧集创作对女性关系呈现一种新的转变。
(三)救世:女性觉醒对性别偏见的超越
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性别身份的刻板印象是一种社会建构。《梦华录》中的女性角色的成长受到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种种制约,不论是朝堂之外赵盼儿开茶坊、办酒楼的情节,还是朝堂之上“救风尘”、皇后辅佐参政等戏码,不合理的社会等级制度为女性个体成长施加了诸多阻碍,女性要实现独立、完成成长,要遭受世俗鄙夷的眼光与封建制度的阻力。
《梦华录》大篇幅描绘了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经商克服各种阻碍,最终将永安楼变成汴京最大酒楼的历程,成为一部鲜活的“古代女性北漂图鉴”。剧集结尾,宋引章为众请命,力谏登闻鼓院免去凡越级诉讼者皆要经受的杖刑,赵盼儿则“以她之名”向官家请愿,希望世人都不再受贱籍之苦。《梦华录》的价值表达不再局限于贱籍女子自救与女性互助,将思想内核升华为打破出身的阶层区隔。
《梦华录》为剧集增设了诸多女性追求独立、实现个人价值的情节,鼓励现代女性观众追寻自我;然而,该剧对母文本《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主人公的身份改动以及男女主人公的“双洁”设置,却偏离了女性主义的精神内核。在关汉卿的剧本中,纵使是沦落风尘的底层女性,依旧闪烁着独特的人性光辉,而在《梦华录》中没能够对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进行人文关怀,由此招致观众对人物身份建构的信任危机,影视改编在此意义上失去了原著的风骨。
结语
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影视工业化与娱乐化的属性被强化,影视艺术传播走向大众化、网络化,艺术表现形式趋于商业化、娱乐化;曾几何时粗制滥造、抄袭媚俗的古装偶像剧充斥荧屏,“土偶丑偶”的创作造成了国产古偶剧的低迷态势。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与受众审美品位的提升,古装剧创作“提质减量”效应明显。《梦华录》没有落于扁平生硬的情感叙事,跳脱出架空历史、戏说历史的藩篱;叙事视野从传统王宫朝堂移至市井烟火的生活图景中,以风雅宋韵的文化想象和女性意识的进阶表达,开辟了古装偶像剧现代价值表达的新维度。
参考文献:
[1]王永芳.另类空间美学:福柯“异托邦”思想的塑构[ 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10):26-29.
[2]张春媚.南宋江湖文人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文学院,2005.
[3]张锦.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8.
[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516.
[5][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6.
[6][美]朱迪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8.
[7]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 J ].心理研究,2012(01):21-27.
[8][美]罗洛·梅.焦虑的意义[M].朱侃如,译.广西:漓江出版社,2016:186.
[9]蒋栋元.生命·再生·罪与罚——《圣经》中的“水”意象[ J ].外国语文,2010(05):115-117.
[10]向柏松.中国水崇拜[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9:1.
[11][1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1,309.
① “网生代”通常是指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群体,也被称为Z世代。“网生代”一词的出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这些年轻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其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受到数字化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和智能手机的深刻影响。他们被认为是在网络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网络,因此他們的思维方式也带有明显的网络特征。
【作者简介】 童晓康,男,浙江兰溪人,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范志忠,男,福建南平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影视创作与批评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电视剧创作现状与传播生态研究”(编号:22VRC13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