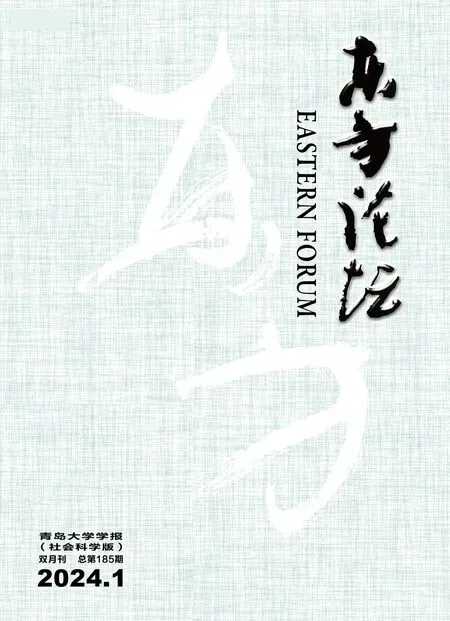“美”的转向与超越:庄子“悲态”美学思想阐微
王康宁 薛振宇
1.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 250014;2.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部,北京 100020
美学中的“悲态”是一种审美意境,“悲态”之美在于人们能够超越否定性的“悲”本身,升华出令人愉悦和享受的精神体验。这意味着“悲态”中不仅有“消极”和“否定”,也有“积极”和“肯定”的成分,而后者是确证“悲态”哲学内涵与价值的重点。审美范畴中的“悲态”与作为艺术形式的“悲剧”以及表征情感的“悲感”差别迥然。前者具有哲学思辨和形上追问的意旨,后者则主要关涉世俗人生的悲楚与痛苦。徐锴《系传》曰:“心之所非则悲矣。”①黄建中、胡培俊:《汉字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355 页。“悲”以“心非”之否定情态为特性,统指消极否定的情感与观念以及由其引发的一系列有违意愿或意志的形态或状态。“美学悲的悲态,是一种偏离的悲,是感到人与社会,人与宇宙对立一面时的悲,是带有询问的哲学高度的悲。”②张法:《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13 页。“悲态”以“悲”为起点,是经由对世俗之“悲”的超拔与升华而达至的精神高境。其中富含的深旨妙义既可被视作生存状态,也是现代人通达与实现自我的重要标志。
一、《庄子》“悲态”美学的理论溯源
“悲态”是贯穿《庄子》的基调与主旋律,庄子重“悲”且从中开出一条超越性的思维路向。以“悲”为中心概念或情感笔触,《庄子》中既有“悲感”的情态,也有“悲剧”的艺术内涵。司空图概括古体诗歌的“悲慨”道:“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抚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③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济南:齐鲁书社,1980 年,第38 页。“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是对自然之悲的描摹;“适苦欲死,招憩不来”,是对人生之悲的叹息;“百岁如流,富贵冷灰”,是对生命之悲的揭示;“大道日丧,若为雄才”,是对社会之悲的揭露;“壮士抚剑,浩然弥哀”,是对个体之悲的阐发;“萧萧落叶,漏雨苍苔”,是借景象之悲映射心理与精神之悲。司空图区区48 个字将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个体—心理之“悲态”予以淋漓尽致的阐释。由是观之,“悲态”是个体生存的必然环境和条件,个体所处的时空条件和心理状态则是悲态产生的缘由。
(一)以“有涯”应“无涯”:无限宇宙与有限自我的矛盾
庄子“齐物”的前提是“天—人”的同源性,“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大宗师》)。然而,“天—人”在存在形式上的非对等性也必然致使“合一”的有限性。在《庄子·养生主》中,造成这种有限性的根本原因是人之生存局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无涯”之宇宙自然的反衬下,个体人生之瞬时短暂尤为凸显,由此衍生的“悲态”注定是个体人生不可回避的必然。“正由于对自己‘此在’的珍视,知觉自己存在的‘有限’和追求超越此有限存在,便与‘时间’处在尖锐矛盾以至斗争中。”①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123 页。面对有限自我与无限宇宙之间的鸿沟,人不免生出“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也”(《庄子·齐物论》)的迷思与慨叹,无以复加的悲态也似乎成为笼罩人生的主宰。“只有在人的有限性、暂时性和不可重复性的背景上,失意才与哲学意义有联系。”②张法:《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114 页。宇宙自然之于人的不可违逆和抗衡性,以及人对宇宙自然的难以尽知尽能,时刻伴随着“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与“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庄子·齐物论》)的哀伤与无奈,而人在“悲态”中求突围又进一步渲染与强化“悲态”的主题与氛围,从而将人生与“悲态”紧裹。
(二)“道术将为天下裂”:对缺乏普世价值和共同伦理的哀叹
庄子以“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概括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虽然学界有关“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解读莫衷一是,但认为庄子以其表达“乱世”主张却基本无异。庄子对“道术将为天下裂”作过隐喻:“昔者十日并出”(《庄子·齐物论》)。“十日并出”既可视作庄子对“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结论性描述,也是庄子对价值解体、秩序混乱、道德不一的现实社会的形象化摹写,其真正意旨在于揭露普世价值和共同伦理的沦丧。庄子详细阐释过“天下之乱”与“文化观念之乱”或“伦理价值之乱”之间相生相依的关系:“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好,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庄子·天下》)“社会之乱”与“文化之乱”或“伦理价值之乱”之间,从来没有明显的先后彼此之分。当周遍之道尽毁而“一曲之士”遍存时,各有所持的观念与行为必然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造成人世社会的争斗与混乱。庄子之时的荒唐世道与险恶人心以“分”“裂”的形式淋漓尽显,“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浑然为一的宇宙秩序与自然法则,一旦被“有心”者做目的性的割裂与取舍,其结果只能如被凿出“七窍”的“混沌”般,走向“死”的末境是必然结局。诚如黑格尔所说:“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③[德]黑格尔:《美学 第3 卷 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286—287 页。庄子对因伦理价值解体而导致的社会乱象痛心疾首,在其有关人事之分的书写中饱含着深重的忧思与悲患。
(三)“丧己于物”与“失性于俗”:对众人生存悲境的嗟吁
成玄英先生疏解《庄子·在宥》“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曰:“六国之时及衰周之世,良由圣迹,黥鼻无刑,遂使桁杨盈衢,殊死者相枕,残兀满路。相推相望,明其多也。”①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218 页。面对天下汹汹颠连无告的不堪境况,庄子之所以予其以深刻揭露与批判,究其根本在悲悯心。承袭老子的理论主张,自然人生观亦为庄子所秉持。在老庄思想中,自然畅意的人生以对自然本性的顺应与持守为原则。然而,“如享太牢,如春登台”“皆有余”“昭昭”“察察”“皆有以”(《老子》第20 章)以及“终身役役”“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庄子·齐物论》)的“众生”沉沦样态与自然人性之间差之千里。“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民”或“蒙蔽之民”(《庄子·缮性》),以思想和精神的沉沦下陷为本质特点,以“滑欲于俗”为生存方式,服从于机心、巧智的干涉乃至宰制。“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齐物论》)“‘间间’之知,‘詹詹’之言,无时不在伺察、交接当中。讳莫如深的提防,秘藏深因。与封闭提防相伴随的是各种形态的恐惧。‘心斗’和恐惧指向自我界限的强化和封闭,这一没有确定性的自我边界往往被执以为实。”②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1 页。疏离与违背自然本性的众人不得不承受自身非自然言行的戕害,“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庄子·齐物论》)。无底线的纵欲和恣行只能导致更深程度的自我遮蔽和自我迷失,而人们对身陷彷徨与挣扎之悲境的全然不知或迷惑不解,实乃蕴藏在镜像之悲后的更为深彻的“悲态”。
(四)“独有”者的“独来独往”:怅然失落的个体心理
尼采对人之悲做过终极追问,认为悲之根本因由“在于其造物的状态”和“造物者的思辨冲动”③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 尼采美学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年,第15 页。。“思辨—悲态”既表明“悲态”之于个体人生的必然性,也表明思辨深度与“悲态”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悲态”之生成不仅取决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和渲染,更取决于主观心理和思想。“思辨—悲态”之间“原因—结果”的直接关联,意味着个体越是具有哲人思维,其于“悲态”的体认和感触愈明彻。显然,庄子对悲态的敏感度和洞察力远远超越一般人。毕竟,将“未来”和“过去”都纳入概念思考的范围,意味着认识将广大范围内的各种痛苦照亮,因而人的痛苦也就急剧增长④刘兴章:《论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身体理论——兼评叔本华的悲情人生观》,《求索》2014 年第4 期。。《庄子》的“悲态”哲学与庄子本人博古通今的开阔思维、达天入地的广大视野和上下求索的哲人精神密切关联。庄子对“独”倾注大量笔墨,视其为理想的人格特质和生存样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逍遥游》),“独来独往,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庄子·在宥》)。与其说庄子重“独”,毋宁说“独”是道家人格的核心特质。《老子》第20 章中区别于“众人”的“我”,便是“独来独往”的典型代表。老庄所谓的“独有之人”,统指“独守道”、抱持不入俗流之“独特”人格者。这类“独有”者相比于陷于流俗的“众生”,思想和精神往往独立与“孤寂”。概观庄子之时“仁义之士”遍存的社会环境,庄子的“重独”在表达观点的“独特”性之余,也传递出自身理论为人们忽视或冷落的“孤独”境遇。“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第70 章)。这种以自我为起点而衍生出的“悲态”,是庄子“悲态”哲学形成的深层原因。
二、《庄子》“悲态”美学的形式与内容
徐公持先生认为承继于先秦的汉代文学的“悲情”是弥漫整个汉代的文坛风气。“悲态”也是道家思想的一贯风格,其集中体现为老庄对“悲态”的哲学沉思与阐释。《庄子》的“悲态”有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经由呈现“悲态”而揭示浩瀚玄远的哲思与真谛,以及引发人们豁然通达的精神体验,既可被视为庄子“悲态”哲学的逻辑进路,也可被视作其特有的表达手法和书写技巧。
(一)难以逾越的天然局限:作为生存境域与心理样态的“无”
批判世俗之“有”而肯定“无”之“大用”,是老庄的一贯逻辑。“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去知与故,循天之理”(《庄子·刻意》)。“故”本为“有意而为”,可引申为“诈伪”①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540 页。。老庄揭露机心、巧智、物欲蒙蔽自然性的实质,主张人们经由“日损”“损之又损”(《老子》第48 章)的功夫促成自然本质的“澄明”,从而达到“无己”“无功”“无名”“无情”(《庄子·德充符》)的境界。然而,人们之于“无”的体认与获得是充满艰辛和曲折的过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庄子·大宗师》)的方式实现“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通达“无”之妙境。由世俗之“有”与终极之“无”间的悬殊而导致的“求道”过程之艰难,极度渲染了“无”之境界的深晦,也为人生理想的实现增添了诸多困惑与艰辛。
“无”不仅被庄子视为理想的精神高地和生存高境,也被用作描述人的心理样态和情感体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在宥》)郭象认为:“窈冥昏默,皆了无也。”②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208 页。“愚芚”(《庄子·齐物论》)的圣人,“如婴儿之未孩”(《老子》第20 章)般纯真质朴,丝毫不受情感的牵绊和束缚。然而,人本质上是“有”,是立于天地之间的“实在”,有其难以避免的“阿喀琉斯之踵”。“人被毫无来由的‘抛’在这个世界上,鬼神不可靠,死亡不可知,人因此陷入绝对的虚空。这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悲剧意识。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那也是悲极而乐(选择乐)的文化。”③冷成金:《“向死而生”: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 年第2 期。现实人生极难脱离“有”的范畴,“无”之深奥晦涩也较难与寻求安定执守的人类心理间形成真切关照。如同“罔两问景”(《庄子·齐物论》)中被动而虚幻的“影子”必须以实体为依据,“无”与“有”也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有无相生”(《老子》第2 章),离开“有”谈“无”,意味着“无”之合理性的自动消解。虽然“罔两问景”有彰显本质之“无”而弱化个体之“有”的意旨,但也明确表明“无”与“有”的本质与现象之间相生相依、相互证成的关系。此外,庄子对拥有“无”之心境和状态的“神人”“至人”“真人”的多维度刻画与描写,虽能为人们的超越性发展提供指引,但也真切地反映出其作为理想状态的难以企及,从而似乎在以一种反衬的手法强化现实中人不可逾越的“天病”——天赋局限。
(二)短暂而荒诞的人生:片段性和戏剧化的“生”
庄子重生,以“养生”为主题的“养生主”阐述的是合理之生的原则与方式。在《庄子》中,万物在“生”处获得绝对意义上的等同,“齐物”“齐一”的前提是对“生”的尊重与珍视。不同于世俗之人“厚生—养生”的生命观和生活方式,庄子基于对自然生命的倡导而极力反对“厚生”:“悲夫!世人之以为养形足以存生”(《庄子·达生》)。诚所谓“五色乱目,使目不明”(《庄子·天地》,由生命有限引发的“厚生”是盲目恐慌的表现,其不仅无益于生命本色的彰显,反而对人之生具有不可逆转的危害。这种对待生命的不当行为,在庄子看来只能导致生之悲。“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庄子·人间世》)不可企及的“来世”与“往世”将人逼促于短暂的“现世”之中。庄子的“重生—养生”以“生”之有限为思想和情感依据。“天下欢之日短而悲之日长,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长,此定局也。”①谢柏梁:《中国悲剧美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108 页。由生之瞬时和短暂,珍视生命与热爱生活也便显得“不可待”,而由此引发的诸种“厚生—害生”的观念与行为,复又使得本就短暂的生命附加不可承受之轻。
倘说庄子以生之短暂证成人生之悲态,进而由中生发出“生”的无限可能的话;以“生”之忽而与荒诞反衬人生之艰难与沉重,则体现出庄子“悲态”哲学的宛转进路。“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庄子·大宗师》);“俄尔子舆有病,喘喘然将死”(《庄子·大宗师》)。生与死的界限只“莫然有间”与“俄而”,此不免令人悲不自禁。《庄子·至乐》中,庄子丧妻后“箕踞鼓盆而歌”,惠施道:“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以,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对此,庄子回应道:“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针对庄子对“鼓盆而歌”的“辩护”,人们多关注其中的“齐生死”观点,并因此认为庄子超越世俗生死观以至于面对至亲的离世并无悲感。然而,惠施以“礼”之“表”对应庄子的外在行为,不仅忘却“礼”之实质,也难以窥见庄子之真实心理。“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虽而哭之,自以为不同乎命”,通晓死之自然与必然而后止悲,定然离不开理性之于感性的强力克制。庄子的“欲悲而不能”反而隐藏着极为深重的悲痛。“感人者,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泣欲诉。”②黄周星、王岱:《黄周星集·王岱集》,长沙:岳麓书社,2013 年,第162 页。看似荒诞的“鼓盆而歌”,何尝不是庄子之悲的极端表现形式;庄子之歌,又何尝不是如泣如诉的大悲歌。
(三)复杂而有待的自我:受限与无力的“身心”
庄子“悲态”产生的根源性动因是人对自然天性的悖离,以非自然方式生存的必然结果是“有待”。在《庄子》中,世间万物绝大多数都“有待”,就连“御风而行”(《庄子·逍遥游》)的列子也有依凭和借据。真正的“无待”者只有道、天地以及极少数得道的“至人”“真人”。庄子致力于刻画与描述的主体以“有待”者占大多数,如身体残缺者、智识有限者、道德缺失者等,而其对“有待”者的生存境遇的揭示,也使得艰辛、无奈、困顿等的悲况与悲像尽显。
“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杨国荣教授以“井蛙”“夏虫”“曲士”比喻不同存在形态的人,认为“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分别对应“受制于特定环境”“为一定的历史条件所限制”“片面性的思想、观念对人的影响”③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111 页。。在生之局限性上,人与井蛙、夏虫并没有本质差别,区别在于人之束缚和局限往往是主客观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④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12 页。受制于外物和自身的限制,人总要面对不可预测和无法抗衡的“不得不”之“悲态”。在《庄子》中,智识、视野和道德的“有待”既是“悲态”的表现形式,也是导致“悲态”的根本原因。
“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夫知亦有之。”(《庄子·逍遥游》)面对接舆对“藐姑射山神人”的“质疑”,连叔以目盲、耳聋之人的感官局限对应接舆浅显的见识,表明凡俗之人与得道者认识层次的天壤之差,从而勾勒出“藐姑射山神人”令人心生向往的生存样态。智识有限,不解与疑惑便难以消解,由此引发的心理、思想、精神、行为之紧张、局促、困顿等“悲态”也便是“常态”。针对蜩与学鸠对鲲鹏“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逍遥游》)的不解与嘲笑,庄子用“行路备粮”的隐喻揭示芸芸众生重眼前实际而忘长远未来的局限视野。这也是“小大之辩”对个体局限性的形象揭示。视野之差别导致人们观念与行为之差异,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嫌隙、矛盾旁生不断、此起彼伏,此无疑是现实中人时常面临与应对的“悲态”。“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庄子·天地》)“机事”者究其根本是“人为”之事,为则伪矣。“机心”重则“道心”浅,道德发展便难入无为之妙境。在老庄语境中,硬性、人为、外在的“机事”必然损伤与戕害柔软、自然、内在的道德,“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机心”导致的道德危机始终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增加与深化着人类“悲态”的形式和内容。
三、《庄子》“悲态”美学价值的生成路径
在对“悲态”的描述和表达方面,庄子是毫不保留与淋漓尽致的;在对“悲态”的态度和方式上,庄子无疑极为积极与乐观。庄子重“悲”却不迷执于“悲”,而是积极寻求多种突围“悲态”的方式和途径。经由“下沉-升华”的过程,庄子将“悲态”与大化流变的宇宙人生相关联,从“悲态”中超拔与升华出关乎个体自我、宇宙自然的积极精神体验和价值观念。勇于突破、消解和超越天赋或后天“悲态”,此既是《庄子》“悲态”哲学的内在归旨,也是其现实关怀的真切表达。
(一)怒生:化悲为力
区别于“无为”“自然”“顺应”等的道家概念,“怒”是理解《庄子》的独特维度。倘由“虚无”“顺命”中可导出消极“避世”或“出世”思想主张的话;在“怒”处,则可明确得见庄子对主体性的高度持重与认可,从而也能够抽绎出庄子思想积极“入世”的内涵和特点。以“怒”的方式打破“生”之种种“悲态”,促成“生”之“绽放”,是庄子“怒生”观的核心意旨。
“怒”字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在描述“鲲鹏南徙”时,“怒而飞”用以表明“鹏”之飞的动作与态势。“怒,鼓怒翅翼”①杨柳桥:《庄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2 页。,以“怒”为修饰,“鲲鹏之化”是鲲鹏奋力突破局限并实现超越的主动行为。“‘怒’中有主动的奋发、振起,在‘怒生’中充盈着的是上达之冲动与不可遏制的生长趋势”。②陈赟:《〈庄子〉“小大之辩”两种解释取向及其有效界域》,《学术月刊》2019 年第8 期。鲲鹏之“怒”飞是一种在原始力量促动下的行为,其中蕴含着机体的勃勃生机与奋力行动。在主动之“怒”中,鲲鹏实现“图南,且适南冥”的宏愿,达至“逍遥”之高美意境。
不同于鲲鹏的“怒而飞”,蜩与学鸠之“飞”是“决起而飞”,斥鴳则是“腾跃而上”。“怒而飞”“决起而飞”“腾跃而上”虽在形式和状态上存在差别,但蜩与学鸠之“决起”、斥鴳之“腾跃”与鲲鹏之“怒”都是对奋力、竭力之主体行动的摹写与表达。如同鲲鹏,蜩与学鸠、斥鴳也是在竭力的“决起”与“腾跃”中突破各自之局限而实现“飞之至”,达到观念与行为的极致境地。庄子善以自然事物比拟个体人生,郭象注“春雨日时,草木怒生”(《庄子·外物》)曰:“青春时节,时雨之日,凡百草木,萌动而生。”①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826 页。鸟兽、草木尚且“怒生”“怒飞”,人之“怒生”更是促成个体摆脱局限、实现自我的根本方式。
(二)显用:以悲为用
符合中国古典哲学“藏体显用”的一贯特点,庄子重视“用悲”。《庄子》中的诸多人物和事物都能凭借“用悲”而尽性全生。比如,“匠者不顾”的“樗”、“无用”之“大瓠”(《庄子·逍遥游》)、“支离疏者”(《庄子·人间世》)等皆因“悲”生“喜”,由世俗之悲处得其天年。
《庄子·逍遥游》中,庄子在指出惠子“瓠”“樗”之困的根本原因在“拙于用大”后,给出疏解郁结的根本方式——“以无用为用”:“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游于江湖?”“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顿哉!”以“无用”为“大用”,关键在于积极转变对待“无用”的消极与否定态度,改变看待“无用”的视角,从而发现“无用”之妙处。“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庄子·人间世》),皆因“无用”而悲戚,庄子却因“无用”而欢欣,“以无用为用”体现出老庄的“反向”思维进路。
庄子不执著于“有”之用,而是在否定“有”之暂时与不确定性后,将视野集中在“无”处,认为生万物的“无”乃是真正的“大用”。“反者道之动”(《老子》第40 章),一旦意识到事物发展的“反向”“返回”的必然规律,则由消极否定的世俗“无用”之“悲”处必然能够导出积极美善之“喜”与“乐”。面对“大瓠”与“樗”,庄子生发的不是极端的“掊之”与挥之不去的“困顿”,而是乘“大樽”而“浮游于江湖”以及“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的“逍遥”心境,其中之畅然自适不可不谓高美之境。
(三)待时:悲中候运
《庄子》的“待时”具有顺应时势和等待时机的双重含义,其以对外部时势的顺应为前提,实质则是在顺应时势的前提下等待机缘以行动。“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庄子·齐物论》)以及女偊答南伯子葵问话(《庄子·大宗师》)中多次出现的“守”字,皆确证了“顺时”“待时”之于“得道”的重要意义。由于“悲态”总是以必然和偶然的形态持续存在,故而以“顺时”的方式积极应对“悲态”是庄子极力倡导的理想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
《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是“顺时”者。庖丁之“顺时”可被理解为“顺势”,即顺应牛之机体的内在走势。在“见全牛”至“不见牛”的漫长历程中,庖丁定然面临和经历过诸多疑惑与困顿,所幸之处在于庖丁始终秉持“顺势”的原则不断精进技艺。经由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庖丁之技艺最终通达“游刃有余”之道境,传递出“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和谐美感。至于庖丁解牛后的“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则可被视作个体经由消解或化解“悲态”而实现理想预期后的积极心灵享受和精神体验。
《庄子·逍遥游》里的“鲲鹏”,同样经由顺应和把握时势而实现突破与超越。“徙于南冥”确然不能凭借“鲲鹏”一己之力实现。“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者,海动也。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海动必有大风,而后可以南徙也。”②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2—3 页。“海运”并非鲲鹏“徙于南冥”的原因,而是垂天之翼依凭而起的条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易传·艮·彖》)倘若没有“海运”这一契机,单凭“不知其几千里”的“鹏之背”和“若垂天之云”的“翼”,绝不可能“适于南冥”。然而,倘若鲲鹏没有“绝云气,负青天”的意志、能力和行动,徒有“海运”之条件,则亦不会“适于南冥”。“鲲鹏之化”的隐喻表明,在“顺时”的前提下通过自觉而合理的行为突破“悲态”的限制,是实现与超越自我的必然途径。
(四)顺命:安悲若命
人人都有突围“悲态”的内在需求,也有各不相同的“突围”方式。有身体力行者,有善于转化和利用客观条件者,有善待时而动者,也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者。庄子认同并主张“顺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在庄子看来,接受与顺应命运是道德达至高点的标志。
以庄子之力倡“自然”而言,“安之若命”无疑最“自然”;以人对宇宙天地本源和终极地位的体认,个体也定然是“不可奈何”者。“不可奈何”是对人之势能的否定,其之于人而言是必然性的“悲”。然而,由必然之悲转向“安之若命”的柔和生存样态,既非逃避或回避“悲态”,亦非在“悲态”中沉沦与堕落,而是以一种柔性迂回的方式安置自我身心。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是传达“被动”的人性和人生观,而是意在彰显人对合于“道”之理想生存样态的主动选择权。人不是被动的“不可奈何”与“安之若命”,而是在理性确认的基础上,主动回归自然、平静、淡泊的生存理念与生活方式。诚然,只有在主动与主体的意义上,人才能成为区别于动物与事物的“德之至”者。
《庄子》中的主体因“顺命”“安命”而受到关注与认可。《庄子·大宗师》中静待造物者施化的“畸人”意而子,将自身缺陷的补救完全诉诸于造物者:“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锤之间耳。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之以随先生邪?”面对身体的残缺之悲,意而子并非毫不在意,否则不会在“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的“悲”例中寻求自我安慰,也不会因对诸此之“悲态”的思索而总结出“皆在炉锤之间”的原理和规律。然而,对比世俗之人沉浸于“悲”乃至于为“悲”所摧毁的情形,意而子的“安之若命”充满着乐观与豁达。这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因身体缺陷而导致的心理和思想困境,从而使人生充满希望与期待。“畸人”意而子的“顺命”既是大悲之后的觉醒,也是个体思维观念不得已的“大转向”。由此“转向”,人之生才能真正摆脱外物的牵绊与束缚,从而驶向豁然通达的自我—自由之境。
四、《庄子》“悲态”美学的现实镜鉴
有学者指出,“在人性面前,三千年的时光几乎没有什么威力”“有时古典文学作者比现在的文士还要更明智勇敢”①钟叔河:《周作人文选 1898—1929》,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年,第480 页。。《庄子》的学说魅力和艺术光华在历史长河中的持续蔓延,与其颠扑不破的时代通用性密不可分。庄子的“悲态”与现代社会的“悲态”在实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互通性,既是促成庄子“悲态”哲学现代性表达的基础,也可为现代人理性体认、预防、消解和利用“悲态”提供有益镜鉴。
(一)认识自我:“悲态”的解蔽与澄明
无论是在专门的哲学理论中还是经由对日常生活的体悟,人们都会时常感受和经历作为人生有机组成部分的“悲态”。以消极和否定为特性的“悲态”是人们无可逃脱的生存环境。既然“悲态”之于人是必然现象,那么个体对于“悲态”的理性认识则是个体获悉自我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逃避”对于“悲态”的感知,虽是一种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和普遍的心理现象,但忽略或否定“悲态”也是拒绝认识自我的表现。其结果是自我人生的模糊和失控,以及人们在“悲态”中的麻木与沉沦。由“悲态”的消极和否定性而言,认识“悲态”即是勇于与不理想的自我“照面”,由此关于自我的模糊认识会得到“澄明”;由“悲态”作为哲学思索的结果而言,认识“悲态”也即经由哲学沉思走向自我“解蔽”,由此自我意义与价值会获得更加清晰的显现。
认识“悲态”就是认识自我,“风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齐物论》)人各有悲,悲各不同,认识“悲态”需要坚持个体性原则。以自身之悲为认识对象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感官和心理的作用,从而更有助于个体从中获知生存与发展的真谛,并赋予自身之悲态以特殊而切己的意义和价值。《庄子》中具备自然德性的主体都能在对自身“悲态”的中肯认识中掘发出有关自我人生及社会人世的一般原理,从而能够随性养身、符道合德。“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庄子·大宗师》)以对宇宙自然之强力与自我身心之局限的理性认识为前提,人才能够合理对待和安置自我。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荀子·正名》)人是群居者,对于自我的认识既可以通过体认自我之“悲”的途径实现,也可以通过间接感受与体认他者之“悲”的方式获得。“有人之形,故群于人”(《庄子·德充符》),与他人共处是人的必然本质和天然需求。这种个体的群居宿命使得“悲态”往往具有“群体”属性。庄子对个体“悲态”的描述背后隐藏的是“群像之悲”。抑或说,个体之“悲态”是他人乃至全体之“悲态”的典型代表与具体呈现,由个体之“悲态”可推至群体之状态与处境。人对他人之悲的体认并非全然依靠“有意而为”,心理机制的相通性为人们的感同身受提供原始依据。“恻隐是一种道德感情,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的道德感情。”①何怀宏:《良心与正义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57 页。由同情心和同理心引发的共鸣与共情,为人们以“悲”为内容的交流和沟通提供可能。有鉴于此,人们既对自身“悲态”进行积极主动的觉察和认识,又借助对他者之悲态的体认而生发切己的感触,可谓全面有效“认识悲态—认识自我”的途径与方法。诚然,“悲态”究其根本是符号动作的结果,这意味着人们对同一悲态的觉察和体认不可避免的存在个体差异。这种经由认识他者之悲而明晰自我处境的方式、过程和效用也往往因人而异,需要人们加以灵活调控和把握。
(二)关怀自我:“悲态”的消解与珍视
“关怀自我”是贯穿中西方哲学的核心命题。先秦道家阐发自然人性的目的在于促成人们对原初本性的体认与回归。道家“复归”的根本意义不是“返回”,而是对原初自我的回望、珍视与坚守。西方哲学家福柯通过赋予“自我技术”以“个体通过自身努力或凭借他人帮助,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进行某些操作,从而改变自身,以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善或不朽的状态”②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 Patrick H. Hutto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8:17-18.的定义,以及追溯古典犬儒主义者的生存样态,构建出其哲学思想“自我关怀”的主旨。“左右一切行为的规则是,生命体总是会本能地保护或增强其生命力。一言以弊之,支配一切行为的生理原则乃是自我保护。”①[美]乔治·萨拜因著,[美]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民族国家(上)》第4 版,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29 页。突破与消解“悲态”是人的原始需求,经由消解“悲态”而关怀自我则是人们实现理想生存的重要途径。
消解“悲态”既源自“关怀自我”的需求和动力,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与方法。基于“自我关怀”的动机与目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实现对悲感的重新叙述、忘却、转移、转嫁,从而成功地把悲感化解②谭光辉:《论悲感的叙述学原理、作用和化解方式》,《兰州学刊》2018 年第11 期。。比如,积极运用个人或群体的力量主动改变不良处境、转化和利用周围环境间接改善不良态势、顺应和把握时机一举打破束缚和限制、经由体认他人处境提前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借鉴他人观点解决自身困境、用开阔的心境和视野在逆境中寻求自我发展等,皆是现实中人消解“悲态”的重要方式。由“悲态”的不可逃遁性而言,消解“悲态”是人生的永恒课程,具备应对和消解“悲态”的能力既是人之主体性确认与彰显的重要标志,也是人达至精神高境的必然要求。
“悲态”之于个体人生的消极影响是消解“悲态”的本原依据。然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第2 章),缺乏或没有“悲态”的人生定然充满缺憾和危机。“对人的力量持乐观信念,常常容易滋生对外部世界(包括社会领域)过强的支配、主宰等意向,并导致各种形式的理性僭越。”③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40 页。人生浩瀚纵横的欲望需要借助“悲态”予其以收煞和消止。个体人生需要“悲态”这盆“冷水”作为镇静剂,从容的人生从来不会只有积极乐观一种旋律。面对不可避免的悲态,人们既要及时消解“悲态”的负面影响,又要合理看待并珍视蕴藏在“悲态”中的积极意义,从而通过恰当地转化与利用“悲态”而达成积极乐观之结果。这种“消解—珍视”“既消解又珍视”的“悲态”观,既是庄子“悲态”哲学欲意传达的核心观念,也是现实中人关怀自我必须依凭的手段与方式。
(三)实现自我:“悲态”的转化与利用
以“苏格拉底主义者”著称的安提斯泰尼,经常借用医学隐喻指出社会价值与理想的病态特点。在安提斯泰尼看来,那些对财富、饮食、性过于贪婪,生性妒忌且又无知的人其实是患了严重的疾病,需要用理性来拯治。道家庄子也善用“疾病”的隐喻,其常借用身体畸形却道境高尚之人,表明“悲态—道德”之间的转化关系。朱光潜先生谈及艺术形式之“悲”道:“这种悲色彩对读者情绪的净化作用正在于将世俗意义上的怜悯和恐惧转变成为合于美德的思想情感。”④朱光潜:《悲剧与心理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154 页。“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51 章)。“道德”是中国古典哲学尤其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悲态”哲学转化与利用的最终指向是“道德”。
作为表达和呈现“悲态”的艺术形式,“悲剧是最上的艺术,就因为它能教人‘退让’,能把人生最黑暗的方面投射到焦点上,使人看到一切都是空虚而废然思返”⑤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38 页。。悲剧艺术所传达的“退让”精神实质和道德观念,与老庄“柔性”“不争”的道德主张互为贯通,是理解“悲态”向“道德”转化的重要介质。“老庄思想是一种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弱者的哲学,是试图用最消极的方式积极把握人生的生命哲学。”①郭忠义:《道家文化内核——复兴的原因浅谈》,《求是学刊》1992 年第2 期。道家之“德”的内在特性是“柔”而非“刚”,以“柔”的方式面对困境并非退让与躲避,而是以“无声”的方式达至转化和利用“悲态”的“胜有声”的理想效果。“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没有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件。”②[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175 页。道德之境从来不会自发形成,而只能是道德淬炼的结果,尤其是主体在“悲态”中以道德安置与回应自我、他人和宇宙万物的结果。由对“悲态”的沉思中获得伦理启示和道德指引,而非沉溺于“悲态”中不能自拔,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阿德勒(Adler)认为,悲感的被动性中隐含着主动性,“这种情感充分展现了以退为进、反弱为强的奋斗过程,展现了个体想要维护自己的地位、想要规避无力感和自卑感的意图”③[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汪洪澜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 年,第229 页。。面对消极否定的悲态,来源于生命的“强力意志”往往“逼迫”人们由对“悲态”的感受与体验中生发出无限的生命期待并将其诉诸于真实行动。这种主动弱化、克服、超越“悲态”而走向理想生存境遇的观念和行为时刻离不开理性的指引与规约。转化与利用“悲态”必须建基于对“悲态”的理性关照。理性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和确证悲态,也在于转变和改善悲态。以理性调控和运载悲态,而非停留在对“悲态”的感性认识中,能够促成“悲态”积极效用的最大化。“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庄子·秋水》)只有经由“理性的沉淀或融化”的“悲态”才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与价值。经由诉诸理性而体认、转化和利用“悲态”,方能真正成就与乐享理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