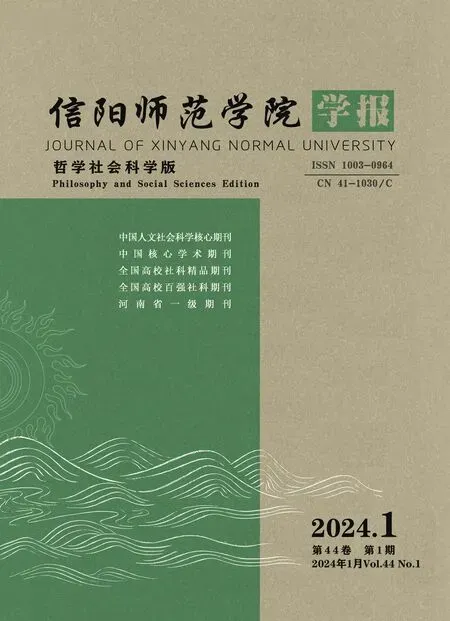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及其完善
李 卓
(武汉轻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00)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在法律层面最直观的体现。自特别行政区设立以来,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相关的法律体系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实施尚存在效力、落地、监督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本文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以后,对既有的全国性法律实施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全国性法律实施路径。本文以《香港国安法》为切入点,探讨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及其完善问题。
一、《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本文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制定之初,关于国安事项的规范条文即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们关注的对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第一稿中就对国安条文的制定背景做出了说明:“现行的《刑事罪行条例》中关于禁止危害英国皇室和背叛英国一类的规定,在一九九七年后肯定不能继续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有义务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届时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来替代,因此认为有必要对此作原则性规定。”立法者对于统一主权国家下的地方政府应当有国安相关立法这一前提基本是没有异议的,但对具体条文设置存在不同意见,主要分歧点包括对港人自由的影响、国安的范围和管辖问题等[1]191-197。
香港回归以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随即展开。其中,国安立法作为《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的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宪制责任,当然也被列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日程,但在推进的过程中却遇到阻碍。除在香港立法会内部产生立法争议以外,国安立法的反对者还广泛地煽动街头政治,多次组织反对国安立法的游行、集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迫于社会压力最终暂停了国安立法工作,同时也没有再行宣布立法时间表,导致香港本地完善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无限期推迟。尽管此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断提到要重启国安立法,但因始终担心由此导致公共关系危机而作罢。2020年《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前,出于维护特别行政区政府管治权威的目的,中央政府也始终未能以主导者的角色重启国安立法[2]。
2019年,反对派将主要政治议题集中于反对《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修订问题,并掀起对抗活动,最终爆发了前后长达一年有余的“修例”暴乱。在这一过程中,外国势力介入香港政治更加深入,集会和游行逐渐暴力化,演变为街头骚乱。应对“修例”风波而制定的《禁止蒙面规例》曾在立法过程面临重大挑战,国安法及涉及国家权力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威性的法律落实进程处于实质上的停滞状态。一方面,香港国安相关立法长期缺位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一大直接诱因;另一方面,香港急需一部法律来使社会恢复到安定的状态。
《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是非常迅速的。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本文以下简称《宪法》)规定了涉及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立法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因此在立法过程中援引了《宪法》第62条第2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和第16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立竿见影地解决了困扰香港一年有余的骚乱,对于“一国两制”政策的实践和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机制都产生了里程碑式的重大影响。
二、《香港国安法》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机制的突破
《香港国安法》作为“一国两制”政策的全新实践成果,是中央针对具体事务、直接行使中央立法权的结果。在面临重大挑战的前提下,依法充分利用宪法机制,以兼顾法益保护和效率的方式尽快地完成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工作反映了中央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充分尊重。在国家早已制定国家安全法的前提下,并未通过直接将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的方式在特别行政区实施,而是在充分尊重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前提下设立的专门法律。尤为重要的是,《香港国安法》也未以国家安全法和刑法国安条款为制定依据,而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现有的司法制度安排,排除了死刑的适用。
《香港国安法》对于既往的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机制有里程碑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中央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适用的新的监督形式。长期以来,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其主要原因就是全国性法律实践运用的不足。《香港基本法》18条规定了全国性法律由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但并没有明确决定实施方式的主体。在《香港国安法》以前的实践中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均由特别行政区立法机构自行决定实施方式。《宪法》《香港基本法》以及其他全国性法律均为特别行政区宪法秩序的组成部分[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责任,《香港国安法》在其立法依据部分重申了这一点。虽然其直接应对的是国家安全问题,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切实履行这一宪制义务的前提下,通过中央立法的形式补足了相关法律的缺位。
第二,完善了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方式。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是最主要的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方式,但其并没有明确由谁决定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在既往的实践中,这一权力均由特别行政区行使。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香港国安法》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授权关系,也开创了由中央直接行使这一权力的先例,即前者有权决定在特别行政区以公布的方式实施全国性法律。《香港国安法》规定的适用方式属于对具体事务的独立适用,在未来没有新的相关法规出台的情况下,不影响其他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模式,特别行政区依然享有判断是否符合其具体情况的权力。《香港国安法》的特殊实施方式,除了在立法层面说明自身的合法性以外,也体现了中央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尊重。
第三,《香港国安法》除了在实施方面的创新以外,在具体内容上也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创设了新的法律依据。《香港国安法》在香港具有宪制性法律地位,在特定的情况下直接引入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指定的检察机关对具体案件的管辖,并在第57条规定了由国安公署和国家监察机关介入的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虽然在基本法原则下这一条款不应当做扩大解释,但其创设的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情形,显然属于和《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并行的法律依据。
三、《香港国安法》以前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情况
在2020年实施的《香港国安法》以前,共有十四部全国性法律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基本涵盖了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各个主要方面,并形成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内的基本运行逻辑。大体上可以将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香港基本法》制定至特别行政区设立前后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占已实施全国性法律的绝大多数,基本属于国防、外交等国家主权性事务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以下简称《外国央行法》)制定实施至《香港国安法》制定为全国性法律实施的第二阶段,相较于前一阶段其立法特点在于主要围绕特别行政区新发生的具体事务和问题展开。
(一)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最初的实施
20世纪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先后设立,最初的全国性法律随即在特别行政区实施。除了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增加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外,其余全国性法律,均在特别行政区设立以前或设立当日即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当中。此阶段的全国性法律均为服务于特别行政区的设立。
从《香港基本法》起草至特别行政区设立之间有较长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已有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中增设、删减的先例,亦有就特别行政区事务的专门性全国性法律立法和司法解释。《香港基本法》于1990年制定完成并公布,同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有六部全国性法律,至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当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通过决定的方式对全国性法律进行了调整,并给出了增删法律的理由和依据,如《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的内容已经由新制定并且新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以下简称《国徽法》)所涵盖,故删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以下简称《国旗法》)未覆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的全部内容,因此一并使用,但其有关国旗的规定可与《国旗法》一并适用,以《国旗法》为准[4]。全国人大会常委会还对其他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同时,在港、澳回归时均以决定的形式强调“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的法律,如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不一致,应以全国性法律为准”[5]。
特别行政区为配合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落地也在立法、司法等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在立法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释义及通则条例》专门增设了有关全国性法律的条款,增设了在香港法律体系内的全国性法律的附属法律、文本说明。
(二)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先例的形成
在特别行政区设立的最初阶段,立法工作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确保“一国两制”方针,尤其是国家主权原则在本地立法上得到充分体现。第二,必须确保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够顺利运作。第三,必须确保与居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事项的顺利解决,尤其是永久性居民制度及国籍、护照、旅行证件等事宜的解决。第四,必须充分考虑原有法律的特点和立法时间紧迫、人手不足等实际情况的制约。其中,对于全国性法律的实施,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已经认识到全国性法律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以后即赋予特别行政区实施此类法律的宪制责任,并且未来可能出现全国性法律和本地法律落地的时间差问题。整体上,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平稳的。一方面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时间不长;另一方面,自“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到最终在特别行政区落地有相当长的过渡阶段,这使得相应的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有相对充足的准备时间。这一阶段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表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逐步完善。在“一国两制”政策提出和实践的过程中,“全国性法律”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化的过程。在政策上,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也是由抽象到具体、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在《香港基本法》制定阶段,有代表就中央所行使的权力进行了讨论。在全国性法律问题方面,最终形成了《香港基本法》第18条规定的若干种实施模式和第3款中包括“其他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兜底性条款[1]97。在香港、澳门回归的过渡阶段,除了《香港基本法》以外还有其他新的全国性法律被制定出来,其中不乏专门针对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法律。除了在过渡阶段被新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以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就国籍法等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做出了专门的适应化解释。
其二,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具有制度性先例的特点。本阶段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实践,包括了全国性法律的增设、删减、实施方式的选择,几乎涵盖了《香港基本法》第18条中一般情况下所有全国性法律实施的所有情况,也包括《香港基本法》第18条未明文规定的部分内容。例如,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全国性法律实施方式的选择主体、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立法和公布实施的具体方式等。部分问题通过具体的实践形成了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运行的先例,对于未来全国性法律的实施有指引作用。
中央可以以包括立法、法律解释、决定在内的多种方式,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进行调整;特别行政区也可以对具体法律做出提前评估和立法,完善本地法律实施机制。
(三)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后续实施
在《香港国安法》制定以前仅有《外国央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本文以下简称《国歌法》)两部法律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但其实施落地的过程却十分曲折。
《外国央行法》的制定肇始于回归初期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原有法律的整理[6]。但在2005年中央完成相应的全国性立法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仅通过新闻公报公布:“我们倾向透过本地立法在香港实施《外国央行法》,对该法律做出必要的变更及适应化,以配合本地情况。”[7]
相较于《外国央行法》更多地在法律技术层面体现不同于以往实施全国性法律的新特点,《国歌法》的制定和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则更多地直观反映了“一国两制”实践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宪法地位,直到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才得以确立。自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定国歌的宪法地位,到2017年《国歌法》的制定,经过了长达13年的时间。其间,2014年“占中”事件发生以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屡有发生“嘘国歌”等侮辱国歌事件。对特别行政区而言,《国歌法》的制定具有一定的针对性。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国歌法》,并同时将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特别行政区实施。从时间上看,《国歌法》不仅晚于《国旗法》《国徽法》等法律制定,也晚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和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因此未能在港澳回归之初与《香港基本法》同步纳入特别行政区实施。《国歌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国歌的尊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而在反对派刻意制造的对立情绪中,国歌和《国歌法》均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国歌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遇到了阻碍。《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依循《国旗法》《国徽法》的前例,决定在香港通过本地立法的方式实施《国歌法》。但是,《国歌条例草案》2019年才被提交至立法会审议。在立法过程中,《国歌条例草案》受到了一定阻碍。直到2020年年中,《香港国安法》制定和实施以后,《国歌条例》的立法工作才得以完成。
四、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机制的完善建议
在《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定的形式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并对特别行政区做出指令,这为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机制,并充分体现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这种模式毕竟充满了紧迫性。未来紧迫性不及《香港国安法》的其他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保障仍是立法者应当思考的问题。在现有的宪制秩序之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是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的制定主体,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仍然以《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公布或立法实施为最主要方式。除了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方式监督全国性法律实施以外或可以以《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改为参照,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增设条款。增设条款应当明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国性法律的效力问题。尽管在部分法律和中央文件中已经明确了部分法律的效力问题,但由于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并非为同一位阶的法律,且部分具体的法律条文能否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问题仍旧存在,因此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应当进一步明确。二是全国性法律实施方式的选择机制问题。在现有宪制秩序下,特别行政区仍是选择全国性法律适用方式的主要主体,但缺乏适用方式选择的法律约束。在中央立法和特别行政区实施存在时间差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进行清晰的制度化安排避免全国性法律效力长期悬置问题。三是全国性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制问题。特别行政区立法权本身作为中央全面管治权授权的一部分,应当接受监督以保证特别行政区及时有效履行宪制义务,这也是对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