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色十字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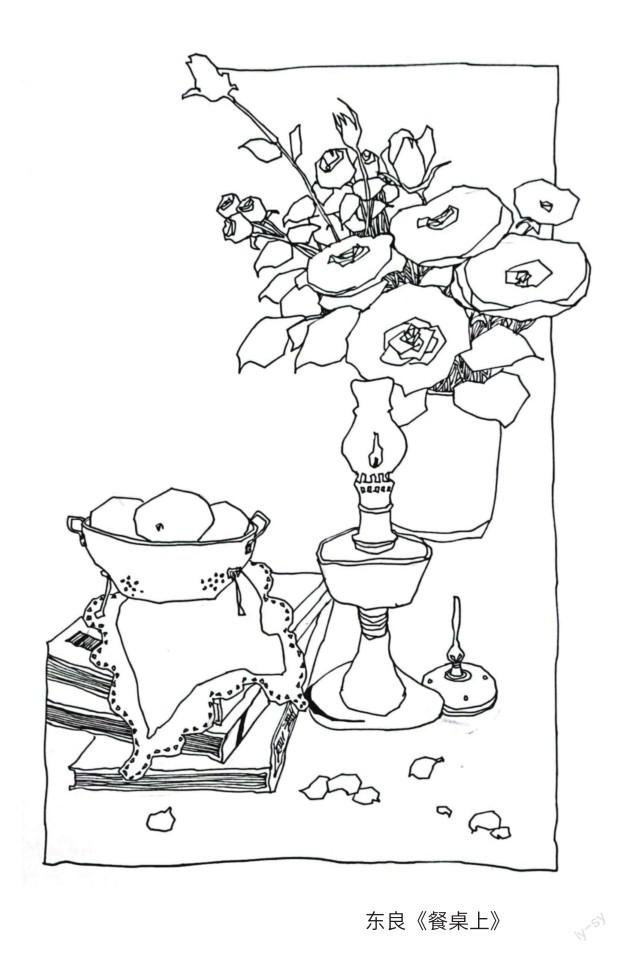
某天,在大学的选修课上,老师讲了些有关文学故事编写方面的知识,和有关神话本源、文学结构的分类。我昏昏欲睡,而在某个片刻,我的瞳孔感知到了一种光,它微微泛着红。我的眼皮垂下来。LED灯高悬,抚摸着我的视网膜,似乎要把我拖入短暂的休眠。
恍恍惚惚地,我听见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清了清嗓子,朗声说:“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挑选一个代表分享一个自己的小故事。”
我的眼睛半眨不眨,如果说,上眼皮是他的头颅,那它最终还是倔强地昂首了,露出一对丝毫不显倦色的瞳孔,尽管它实在有些黯然。
坐在第二排还是第三排?我忘了。我别过头,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后面一些不认识的同学。他们同我一样,都没精打采的。我们在这水泥箱子里坐着,每个人都像是半熟的稻子,或端坐或叉手或趴着。这个晶体一样的房间,有人进来,有人出去。这样的过程,又是多样性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两个元素,就好像构成了整个晶体的各向异性。教室不是千人一面的建筑艺术作品,灯光一开,便是生机。
只听见老师又不紧不慢地说道:“也不一定是你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可以是听说过的一些事情,但又必须是让自己随时随地拿起来都能够记得的东西。”
有的人抬起了头,有的人神色焦虑,有的人坐在后排,眼神游离。
我本想着找来一些《故事会》或者《新锐阅读》之类的,或幽默、或惊悚的小故事。说到底,那些事情都是我们在少时视若珍宝的回忆,那些如同快消品一般的文字,仅仅有某些只言片语被篆进了我们的脑海。如果单拎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讲,却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说到底,我们视若珍宝的,也只是当年偷偷看那些文字的过程,看它们时浮现在脸上的欢喜、震撼,在心里萌芽的悸动与感怀。这些才是真正被我们封存在回忆里的东西。
课前,我耳机里循环着肖佳的《奴隶》。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真心话说给墙听”。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想去讲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往往无法在短暂的时间里组织好满意的语言,去表达那些自己最珍重的回忆,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我们又往往只愿意说给自己心里那堵高高的、厚厚的白墙听。
我又想起来那件事。每每想起还是会含着泪,每每讲出这字字句句,我都会如鲠在喉。最后,在静静地听完排在我前头的其他同学讲述完一切后,我站起身子。
当时我还在岳阳老家,念小学。那时,从我的老家平江县到省城长沙的高速还没修建。我爸爸是他这一辈的兄长,他的堂亲表亲很多还在念书。他们如果去上大学,便常常在我们家落脚,然后去城中央的老火车站坐车,即便是坐大巴,也要方便很多。
那是个晴朗的日子,我正在小区院子里玩耍,想要从那堵铁栅栏钻到隔壁小区去,结果把自己的大脑袋卡在了围墙的两个铁杆子的中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的小伙伴们在一边干着急,我自己更加慌了,除了哭泣以外,我把一切能够表现出我慌乱情绪的面部动作都做了出来,就像憋尿一样。我的头发贴着头皮,而脑袋又紧贴着铁栏杆。我用两只手拼命地去拉扯那比我骨头还要坚硬的铁。我的手上也抹上了一层从栅栏上脱落下来的锈。我手心手背都是汗涔涔的,慢慢地,把那锈迹化成了一坨坨漆黑的印子。时间也随着我的汗水,一滴一滴,止不住地流逝着。
霎时间,我听见了一句平江话——我老家的方言属于赣语系,跟岳阳的湘语区别很大。这一句话分外清楚,仿佛全世界除了那流汗的声响,我只听得到这一句话:
“把头向上挪。”
我看不见人,但我如获至宝。我拼命地把自己的脑袋向上挤,擦着钝化的铁的棱角向上蹭。渐渐感觉好像上面宽敞了些。于是,我开始把脑袋往外拔,先是缓缓地试探性地动,后来就像拔木塞子一样狠狠地往外拔,也顾不上那些青筋上钻心的疼痛。我把脑袋一下子拔了出来。
我带着胜利式的笑容回头望,只见她咧着嘴,笑了。暮色中,那笑容似一朵深秋的芙蓉,稍稍有些疲倦,带着自然的弧度。我用独属于孩子的高音大喊了一声:“炼姑!”
炼姑是我第二小的姑姑,也是我爸最小的堂妹。
那时候我念三年级,刚开始学英语不久。晚上,在我家书房,她便教我念英语书上那句“nice to meet you”。那时候,步步高点读机是学英语最流行的物什,但我妈舍不得买,家里CD机也烂了。我装模作样地学习着我的第一个英文句子。后来,她又教了我更多,一个又一个……她回过头来,问我第一个“nice to meet you”怎么讀,然而,我竟然把它忘记了。我龇着牙齿,露出无比尴尬的笑。过了一会儿,我们在客厅闲聊,她同我爸妈讲着我傍晚在围墙边的趣事。我连连叫她快快打住,她倒更加兴致勃勃了,笑盈盈地讲着。我窘得上门牙咬下嘴唇,脸上也酡红一片。终于,她停了嘴,关于我的窘事已经彻底说完了。他们都哈哈笑着,我气得浑身发抖。
炼姑对我说:“拓拓,我奖励你个东西。奖励你今天克服了大困难。”
一听到有奖励,我便忙不迭说好,把之前所有的不开心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近我在学一个小手艺,绣十字绣。你喜欢什么样的啊,我绣一个送给你。”
“什么是十字绣?”小孩子嘛,总对那些新事情好奇,乃至忘了过问礼物的事情。
我妈妈边剥着橙子边对我说:“就是你外婆家电视机墙上挂的,你舅妈绣的那个‘家和万事兴,还有一朵芙蓉花咧!”
我恍然大悟,连忙又把话题调转到礼物上去:“‘喜羊羊,你绣一个‘喜羊羊送我,好吗?”
炼姑答应了,说等下一次来我家的时候,她一定送给我一个崭新的“喜羊羊”。
第二天,炼姑去上学了,我爸爸送她去车站前,她带我出门吃早餐。还记得,那是一家常德津市牛肉粉,开在马路对面,牛聋子牌的,在这条街道上很有名气。我念小学时,零花钱多取自早饭、公交车费的结余,我向来舍不得吃那十二块一份的牛肉粉。每次要到这家店里嗦粉的时候,我总会偷偷跟老板吱一声:“老板啊,给我的肉丝粉里加点儿牛肉汤呗。”老板人好,总是笑嘻嘻地答应我。自然了,那次也不例外。可炼姑见了,说:“这怎么能行呢?你小姑我请你,要加多少牛肉加多少,直到你满足。”而“拮据”惯了的我,当然是感动得稀里哗啦。
第三天,我把我的“喜羊羊”十字绣变成了心心念念的事情。上语文课对自己讲,上数学课对同桌讲,只有上英语课我认真地听。只因为炼姑最后告诉我,要是再念不对那一句“nice to meet you”,就会没收我的“喜羊羊”。
但这十字绣版本的“喜羊羊”在我的脑子里也没待多久,第二周,又或许是下下周,我心心念念的玩物,就变成学校外面小卖部挂着的、最新款的陀螺了。
湘北的晚秋和冬天别无二致,南方的植被不同于北方的落叶阔叶林,那些绿叶总是与寒冬做著斗争,负隅顽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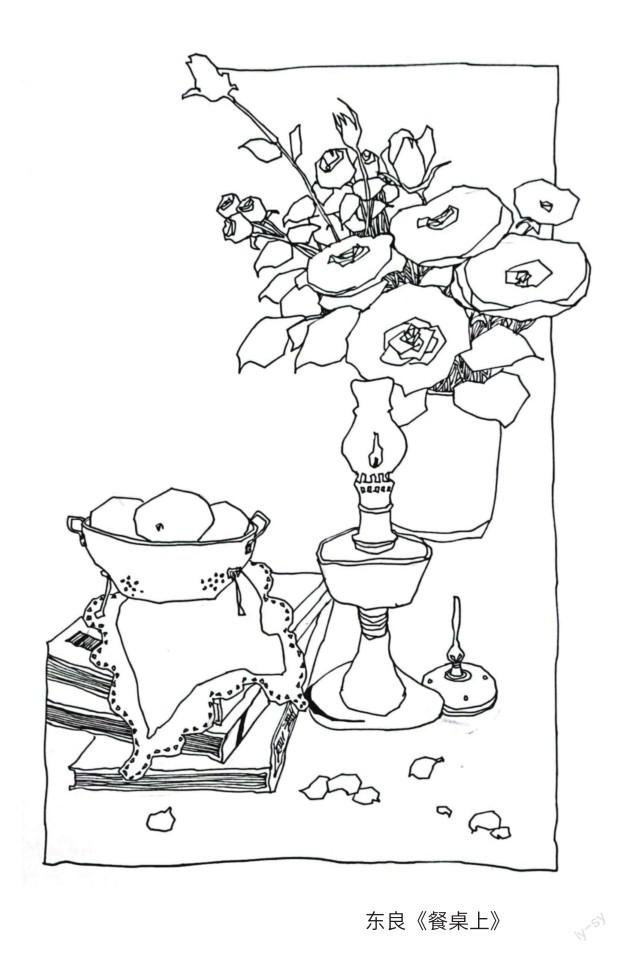
炼姑回来时,我都不知道已经到快要放寒假的时候了。在客厅的炕桌架子上,躺着一个白毛黄铃铛蓝带子的“喜羊羊”。我的脚步追随着目光,从门口朝着那边一路小跑。我抓起它,捏着,里面都是绒毛,也许是棉,也许是羽绒。这一点,尚且幼小的我还傻傻分不清楚。正当我兴高采烈的时候,炼姑从厕所里走出来,洗了把脸。我看到她还是冲着我笑,只不过,这次挂在那笑容上的不再是白天时浓烈的阳光,而是一颗颗的水珠,晶莹剔透。
是了,是我曾经心心念念的十字绣。
可是,我越发觉得这铃铛的带子和鞋子的蓝色有点淡了,我就问她。炼姑挠挠头发说:“没有那种稍微深一点的蓝色的线,只有这种水蓝色。”
我爸爸小啜着一杯君山银针茶——这是我故乡的特产,他轻轻地瞪了我一眼,还算平和地说:“说谢谢炼姑了吗?还要在这里挑三拣四的。”
我不大高兴,嘟囔着说:“什么嘛,什么水蓝不水蓝的,不就是天蓝色吗?”
炼姑反倒富有激情地问我一句:“你看过海吗?”
我说没有。她说她也没有,紧接着又说:“水蓝色不是说的我们这边的湖水,是海水那种淡淡的蓝色,或许是倒映出来的天空,但也有自己的变化。天空的蓝并不稀有,这样经过处理的水蓝色才稀有,不是吗?”
“啊……就像那些稀有的金色画片一样,是吗?”我似懂非懂,仰起了脑袋,张着嘴巴问。
那个时候,我没有,也不会注意炼姑说这句话时候的眼睛。现在想来,她那时的眼睛,一定是晕染了倒映着天空的水蓝色,像是一种萤火虫般的希冀在闪烁,在发光。
过年回来,炼姑再经过我家的时候,我却把那个“喜羊羊”落在乡下了,怎么找也找不到。炼姑对我说,没事,大不了她再给我绣一个。
是啊,再给我绣一个就是了。我挠了挠头,有点儿不好意思。第二天,她走了,去湘西的怀化上学,那是离海更远一点的地方。从岳阳到怀化,杭瑞高速上四百七十一公里的距离。从彼时不久的将来去看,这个数字竟变成了生与死的距离。
收到炼姑死讯的那一天,正值寒冬腊月,冻得我两耳生疮。
事情源于一次车祸,她急忙躲闪飞驰而来的车辆,一不小心,竟掉进了路边的小河。据说,这河不宽,但也有两三米深。我们整个大家庭都感到错愕,然后是恍惚,没有谁,哪怕仅仅是一刻,愿意去相信去接受这个冷冰冰的、铁一般的事实。炼姑是多么阳光的一个女孩啊!怎么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无论如何,这种不幸的、作孽的事情也轮不到她呀!我不愿相信,我的炼姑,指导我把头从铁栅栏里拿出来的炼姑,给我绣十字绣的炼姑,让我吃上一大碗热腾腾的常德牛肉粉的炼姑,竟然成了铁栅栏上的锈渣,风轻轻一吹,就落了地。生命凋零的时候是多么凄惨啊!这凋零常常是美的,是物哀,但落到我的炼姑身上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最不能接受的,便是这种象征着生离死别的凋零。我的炼姑,她也同这铁锈一样,竟是那样的不起眼,飘零,幻灭在这沉闷的空气中。
那些日子,我总能听到那声熟悉的“nice to meet you”,可我再也回不上一句“nice to meet you too”了。那时候,我仅仅只是纯粹的伤心、恐惧。我所伤心的,不仅仅是失去亲人,对于天真烂漫的我来说,我再也见不到她给我的十字绣了。我所恐惧的是,她会在某个夜晚,从我家那扇嘎吱嘎吱响的厕所门口走出来,微笑着,又把那个十字绣放在炕桌架子上。
小孩子的思维能有多复杂呢?它是多么直白啊!过了这么多年,再去回想这件事,我宁愿相信,我的炼姑在另一个地方栖息着,就在那片丰饶的水色之中。尽管它不是海,可是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呢?
后来,我爸爸帮小爷爷整理遗物时,他们找到了一个十字绣,是个半成品。他招呼我,叫我过去看看。其实,它接近成品了,只是里面没有被那双小小的手塞进去棉花。我用自己渐渐长大的手捏了捏。它干瘪瘪的,好像已经没有了生命。
我又注意到,“喜羊羊”铃铛的带子和鞋子都变成了更深一点的蓝色。这次她换上了颜色更深一点的线。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它本就没有生命啊。生命是由绣它的人所赐予的。至于绣它的人——我的炼姑,她向我摊手,向我妥协了。她不再追逐那千里外潮湿的海边,也不再把那水色的记忆编织进那桩深色的梦里。
最终,她坠入了那片沉郁的水色里,生不能得到的,终究愿意在死后相拥。
炼姑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有十多年了。我最终还是在课堂上分享了有关炼姑的故事,提及关键处,我的嗓子甚至还有些颤抖。其实,就像选修课的老师说的那样,大概率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想了又想,不管是在脑海里还是在梦里。在暗流汹涌的潜意识之下,人都会有一种冲动,去重复扫描那些同样的东西,就像我们不厌其烦地观看、咂摸1986年版的《西游记》电视剧一样。我总把这样一件事情,放在脑海中一个隐蔽的、但又能不费周章地找到的犄角旮旯里。每每我重新拾起这样一个记忆的只影,都会感到一种扎心的疼痛。它反反复复敲击着我,同时,也未尝不是我反反复复地敲击着它。
那天夜里,我坐在亮堂堂的教室里,心里却始终空荡荡的。我全然感受不到旁人的存在。其实,不会有人没有自己的故事。至于这些事情,即便不是我们所必经的,可它们带来的影响,对于一个已经成年了的“孩子”来说,也必将不可或缺。或欢喜,或悲伤;或窘迫,或无助。它们对于我们的意义是非凡的,是无价的。我愿不愿意分享出来,这是我的自由;我想如何去尽力地诠释它,也是我的自由。当一个无价之宝被我们牢牢掌握在手中,任由自己支配的时候,我们无疑是幸运的。只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大概不会留意这些我们所一直拥有的东西。它们永远都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瑰宝,从来都是这样。我也愿意去相信,这些美好的东西绝非刻意而为。它们永远是这样洗练,又是那么自然。
我会一直想念着我无比亲切的炼姑,会想念她的笑,想念那个被遗失的、由她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十字绣。不论何时何地,我感谢她,也怀着这份感谢,哽咽着写完了这一段文字。把我跌跌撞撞的思念寄托在故事里,把有关于炼姑的回忆写成一些今后看了,一直都会热泪盈眶的文字。
其实,那十字绣上的颜色,一直都是水色的吧。
责任编辑 王娜
作者简介
手石,本名陈拓,2002年生,湖南岳阳人,西南交通大学2020级土木工程专业在读本科生。作品见于《星星》《上海文学》《滇池》等,曾获第六届零零国际诗歌奖、香港明月湾区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