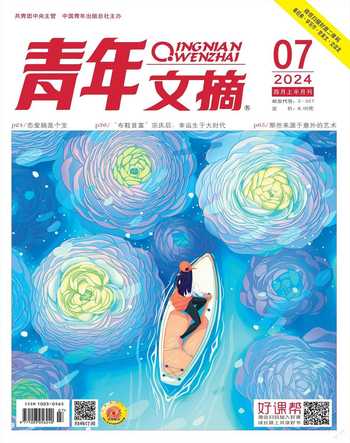跟着名师学写作
特邀名师刘艳军,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惠州市首席教师。发表文学作品和教学论文约10万字,散见于《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语文报》《羊城晚报》等。
作文题
有一个农夫,在树林里盖了一所坚固又宽敞的房子。林子里的动物都希望搬进去。孔雀跑到农夫跟前说:“让我和你住在一起吧,我长得最好看。”八哥飞来对农夫说:“叫我搬来住吧,我的嘴巴最巧。”母鸡也来到农夫房前说:“我长得不漂亮,嘴巴也不巧,我能干的事,就是下蛋。”农夫听了母鸡的话,说:“踏踏实实地下一个蛋,比摆弄一百次漂亮的羽毛、说一千句好听的话都宝贵得多。欢迎你到我这里来住。”孔雀和八哥听了农夫的话,都羞愧地走了。
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
[名师范文]
愿你爱上孔雀和八哥
饥肠辘辘的时候,鸡蛋的诱惑力的确比孔雀的羽毛、八哥的声音大得多。然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我们为什么还执念于一颗鸡蛋,对孔雀的羽毛、八哥的声音无动于衷,甚至嗤之以鼻?
我们的审美出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只大力颂扬实用之美,对色彩、形状、线条、声音等呈现出来的形式美不遗余力地进行贬抑。
还记得那条洁白的连衣裙吗?还记得曾经长发及腰的童年吗?然而,父母和老师让你把裙子藏箱底了,让你把长发剪短了,因为“臭美”会影响学习的。结果呢?你不但丑了,而且成绩还差了!殊不知,一个人的成长,是穿上斑斓蝶衣的蜕变。一个孩子,打扮得美美的,往往是自信心增强了,交往能力提高了,学习成绩也进步了。
如果对形式美的追求有错的话,人类真的是错得太久了。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已经用兽齿串连起来作为项饰,在磨光的鹿角和鸟骨上刻上疏密有致的线痕。法国的拉斯科洞穴被誉为“史前的卢浮宫”,其壁画绘于约一万五千年前,风格抽象,线条简练生动,对形式美的追求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普通大众以貌取人,自然是西施美,东施丑。而圣人呢,竟也有免不了只看脸的时候。澹台灭明,孔子的著名弟子,当初请求拜孔子为师的时候,因其“状貌甚恶”,孔子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材薄”。在国外,还有更离谱的案例呢。公元前340年,雅典一女子按律当死。辩护人用动情的言辞质问:“难道你们忍心让这位阿佛洛狄忒的弟子香消玉殒吗?”这打动了陪审团,最终判女子无罪。金玉其外并不天然与败絮其内联系,而且作为人的第一印象,可以增加人生的可能性。
在当代国际社會,公众人物的个人形象不仅仅关乎个人,更关乎民族和国家。2013年3月,彭丽媛随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以一袭端庄的织锦外套向世界展示了青花瓷般精美的中国风格,传递了民族自信,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至于艺术,对形式美的追求就更加自觉了,它根本就不是给你吃的鸡蛋。屈原的《离骚》能吃吗?随州的编钟能吃吗?断臂的维纳斯雕塑能吃吗……人终究是一种美好动物。所以,人总是沉浸于赞美、搜集和创造美色、美音、美景、美酒、美好的人格。
孔雀的羽毛不漂亮吗?八哥的声音不好听吗?可是,孔雀和八哥却“羞愧地走了”。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
[名师感言]
材料的价值取向比较明显,赞美母鸡的“实用价值”,贬抑孔雀和八哥的“形式美”。但我在写这篇作文时反弹琵琶,结合中外的历史和现实,用发展联系的方法来挖掘材料的“启示意义”,论证了审美的重要价值。围绕“审美”这个关键词,本期《青年文摘》可以找到很多素材。比如《成长,是穿上斑斓蝶衣的蜕变》,既讲述了妈妈对我审美的限制和束缚,也讲述了我打扮好看以后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好不止在故事,更因这故事传达的观念。再如《人是一种美好动物》,从音乐之美切入,将文章的意旨升华至人对所有美的自觉追求。这些文章的相关文字,稍微整理一下,甚至直接照抄,即可化为我们作文的事实论据或者道理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