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逸话:爱乐世界的一抹亮色
孙国忠
音乐逸话(m u s i c a l anecdotes)通常指的是音乐“正史”之外的关于音乐艺术的传说、轶事、掌故和趣闻。虽然这些内容与专业的音乐学术研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对广大音乐爱好者来讲却有着音乐欣赏的引导和助兴作用。音乐逸话不仅有趣,也有一定的知识蕴涵。爱乐生活中如果有音乐逸话的点缀,那么音乐的聆听和感知肯定会多一种趣味与智性交织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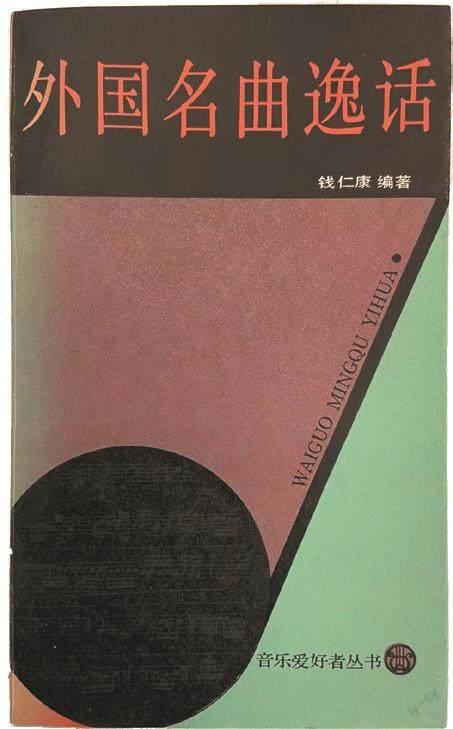
钱仁康先生是音乐学大家,在他留下的逾一千万字的学术遗产中,就有一本很好看的《外国名曲逸话》。这本书有两个版本,第一版问世的时间是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二版是201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除了一些文字上的修订以外,第二版与第一版的主要区别是增加了一篇文章,从原先的一百篇短文增加到一百零一篇。这本书面对的读者主要是音乐爱好者,但音乐界的专业人士同样可以从中获取知识,得到一些启发。正如钱先生在此书前言中所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除了使音乐爱好者增加欣赏音乐的兴趣外,还想为音乐工作者提供一些野史资料,使他们得以从侧面了解部分外国名曲的创作动机、创作构思和标题命意等等,以便对分析和研究外国音乐作品有所启发。”
《外国名曲逸话》的整体构架非常清楚,按音乐体裁来呈现逸话,包括歌曲、圆舞曲、特性曲、变奏曲、钢琴奏鸣曲、室内乐、协奏曲、交响曲、歌剧等,只有最后一部分“名曲纵横谈”是综合性杂谈。从这样的布局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对名曲逸话的明确归类,也能感觉到所谓“野史”资料与音乐“正史”叙事的某种内在联系。我曾经讲过,钱先生的谈音论乐语词清澈、笔调从容、行文畅达、文风质朴。这种书写风格尤其体现在钱先生为音乐爱好者的写作中。阅读这本《外国名曲逸话》,我想每一个音乐爱好者都会感到轻松愉快,如同好友之间的音乐闲聊,既有知识分享,又有随谈的舒畅。


此书的第六十篇短文可以更正我们对海顿交响曲“曲名”的认知。我们知道,海顿的一部分交响曲都有一个“曲名”,虽然不是作曲家自己起的,但这么多年叫下来已形成约定俗成的“曲目指称”,例如《告别交响曲》《惊愕交响曲》《军队交响曲》和《牛津交响曲》等。《D大调第九十六交响曲》亦称《奇迹交响曲》,传说此曲于1791年首演时,一盏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却没有伤及听众,可谓“奇迹”,此曲因此得名。然而,据海顿研究专家 H. C. 罗宾斯·兰顿考证,这一奇迹般的事故确有发生,但具体场景并不是1791年《D大调第九十六交响曲》的首演,而是《降B大调第一百零二交响曲》于1794年的初演。因此,通常所说的《奇迹交响曲》实际上是一部作品的“张冠李戴”。
第八十八篇短文的标题是“急来抱佛脚”,说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趣事。罗西尼的创作向来有“急来抱佛脚”的习惯,他的许多歌剧序曲都是在歌剧上演的前夜或当天赶写出来的,他甚至还很自豪地向一位青年作曲家传授这种“急中”才能“生智”的作曲状态和方法:“没有比急迫的需要更能激起灵感的了。抄谱员等着要稿子,经理急得扯头发,对创作是一大帮助。在上演我的歌剧期间,所有的意大利经理都是三十岁就秃了顶。……《贼鹊》的序曲,是在第一次上演的当天写出来的。换布景的工人们在旁边看着我,他们奉命每当我写好一页,就把稿子从窗户里扔出去,递给等着抄谱的人——如果我写不出稿子来,他们会把我的身体也从窗户里扔出去的!”
《外国名曲逸话》中有些故事很让人感动,例如柴科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交往,一首弦乐四重奏让两位俄罗斯文化名人之间产生了艺术知音才有的情感波澜。众所周知,柴科夫斯基特别擅长写旋律,他的许多作品都有非常吸引人的优美旋律,其中有些旋律是他从民间歌手那里听来的。他于1871年创作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的演奏标示为“如歌的行板”(亦称“歌谣风行板”),优美动听的第一主题的音乐原型来自作曲家两年前在他妹妹的庄园里听到的一首民歌《瓦尼亚坐在沙发上》。当这首淳朴的民歌變为弦乐四重奏的慢乐章主题后,音乐的抒情性更为浓郁,沁人肺腑的音乐美感中渗透着些许悲伤。正是这种带着忧伤、悲酸的抒情音乐让1887年作客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托尔斯泰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已接触到苦难人民的灵魂深处。”柴科夫斯基在日记中记录下了那个让他永远铭记在心的动容场景:“在我以作曲家自许的一生里,至今还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满足和感动。今天列夫·托尔斯泰坐在我身旁,当他听到我的行板时,泪珠挂满了他的两颊。”他还在给托尔斯泰的回信中写道:“知道了我的音乐能够使你感动,使你入迷,我是多么幸福和自豪呀!”
如果说柴科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名曲交知音”的故事让人感到温暖的话,那么歌德对舒伯特“迟到的赞扬”则显露出遗憾中的凉意了。舒伯特根据歌德的叙事诗创作的歌曲《魔王》堪称德奥艺术歌曲领域前无古人的惊世之作,很难想象这首作品竟出自一位十七岁的青年之手,那种独特的音乐布局、自如的“身份”转换和极富戏剧性张力的悲情展现,让人不得不佩服音乐天才的巨大创造力。舒伯特写完《魔王》后曾恭恭敬敬地抄了一份乐谱寄给歌德,但这位大文豪可能看都没看,信也不回。多年后,年迈的歌德在一次音乐会上听到女高音歌唱家德夫里昂夫人演唱《魔王》时大为感动,他不仅热烈鼓掌,还流下了眼泪。遗憾的是舒伯特再也不会知晓这位伟大诗人对自己所作歌曲的赞扬和感动了,因为那时作曲家已经辞世两年。


英国人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既是乐评大咖,也是音乐逸话写作的高手。他在中国爱乐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人称“老莱”,所撰写的多本著作很受乐迷欢迎。二十多年前就有中译本的《谁杀了古典音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让中国的爱乐人了解了西方乐坛的阴暗面;《为什么是马勒?》(三联书店,2018年)所呈现的对马勒其人其乐的另类评说则让读者见識了非学院派传记写作的独特叙事和话语能量。老莱乐于“八卦”、擅于“爆料”的爱乐姿态和乐评风格自然促使他关注、挖掘有关音乐和音乐家的轶事和“野史”。从他已出版的两本相关图书中,可见老莱对音乐逸话收集、整理和写作的浓厚兴趣。
老莱的《永恒的日记》
(A Musical Book of Days : A Perpetual Diary),光看中文书名可能会产生疑惑,但一看英文原著的书名,就可以马上知晓它的内容。作者用“音乐日历”的构架,按一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进程”来叙说与每天相关的曾发生过的音乐“要事”和名人逸事,以满足音乐界和爱乐圈对“音乐日历”的特殊爱好。与其他艺术领域相比,音乐界确实对所谓“周年纪念”特别重视,音乐家、乐团、演出公司都会抓住“周年纪念”的机会来策划、宣传和举办各种纪念音乐会和相关的系列演出。例如,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颇为热闹的“拉赫玛尼诺夫年”(作曲家诞辰一百五十周年,逝世八十周年),2024年最重要的作曲家“周年纪念”当然是献给诞辰两百周年的布鲁克纳的。因此,“音乐日历”的编排、制作就成了不少与音乐艺术打交道的个人和机构乐于从事的工作。
读这本《永恒的日记》,可以看出老莱对“音乐日历”制作的热情和所花的精力。如书中“前言”所说:“这本书收集的事迹跨越西方音乐中整整十四个和声世纪,也偶有不和谐之时,并侧重于重要的演出时刻或是伟大音乐家私生活中的片段。无论这些日常事件是琐碎还是宏大,是高尚庄严还是低级庸俗,它们绘成了一幅音乐发展史的迷你画像。”这里,我挑选书中的两日,看看老莱是如何用他收集的事迹来书写他乐于分享的“音乐日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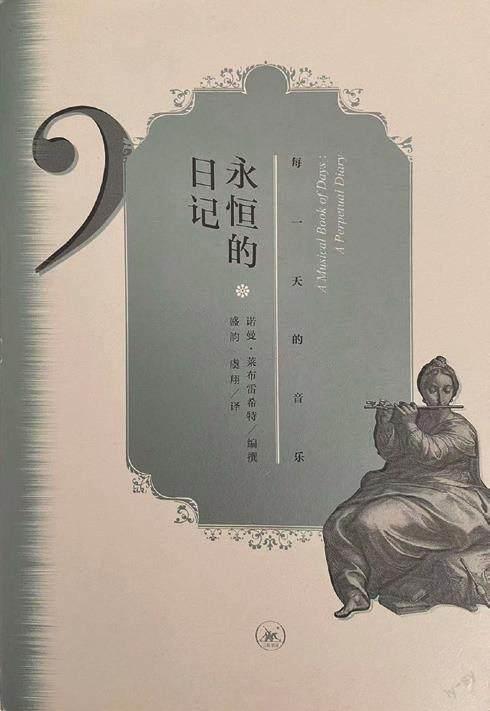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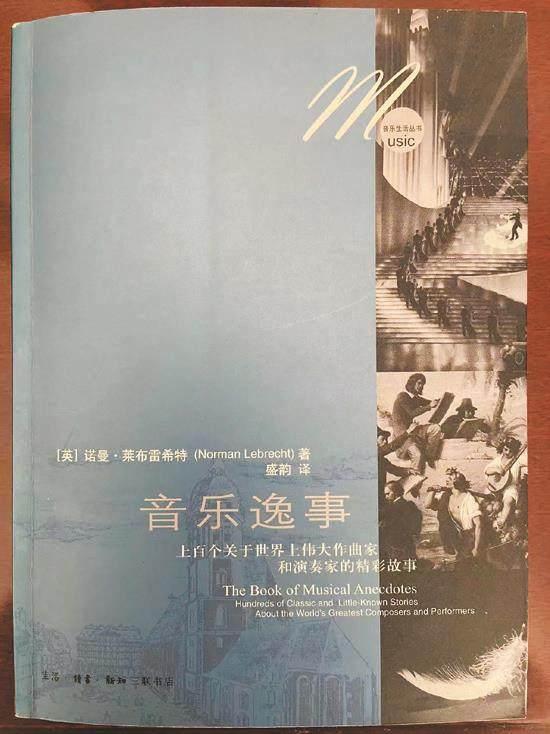
1月1日那天,老莱呈现了十二项内容(按时间顺序),从1782年的J.C.巴赫(人称“伦敦巴赫”)在伦敦帕丁顿区的辞世,到1865年柏辽兹完成其回忆录时所发的感叹:“今时今日,方可死无怨尤”;从1908年马勒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举行他的美国首演——指挥演出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到1945年泽纳基斯(Iannis Xenakis,1922—2001)领导一支游击队在雅典的巷战中盲了一眼,险些送命。
再看5月15日,共有四项内容,每一项都是值得了解的音乐史知识:
1501年,威尼斯商人彼得鲁奇(Ottaviano Petrucci,1466—1539)用活字印刷术印制了第一本音乐书:主调合唱曲集《歌曲一百首》。
1567年,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在克雷莫纳出生,他是一名理发师兼江湖郎中的儿子,日后他将成为伟大的作曲家。
1858年,鲍罗丁凭借论文《砷与磷酸的类比》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作曲只是这位科学家的“第二职业”。
1920年,在巴黎上演的《普尔钦奈拉》(Pulcinella)标志着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创作阶段的开始。
老莱的音乐逸话写作的“重头著作”是一本四十多万字的《音乐逸事》(三联书店,2007年),此书副标题是“上百个关于世界上伟大作曲家和演奏家的精彩故事”。这是我目前读到的最“厚重”的音乐逸话类专著,所说的逸事涉及一百八十七位作曲家和音乐表演艺术家,按人物出生的年份排序,从中世纪的圭多·达雷佐(Guido dArezzo,约997—约1050)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派音乐代表人物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28—2007)。全书共有逸事七百八十六则,堪称“音乐逸事大全”。此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85年,很受乐迷喜爱,所以一直不停地再版,并且已有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译本。在原序中,老莱明确指出:“在许多领域,尤其是社会学、政治科学以及一些艺术方面的研究中,逸事是必不可少的成分。”他对过去半个世纪音乐领域对逸事的种种骂名感到强烈不满,力图为音乐逸事“正名”,讨回它的正当性。作者认为,一则与作曲家相关的音乐逸事所表达的个人洞见,往往能提供一种探索音乐的深层含义和动因。“如果这故事足够离奇或富于灵感,就更为音乐平添了一种风味。”因此,编写此书的目的是:“重现音乐史上久被遗忘的事件,时而揭示不为人知的插曲,通过这种曲径来纠正当下音乐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平衡现象。”这部“音乐逸事大全”的内容丰富多彩,在此我仅挑选四则趣事分享,从中可见音乐大师的幽默和睿智:
经常有人请巴赫演示一些极简单的乐曲,他通常会说,“嗯,看看我能做什么”。这时,他会选择一个简单的主题开始,但是,当他充分发展主题之后,别人总会发现这曲子其实并不简单。如果大家开始抱怨这曲子还是太难的时候,巴赫会笑着说:“只要多练,就能弹好;你不是跟我一样有十个健康的手指吗?”
在听了《后宫诱逃》的排练后,约瑟夫二世要求见莫扎特,并对他说:“我亲爱的莫扎特,这对我的耳朵来说实在过于美妙了,有这么多的音符。”莫扎特回答:“请陛下原谅,这些音符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我(霍洛维茨)问施纳贝尔他弹不弹肖邦和李斯特。“不,我不弹,”他回答,“但等我弹完所有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也许我会弹的。”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说:“我恰好准备反过来。”
一次,他(卡拉扬)向一个德国记者解释为什么他喜欢柏林爱乐甚于维也纳爱乐。“如果我告诉柏林人往前走,他们会照做。如果我告诉维也纳人往前走,他们也会照做,但接着他们还要问为什么。”
除了知晓音乐家们的幽默和睿智以外,我们还能从流传的音乐逸事中看到关联人生意义思考这样的严肃话题。读贝多芬抄写的三句埃及铭文(据辛德勒说,贝多芬把它们镶框后挂在工作台上),让我们再思音乐逸话这一抹爱乐亮色所蕴藏的艺术深意:
我便是存在。
我是现在、过去、将来的一切。没有一个凡人揭开过我的面纱。
他孤身一人,正是这种孤独成就了万物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