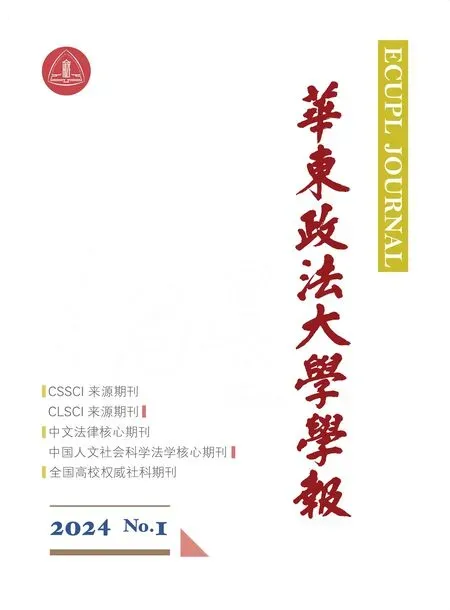“列我藩服”:清朝对中亚地区理藩体制之法规范研究
邱 唐
目 次
一、前言
二、《大清会典》呈现清朝对中亚地区理藩体制的整体架构
三、《理藩院则例》关于边境管理的禁令
四、《大清律例》对于与外藩交往的禁止性规定
五、余论
一、前言
今日论及所谓“国际法律秩序”,系与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理论伴随而生的,其历史即便上溯到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1〕参见何志鹏:《国家本位:现代性国际法的动力特征》,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5 期,第126 页。也不过370 余年;以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为标识,该体系影响中国的时间更短,只有区区182 个春秋。在此之前漫漫数千年的中华政治与法制文明历史中,中外交往互动班班可考,其背后自然也有另一套规范与制度体系。今人通过考察传统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制度与规范体系,可以重见前国际法时代中国固有的“世界秩序”,这对于在当下“一带一路”时代大背景下,探索运用中国智慧与传统资源构建更加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今日中国之疆域,基本是对清朝舆图的赓续与嬗变,因此,研究传统中国的对外法律秩序,清朝是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专论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者,自费正清以降,多习惯于将明清合论,无论是费氏的“朝贡体系”,〔2〕See John King Fairbank and S.Y.Teng(邓嗣禹),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6 (2)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5-246 (1941).还是日人所提出的“互市体制”,〔3〕参见[日]岩井茂樹:《朝貢と互市:非”朝貢体制”論の試み》,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秩序と交流の歴史的研究,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21 世紀COE プログラム,ニューズレターNo.4,2006 年3 月。甚至是黄枝连提出的“天朝秩序”,〔4〕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秩序研究》(上、中、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 年版。都试图用某一种理论范式来归纳与概括明清时代对外交往的制度设计与规范体系;但从明清两代的传世法律文献相关规范条文所反映的规范架构与交往史实来看,上述种种一概而论的做法,对于明、清之间的代际差异以及清朝对外法律秩序体系本身均无法清晰而圆融地反映。约言之,单就对外法律秩序体系而言,由于交往对象、主管机关以及适用规范发生重大变化,清朝对外法律秩序体系相较于明朝,并非简单地复制沿袭,而是经历由单一模式走向多元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简言之,明朝基本形成了以礼部主客清吏司主管的,以朝贡为最重要特征的对外秩序模式,其秩序规范主要见于《明会典》的“主客清吏司”部分。该部分开宗明义,对主客司职守作了说明:
主客清吏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分掌诸番朝贡、接待、给赐之事,简其译伴,明其禁令。〔5〕(明)申时行等:《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卷一〇五,“主客清吏司”,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571 页。
之后则分为“朝贡”“宾客”以及“给赐”三个部分,对朝贡国名单、贡品、回赐物品、典礼礼仪、后勤供给以及翻译事务等朝贡过程中各个环节做出了巨细靡遗的规范。〔6〕参见(明)申时行等:《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卷一〇五至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571-600 页。类似的制度,的确为清朝所承袭。清朝仍然将礼部的主客司作为“朝贡/册封”事务的主管机构,《大清会典》“主客司”部分的规范体例与内容上承《明会典》,但其载进入清朝“封贡体制”的国家仅有朝鲜、琉球等数国,与《明会典》中数十个朝贡国相比落差明显:
凡四夷朝贡之国,东曰朝鲜,东南曰琉球、苏禄,南曰安南、暹罗,西南曰西洋、缅甸、南掌,西北番夷见理藩院,皆遣陪臣为使,奉表纳贡来朝。〔7〕(清)允裪等奉敕撰: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宾礼·朝贡”,《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一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484 页。
另一个明显的差异则是,清朝礼部的主客司不再是唯一的外事主管机构,“西北番夷见理藩院”明确了理藩院分司清朝与西北方向各“外藩”的交往。理藩院由崇德年间的“蒙古衙门”发展而来,原本是专门处理蒙古事务的机构,随着清王朝版图不断地开拓,其逐渐开始管理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事务。〔8〕参见赵云田:《清代理藩院初探》,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1 期,第18-26 页。以今视古,理藩院大致是一个专门处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内政机构;然而,正是因为清王朝加强了对新疆等地区的有效统治,才不可避免地与新疆邻接的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各部产生联系与互动。因此,作为新疆事务主管机关的理藩院,兼理中亚各外藩事务,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清朝这种将原属内政性质、民族宗教事务的理藩制度外推,用于处理各外藩事务的制度设计,其规范架构主要为《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以及《大清律例》三种不同的规范文件。其中,《大清会典》“以职举政”,〔9〕(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凡例》,《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二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1 页。规范了清朝几乎所有中央机关的具体职权,因此,其对于对外理藩制度的记录也比较完备。通过对各部院衙门,尤其是理藩院、军机处、鸿胪寺等机构各自执掌的梳理与汇整,庶几可以拼凑出清朝对外理藩体制的全貌。《理藩院则例》系理藩院行政内规,专注于理藩院本身的职权,主要涉及清朝与各藩部的贸易以及边境管理问题。在笔者看来,《大清律例》是极具内国法与刑事法色彩的法律规范,其在对外理藩制度面向所呈现的规范,主要着眼于解决清朝人民违法贸易与偷渡等违反边境管理法规的相关问题。
二、《大清会典》呈现清朝对中亚地区理藩体制的整体架构
据笔者统计,依《大清会典》所见的规范条文所呈现,清朝的对外理藩制度至少涉及军机处、户部、兵部、理藩院以及鸿胪寺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各有其执掌,各自分工又彼此配合联结,其各自的相关法规范在不同面向上共同架构起清朝完整的涉外理藩制度。当然在上述诸多部门之中,理藩院是处理与藩部关系最重要的部门,兵部主要处理的是跨国贸易和边境贸易的相关问题,而其他部门则大多是就自己的职权范围提供专业性或者物资保障性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以前的规范记录在乾隆朝会典中(理藩院部分扩展到乾隆二十九年,另有其他部院奉旨加入的内容),乾隆二十三年至六十年(1795 年)的规范则见于嘉庆朝会典中。而清朝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平定准噶尔以及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平定大小和卓之后才真正对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各藩部有比较稳定的影响力,因此,从时间上考察,在法规范记录层面,清朝对西北各外藩的理藩制度,在嘉庆朝会典中才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一)《大清会典·理藩院》对中亚地区理藩体制的总括性规定
综观清朝的理藩制度,充分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灵活性与多样性特征,因蒙古、西藏、回部等民族地方文化、习俗与制度的不同,理藩制度本身也被认为至少可以再细分成八旗、扎萨克盟旗、西藏与回疆四种不同的模式。〔10〕参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7-258 页。就宗教文化和社会形态而言,西北各外藩与回部新疆存在较大的相似性,清廷对中亚地区的外藩,在很大程度上采用比较一致的规范,因而清朝对外理藩制度基本可以看作是其对回部理藩政策的一种变形与延续。理藩院作为理藩制度最主要的执行机关,其下设徕远清吏司专门管辖回部新疆事务,兼理中亚地区外藩交往事务。因此,在整部《大清会典》的规范层面,对外理藩体制最重要的规范主要呈现在“理藩院·徕远清吏司”两个部分。
如前文所述,乾隆朝会典编纂之时,西北诸部刚刚归附,因此这种外藩制度尚未臻成熟,乾隆朝会典对这一问题的规范比较简略。西北诸部的管理机构是理藩院徕远清吏司,《大清会典·理藩院·徕远清吏司》只是简单明确了中亚诸部“列我藩服”的范围,具体包括哈萨克、布鲁特等共计14 部:
其哈萨克之左右部、布鲁特之东西部以及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等部列我藩服,并隶所司。〔11〕(清)允裪等奉敕撰: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徕远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一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726 页。
同时也规定其贡期贡物情况: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汗长皆重译来朝,遣使入贡;或三年、或间年,无常期;厥贡罽刀、马匹。〔12〕(清)允裪等奉敕撰: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徕远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一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726 页。
从这条规范记录不难看出,乾隆时期对于此类外藩的具体规范因为彼此建立关系不久,表现出很明显的粗疏、简略的特征。不似在礼部主客司项下,清朝对朝鲜、琉球等属国的贡期、贡道进行了个别、细致且明确的规定。但在对外理藩层面,至少在乾隆时期,可以明显看出清朝对待新归附的这批西北“外藩”与对待属国态度的差异。会典理藩院部分的条文并不像礼部对属国的规定那样,精准限定每个部族进贡的时间与品项,只是笼统地规定,这些部落二年一贡或者三年一贡均可,还特别强调这些部落进贡没有“常期”。同时,对于贡物的品项,也只是简单列举了罽刀、马匹两类,且没有具体数量限制,与对朝鲜等属国动辄罗列十余种,且明定数量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明显地折射出清朝在规范制定层面区别对待“属国”与“外藩”的治理逻辑。
随着新疆回部的完全平定,清朝与中亚各部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比嘉庆朝会典与乾隆朝的相同规范的细致程度看出。与乾隆朝会典相较,嘉庆朝会典“理藩院·徕远清吏司”部分除了罗列“外藩”部族名号,还以小字形式更加详细地列举了各藩部的地理位置和疆域范围,甚至包括其部族、官制等社会、政治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以浩罕等部为例:
附牧于回城卡伦之外,……若霍罕霍罕部在喀什噶尔所属喀浪圭卡伦外,其所统有安集延、那木干、玛尔噶朗三部。安集延在喀什噶尔所属乌帕喇特卡伦外,那木干、玛尔噶朗在其西。若博罗尔博罗尔部在叶尔羌所属和什拉普卡伦外。〔13〕(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三,“理藩院·徕远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三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638-639 页。
这一规范的变迁,正说明在乾嘉时期,清朝通过一系列对新疆的开拓与经营,开始对西北边境之外的各外藩部落有了更加明晰的认知,这是清朝在此地区推行实质有效的理藩制度的基础。另外,这种列明外藩地理位置的规范设计,也反映出清朝在法规范层面已经有了比较朴素的疆域与边界观念,《会典》的这种叙明,可以成为外藩与中国以及外藩之间领土冲突解决的法律依据之一,这也是清朝对外关系规范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
另外,尽管此时清朝与中亚各藩属关系已经比较稳定,但嘉庆朝会典中“徕远清吏司”部分的规范仍然延续乾隆朝的立法精神,并不如“礼部·主客清吏司”当中的“朝贡通例”那样,对外藩的贡期、贡物等作出细致的规范。此时的规定较乾隆朝甚至更为宽松,乾隆朝会典中尚有对贡期以及贡物最粗疏的规范,但到了嘉庆朝,非但移除了这些原有的规范,反而强调其“无定”的特征:
各部来朝无定期。其贡亦无定物。自高宗纯皇帝平定西域陆续通贡后,至今咸输诚效顺。〔14〕(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三,“理藩院·徕远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三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639 页。
上述“理藩院·徕远清吏司”部分的规范,到光绪朝会典当中一字不易。可以看出,终清一世,对于西北、西南外藩的“理藩制度”与传统的对于东方、东南方属国的“封贡体制”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最根本的就是明显淡化了汉人王朝对于三代以来形成的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于“礼”的执着,也即不再如同对“属国”那样追求“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天下秩序,也不再强调糅合“君臣父子”关系的“家国一体”的礼法制度。〔15〕参见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6-11,22-23 页。具体而言,一方面,对于各藩部朝贡的贡物、贡期也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不似礼部对于其主管的各属国的贡物、贡期、贡道甚至使团规模、文书制式都有巨细靡遗的规定;另一方面,对外藩,清廷并不像对于属国那样特别强调对其首领的“册封”权力。尽管乾隆皇帝在平定大小和卓之后,对哈萨克首领阿布赉有过册封的承诺:
尔称号为汗,朕即加封,无以过此。或尔因系自称,欲朕赐以封号,亦待来奏。〔16〕《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丁未,来源: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1819851924^807^^^702110010008054800010002^1@@1442316776,2023 年10 月1 日访问。
但这种册封是一种“奏请—册封”的被动模式,同时不强调如属国一般的世代册封,甚至是通过“册封”行为赋予和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考察会典“理藩院”部分的规范,也没有任何对于外藩册封的礼制或者仪制式的规范。
事实上,从目前的规范文献来看,相较于册封与朝贡这类“礼法”要素,清朝似乎对于与这些外藩的贸易更为着意,《大清会典·理藩院·典属清吏司》的相关规范明确设立清朝与哈萨克牲畜贸易的官市,不仅在贸易场所,甚至对货品定价都作出了保障:
凡哈萨克之牲畜设官市。伊犁塔尔巴哈台与哈萨克互市牲畜。每马十,给回布三十至五十疋;牛十,给回布二十至四十疋;羊百,给回布七十五至八十疋。每回布十疋,合银四两。如哈萨克愿得绸缎者,计值给与皆官为经理。〔17〕(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三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624-625 页。
甚至对于严格限制出口数的丝绸,〔18〕安南使团求购丝绸还需要皇帝破例特许,参见《钦定户部则例》卷五十七,“关税·稽查海船”,故宫博物院编:《钦定户部则例》,海南出版社2000 年版,第85 页。竟在会典层级明确准许交易,可见清朝对这些外藩还是相对比较优待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立法技术上讲,会典理藩院项下对各外藩的条文排列位置是很值得深思的。西北哈萨克、布鲁特等外藩隶属于徕远清吏司的管辖范围,徕远司最主要的执掌则是新疆回部事宜,而哈萨克此等外藩就直接列于新疆各回城这些回部藩属之后。事实上,这些西北外藩也需要受到伊犁将军、喀什参赞大臣等清朝驻疆官员的节制,与传统的“朝贡国—中国”模式相比,中亚各外藩似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外藩—新疆—朝廷”三级间接的关系模式。
这样的立法模式与同列于会典的礼部对于属国的制度设计差异是明显的,礼部单设主客清吏司专管属国封贡事宜,是专门的外事机构,与内政全无关涉;而对于西面的外藩,清朝的理藩制度则显示出一种内政、外政模糊杂糅的状态,依地理位置将外藩与新疆等民族地区并列,且对于外藩政策有明显的内化趋向。另外,新疆地方本属清朝最新进行有效统治的区域,对于因统治疆域扩大而新接触的外藩,可能更多一层考虑,即基于国家安全〔19〕尽管清人未必有“国家安全”的概念或者理论抽象,但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重视安全考量则古今理一。参见沈伟:《国际经济法的安全困境——基于博弈论的视角》,载《当代法学》2023 年第1 期,第28-29 页。的有效管理和谨慎防范的考虑,而少了一些礼制和文化层面的苛求。从这些外藩的角度而言,西北各部已经完全伊斯兰化,从宗教和文化上都远离传统东亚社会的儒家文明,要求这些国家严格遵循以儒家礼法为理想归趋的“封贡体系”可能确实强人所难,因此用这种“因俗而治”且长期在蒙藏疆等民族地方行之有效的“理藩政策”加以管理,或许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确实有其合理性甚至是必然性。
(二)《大清会典·兵部》对于外藩贸易的具体规定
通过对会典当中理藩院相关条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清朝对于与诸外藩的互动,与封贡体系下的属国相比,并不十分强调“封”这类“礼法”的程序,特别是对于中亚地区各藩部,似乎更重视其“贡”与“市”的互动,尤其是马匹的交易。除了在“理藩院”的部分,会典在“兵部·车驾清吏司”条文中则进一步对与外藩进贡和马匹交易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
车驾司的相关规范首先明确规定了对于外藩进贡、贸易者的物质保障与限额,包括车马、行李和仆役的数额:
凡给驿,各以其等。回子及土尔扈特、和硕特、哈萨克部落汗、王、台吉、伯克来京者从役行李,均照定额给车。土尔扈特、和硕特、哈萨克汗行李四千斤,从役七名;亲王行李三千斤,从役六名;郡王行李三千斤,从役五名;贝勒行李二千四百斤,从役五名;贝子行李二千四百斤,从役四名;公行李一千八百斤,从役三名。〔20〕(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九,“兵部·车驾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三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466 页。
值得注意的是,会典“兵部”的条文仍然将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藩部的规范列于新疆“回子”和漠西蒙古藩部之后,说明在清朝的治理逻辑当中,中亚各藩部更接近于新疆各部,而非礼部主管的属国之列。
“兵部·车驾清吏司”的另一条规范则特别针对与外藩的马匹交易行为,规定了有权收马的主体范围,何种情形可以收马,这些马匹如何处理,甚至外藩进贡不足时如何补足马匹等问题:
哈萨克、布鲁特之贡者、市者,哈萨克、布鲁特每岁来通市时贡马无定额。哈萨克由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叅赞大臣,布鲁特由喀什噶尔赞大臣乌什办事大臣各收纳回赏。又每年冬季塔尔巴哈台收移卡伦向内,俾哈萨克借处其地过冬。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赞大臣于巡边时亦收取贡马,皆随时具奏。其每年通市时换获哈萨克、布鲁特之马,各收入本处备用羣牧放。供用亦如之。伊犁等处所收贡马及换获之马,以给各城台站卡伦之用及备伊犁等处营马屯马之缺。以其余者解交甘肃内地备用。其解马,由将军等挑选臕壮,烙用印记,派员缓程解至乌噜木齐,转解至巴里坤,由巴里坤总兵委员解至肃州。其换获不多之岁,将内地所调之马拨给一半,或将巴里坤牧场骟马拨入内地添补。如甘肃拨补有余,卽由近及远,以次充补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营马驿马额缺。〔21〕(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九,“兵部·车驾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三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460-461 页。
从上述规范的细密程度可以看出清朝对来自中亚的马匹进贡与马匹交易的重视程度。在笔者看来,清朝经营与西北各藩部的关系,最重要的现实动因除了边境的安定之外,就是对于马匹的需求。西北外藩进贡、销售之马匹已经成为清朝军备用马的一个固定而重要的来源,清朝在理藩制度之下,以银两、丝绸易西藩之马匹,应当说确实起到了互通有无、资源互补的作用。
(三)军机处、鸿胪寺相关条款彰显了清朝的二元治理逻辑
鸿胪寺是中国古代执掌朝会礼仪的专司机构,考察会典“鸿胪寺”中关于外藩的规范条文,对照会典对于封贡体系下的属国的相关规定,则可以明显看出理藩与封贡两种完全不同的规范体系设计,从而彰显出清朝在对外交往上的二元想象。鸿胪寺相关条文明确将与清朝有交往的国家分为两类,即朝鲜等“外国”和哈萨克等“外藩”,并且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对象分在完全不同的朝觐班列之内:
哈萨克回子等封王公品级者,入蒙古王公班内。封王者在王之次,封公者在公之次。外国贡使在西班百官之末,以朝鲜国领班。新附外藩应入何班朝贺,俱由礼部奏定。〔22〕(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十,“鸿胪寺·鸣赞序班职掌”,《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三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698 页。
这条规范明确指出,哈萨克部王公在朝贺天子时,与回部、蒙古王公站在同一班;而朝鲜等属国使臣则是与文武百官同列,站在西班之末。这种将外藩与属国完全分在两班的做法,显示出清朝在整体设计规范时,赋予了外藩与属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
除此之外,光绪朝的《钦定大清会典图》当中无论是《太和殿朝贺位次图》还是《万树园筵宴位次图》都将哈萨克等外藩列入蒙古王公、新疆伯克序列,而不混入朝鲜等属国序列:
太和殿朝贺位次图外藩蒙古王公、位次在宗室王公之下,各依品级为序。哈萨克、回子等封王公品级者,入蒙古王公班。王在王之次。公在公之次。外国贡使、在西班百官之末。
万树园筵燕……前引内班,位次均如仪。蒙古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暨一二品大臣席于东西。如有哈萨克,则哈萨克台吉,暨正使,席于西班一二品大臣之次。……帐殿南,额驸席于东。三品大臣分席于东西。蒙古台吉又席于东西。如有哈萨克,则哈萨克副使席于西班台吉之上。礼部堂官、内务府总管席于南,均东西向。
由此可见,不论是朝贺还是宴饮等一切礼仪场合,清朝的外藩与属国是绝对不可混同的。在清朝的统治逻辑和话语之内,外藩与属国显然被特别区隔成两种不同质的交往对象,其适用的礼仪规范、法律制度和交往模式显然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清朝统治者可能视朝鲜等属国为“外国”,但对于西面的诸外藩,显然更愿意将其等同于蒙古、新疆,或者将之视为这些地域的延伸与拓展。
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或许是传统的东方属国大多属于农耕文明,对于出身关外、以采集狩猎起步的满洲贵族来说仍然稍有隔膜,延续明朝的“封贡体制”是有效且安全的统治策略;而西面的诸外藩大多属于游牧文明,显然满洲人对于他们有更多的天然的亲密感,因此更容易与之形成某种民族间的理解与联盟。同时,满洲统治者有意将此等外藩事务与汉人完全隔离开来,使此类理藩制度亦成为防范汉人的重要制度屏障。因此,此种模拟新疆、西藏统治策略的对外理藩制度,正如论者所言,不仅是清王朝能够统治当地民族社会的手段,更是清王朝为了构建可以控制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进行的特殊设计。〔23〕参见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台湾政大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4 页。于是在对外关系上发展出封贡与理藩两种截然不同的法秩序模式,前者追求的是礼仪层面的尊严与和谐,后者则隐隐显示出一种内化的趋势。
与这种对外关系上二元化模式相对应的则是内政上的二元分割,质言之,即“满汉”或者说“旗民”的分治。自雍正朝之后,军机处就成了清王朝实际上的中枢所在,会典中“办理军机处”部分关于军机章京分工的相关规范则将清王朝对内满汉分治、对外东西分列的二元治理模式展现无遗:
军机章京,满洲十有六人,汉十有六人。各分为二班,每班满洲章京八人,汉章京八人。其八人内,各以一人领班,曰达拉密,由军机大臣拣派。掌分办清字、汉字之事,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系清字者,皆归满洲章京办理;系汉字者,皆归汉章京办理。在京旗营及各省驻防西北两路补放应进单者,内、外蒙古藩部及喇嘛并哈萨克、霍罕、廓尔喀朝贡应拟赏者,皆隶满洲章京;在京部院及各省文员绿营武员补放应进单者,王公内外大臣应拟赏者及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掌等各外国朝贡应拟赏者,皆隶汉章京。〔24〕(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办理军机处”,《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二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26 页。
依据这个分工规范,中亚地区的外藩又和回疆事务归在一类,专由出身满洲的军机章京负责;而朝鲜等属国事务则属于汉章京的职权范围。同样的情况,从礼部与理藩院员缺的设置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主管各属国封贡事务的礼部主客清吏司有汉缺:
主客清吏司,郎中,满洲一人、蒙古一人、汉一人;员外郎,宗室一人、满洲一人;主事,满洲一人、汉一人。〔25〕(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一,“礼部·主客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二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345 页。
而主管西北哈萨克等藩部的徕远司则不设汉缺:
徕远清吏司,郎中,蒙古一人;员外郎,满洲二人、蒙古三人;主事,蒙古二人。〔26〕(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三,“理藩院·徕远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三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634 页。
这种分理的模式,固然有语言文字的便利性甚至文化亲缘性的实际操作面的考虑,但推究这一制度设计背后的本质动因,或许人数鲜少的满洲统治者面对人数数百倍于自身的汉人,还是难免存有戒慎怵惕之心,对于其新克复的“西域新疆”,甚至更西面的广袤土地,不欲其与汉人发生过多的联系,以免合流危及自身统治也是不难想见的,因此,清朝一方面严禁基层的民人与外藩产生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联结;另一方面,更在制度层面切断外藩上层与汉人官员的来往可能,而将其交往事务完全划归军机处满章京与没有汉员的理藩院,似乎也是可以解释的。
自嘉庆朝迄光绪朝,《大清会典》项下的对中亚地区的理藩规范并未发现有任何的增删与更动,基本可以认为,至少在法规范层面上,清代的对外理藩体制在乾嘉时期已经成熟定型,直至清末沙俄势力完全控制中亚,传统的中国对外法秩序当中的立法体制基本上不再有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通过对于《大清会典》相关规范的整理与分析,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粗疏但完整的清朝对外理藩体制的全貌,其是一个相当复杂而细致的制度设计,需要上至军机处下至六部诸司的联动以确保该制度有效地运转;另外,该体制与封贡体系的并立与区隔也充分印证了清朝统治的满汉二元分治的立法取向与治理原则。
三、《理藩院则例》关于边境管理的禁令
因清代各部院则例同样是依照官署职掌未分类标准分别进行编纂的,正可与“以职举政”的《大清会典》呼应对看,可以说,各部院则例的规范往往是会典对应部院衙门规范的进一步细化与补充。
处理西北诸外藩的交往、贸易事务的主要管理机构是理藩院,因此在部院则例这个层级的对外理藩体制的法律规范主要应当集中在《钦定理藩院则例》;然而,考察目前所见的各版本《理藩院则例》,笔者发现其对于中亚各外藩事务的规范仍然显得简略而粗疏。其中,有关中亚各藩部的规范仅见于卷三十四“边禁”门,共计四条。这四条例文全部于道光年间纂入则例,并且完全专注于边境管理和边境犯罪。具体而言,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的《理藩院则例》为例,该版本“续纂”了三条针对哈萨克部的边境管理规范;又“修改”了一条“哈萨克私入卡伦拒捕拟罪”的例文。以下进行简要的分析,首先是“哈萨克私入卡伦劫窃分别拟罪”条:
哈萨克私入卡伦劫窃分别拟罪:一、哈萨克私入卡伦窃案得财者,首犯即行正法;从犯发烟瘴。劫案得财者,不分首从,即行正法。〔27〕《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三十四,“边禁·哈萨克私入卡伦刦窃分别拟罪”,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第二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4 页。下引《理藩院则例》各条,新式标点均为笔者添加。
这是一条针对哈萨克人越境进入中国犯罪的规范。根据该例文,哈萨克人偷渡入境后若犯窃盗罪既遂,区分首从犯,首犯科以死刑,从犯则要发配烟瘴地方充军;若犯抢劫罪既遂,则不论首从,一律处死。这条例文有以下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这是一条刑事法律规范,而且是直接叙明刑罚后果的例文,这种规范书写的情况,在各部院则例当中是罕见的。各部院则例的例文即便涉及刑罚后果,也往往是以“议处”“照某某例治罪”这种方式呈现,很少有直接规定刑罚的情况。
其次,对比《大清律例》“盗窃”条的规定:
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不论分赃、不分赃)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指上得财、不得财言)减一等。……一两以下,杖六十;一两以上至一十两,杖七十;……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28〕《大清律例·刑四·盗贼中之二·盗窃》,(清)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卷二十八,成文出版社1970 年版,第649-650 页。
对于一般清朝子民而言,初犯盗窃罪“得财”既遂的首犯,其刑罚后果是“计赃论罪”的,犯罪金额要达到一百二十两以上才会获判绞刑,且是监候;而对于哈萨克越境的盗窃罪既遂之首犯,根据《理藩院则例》的这条规定,不论犯罪金额,都是“即行正法”,死刑立决。《理藩院则例》的此处规范对于哈萨克越境犯罪的刑罚显然是重于一般国内主体的犯罪,其背后的立法动因究竟是出于对外藩人的特别防范,还是此类越境犯罪案发频仍故而特别制定重典,尚待进一步探讨。
最后,该条例文明确对于境内犯罪之外藩人的刑事管辖权,并且直接处分了外藩人的生命与自由权,这种规范设计在清朝对外法律规范体系当中是罕见的。如《大清律例》中关于朝鲜使团人员在华犯罪的一条例文:
一,朝鲜使臣来京,其随带货物银两遇有偷窃,将该管地方官及护送官均照饷鞘被失例,严加议处。所失银物着落地方官并统辖专管之各上司,按股赔还,仍缉拏偷窃之人,照行窃饷鞘例计赃,从重科断,追赃入官。如来使人等有籍词妄报,滋生事端情弊,由礼部行知该国王,一体治罪。〔29〕《大清律例·刑四·盗贼中之二·窃盗-08》,(清)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卷二十八,成文出版社1970 年版,第655 页。
从该例文可知,属国人在华犯罪,清朝尽管认为自己有“治罪”的管辖权,但仍须“行知该国王”,先行通报;但根据《理藩院则例》的上述条文,却无须告知外藩首领,可以直接处分。由此可见,在清朝对外法律规范体系当中,属国与外藩的性质及地位是有着微妙的差别的。在笔者看来,尽管封贡体制下清朝与属国的互动可能更加频繁,规范体系和制度设计也更加成熟,但同时内外之别的界限也更加明确,“治其君而不治其民”,〔30〕参见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285 页。因此要处理属国朝鲜人,需要告知朝鲜国王;但对于外藩,尽管彼此的互动或许显得比较简单粗疏,但其内外分际显得更加模糊,在清朝的法律规范和官方文书当中,中亚各部都是列在新疆各回城或厄鲁特蒙古之后,这部分外藩似乎一直处于内外之间的暧昧地带,因此清朝对于这些藩部的法律规范也往往摇摆于内国法与对外法的分际之间。
这部分另外两条例文都类似于今日的边境管理规范,一条是建立哨卡,派兵防守,严禁哈萨克人私自越境:
哈萨克不准私入内地:一、乌梁海西界设立卡伦,四处派兵防守,不准哈萨克潜入。乌梁海游牧地方如私入内地,立即驱逐,仍责成卡伦官员不适严查。〔31〕《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三十四,“边禁·哈萨克不准私入内地”,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海南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7 页。
另一条则是对边境管理官员的奖惩规范,即塔城地区管理各卡伦的台吉,该职务以一年为期,期内无过失,“纪录”一次(“纪录”到一定次数则可以获得拔擢);若疏于稽查,使得哈萨克人偷渡入境,且在其他地方被发现,则该管台吉将受到罚没牲畜的处罚:
塔尔巴哈台守卡台吉失察哈萨克私越卡伦议处:一、塔尔巴哈台管理霍尼迈拉虎等卡伦台吉,一年更换。期满无过,各予纪录一次;倘遇有哈萨克私越卡伦行走,该台吉等疎于防查,致被他处盘获者,将该台吉等各罚二九牲畜。〔32〕《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三十四,“边禁·塔尔巴哈台守卡台吉失察哈萨克私越卡伦议处”,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海南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8 页。
上述两条例文从不准哈萨克人越境和加重边境管理官员的责任两个方面来阻隔哈萨克人随意进入中国内地,足见清朝政府或者至少是道光皇帝对于哈萨克越境的防备戒惧与抵触之心,这一点从“修改”的“哈萨克私入卡伦拒捕拟罪”例可以看得更加透彻:
哈萨克私入卡伦拒捕拟罪:一、伊犁等处如有哈萨克迷路误入卡伦,因被查拏拒捕者,照窃马例拟以绞决。〔33〕《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三十四,“边禁·哈萨克私入卡伦拒捕拟罪”,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理藩院则例》,海南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3 页。
从这条例文来看,仅仅因迷路而过失越境的哈萨克人,若在被中国官兵稽查捕拿的时候有拒捕行为,则一律判处绞立决的死刑,这一刑罚不可谓不严峻,足见清廷充分利用立法手段,严厉禁止哈萨克私入内地。似乎可以合理推断,尤其到了道光年间,哈萨克部偷渡入境且从事犯罪活动的现象应该比较猖獗,因此清廷才特别设禁令,并以相对严峻的刑罚,希图遏止这一犯罪潮流。
哈萨克等中亚外藩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游牧模式,因此人口对于其部族的整体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乾隆朝以前,哈萨克部一直有人投奔清朝,根据《大清会典》“理藩院·典属清吏司”的记载:
凡游牧之内属者……曰哈萨克,塔尔巴哈台以哈萨克投诚之人编为一佐领,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自乾隆四十四年以后定例,凡哈萨克来投者皆不纳。〔34〕(清)托津等奉敕撰: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二,“礼部·典属清吏司”,《大清五朝会典》(第十三册),线装书局2006 年版,第628-629 页。
清朝中前期对于前来投靠的哈萨克人是接纳的,并且将其编成了塔城参赞大臣麾下的一支佐领。但会典的规范很明确,自乾隆四十四年(779 年)以后,清朝或许出于对外藩政权的体谅与善意,就不再接纳哈萨克人的内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藩院则例》上述四条例文正好可以与会典所记录的清廷对于哈萨克等部的移民政策相对照,道光朝四条则例的立法动因似乎正是为了践行会典上“凡哈萨克来投者皆不纳”这一规范,这一点也正反映出会典与各部院则例在整个清朝对外法律规范体系当中的联结性与系统性特征。
前文已经论及,清朝在对外法规范体系的整体设计上是通过区分属国与外藩来实践其满汉二元分治的基本治理逻辑的。《理藩院则例》当中针对哈萨克越境的规范似乎也能够说明,直到清中晚期,满洲统治者仍然非常介意外藩人进入中国内地,显然对于外藩与汉人的接触缺乏信心,仍然希望通过强制性规范的设立来阻隔外藩与中国内地的联结。
四、《大清律例》对于与外藩交往的禁止性规定
《大清律例》在清朝对外法规范体系的整体架构中,表现出很强烈的内国法和刑事法色彩,甚至可以说,在对外法律规范体系当中,《大清律例》并不是最重要的法律渊源。根据笔者的统计,整部《大清律例》当中的涉外规范,包括律文与例文,共21 条。
从立法语言〔35〕参见刘晓林:《唐律中的“人口买卖”:立法的表述、量刑及其逻辑》,载《当代法学》2022 年第3 期,第152 页。的角度来分析,《大清律例》中的涉外条文规范似乎并不如《大清会典》和各部院则例那样,严格地区分“属国”“外藩”或者“互市国”这样的概念,而更多地使用“外国”这一比较模糊而笼统的概念,因此上述各条例可视为清朝对所有对外交往的刑事规范。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亚各外藩,清朝所有的规范文件当中从来不以“国”相称,而始终待之以蒙古、回部的待遇,称之为“部”。因此,从法律的文义解释上论,《大清律例》当中所指的“外国”包含“属国”与“互市国”两种交往对象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否包括西北各藩部,则必须期待更多当时的司法案例的发掘和证明。
因此,整部《大清律例》中非常明确的关于外藩的刑事规范,仅有“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34”一条。该条例文规范的是与西北外藩的贸易,严禁中国商人越境或与越境偷渡至新疆喀什的布鲁特人进行贸易,无论是军械等违禁品,还是茶叶等专榷品,甚至其他普通商品的交易,都会受到不同程度但都相对严酷的刑罚,甚至居间中介都“与本犯同罪”,以期杜绝此等交易行为:
凡商人有携带引茶货物,在喀什噶尔等处,与私越进卡之布鲁特等易换货物,或相买卖者,除违禁军器、硝黄实犯死罪外,余倶发边远充军。如系私茶,即照兴贩私茶与外国交易例发烟瘴充军。知情容留之歇家、说合之牙保,各与本犯同罪,货物入官。如商人携货私越卡外及越卡进内交易之布鲁特,倶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36〕《大清律例·兵三·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34》,(清)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卷二十二,成文出版社1970 年版,第519 页。
值得注意的是,例文显示,对于违例的中国商人和布鲁特人,是“倶发边远充军”“倶发云贵烟瘴地方充军”,即一体治罪;反观前文提到的“盗窃-08”例,对于在中国境内犯罪的朝鲜使臣,则要行文知会其国王,之后再治罪。这其实也反映出,尽管在用语上比较笼统,但《大清律例》对于“属国”和“外藩”民众的效力,还是有差异的。同时说明清朝统治逻辑中对这两类外邦确实是有所区隔的,这与清朝刻意不将自己的律法强加到东南各属国身上的做法是大异其趣的。这也体现出对于西北外藩,清朝确有一种将其内藩化的倾向,或者说是其新疆政策有隐隐的扩张性趋势。
另外,该条例正可与《理藩院则例》当中关于防范哈萨克部越境的例文相对看,形成了在对外理藩体制的法规范架构内,不同规范形式之间的逻辑呼应。探求其立法动机,一方面,固然是对于严峻的外藩越境犯罪形势做出的回应;另一方面,旗人不事生产,清朝从事边贸的商人多为汉地民人,这一系列严厉的规范恐怕多少也有隔绝汉人与外藩的意味。非常有意思的是,从时序上考察,这一条例系道光十年(1830 年)刑部议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等奏准定例,〔37〕参见(清)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卷二十二,成文出版社1970 年版,第519 页。而《理藩院则例》关于西北外藩的禁止性规定也是道光年间增修的,似乎道光朝特别加强了对于西北外藩边境和贸易问题的管防,且手段相当激烈,个中玄机,值得进一步探求。
而再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项下的整个律例体系,该条律正文之外有44 个例文,仅有1 条涉及与西北布鲁特等外藩贸易问题,而处理与东南属国尤其是朝鲜、安南相关问题的条例则有6 条。由于《大清律例》各例文多是由具体个案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这种规范数量的比例也可说明确实清朝与属国的互动,相较于外藩更加频繁和热络。用历史的后见之明来反推,清朝统治者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治理理念,似乎“海防”一直是重于“塞防”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至清末,清廷对于用坚船利炮打来的西洋、东洋各国尚怀戒惧之心;而对于俄国自中亚而新疆的入侵则显得相对麻木与懵懂。
五、余论
通过对《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以及《大清律例》等法规范的梳理,大致可以还原出清朝处理与中亚地区各国关系的对外理藩制度的某些制度特征与规范体系。从规范体系而言,清朝对外理藩制度的规范架构主要是《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和《大清律例》三大渊源。《大清会典》的规范比较全面和成体系,涉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官署;《理藩院则例》和《大清律例》的规范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边境管理和贸易的禁令,刑事规范的性质比较突出。
单从规范的数量来看,相较于封贡体制相关规范庞杂而浩繁的规模和体系,关于对外理藩体制的规范显得尤其零散而粗略,何以致之?笔者以为,大致有三个原因。
其一,从历史角度考察,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各属国基本从汉唐时期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长期以来受到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浸淫;而尽管中亚各藩所处的地域属于汉代广义的西域,但该地区到清朝时,在文化、宗教、政治甚至种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对于中国或者说清朝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就无法与属国相提并论,再加上清朝与中亚各藩部的关系是伴随着乾隆朝的军事活动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本身就显得比较淡薄,嘉庆以后又随着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侵入而更加式微。与远绍汉唐、近承朱明的封贡体制相比,清朝乾嘉时期才逐渐成型的对外理藩体制并不曾有历史的机遇进一步发展成熟,因此在当时的规范设计层面,客观上不需要也不可能发展出如封贡体制那般繁复的规范体系。
其二,对比清朝和历代中国王朝在对外关系领域的作为,不难发现清朝表现得非常矛盾。一方面,清朝开拓了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最大的疆域,对蒙古、新疆、西藏和台湾等地方进行了有效且长期的经营与管理,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抟成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清朝对于自身的疆域问题,又表现出明显的收缩性、保守性特征,对于域外世界,清朝显然缺乏前代王朝的开拓与经营之心。在对外关系领域,清朝似乎不再完全信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8〕《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322 页。的天下观,而是注意到自己的统治是有边界的,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乾隆皇帝对哈萨克的态度上,首先是乾隆皇帝明白宣示其对中亚各部的归属表现出相当的豁达:
尔若仰企仁风,愿沾恺泽,朕当令尔不离故土,仍尔故俗,子孙乐业,尚有殊恩;尔若谓哈萨克原属化外,不便内附,亦听尔自便,朕不相强也。〔39〕《清高宗实录》卷五〇六,乾隆二十一年壬子,来源: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1819851924^807^^^702110010008051100010014^1@@1267106753,2023 年10 月1 日访问。
此外,对于哈萨克部向俄国同时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在中俄之间搞“两属”投机,乾隆也表现出相当的淡漠,俨然一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40〕《孟子·尽心下》,(汉)赵歧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下册),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版,第469 页。的淡定:
前大兵进剿厄鲁特,抵哈萨克边界,伊等慕化投诚,我大国之体,自当抚纳。非若汝外邦,动以威力相加,与之誓约,责其贡赋。亦未尝禁其服属他国也。嗣后尔等即与俄罗斯往来,亦所不较。〔41〕《清高宗实录》卷五八〇,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壬戌,来源: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1819851924^807^^^702110010008058500010011^1@@1252313571,2023 年10 月1 日访问。
甚至在查获了哈萨克首领阿布勒比斯之子阴谋投奔俄国的信件后,乾隆皇帝还抱持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态度:
今观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欲将伊子遣往俄罗斯托奔城,请示于俄罗斯,则伊又欲归附于彼,其意显然。此事虽不甚关紧要,仅可作为不知,置之不议。〔42〕《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九四,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辛巳朔,来源: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1819851924^807^^^702110010008058500010011^1@@1252313571,2023 年10 月1 日访问。
由此可见,对外关系,尤其是其中的对外理藩制度,在清朝整体的施政擘画中并不处于优先和重心地位,清廷主观上缺乏对于中亚地区经营的热情与动力,因此在规范建构上自然也不会忒以详备。
其三,从外部因素即清朝时期中亚的整体地缘政治局势来看,早在乾嘉时期,沙俄已经开始着意经营中亚地区,即便是通常列于外藩之首的哈萨克,在事实上已经与中、俄两国都保持某种依附关系,受到俄罗斯很大的影响。譬如哈萨克部首领阿布勒比斯臣服于乾隆皇帝的同时,和俄罗斯亦保持密切的联系。1762 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时,哈萨克部中玉兹阿布赉汗与小玉兹努拉里汗等首领,向俄皇做了效忠宣誓,事实上具有了同时臣服清朝和沙俄的双重臣服身份。〔43〕参见厉声、石岚:《哈萨克斯坦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第155 页。又如前文所分析的,清朝方面虽然对中亚各部这种普遍的“两属”事实有所掌握,但默认此种现象发生,未加干预。中俄双方在中亚地区的进退攻守之势不难想见。这种在中亚大草原的敌进我退的大变局,使清朝对外理藩体制尚未完全发展成熟就匆匆退场,历史似乎并没有给予清朝发展和完善对外立法规范体系的机会与可能。
论及清朝对外理藩体制的特征,即其与传统封贡体制的不同,就在于清朝将中亚地区的诸外藩与传统的东亚、东南亚各属国在法规范层面截然分开,鲜少混同。尽管如前文所述,清朝的封贡体制规范更加成熟与完备,清朝与属国的互动似乎也更加频繁与持久,但正因为封贡体制本身的成熟,清朝与属国之间的“内”与“外”的分际也显得尤为分明。但对外理藩体制不一样,在清朝的法规范文件中,中亚地区的外藩始终列于新疆回部之后,而绝不列在“属国”或者“外国”范畴之列,这其实就将这部分外藩置于一个内外之间的灰色暧昧空间。我们可以说,清朝对于中亚各“外藩”的处理方式,基本是新疆“藩部”政策的延伸与变形。因此,尽管从法规范层面来看,清朝与各外藩互动似乎比较少,但在内外分际上,外藩相较于属国,应该更接近清朝统治的核心内圈层。这看似是一个悖论,但背后却有其合理性,以清朝的新疆地区为例,也经历了作为外藩的准噶尔汗国到隶属版图的藩部即回部新疆再到内化建省的过程,同属理藩院管辖的西北各外藩,如果有更长的时间发展对外理藩体制,是否有进一步内化的可能呢?历史不能假设,但前人留下的足迹足以供后人思索。
遍览清朝各种对外法律规范,对于朝鲜、琉球这些礼部所司的属国,其国家皆称“国”,其首领皆称“国王”,尽管传统中国语境下的“国”与今日所谓“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却多少表现出清朝统治者对这些属国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自主与统治界限的承认;反观对于西北诸外藩,无论是《大清会典》还是《理藩院则例》,对其部族或政权绝不称“国”,而仅称“部”,对其首领往往以其民族语言之音译称之,如哈萨克之“汗”、霍罕之“伯克”等,这种处理方式与内国藩部地方如出一辙,如蒙古有“汗”、新疆回部有“伯克”等等。从这种做法很明显地表现出至少在礼宾层面,这些外藩是与各藩部等列,而不是与属国齐论的。这种规范条文的排列方式以及规范语言的选用似乎也可以看出,清朝对于西北各外藩地区,隐隐有一种试图以统一的理藩制度而将其进一步内化,最终实现外藩“内藩化”的尝试。这种“内藩化”并不是一种对于领土的积极索求,而是基于边界稳定和民族隔离的“臣服”需求,因此注定是相对消极的。
尽管从法规范层面来看,清朝对于中亚各部的理藩制度发展是不成熟的;从历史的结果论,在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狂潮中,这一制度也未能长期有效地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双方的关系。然而,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值得后人总结与扬弃,清政府发展出的针对中亚各部的不同于传统封贡体制的对外理藩体制,对当地民众文化、宗教以及政治传统上的尊重与保护始终是值得后人借鉴的。这种正视与关注对方独特个性的政策制定导向,对于当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44〕《习近平在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来源: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5/content_6874886.htm,2023 年10 月1 日访问。愿景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史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