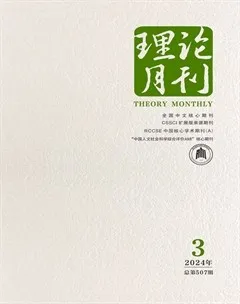数字平台“产消合一”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辨析
[摘 要] 数字平台用户的“产消合一”现象备受学界关注,但福克斯等人的“产消合一”界定过于笼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将“产消合一”分成平台用户纯粹的使用行为、创造性的内容发布行为、通过发布内容获取收益的行为,以及受雇于平台或第三方而进行内容创作的行为。其中,前两种类型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行为,后两种属于生产行为,也是创造价值的行为。前两类用户创造的数据实际上来自平台公司雇佣者的劳动,用户并未在平台使用过程中创造价值。平台与用户之间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那么用户就没有直接受到平台剥削。但用户行为数据确实为平台带来了大量收益,这是由于平台既通过垄断数据获得了生产要素价值分配的租金,又凭借金融资本的投入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透过“产消合一”现象探查其背后的机制,才能解决当前用户和平台的矛盾,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 数字平台;产消合一;政治经济学;价值分配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3.008
[中图分类号] F014;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3-0071-07
作者简介:李育松(1994—),女,法学博士,浙大城市学院讲师。
数字时代带动了全新形式的平台经济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用户“产消合一”现象的广泛讨论。许多学者认为平台用户逐渐转变为互联网“产消者”,并对这一现象作了全新的阐释和分析。本文将基于多方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辨析“产消合一”现象,以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辩证分析厘清“产消合一”概念的本质,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壮大数字消费提供学理支撑。
一、何为“产消合一”:基于行为类型的再定义
学界对于“产消合一”现象、“产消者”的讨论主要基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数字劳动批判理论中的相关定义。福克斯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与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的“受众商品”理论相结合,主张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所进行的如联系、写作、阅读和观看等活动都属于“产消合一”劳动,都属于在消费过程中进行生产[1](p136)。在认同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相关理论分析主要集中于对数字平台用户的行为辨析,以及平台基于用户行为获取收益等现象。有的学者认为平台资本通过对用户即“产消者”进行“玩工”剥削而实现资本积累,有的学者认为“产消合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平台时代的局部形态,有的学者认为“产消者”在数字世界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笔者认为,福克斯对“产消合一”的定义过于宽泛、不够明确,对“产消合一”现象的总结也混淆了多种行为。基于福克斯对“产消合一”的概念描绘,本文主张将现阶段广泛讨论的“产消合一”现象重新分类为以下四个类型,以遵循马克思对相关概念的界定,深入辨析“产消合一”现象的本质内涵,确定“产消合一”的真正范围。
第一种类型的“产消合一”行为是平台用户较为纯粹的使用行为。它涵盖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的日常浏览、点赞等行为,以及通过平台中介消费实体产品的行为,例如线上团购线下用餐、线上购买线下取货等。这些行为的共性在于,用户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进行创造性的活动。第二种类型是用户在平台上进行的带有内容创作性质的使用行为。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在视频平台上传个人作品等用户自发参与线上内容创作的行为,以及在养成类游戏中模拟真实世界进行创造的行为,在对抗类游戏中“氪金”以提升装备、技能继而实现游戏角色的性质改变等行为。
以上两种类型的“产消合一”行为是学术界所讨论的“产消合一”行为的主要类型,国内外关于“产消合一”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此。一些学者认为,用户开始轻点鼠标、网上冲浪、直播带货、点赞评论、存储资料、交易股票等活动时,数字劳动就开始了[2](p39)。而平台用户通过Youtube或博客等媒介创造的劳动产品表现为非物质产品,如文化内容、知识、情感和服务[3](p44)。进而得出结论:数字时代的用户呈现“产消者”态势,产生了数字劳动分工,前端的消费者在数字平台选购商品时也成为用户型数字劳动者的一员[4](p22-23),而平台就是利用非雇佣性的用戶来实现数字生产和劳动[5](p81)。有学者对这一“产消合一”范围界定表示异议,认为上述“产消合一”行为本质上来说是运用数字化的生产资料进行活动,而数字化生产不只是使用数字化的生产资料来生产数字化的产品,那么所谓的平台用户“产消一体化”特征自然化为乌有[6](p78-80)。部分学者表示,用户对平台的使用只是一种消费活动,并不算是一般生产劳动,甚至算不上是劳动,用户只为平台提供了原始浏览和点击痕迹[7](p55)。另有学者认为数字劳动并不是互联网用户的网页浏览、网络社交、网络消费等所谓的“玩劳动”,“玩劳动”制造的数据只是具有潜在使用价值的数据资源[8](p12)。
第三种类型的“产消合一”行为是用户使用平台进行内容创作,并通过平台的相应机制获得创作内容分成,即能够换取个人收入。例如在自媒体平台上进行直播活动并收到金钱打赏,在bilibili等视频网站上因为视频内容达到一定浏览量而获得“创作激励”等。这类用户同第二种类型用户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活动性质更像兼职工作。同样是使用平台进行创作,他们获得了第二类用户没有获得的收入。第四种类型的“产消合一”行为是用户受雇于平台方或第三方机构在平台上进行内容创作。相关用户主要是同视频平台、文学创作平台、MCN机构或平台相关公司签订雇佣合同的用户,这类用户可以算是专职内容生产者,他们普遍能够获得更多的浏览量及点击量,相对前一种用户而言,第四种类型的用户收入一般都相当可观。
相比于第一、二类用户,第三、四类用户的行为性质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前两类用户行为并不直接就是生产,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用户行为所产生的数据给平台带来了不容小觑的收益。福克斯就是在此意义上将这些用户行为理解为新型的生产。笔者认为,要确认以上各类行为的性质,特别是要判定前两类行为是否属于生产,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在平台创造数据、分配收入的整个过程中,究竟谁在生产?又是哪些行为创造了价值?
二、“产消者”中哪些在从事生产?
要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生产的概念和性质,就要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回到经典文本中考察马克思对生产的定义。
马克思始终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看待问题,在生产方式的宏观视角下理解社会现实。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时就强调:当有生命的个人根据生活需要开始进行生产的时候,人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首要依据,就是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9](p24)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会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人类漫长历史的基础就是人类首先能够依托现存的生产条件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进而产生社会关系,即产生人和人之间的联系。随着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人类社会的分工得以出现。“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9](p36)。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现实,才出现了不同生产阶段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同矛盾。“如果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矛盾。”[9](p612)
因此,当视线落回现代社会,就必须以现代生产方式来分析社会现实。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物质生产”为出发点,对市场经济下的个人生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过去简单商品交换的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在交换中要得到商品,是由于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由于需要(商品是需要的对象)”[10](p97)。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产生并逐渐细化,人和人的社会联系在市场经济诞生以后就完全表现在了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0](p106)也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活的人们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来换取货币,继而再通过货币购买相应的商品,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10](p108)个人必须通过生产满足他人需要的使用价值,以期换得相应的价值,再交换成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总而言之,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生产,不是单纯的创造性活动本身,而须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来判断这一创造性活动是否能够满足他人需要,是否能够通过市场交换得到价值支付以间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马克思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视野下讨论了生产的特性,并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11](p58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是被资本所支配的生产,也是服务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此语境下,他区分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12](p136)。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并且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就是资本存在的基础。因此,也可以得出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12](p141),即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中的劳动。
综上可以看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生活需要来界定生产的范围是非常模糊的。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想要判断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属不属于生产,应该主要看这一行为能否通过满足他人的需要而换得货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前文划分的四种类型“产消合一”行为中,第一类和第二类不是直接满足他人需要的行为,不具备生产的相关特性,不能称为生产活动;第三类和第四类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认同的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上,同雇佣方签订劳动合同的第四类用户行为还属于受資本支配的生产性劳动。
三、“产消合一”的消费是否创造了价值?
在考察平台“产消合一”行为中的生产范畴之后,还要继续辨析这一概念中的消费行为。福克斯对“产消合一”行为创造价值的判定逻辑是:用户的消费行为创造了数据,而数据是有价值的,也即用户在消费的同时创造了价值。下文将从两个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理解消费行为和价值创造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消费对生产具有直接的、内在的作用。从具体的个人活动的角度,生产和消费单纯作为人的两种活动,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但不是直接合一的。人们可以只进行生产而不进行消费,也可以只进行消费但不从事生产。如果将视野放大至市场经济系统,生产和消费作为两个相互作用的经济环节,尽管表面看上去毫不相干,但实际上二者之间不可割裂。马克思在考察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时批判了传统意义上对生产—消费关系分析的肤浅:“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10](p30)古典政治经济学这种简单将生产作为起点、消费作为终点的理解显然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解释其现实的关系。对此马克思直接反驳:“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10](p31)与此同时,“消费直接也是生产……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10](p31-32)。他就此提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10](p32)。
在马克思看来,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是同一的,并且消费对生产的内在作用是完全不能忽视的。“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10](p33)如果没有消费,就没有需要,生产就失去目的,不再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也就是说,作为主体完成对象化活动的证明,如果没有消费环节,生产者的价值实现过程将不复存在,社会再生产也就失去了继续进行的动力。
就现实而言,平台用户“产消合一”所贡献的点击、浏览、购物等消费行为能够直接影响平台经营的活跃程度,平台方也会将用户累计数量、用户点击率、用户消费金额作為衡量经营状况的标准。这类现象更加直接地体现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影响和作用,并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愈发高速的循环中,生产和消费的联系也愈加紧密,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消费对生产者的价值实现过程的重要意义。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一直存在,只不过在马克思的时代尚没有出现如此直接的经济现象。
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因此认为消费能够直接创造价值。要想判断消费是否创造价值,还要回归价值本身的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时明确提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在厘清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还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1](p51)。而判断价值是否存在的前提是商品是否存在,“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11](p54)。也就是说,价值的本质其实是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商品中,“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11](p54)。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活动,如果一个行为创造的使用价值换得了价值,那这个行为就是劳动。而劳动又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以单纯的消费行为不能创造价值。如果要对“产消合一”行为是否创造价值进行界定,还要判断其相关使用行为是不是劳动。
具体到前文分类的四种“产消合一”行为,第三类和第四类用户创造了对其他用户有用的使用价值,因此其行为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行为。前两类行为表面上带来了对平台有用的数据和流量,但问题在于,这些数据究竟是不是由用户的使用行为创造的。一些学者认为“产消合一”活动为平台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因此其价值创造性是毫无疑问的。福克斯就明确提出,平台用户在消费中进行生产的“产消合一”劳动为平台提供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等信息数据,为平台创造了大量价值[1](p137)。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用户消费是满足生活需要的过程,产生的数据废料也只是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材料,这种所谓的“产消劳动”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13](p52)。还有学者认为用户无法独立创造价值,必须通过在线活动产生各种数据信息,再通过平台程序驱动来产生价值[14](p109)。这也是学术界一直以来争议的焦点问题。
笔者认为,判断平台用户“产消合一”中的消费行为是否创造价值,核心就是判断用户创造的数据是否具有价值。实际上,用户在平台上的行为不是目的性明确的数据生产活动,用户自身也无法将其行为转化为数据。数字平台公司雇佣大量程序员进行劳动,以算法和程序作为其劳动产品,最终实现对用户行为数据的采集[15](p100)。那么用户在平台上进行的浏览、点赞、购物等纯粹使用行为能够转化成为平台所用的数据,显然不是用户本人生产或劳动的结果。前文提到的平台用户在虚拟世界、游戏世界进行建构的行为,例如热度很高的《我的世界》《模拟人生》等游戏,还有各种各样的“乙女向”游戏,都需要玩家用户在线上平台完成设计创造,有时还需要不同额度的消费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或实现目的。这些游戏看似是让用户在消费过程中进行“自主生产”,但其呈现出的最终画面都是通过算法设计出的不同且固定的内容,本质上都是数据和程序的堆砌。又如“粉丝”这一被数据严重捆绑的典型群体,他们可以通过在平台上“打投”、购买虚拟产品等行为来表达其对偶像的支持和关注,通过消费行为来获得为偶像奉献、创造数据流量的优越感,进而获得精神满足。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社交平台分享原创内容的用户、游戏中的用户,还是疯狂“做数据”的“粉丝”群体,其消费行为背后所谓的创作或生产,实质上都是由程序员的算法支撑,最终生成的数据也都是经过算法抓取以及大量程序运行之后的产物。一言以蔽之,前两类平台用户的行为并没有真正创造出有价值的数据,因此其“产消合一”行为不创造价值,所以也不参与价值分配。
但从平台运行实际来看,用户的广泛参与度以及活跃度的确为平台带来了流量,平台靠流量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继而获得大量收入。而平台收入并没有反馈给用户方,即用户的贡献并没有体现在其收入中,那么这是否为平台对用户的一种剥削?剥削又是如何存在的?
四、“产消合一”是平台对用户的剥削吗?
第一,从生产关系上看,前三类用户行为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没有被平台剥削。在福克斯的理论体系中,平台通过剥削用户在消费过程中进行数字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盈利,平台也就此完成向资本的身份转换。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1](p269)。资本作为支配活劳动的死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11](p582)。劳动者与资本家签订雇佣劳动合同,进行生产性劳动并创造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就是劳动者受到剥削的过程。并且,劳动者受到剥削与劳动者创造出有价值的、可以进行交换的商品是两个维度的事情,不能同一而论。上述几类“产消者”,只有第四类用户的行为属于生产性劳动,受到其雇佣方(有可能是平台)的剥削。自平台作为雇佣方同用户签订雇佣合同开始,剥削关系就建立了,这些内容创作者同平台公司雇佣的后台程序员没有本质区别,平台的部分收益就是这些被雇佣者的剩余劳动带来的剩余价值。第三类用户的行为属于创造满足他人的使用价值而间接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行为,他们创造了有用物并获得了价值,尽管如此,这类用户和平台没有契约关系,也就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没有受到资本的剥削。对于前两类用户,他们在没有直接进入生产的前提下,其活动之外产生的所谓数据本质上也只是无价值的“消费废料”而已,显然也不存在平台剥削。
平台公司通过其雇佣的程序员的生产劳动创造出能够抓取数据的劳动产品,继而通过数据获得收入,就像消费者在线下实体餐饮店消费后,商家根据消费者的餐品剩余情况进行菜品的更新迭代并因此而获得更高收益。这一过程并不是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为商家付出劳动或进行生产创造的过程,而是商家付出劳动捕捉到有效的相关信息以实现增收。诚然,用户的涌入为平台提供了流量,也因为其提供的流量而给平台带来了更多的流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提供流量这件事本身是平台用户被剥削的过程。例如消费者在餐厅靠窗的位置用餐,他在消费的同时也成为餐厅的实时宣传样板,但对消费者来说他的消费行为并不意味着他正在被剥削。
第二,從收入分配上看,平台依靠数据获得的收益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凭借其对数据的所有权而获得的租金,二是凭借金融资本的投资而获得的资本增殖。马克思指出:“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三者的所有权,就是商品的这些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转化为他们的收入的原因。”[16](p982)也就是说,资本家和地主都是凭借其对资本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才获取收入的,同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无关,但“价值并不是因它转化为收入而产生的”[16](p982)。平台资本得以通过数据获得收益,是因为其拥有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的所有权,与数据的价值无关。现如今各大平台上第三类用户数量激增,自发上传创作内容的博主仿佛也获得了数据或流量变现带来的收入,这也是目前许多错误观点的主要现实依据,其错误之处就在于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的收入同数据的价值混淆。这类博主能够通过内容创作获得以使用价值换取价值的部分收入,但因为其不掌握数据所有权,无法获得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创作者与平台看似平等的关系背后也存在着生产要素分配的不平等。
除了剥削数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及获得垄断数据的租金,数字平台企业收益中更大的部分来自金融资本的投资。数字资本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金融资本在所有经济活动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是融合发展的[17](p10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指出,生息资本的借入者接受作为商品的资本,然后将货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当资本实现增殖之后,再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利息)来偿还。即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资本,其增殖的本质都是无偿榨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平台通过收集、处理和占有大量用户数据,通过在资本市场获得相应的投资,然后将原始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起来,进一步扩大生产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最终实现资本增殖。以具体平台为例,淘宝采用开放平台的模式,其主要机制就是以数据垄断为核心,通过与商家合作扩大数据库,同时向商家收取相应租金,并通过程序员创造的剩余价值整合数据资源,吸引金融资本。京东则采用价值链整合的模式,既通过垄断数据和用户信息获得收益,又通过由下至上生产链上的劳动者们创造的剩余劳动获得收益。还有现阶段用户捆绑最严重的视频平台,无论是主打长视频的bilibili还是主打短视频的抖音,其收益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金融资本的融资。归根结底,金融资本实现增殖的过程也是劳动者受到剥削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但并不能就此得出用户正在受到平台直接剥削的结论。
总而言之,“产消合一”在数字时代能够获得新的学术热度,是因为它揭示了数字平台和用户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这一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外在地套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认定“产消合一”行为本身就是生产行为,用户的消费过程也是价值创造过程,用户直接受平台剥削。在“产消合一”现象背后,数字平台的盈利模式较为复杂,需要深入辨析,尤其要避免用表面的不平衡现象掩盖真正的剥削。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厘清数字平台与各方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助于解决当前面对的现实问题,助力数字经济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1][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2]王卫华,宁殿霞.数字劳动和数据资本权力:平台资本主义研究的两个重要向度[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2(8).
[3][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4]温旭.从分工到异化:数字劳动分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视[J].学习与实践,2023(4).
[5]蓝江.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9).
[6]余斌.“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5).
[7]魏旭.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生产、度量与分配——对“价值规律失效论”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2).
[8]邓伯军.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劳动——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王珊,刘召峰.“数字劳动”的生产性:基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辨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3(8).
[14]赫曦滢.数字现代性的迷思与真相——论福克斯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条进路[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3(2).
[15]张义修.数字时代的劳动辩证法——基于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当代阐释[J].浙江社会科学,2023(9).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7]李策划.数字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研究[J].企业经济,2023(6).
责任编辑(见习) 倪子雯
——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