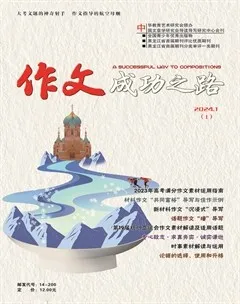不动声息地绽放
谢铭
朱良志《真水无香》曾记载了半首咏梅诗:“以月照之自偏瘦,无人知处忽然香。”孤独而清雅,如同书中所言,“中国艺术的梅花,在清冷的世界中,不动声息地绽放。”
从梅花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文化所追求的美,是一种顺其自然却又不敛个性的态度。如同梅花一样,不被人工雕琢,又不被自然所形役;虽不动声息,但依旧能一展芳华。“不动声息地绽放”,不失为中国美学的最高范本。
然而,时至今天,仍然有一些學者认为中国美学所追求的顺天之道、规避雕琢之野趣是一种求怪、求异的病态美学。如同19世纪下半叶法国商贸团的一位叫莱纳德的学者在广州看到的中国盆景那样,“是一种病态的、不健康的形式”,认为只有服从人工秩序、极展人间奢华的法国美学才能称之为美。
诚然,经典的洛可可式法国美学高贵、骄奢,给予人以绚丽色彩、甜糯香气的直观享受,但这样一种直观享受并不是中国美学所能够接受的美,反而是一种“快感”。如同朱光潜在《希腊女神的雕像与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中所说“最易引起快感的东西也不一定就美”,所谓快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真正意义上的美,应当是一种停留在时间之外,使人意识到取法自然、真水无香的一种永恒的心灵震颤,而不是弗洛伊德“快感原则”所强调的那样在短时间内刺激敏感神经、激起物欲的享乐主义。
因而,中国式顺遂自然又不乏张扬个性的审美原则,才应当是衡量美的标准。为何?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对于一件依照中国美学的原则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我们在第一次欣赏时大概率会认为是一件普通的家常物什,并不会有感官上的刺激与情感上的兴奋;而时隔几天再次赏玩时,就会发现这件艺术品不同于普通物件的精巧之处:可能是翻着白眼桀骜不驯的鸬鹚,也可能是绽放与凋零共存的杏花……在描摹自然时,艺术家通过对小部分现实的改造,传递出内心的声音,形成了一种挑逗心灵的力量,使人在那一次欣赏之后的很多年里,会偶尔记起那件艺术品的模样,想起它背后的人和事。不同于法国美学那般直击人心的高调与张扬,平和低调、抚慰人心的中国美学才能够彰显美的本质,而这也是“不动声息地绽放”能够成为一代代中国人欣赏美、创造美之准则的原因吧。
顺遂自然而不乏个性的中国美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原则与处事态度。从中国的书画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朴素低调、温良坚毅的民族性格。细看赵国经、任美芳所绘的《李清照小像》,画中云髫垂缕、素钗珠环的千古第一才女缄默无声,独坐于莲中小舟,但眼神中所透露出不信天、不认天的傲气早已胜过千语万言。画家通过对李清照的勾勒,再现了中国文人追求个性解放但依旧敬重自然的风骨。反观收藏于卢浮宫的《大宫女》,画家安格尔借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宫女的露骨的描绘,满足了法国人对战败于土耳其而祈求精神发泄的欲望;一个无法正视战败,直面耻辱民族,再怎么创造出所谓“最伟大的作品”,似乎也都缺少了一点大气与风度。
“以月照之自偏瘦,无人知处忽然香”,顺其自然却又不敛个性的中国美学教会了一代代中国人要学会“不动声息地绽放”;那个无香胜有香的中国式美学世界,或许才是决定生命意义的根本,才是安顿人心的灵囿。
(指导教师 徐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