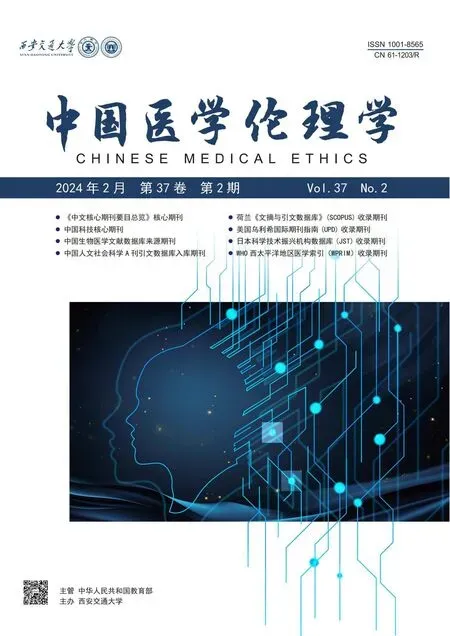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研究现状及启示*
朱向伟,卢根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 201203)
ICU 患者由于疾病和治疗的影响,常处于昏迷或镇静状态,没有能力对后续治疗作出自主决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需要决策代理人提供知情同意来作出维持患者生命的治疗决策,如气管插管、血液透析、心肺复苏等高风险操作[2-3]。面对ICU 患者病种复杂、病情多变的情况,家属需要配合医生在短时间内多次紧急作出决策以挽救患者生命,然而维持生命治疗的突发性和临床不确定性往往使家属在决策时陷入决策困境。相关矛盾因素如家属的想法与患者的治疗偏好、治疗方案的风险与益处、患者需要生的权利还是死的尊严等,易使家属在决策时产生决策冲突[4]。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家属产生严重的心理综合征,如焦虑、抑郁及创伤后应激障碍,从而降低家属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质量[5]。但是,目前关于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的研究较少,故本研究综述了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的研究进展,旨在关注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现象,提高ICU 患者家属代理决策质量,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改善患者健康结局,从而提高医疗护理满意度,为未来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概述
1.1 相关概念:决策冲突、决策困境
根据美国医学会规定,当患者没有能力作出治疗决定时,或者当决定不在预先指示的范围内时,会由指定的代理人或家属替代其作出医疗决策[6]。美国《统一医疗保健决策法》给出了明确的家庭决策层级,依次为合法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成年兄弟姐妹[7]。有研究[8]表明,当决策代理人在复杂的环境下作出与本人内心倾向或患者真实意愿相反的决策时则会引起决策冲突。决策冲突这一概念最早由Janis 等[9]提出,用来描述决策代理人作决策时内心犹豫不决的复杂状态,渥太华决策支持框架(the ottawa decision support framework,ODSF)[10]把决策冲突定义为决策者选择决策方案时涉及风险、损失或挑战个人生活价值观的不确定行为。本研究认为决策困境则是指决策者面临潜在的风险与损失、挑战价值观等冲突时的难以抉择的痛苦状态[9],这种状态会引发决策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创伤后应激障碍。
1.2 道德困境
决策者在复杂的决策历程中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符合双方内心渴望及利益的决定时,常会陷入道德困境。道德困境是指个人对采取的行动作出明确的道德判断,但由于缺乏时间、消极监管、医疗权力被抑制、法律政策不明确等障碍无法采取相应行动而导致痛苦的心理失衡状态[11]。有学者认为[12],当个人知道怎样做正确的事情,但因为某种约束使其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行动,道德困境就会发生。在复杂的医疗决策系统中,关于护士道德困境的报道最多[13],因为护士作为患者的护理责任人,经常在医生、患者及家属等多方决策下面临“伦理两难”的决定,不知采取何种行动或无法采取正确行动,从而陷入道德困境。研究[14]表明,家属作为患者的决策代理人,面对临终关怀、提前制定护理计划、改变护理目标、隐私信息保护、医疗保健成本、与医生建议的分歧、器官捐赠、基因检测、生育决定等问题时,实际选择与本身价值观或患者意愿相矛盾时,也会陷入道德困境。一方面因为强大的亲情纽带力量或因人道主义减少对患者未能“床边尽孝”的愧疚感,有些家属会不惜一切代价调动身边的相关资源来维持患者的生命,甚至接受患者的低生活质量状态,使其毫无知觉或痛苦地“活着”;另一方面迫于经济压力或利益关系,即使患者有生存的希望,也不得不放弃治疗。全力抢救或放弃治疗都涉及决策代理人在道德层面上作出正确或错误的决策,而复杂的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评价都会使决策代理人产生困惑进而陷入道德困境[4]。
1.3 决策困境与道德困境的关系
决策困境与道德困境两者相关但不完全相同。决策困境可以涉及多种因素,如个人利益、道德原则、风险和不确定性等[15],而道德困境是一种特殊的决策困境,涉及伦理道德的两难问题。在道德困境中,决策者面临的选择关系到对道德准则的遵守或违背,或者在不同的道德准则之间作出权衡,可以说每一种选择都承担着一定的伦理义务,不管决策者作出何种选择都要承担道德风险。在ICU 患者家属的决策中,道德困境常常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自主决策权、隐私保护等伦理原则。李良[16]发现道德困境的决策任务有三个特点:①在道德困境中存在决策回避现象;②道德困境受情绪和情感的影响;③道德困境中的决策选项涉及多种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三个特点,有助于加深人们对道德困境决策行为的认知。无论是决策困境还是道德困境,两者都是陷入抉择时摇摆不定甚至选择逃避的内心痛苦状态,可以交叉存在于同一个决策中。因此,在复杂的医疗决策网络中,帮助决策代理人解决决策困惑,摆脱决策困境,基于道德层面建立正确的决策价值观,对决策代理人的道德修养和患者的利益有重大意义。
2 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的评估工具
O'connor[17]认为应对决策困境的第一步就是判断决策者是否存在决策困境,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是及时发现决策者决策困境的前提。美国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18],48.0% 的ICU 患者家属存在中高度的决策困境;郭园丽等[19]研究发现,急性脑卒中溶栓患者家属决策困境发生率高达56.4%,可见急危重症患者家属普遍存在决策困境。对ICU 患者家属而言,通过评估其决策困境现况,可以快速识别决策困境的影响因素,了解患者家属的决策需求,为后续的干预措施及决策质量评价提供参考依据[20]。现有文献研究中常用决策冲突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自我效能量表等评估工具来评估ICU 患者家属的决策困境水平。
2.1 决策冲突量表与家属版决策冲突量表
决策冲突量表(decision conflict scale,DCS)由O'connor[17]在1995 年研制用于评估患者的决策冲突水平。DCS 包括三个维度,即决策不确定性、导致不确定性的因素和决策效能感,共16 个条目,每一项都按照Likert 量表的五分制进行评分,即从非常同意(1 分)到非常不同意(5 分)。2011 年Hickman等[21]首次将DCS 量表应用在决策代理人的决策冲突评估上,报告决策代理人的决策支持偏好以减少决策冲突和决策后悔。2015 年Lam 等[22]对DCS 量表进行汉化和信效度检验,得到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0.81。2021 年廖宗峰等[20]编制家属版DCS 并在191 例神经内科ICU 患者家属中进行信效度检验,量表共3 个维度(决策压力、明确决策价值观、感知决策有效性)16 个条目,条目采用Liket 5 分制计分,从非常同意(0 分)到非常不同意(4 分),总分为所有条目得分之和除以16 乘25,总分0~100 分,分数与决策冲突程度呈正相关,内容效度为0.990,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5。
2.2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是Spielberger 于1983 年编制的用来评估患者的焦虑情况,该量表共有40 个条目,前20 个为状态焦虑分量表,用以评估短暂的焦虑情况,后20 个为特质焦虑分量表,用以评估稳定的焦虑情况[23]。2022 年郭园丽等[19]用状态焦虑分量表评估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决策代理人在决策过程中的焦虑状态,采用Liket 4 分制计分,从完全没有(1 分)到非常明显(4 分),总分20~80 分,分数与焦虑水平呈正相关,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3。
2.3 自我效能量表
家庭决策自我效能量表(family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FDM-SES)于2009 年由Nolan 等[24]编制以衡量家庭成员对绝症患者作出决策参与的信心程度,共26 个条目,分为患者有/无决策能力家属参与的两个子量表,采用Liket 5 分制计分,从完全不可以(1 分)到完全可以(5 分),Cronbach's α 系数为分别0.91、0.95。决策替代自我效能量表(surrogate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SDM-SES)是2013 年Lopez 等[25]编制以评估决策代理人自我效能的评价工具,2021 年Wang[26]根据Brislin 的翻译指南,将SDM-SES 的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并在ICU 的107 名患者的决策代理人中进行信效度检验,采用Liket 4 分制计分,从完全不可以(1 分)到完全可以(4 分),总分5~20 分,Cronbach's α 系数为0.86,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说明此量表可用于ICU 患者决策代理人自我效能的评估。
决策冲突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自我效能量表最初的研究对象均为患者本人,后相继被多个国家的学者重新修订应用于决策代理人,经本土化使用也被证实有良好的信效度。但是考虑到ICU 环境、患者病情、ICU 患者家属特点、文化差异等因素,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还需进一步开发和验证适合我国ICU 患者家属的决策困境评估工具。
3 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的影响因素
3.1 外部因素
ICU 和普通病房不同,防止交叉感染、协调抢救管理、保证监护治疗质量等原因严格限制家属探视。除了医护人员通知家属需要在场对患者的治疗提供知情同意,一般家属无法与患者本人讨论医疗选择,因此,家属对患者病情的担心和忧虑在所难免,更加引起对患者疾病的不确定感[27]。研究表明[28],ICU 患者家属的疾病不确定感与决策冲突呈正相关,即家属对疾病的不确定感越深,决策冲突水平越高。此外,ICU 患者病情危重紧急,家属在短时间内不能理解治疗方案的益处与风险,也不知晓患者的意愿和偏好,容易产生决策延迟与困惑,陷入决策困境[29-30]。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家属要考虑每位家庭成员的想法,协调好家庭成员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左右邻里和亲戚朋友的关注与关心,避免决策代理引起的冲突[31]。研究发现[32],家庭类型也影响着家属的决策体验,强大而稳定的家庭动态可以缓冲压力,通过开放的沟通促进共同的责任和凝聚力,并为培养重要的关系提供安慰。相反,功能失调的家庭可能会经历更多的冲突和分歧,增加心理症状、更复杂的悲伤过程和更差的社会功能。Chiarchiaro 等[18]指出,参与过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对话的代理人的决策困境水平显著低于没有进行对话的代理人,即参与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可以事先了解患者决策偏好,从而降低决策的复杂性。综上所述,家属对患者疾病不确定性、对信息完整度的掌握、社会支持情况、家庭类型、是否参加过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等外部因素使ICU 患者家属陷入决策困境。
3.2 内部因素
有研究显示[19,33-37],影响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的内部原因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经济压力等人口学因素。郭园丽等[19]研究发现,女性更容易在决策时陷入决策困境,在风险偏好中,男性喜欢寻找风险,而女性偏向回避风险,对决策风险敏感性较高[33],更易引起决策压力。有研究[34]认为,年龄也是影响决策困境的重要因素。WU 等[35]通过调查发现老年人的健康素养、理解力和接受度较低,他们在决策中往往表现出被动的态度,这对应对能力和决策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此外,Metz 等[36]发现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往往不能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获得所需信息,不能够快速理解和接受医学知识,难以评估治疗风险与益处,在决策中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作出重大医疗决策时更容易犹豫不决,不知所措。Oliveira 等[37]认为医疗费用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代理人的治疗选择,在经济负担和亲情纽带双重压力下,家属不得不选择放弃抢救而陷入道德困境。另外,个体价值观的不同也会导致决策冲突发生[38],当家属不惜一切代价要求奋力抢救的孝道文化价值观与患者要求自然老死、“无为而治”的人生观相矛盾时,则会引起决策冲突、困境。还有研究[39]表明,有稳定工作且从事医疗相关工作的家属决策困境水平更低,由于其收入稳定,有着广泛的社会支持,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有所了解,则不易陷入决策困境。
4 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产生的影响
4.1 产生负性心理,影响日常生活
研究[40]表明,超过30% 的决策代理人在家庭成员入住ICU 时,存在焦虑和抑郁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部分患者家庭中,焦虑抑郁往往会演变成与临床相关的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41]。参与ICU 患者日常决策的代理人的PTSD 患病率几乎为50%,当决策涉及临终决策时,PTSD 的患病率超过80%。在一项定性研究的系统综述中[42],被访谈的家属进入ICU 面对陌生的医疗环境和失去健康外表的患者,则会移情他们的痛苦,会用“震惊”“害怕”“心烦意乱”“无助”“像在悬崖上一样”“洪水泛滥”“残酷的地狱”等词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内心感受,同时作出的医疗决策使他们内心更加痛苦甚至产生决策后悔[43]。之后重症监护医学会将ICU 患者家属出现的一系列不良心理后果,如焦虑、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抑郁和悲伤称为ICU 综合征[43]。除了负性心理体验,患者家属还面临着日常生活的中断、往返于医院和家庭之间的忙碌、请假的经济代价、家庭内部的冲突以及在ICU 外等待几乎时刻保持警惕而导致的身心疲劳[32],打破正常生活节奏,严重影响家属的日常生活质量。
4.2 影响患者结局,降低医疗护理满意度
ICU 患者家属陷入决策困境时,会对接下来的决策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出现决策延迟从而耽误患者的最佳抢救时间和治疗方案的实施,延误病情,最后表现为难以接受患者的不良结局[44]。另外,决策困境会降低家属的决策质量以及信息处理能力,一项ICU 急性肾损伤家属决策困境的现象学研究[30]发现,持续高强度的决策会降低家属的认知处理能力,从而产生决策回避或被动决策行为,影响后续决策;当家属目睹ICU 患者在治疗中的痛苦表情与虚弱的外表则会出现预感性悲伤[45],与患者感同身受,无法作出理性判断,从而影响医患沟通,或将患者的不良预后归咎于医生,对医生产生不信任感,影响医患关系,降低医疗护理满意度[46]。
5 应对策略
5.1 召开家庭会议,促进医护患三方沟通
Curti 等[47]表示ICU 医护人员可以在ICU 床边或走廊等非正式场所定期与患者家属召开“家庭会议”,出席人员有ICU 医生、专科医生、护士、患者及家属。ICU 医生在与患者和家属沟通之前,系统回顾疾病的诊断、预后、治疗方案和不同治疗的结果,并了解家属对疾病、治疗和死亡的态度。在正式会议过程中,医生尽量站在患者及家属的角度对家属“答疑解惑”,帮助其理解各项治疗的风险益处及可能出现的预后,同时关注家属的心理活动,如焦虑、悲伤等,沟通交流中避免使用专业医学术语,打破家属的治疗信息差,促进医护患三方有效沟通。有研究[48]表明,参加过医生的预期指导、与其讨论过患者的医疗护理目标的家属决策冲突评分更低,家属参与医护患共同制定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并在治疗决策中达成共识,可以减少决策压力和决策负担。此外,医护人员要以诚实的方式讨论预后,例如用“存活到出院的百分比”来描述预后可能更有用,但也要承认这些预测的不确定性,并与家属讨论患者出院后可能的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让家属在面对不良预后时保持希望,同时对医护人员产生信任感,从而在决策时减少冲突矛盾感,脱离决策困境[49]。
5.2 培养“家庭支持专家”,提供决策指导
基于认知—情感决策框架和渥太华决策支持框架[10,50]培养家庭支持专家为患者或家属提供“四项支持”干预措施,旨在降低决策代理人的心理困扰,提高决策质量[51]。“四项支持”包括沟通支持、决策支持、情感支持以及预期的悲伤支持。家庭支持专家需要协助ICU 医生在召开家庭会议之前,收集有关家庭压力源、结构、问题和担忧等信息,为解决家庭问题提前准备实施措施;与家属保持联系,建立融洽关系,对其悲观情绪提供同理心;向家属解释决策代理的原则,确保家属参与讨论治疗方案、预后和风险;激发家属的精神需求,并根据需要进行精神护理;普及死亡教育及安宁疗护理念,引导家属建立科学的生死观,将家属希望的治疗结局变“治愈”为“舒适”;为家属提供与患者床边交流的机会,创造告别空间,主动讨论死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家庭支持专家向家属提供“四项支持”干预措施以满足其认知需求、情感需求、社会支持需求,促进医疗决策,提高决策自我效能[52]。
5.3 应用决策辅助工具,改善家属决策困境水平
研究[53]表明,护士应用决策辅助工具,对患者家属进行决策指导,可有效降低家属决策困境水平,帮助家属脱离决策困境。Scharf 等[54]设计了一款名为“让我们帮你做”的小册子,指导家属如何进行决策以及如何做当下该做的事,除此之外,还配有“家庭支持小推车”,里面有纸巾、水瓶、小饼干、纪念品手模,并固定一缕患者的头发,还有空白的商务名片,上面写着鼓舞人心的引文,可以为家属提供身体和情感上的支持,协助家属决策,减少决策冲突。在一项晚期痴呆患者家属为其选择喂养方式的混合性研究中[55],研究者在干预组运用视听印刷决策辅助工具来协助家属选择鼻饲还是口服喂养,结果干预组家属的整体决策冲突水平有所下降,并提高了辅助口服喂养为最佳护理的确定性。
6 小结与启示
我国关于决策困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对象多集中于患者、护士及医生,而有关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的研究较少,在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的研究和实践上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不论是渥太华决策支持框架下的决策困境,还是基于道德伦理原则下的道德困境,决策代理人的内心都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痛苦的。因此,建议未来开展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的质性研究,深入挖掘其内心真实体验,多维度了解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另外,我国可借鉴国外针对决策代理人决策困境的应对策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应对模式。给我们的启示如下:①受ICU环境和探视制度的约束,家属无法随时与患者床边沟通,医护人员可在ICU 外准备一个小型会议室,用于召开家庭会议或按需与患者家属沟通。若患者知晓病情、意识清晰有自主决策能力,医生则需评估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并询问家属是否允许患者参与决策,这样既尊重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又减轻了家属决策时的无助与压力。在此之前,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进展、可能出现的预后、治疗方案的风险利弊等情况列出决策需求清单[56],以便患者家属选择性咨询。②培养ICU 责任护士为“家庭支持专家”,把“眼里看到的、耳中听到的”及时与医生沟通,发挥医患间的桥梁作用。建立由ICU 医生、专科医生、ICU 护士、心理咨询师、医学伦理专家等组成的多学科决策指导团队,深入研究国内外ICU 患者家属的决策困境水平、影响因素、决策需求、决策辅助工具,定期以专家授课、案例讨论、角色模拟的形式进行决策指导培训,及时关注家属决策时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及道德需求,给予人文关怀。另外,医院有条件的话,可以建立社工部为ICU 患者家属协调家庭关系,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家庭寻求社会支持减轻经济负担,保证家属的决策质量。③医护人员可借鉴Scharf 等[54]设计的决策辅助小册子,研发基于ICU 患者病情、治疗方式、家属需求等因素的个性化决策辅助工具,如在家属等候区播放通俗易懂的决策辅助科普视频、张贴疾病治疗相关知识科普海报、举办家属决策需求讲座等,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及文化程度的家属的决策需求。④可结合国情开展决策支持体系的建设,如构建决策评价方案、研发多类型决策辅助工具,以推动决策支持模式在国内的落实[57],从而降低ICU 患者家属决策困境水平,提高决策质量,改善患者健康结局,提高医疗护理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