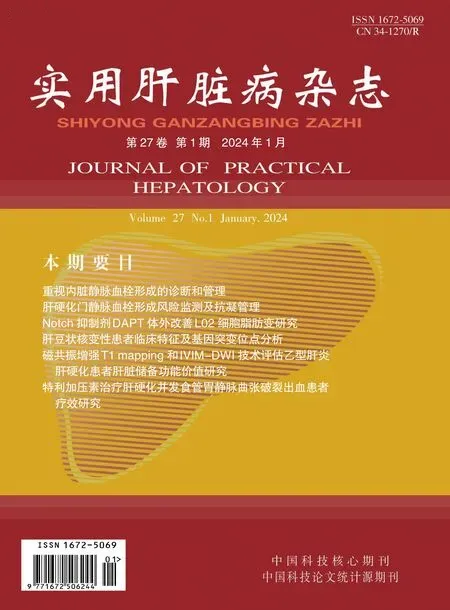巨噬细胞DHA代谢表型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发病过程中的作用*
潘 勤,薛 芮 综述,范建高 审校
近20年随着肥胖、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日益加剧的全球化流行态势,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的患病率不断攀高,并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第一大慢性肝脏疾病,与当前全球肝病并发症及死亡人数增加密切相关[1]。NAFLD的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simple fatty liver, 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及其相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1, 2]。NAFLD患者的疾病进程和预后主要取决于肝组织病理学表现类型。随访NAFL患者10~20年肝硬化发生率仅为0.6%~3.0%,而NASH患者10~15年肝硬化发生率可达15%~25%,NASH患者5 a和10 a生存率分别为67%和59%[1, 2]。因此,NASH处于NAFLD患者肝病进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临床防治NAFLD的主要干预群体。如何做好分级管理,做到早发现高危人群,规范地随访,合理的检测和检查,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高脂血症、高血压、胆囊结石、代谢综合征和心脑血管疾病,对改善预后非常重要。
NAFLD的“多重打击”学说认为,肝脏经历胰岛素抵抗等“初次打击”后发生NAFL,其对各类损肝因素的敏感性增加,并因肝细胞脂肪变性而为脂质过氧化提供了反应基质;进而在肠源性内毒素、酒精毒性、缺血再灌注损伤等“附加打击”触发下,因糖脂毒性和氧化应激相关脂肪性炎症而进展为NASH[1, 2]。另一方面,临床研究发现饮食治疗和有氧运动等减肥的生活方式干预措施能够减轻肝内炎症反应,降低NAFLD活动度积分(NAFLD activity score,NAS)和脂肪变/炎症活动/肝纤维化评分(steatosis, activity, and fibrosis (SAF) score),延缓甚至逆转NASH进程[1, 3]。然而,既往针对NASH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往往集中于抑制肝脏炎症的发生和避免其持续进展,较少关注去除病因或危险因素后NASH的自然消退过程。由此导致NASH相关脂肪性炎症的发病机制迄今为止仍不甚明了,临床上NASH的无创诊断和新药研发至今仍无突破性研究进展。
1 肝脏代谢性炎症“激活-消退”是受单核巨噬细胞系统调控的主动过程,促炎症介质/maresin的平衡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众多研究表明,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在NASH等代谢性炎症的发生和进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脂毒性损伤的肝细胞既可分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等细胞因子,也可通过肌醇需要激酶1α(inosital-requiring enzyme-1, IRE1α)/X-box结合蛋白1(X-box binding protein,XBP-1)/丝氨酸棕榈酰转移酶(serine palmitoyl-transferase,SPT)/神经酰胺信号途径的激活引发促炎外泌体释放,从而共同募集并诱导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扩大肝脏巨噬细胞池的规模[4-6]。另一方面,脂毒性的肝细胞通过病原体相关分子机制(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和危险相关分子机制(danger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激活肝脏固有巨噬细胞(Kupffer细胞)和单核细胞来源性巨噬细胞的Toll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 TLR)依赖性先天免疫反应,增强其促炎表型,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tic factor α, TNF-α)、白细胞介素1α(interleukin 1α, IL-1α)、IL-1β、IL-6、IL-12、IL-18、IL-23等促炎细胞因子释放增加,并产生一氧化氮、活性氧和活性氮自由基,伴抗原呈递能力增强等[5,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趋化中性粒细胞,促进1型辅助性T细胞(T helper cell 1, Th1)和Th17的免疫应答,最终引起NASH患者特征性的肝小叶内炎症[6]。但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对肝脏炎症消退的影响至今仍存在争议。
传统观点认为,脂质过氧化损伤的肝细胞诱导IL-1β、IL-6、TNF-α等细胞因子,抵抗素、瘦素等脂肪因子,以及白三烯(leukotriene,LT)、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s,PGs)、肝氧蛋白(hepoxilin)、氧化脂质(oxylipin)等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产生和释放增多,由此引发肝内代谢性炎症及其相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2,3,7~9]。肝脏炎症消退则是多种促炎因素减弱、消失,进而降低上述促炎症介质水平后发生的被动过程,不受机体主动调控。近期多项研究挑战了上述观点。
在ω-3 必需脂肪酸-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来源的巨噬细胞代谢产物中,已经分离并鉴定出maresin-1、maresin-2、maresin-L1、maresin-L2等一类含多羟和多不饱和共轭双键分子[10,11]。maresin-1通过抑制髓细胞白血病序列-1(myeloid cell leukemia-1,Mcl-1)、B淋巴细胞瘤-2(B-cell lymphoma-2,Bcl-2)表达,以caspase依赖方式诱导中性粒细胞凋亡;在清除免疫效应细胞的同时,避免焦亡和细胞外诱捕网形成(NETosis)可能引发的炎症加剧[10-14]。此外,maresin-1和maresin-2等均可促使巨噬细胞向M2表型极化。在促炎表型消退的基础上,M2型巨噬细胞由表达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6等)和趋化因子(CXCL9、CXCL10等)为主,转变为表达抑炎细胞因子(IL-10等)和趋化因子(CCL17、CCL18、CCL22、CCL 24等)为主[15,16]。不仅如此,maresin诱导的M2型巨噬细胞还能够借助胞葬(efferocytosis)功能来清除炎症部位凋亡的中性粒细胞[12,17]。携带胞葬体的巨噬细胞继而通过迁移作用离开肝脏,向淋巴结、脾脏等淋巴组织归巢[10,18]。多项研究报道显示,maresin的作用与抑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核因子κB ( nuclear factor κB,NF-κB) 信号途径,以及激活脂氧素A4受体(lipoxin A4 receptor,ALXR)/Akt信号途径等机制有关[19-22]。
因此,肝脏代谢性炎症的启动、进展、消退是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受到促炎症介质与以maresin为主的特异性促炎症消退介质平衡调控的一系列主动过程。Maresin多环节激活中性粒细胞凋亡、诱导巨噬细胞向抑炎表型转化、增强抑炎表型巨噬细胞清除凋亡的中性粒细胞、引导完成免疫细胞清除任务的巨噬细胞向肝外归巢,从而成为启动炎症“程序性消退”阶段的关键诱导因子。
2 HDAC/12/15-LOX/maresin信号途径紊乱引起促炎症介质/maresin失衡,通过阻断炎症“程序性消退”诱发NASH
研究发现巨噬细胞表达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 HDAC)[23,24],并发挥重要的免疫调节功能。已知组蛋白乙酰化主要发生在H3、H4 N端保守的赖氨酸ε氨基位置上,这有利于双链DNA与组蛋白八聚体解离以及核小体结构松弛,从而使不同转录因子和协同转录因子能与DNA结合位点特异性结合,最终激活基因转录。HDAC催化的组蛋白去乙酰化则由于形成封闭的染色质构象,降低了转录因子的可及性和基因的转录活性。编码脂氧合酶(lipoxygenase,LOX)的ALOX15被证实为HDAC调控的关键下游基因[25]。位于活化巨噬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中的DHA能够经磷脂酶A2的水解作用释放入胞,进而通过LOX介导的氧化途径合成多种maresin等特异性促炎症消退介质[26]。不同物种ALOX15 基因编码的 LOX 统称为12/15-LOX,在以DHA为代表的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PUFA)代谢网络中处于关键节点[27,28]。当代谢底物为 DHA时,12/15-LOX可将其催化为14-过氧化氢基二十二碳六烯酸(14S-hydroperoxy-docosa-hexaenoic acid,14S-HpDHA),并进一步环化形成13S, 14S-环氧化物中间体。这个环氧化物一方面可水解产生maresin-1,另一方面则通过可溶性环氧化物水解酶的作用生成maresin-2[10,11,27,28]。在此基础上,12/15-LOX通过催化maresin合成,能够实现对炎症“激活-消退”过程的主动调控。
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道,无论高脂高果糖饮食和胆碱蛋氨酸缺乏饮食(methionine/choline deficient diet,MCDD)诱导的NASH模型,还是2型糖尿病合并的NAFLD小鼠肝脏均存在HDAC高表达以及组蛋白低乙酰化水平的特征[28-30]。与之相应,肝脏巨噬细胞的12/15-LOX和maresin在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NAFLD患者中往往呈现出表达不足的特征,并与中央静脉周围炎症以及门静脉和肝窦部位的炎性细胞灶性浸润伴随发生[28-31]。一项针对124例NAFLD患者和116例对照人群的横断面研究显示,NAFLD患者血清巨噬细胞来源性maresin-1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进一步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证实低水平maresin-1与NAFLD显著相关。不仅如此,血清maresin-1还与血液AST和ALT水平呈负相关[31]。提示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maresin低表达可能破坏了促炎症介质与maresin之间的动态平衡,导致炎症自限及消退机制受损,进而在炎症慢性化的基础上促进NASH进展。
与之相反,HDCA抑制剂干预、上调12/15-LOX水平、外源补充maresin或其前体等皆具有诱发和加速肝脏炎症消退过程的作用[10,11,32,33]。采用基于ω-3 PUFA的全肠外营养可以诱导肝脏高表达maresin-1、maresin-2,进而刺激人单核细胞来源性巨噬细胞产生抑炎细胞因子(IL-10),并可避免CD4+T细胞释放促炎细胞因子[34]。直接给予maresin-1治疗,同样可以抑制肝脏MCP-1和LTB4刺激所致的单核细胞迁移、粘附,减少肝内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浸润数量;抑制活化巨噬细胞介导的先天免疫反应,并诱导其由促炎(M1)表型向抑炎(M2)表型极化[10,11,35]。最终,maresin显著降低了肝脏髓过氧化物酶、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环氧合酶2等炎症标志物,以及血液TNF-α、IL-1β、IL-6等炎性因子和转氨酶的水平[18,19]。此外,借助其促进炎症消退的作用,maresin-1还能够改善TGF-β1/Smad2/3诱导的肝星状细胞上皮-间质转分化,从而阻断甚至逆转NASH引起的肝纤维化[10,11,35,36]。
综上所述,HDAC/12/15-LOX/maresin是维持促炎症介质与促炎症消退介质maresin之间动态平衡的重要信号途径。其功能紊乱引起的maresin缺乏,通过阻断肝内炎症“程序性消退”能够诱发并加速NASH进展。补充外源性maresin能够促进肝内炎症消退,对NASH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其存在无法预防NASH发生、药理作用缺乏肝靶向性、体内半衰期较短且血药浓度较低等缺点。通过干预HDAC/12/15-LOX/maresin信号途径来重塑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DHA代谢表型,重建肝脏促炎症介质/maresin平衡,则可望借助炎症“程序性消退”促进NASH的缓解或逆转。
3 肠菌源性丁酸重塑单核巨噬细胞系统DHA代谢表型,通过促炎症介质/maresin再平衡,促进炎症“程序性消退”和NASH的自然缓解
多项最新研究显示,结肠等部位的益生菌群(拟杆菌属、双歧杆菌属、真杆菌属、瘤胃球菌属、梭菌属等)通过分解膳食纤维素,产生可溶性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等肠菌代谢产物[37]。较之细胞内脂肪酸氧化形成的少量内源性SCFA,肠菌代谢产生的外源性SCFA是体内SCFA的主要来源。SCFA包括甲酸、乙酸、丙酸、丁酸和戊酸等不多于 6 个碳原子的有机酸,其中丙酸和丁酸丰度相对较高[37,38]。业已发现,肠道内的丁酸主要由酪酸梭菌(ClostridiumButyricum)、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prausnitzii)、罗斯氏菌(Roseburia)、霍式真杆菌(E.hallii)、直肠真杆菌(E.rectale)、丁酸弧菌(Butyrivibrio)等厌氧菌群通过缩合乙酰基辅酶A形成,并在SCFA中展现出最强的免疫调节活性[39]。真杆菌属(Eubacterium)、罗斯氏菌、普拉梭菌利用菊粉等果聚糖的代谢产物,也可生成丁酸[40]。上述产丁酸菌群来源的丁酸经肠粘膜吸收入血后,主要通过门静脉流入肝脏。肝脏因其“首过效应”而成为丁酸作用的关键靶器官。
除作为结肠上皮细胞的能量来源、维持上皮粘膜屏障等生物学效应之外,丁酸还被发现具有广谱的HDAC抑制作用,能够导致I类(HDAC-1、-2、-3、-8)、II类(HDAC-4、-5、-7、-9)、III类(SIRT 1-7)和IV类(HDAC-11)等绝大多数HDAC失活,并可能下调其表达水平[41-47]。通过广泛抑制HDAC及其催化的组蛋白H3和H4乙酰化,丁酸(钠)可恢复肝内固有巨噬细胞(Kupffer细胞)和单核细胞来源性巨噬细胞的12/15-LOX表达[26,48]。12/15-LOX水平上调后,在促进DHA生成maresin的基础上可能进一步诱导肝内炎症由持续激活转向主动消退。课题组前期分别采用酪酸梭菌移植和丁酸(钠)灌胃来治疗高脂高胆固醇饮食诱导的NASH模型小鼠。证实两者在诱发HDAC失活的基础上,均能够促使肝内炎性因子的表达模式趋向正常,肝小叶内炎症程度较NASH模型组显著减轻,NAS积分明显下降[49,50]。然而,NASH患者和模型动物结肠及肝内丁酸含量常因肠道菌群紊乱而明显降低,并可能成为HDAC/12/15-LOX/maresin信号途径功能紊乱和炎症“程序性消退”受阻的始动因素[51,52]。
总之,肝脏代谢性炎症“激活-消退”可能是免疫系统受机体精细调控的主动过程,PUFA代谢产生的以maresin为主的特异性促炎症消退介质在炎症消退阶段可能发挥关键的诱导作用。肠道菌群紊乱所致的丁酸缺乏通过激活肝脏HDAC依赖性组蛋白乙酰化、下调12/15-LOX表达、减少maresin产生,干扰了HDAC/12/15-LOX/Maresin信号途径,从而可能在促炎症介质与促炎症消退介质(maresin)失衡的基础上,阻断代谢性炎症的“程序性消退,“导致NASH的发生和发展。借助肠菌来源性丁酸重塑免疫系统的PUFA代谢表型,可能恢复促炎症介质与maresin平衡,进而通过促进炎症“程序性消退”诱导NASH缓解并降低NASH相关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发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