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短篇之王的“月之暗面”
杨殳

如果说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那只因恐惧源于未知。“对未知的恐惧”这一主题,就像莫泊桑的“月之暗面”,既是他热烈而荒唐一生的底色,也是他在文学史上深埋的宝藏。
1890年,莫泊桑对一位朋友说:“我像流星一样闯入文学界,又像雷电一般地离开。”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3年。虽然他心中仍激荡着不熄的创作热情,同时构思着两部长篇,但显然他已预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身体病痛和精神疯狂的双重摧残中走向终点。
热烈地活 玩命地作
莫泊桑师出名门,他的母亲有一位童年好友,是法国大作家福楼拜,在莫泊桑12岁时,母亲就为他朗读福楼拜的作品。在巴黎大学念法律时,他的学业和写作都直接得到福楼拜的指点,两人情如父子。
除了福楼拜,还有一位诗人指导莫泊桑写作,后来诗人不幸去世,福楼拜“赢”了——他不想让莫泊桑沉溺于抒情诗,教导他艺术要学会观察,要运用理性,要学会用一句话写出一匹马和其他马的不同。这一理念看似不起眼,却成为莫泊桑独特艺术风格的起点。
这位文坛“社牛”虽然私生活腐化,却坚守精神独立。他拒绝加入任何团体,拒绝信奉某种学说,包括左拉创建的“自然主义”流派;他也拒绝各种奖项,甚至对福楼拜的“投机取巧”也表示不齿;他不向任何教义和金钱低头,因为要保留自己的批判权力。他害怕锁链,“不管它来自一种思想,还是一个女人”。这种精神独立意味着内在的自由,但也意味着他必须承受心灵无所依附的孤独和恐惧。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莫泊桑入伍。两年后他退伍到海军部做小公务员,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他几乎每周到福楼拜家参加沙龙,与都德、左拉、屠格涅夫等前辈交流。他的诗歌、戏剧和小说都能第一时间得到名家点拨。他不断尝试各种题材,他遵从福楼拜的建议,并不心急,写作力求精确、节制,打算找到自己的风格之后,憋个大招一鸣惊人。
1880年,命运转捩点到来。这一年,莫泊桑在福楼拜帮助下,转到教育部门上班、做编辑,同时继续努力写作。虽然他又一次因写诗惹上官司,却终于憋成大招,写出突破之作《羊脂球》,与其他同主题小说一起收录于小说集《梅塘之夜》。
此后不久,福樓拜中风离世。莫泊桑亲自为老师更衣修面,合上双眼,并像儿子那样守灵。他因悲伤而空虚,不知今后如何。次年小说集《泰利埃公馆》出版,莫泊桑声名鹊起——地地道道的十年磨一剑。
和《羊脂球》一样,《泰利埃公馆》同样以妓女为主角,把世俗生活写得风趣生动,又暗藏对秩序的反抗。这篇小说不但让法国文学圈对莫泊桑刮目相看,还惊动了俄国同行,屠格涅夫特意告诉托尔斯泰,莫泊桑不错。其后10年,名利双收让莫泊桑拥有了自由写作的权力,他完成了《月光》《菲菲小姐》《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米隆老爹》《两个朋友》等名篇,还有《一生》《漂亮朋友》《温泉》等长篇。
肉身不羁 精神独立
不夸张地说,莫泊桑的写作始于身体经验,终于精神体验。早在其16岁于教会中学念书,就已初尝鱼水之欢,并写诗记录体验:“一团幸福之火燃遍我俩全身”。后来他又爱上表姐,写诗表白,诗作流传甚广,也因此被学校开除。这让小小年纪的他感受到了世俗的约束,正如在一首诗中感叹——“天太低,地太窄,环宇于我皆太小。”
莫泊桑做公务员的那些年,过着枯燥与放纵交织的双面生活。除了上班和写作,就是到塞纳河上组织一群花花公子玩快艇、在浴场寻欢作乐。他热衷下流段子和搞恶作剧,还组织过一个吃喝玩乐团体,取名“屁神协会”。他狂热追求女性,却不投入情感,只为满足原始冲动,甚至公开统计“战果”,声称一个男人在40岁之前可以拥有300个女性。
莫泊桑的写作方式是怎么活就怎么写,其作品几乎都取材于自身经验。他的小说里写有形象各异的芸芸众生:妓女、农民、士兵,以及上流社会和精神病人——足见其人生体验之丰富,洞察之敏锐细致。法国文学翻译家张英伦曾将他的中短篇作品按主题分类结集,分出了“奇异”“情爱”“战争”“诙谐”和“世态”这5册。
莫泊桑在发表处女作的同时,也收获了放纵生活的“成就”:感染梅毒。可他对此表现得毫不在意:“雄伟的梅毒,纯粹简单;优美的梅毒……我觉得骄傲,去他的布尔乔亚。”即便在导师和前辈面前,他也毫不掩饰自己不羁的生活,这让福楼拜很头痛,总担心这小子会纵欲而亡。不过他也从未干涉,毕竟对法国人来说自由高于一切。
梅毒的不断恶化,令他不到30岁就开始遭受眩晕、头疼和眼疾的折磨,严重时以头撞墙。莫泊桑成名后开始建别墅、买游艇、到处旅行。他一生未婚,却处处留情,生下两个私生子和一个私生女。然而,身体的痛苦让他患上了躁郁症。
莫泊桑越是纵欲,就越觉空虚。他时而狂躁如愤怒的公牛,对名利斤斤计较;时而又陷入深深的抑郁,觉得自己不过是“制造文章的工人”,既要玩儿命卖钱,又觉得写作很没意思。
狂人日记 未知恐惧
莫泊桑在25岁那年以笔名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名为《剥皮的手》,是爱伦·坡风格的恐怖故事。作品灵感来源于莫泊桑本人的收藏品:一只剥了皮的断手。
福楼拜认为这篇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可老师的不屑阻止不了莫泊桑病态的爱好和对幻想的痴迷。他一生都在写的奇幻故事,内容涉及幻觉、死亡、催眠、双重人格还有外星人,光是直接题为《恐惧》的作品就写过两回。在无信仰的莫泊桑那里,表现可知的生活,和探究不可知的精神世界,都是对“真实”的探究。因此奇幻小说不但是莫泊桑作品谱系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而且相比现实题材,更接近其内心。
1886年,莫泊桑写了一篇小说名为《疯子的来信》。次年,他用对话体重写了一版,后又改成日记体,命名为《奥尔拉》(法文“le Horla”是他的自造词,没人知道确切意思,可理解为“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
《奥尔拉》的主人公总感觉家中有鬼——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盯上了自己。他在日记里记下所见所想,称那东西叫奥尔拉。他越是提防,奥尔拉越强大,不但折磨他,还要侵入身体和思想取而代之。后来他出现幻觉,身体也失去控制,最终发疯,决定与奥尔拉同归于尽。
这是否是叙述者的疯人疯语?没人能辨得清,但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莫泊桑的中枢神经已遭到破坏,常常分不清现实与幻想。1892年的一天,他先用枪再用刀,最后跳窗,一口气自戕3回,不得不被人送进精神病院。临死前的一天,他把木棍插进泥土告诉护士:把这个种下去,来年就能看到一些小莫泊桑。
在莫泊桑八九岁的时候,他目睹父亲发疯一样殴打母亲后逃出家门,在树林里躲了一夜,内心完全陷入痛苦和恐慌,“这种令人心碎的无法解释的恐惧,就像另一个世界吹来的未知的风”。
纵观莫泊桑一生,这种恐惧与疯狂几乎如影随形,却因过于难解和复杂而常为人所忽视。就像我们谈论其文学成就,总会提到他对卡佛、毛姆等主流作家的影响,但很少有人提及他的奇幻作品,尤其是《奥尔拉》对奇幻文学和“克苏鲁小说”产生过的深远影响。
(责编:常凯)
人物简介

莫泊桑,1850年出生,1893年病逝,只活了短短43年,却写出了359个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3部游记,以及剧本若干。其中大部分作品——包括令其名垂青史的经典中短篇小说《项链》《羊脂球》和长篇小说《一生》《漂亮朋友》等,都创作于40岁之前。这位与契诃夫、欧·亨利齐名的“短篇小说之王”,曾以流星、雷电来自喻,可谓自信满满,名副其实。
《羊脂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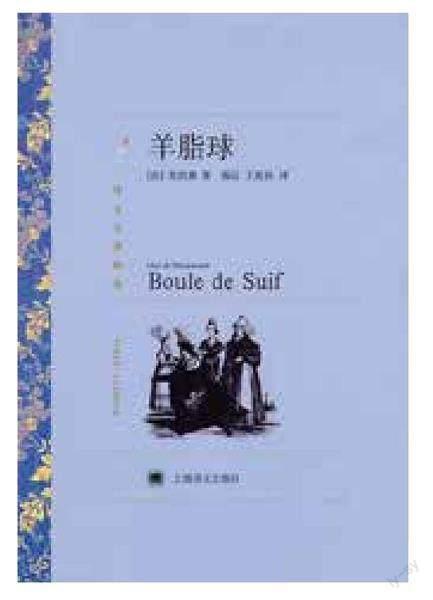
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战争的洪流播弄着众生的命运,巴黎的浮华喧嚣着世人的疯狂。这位短篇小说大师以精炼的文笔谱写了一组法兰西生活组曲。
《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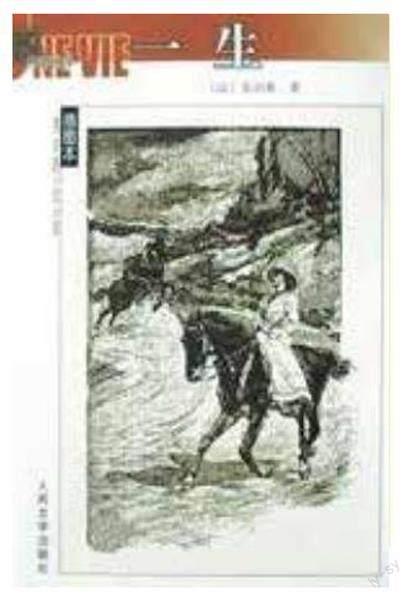
《一生》是莫泊桑对长篇小说的初次尝试,这部小说试图通过一个女子平凡而辛酸的身世来剖析和探索人生。
《俊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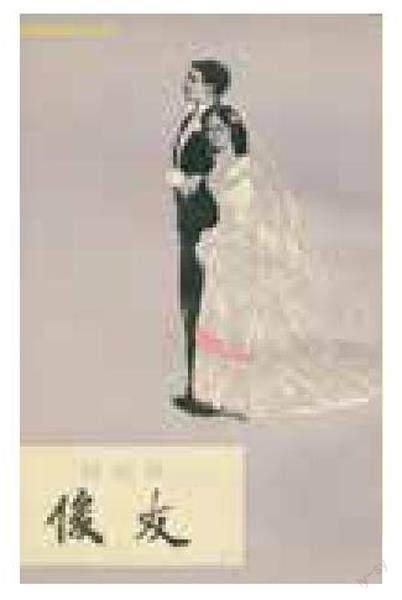
(《漂亮朋友》)
這部莫泊桑的代表作1885年5月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几个月内再版30余次。它被誉为19世纪末法国社会的一幅历史画卷,描写了19世纪80年代巴黎一个小职员杜·洛华发迹的经历。
《梅塘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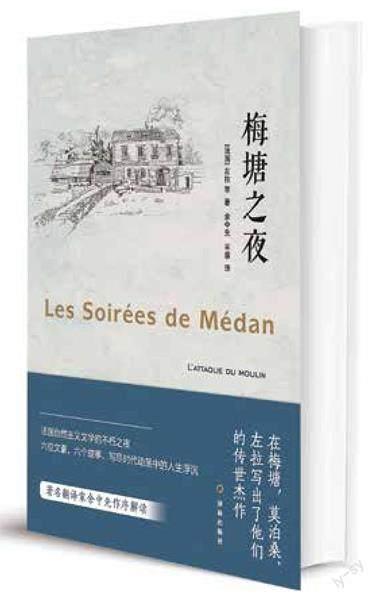
《梅塘之夜》共6篇小说,均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其中有左拉的《磨坊之役》和其他名家作品,而年轻的莫泊桑以《羊脂球》技压群芳。福楼拜为之狂喜,认为学生的这篇小说“构思浑然一体,独具一格,景物和人物跃然纸上,心理描写很见功底”,断言是可传世之作。他在给莫泊桑的信中说道:“《梅塘之夜》已经出了8版,我的《三故事》才出了4版,我简直要嫉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