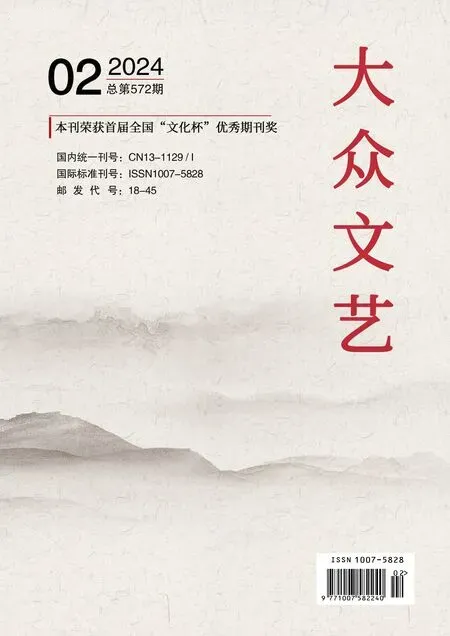传播与转译
——以维米尔图像为例展开的思考
周冠玮
(信阳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在艺术实践中艺术精神被观者接收,必先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被人为制造产生,这恰好符合迪基对于艺术品定义“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的资格或者地位。”[1]中的第一要素。以人工制品为基础上的传播行为从人类启蒙时期就已经开始,旧石器时代法国拉斯克洞窟壁画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中的彩陶制品等。艺术品依赖于人工制品下图像形式被观者欣赏、接受或批判、拒绝,直至现当代,艺术图像是文化的载体和具有记录性的审美图式,是不同区域、国家、民族等意识形态交流的物质载体。当意识形态开始交流,传播就起到重要的作用,传播渠道建立的综合场域即会对艺术品图像的呈现产生影响,且导致观者对艺术家创作意图上的误读。
维米尔作为重要的西方艺术家,他的艺术品走过较为曲折的道路才被世人所知。所以维米尔的艺术图像传播在当代的研究中具有极高价值。笔者将从图像传播的多个方面展开讨论:建立在艺术品基础上的图像传播行为在过去和当下是以何种渠道完成的?艺术品放置在不同渠道架构的场域中,图像是否维持创作初始的固有表征?建立在单纯的图像上的传播行为能否维持艺术精神的稳定性?观者面对同一图像是否产生相同的认识?
艺术家的名字习惯性作为其艺术的概念性表达,如:“伦勃朗”即为伦勃朗艺术。本文将以“维米尔”作为维米尔艺术的概念性表达。
一、商业渠道下的“维米尔”
维米尔继承父亲留下的画商生意和成为Dеlft小镇的画家行会的领导者身份让他维持正常的收入,但由于子女众多,不得不依靠商业订单进行更多的艺术活动。在当时,维米尔的作品已经深得一些收藏者的喜爱,在他生前作品已炙手可热。[2]如重要的赞助人彼得·凡·鲁伊汶(Рiеtеr.vаn.Ruijvеn,1624-1674)至少拥有约二十一幅维米尔作品。1696年5月16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艺术品拍卖会上,展示了维米尔所创作的二十一幅作品。[3]其中,油画《称金子的女人》《倒牛奶的女人》和《德尔夫特的风景》分别以155、175和200荷兰盾的价格拍卖出,这三件作品都流传到了今日。[4]这个时间维米尔已去世二十一年。十七世纪在荷兰订单画尤为繁荣。维米尔的艺术创作,精神属性被商品属性掩盖,商品属性下的艺术图像易被忽视,但维米尔艺术精神却借以洒下了传播的种子。维米尔在订单渠道下,作品受众多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和以手工业谋生的新市民阶级。这个时期的维米尔作品的图像传播依赖于商业行为,精神意图的传播同样隐藏于订单者的购买行为之内。其原因在于当时订购者更关心是否符合自身的审美需求而非艺术家的内心世界。精神相对于物质有自身的独立性,维米尔的创作意图在这商业渠道中并未消解或改变,而是与作品图像结合隐喻其中。
两百年时间里,“维米尔”处于潜藏期,直到二战时期汉·凡·米格伦将一部分维米尔的作品出售给一位纳粹军官赫尔曼·戈林(Неrmаnn.Gоring).事情发展到后来汉·凡·米格伦被审判通敌卖国罪,但转折点在于他出售的作品是自己的仿作,而非真正的维米尔作品。这一事件直接促进了“维米尔”价值的发掘和传播。该传播的渠道依然是建立在艺术品的商品属性之上。艺术传播范围在商业渠道的场域中得到扩张,艺术图像的传播是跟随艺术品的流通进行传播的,战争的掠夺性同时伴随着艺术品的转移,该转移行为不仅使得“维米尔”图像传播范围的扩大,更是区域文化精神边界的交叉和重组。这种精神边界的交叉和重组在战争中伴随艺术品的跨区域流通进行传播。但同时因本身掠夺性的特质,无法对艺术品本身行之有效的保护甚至造成破坏,如侵略战争下真正艺术品被掠夺而导致的破损。基于以上的阐释,战争对于艺术图像的传播具有不稳定性,而造成的艺术品的损毁对之后的图像研究及学术讨论的判断产生影响。
现代艺术品流通虽然同样在商业渠道下,但与前面提到“订单式”购买不同,该商业行为购买者对“维米尔”是认同的,图像和精神在这种传播渠道内得到较为完整的接收。
二、公共艺术空间下的“维米尔”
二战之后,艺术工作者重新思考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艺术的讨论也愈加热切。在艺术表现之外,其传播也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化交流通过艺术展览的形式交织在一起。艺术展览有多种形式,广泛见于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等公共艺术空间。[5]
“维米尔”在公共空间下得到了重新定义,在传播上不仅仅限于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仪式。公共空间承接了宗教场所的特质,“博物馆不仅在建筑上与宗教仪式场所遥相呼应,它们更是仪式的发生地”。[6]
我们将“维米尔”放置在博物馆中展出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仪式。博物馆给予艺术品一个稳定的展出空间,这个空间的稳定不仅来自展馆的布置,更是文化语境的稳定。通过该传播渠道,建立观者对艺术图像固定的观察范围及角度,博物馆在语境上尽可能搭建了一个符合历史文化的展览场域。在这个场域内,“维米尔”图像的文化输出还原了艺术家原本意图。馆藏展是一种艺术精神的稳定性传播渠道,观者在面对艺术品原作时,当代社会意识会缩减而艺术品本身意图会扩张。馆藏展对于艺术图像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基础,且在馆藏展的语境下,观者的观展行为中得到了约束,必须到达指定地点、必须遵循某种观看方式。该约束行为在人类活动上又拥有了教化的意图。卡罗尔·邓肯提出艺术博物馆经常被拿来与仪式场所作比较,认为艺术博物馆是代表着某种社会秩序的信仰场所。[7]笔者认为:具有信仰仪式的交互行为中,展览场域的稳定性利于艺术实践工作者更好的接收“维米尔”图像和精神。以博物馆渠道研究为例,对于艺术理论研究人员便于整理图像志的同时更好地了解艺术品传播渠道。通过对传播渠道的研究,进一步解读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解读建立在艺术展览行为的基础上。艺术展览体现了这种文化共享行为,共同的美学体验使观众形成一种“想象共同体”,观展行为促进了观众之间的精神交往和关系连接。[8]如观众在博物馆中接收“维米尔”图像同时也接收到维米尔时期的文化世界。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也有这种情况,感觉到自己完全脱离了内容,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是在通过作品和艺术家打交道。[9]接收是不尽相同的,这依赖于自身的文化审美。
与博物馆展出有所不同,现代美术馆、画廊的交流展更为频繁,该渠道建立的是不断重构的展览语境。以涉及“维米尔”的展览为例,常与其他艺术家作品共同展出。这种展出的方式是将区域艺术研究转向场域艺术研究的重要途径。“维米尔”的初始意图,必然依托于其生活的区域所带来的局限,主题性展出的方式将“维米尔”的意图放置在可以被更多受众接受的渠道中。首先,跨越艺术家所属的区域展出行为不仅是艺术品空间的转移,更是不同区域文化建立交集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策展机构的主动调整,调整需应合观者的认同(其包括:社会、民族、心理、审美等)。那么在该传播行为中,艺术家原本意图将服从于展览整体的特定宗旨。如2017年仲夏之际,6月17日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的“伦勃朗和他的时代:美国莱顿收藏馆藏品展”,这次展览中带来维米尔的画作《坐在维金纳琴旁的年轻女子》。维米尔的作品依附于展览整体的文化场域,即“伦勃朗和他的时代”。在时代主题的文化背景下,维米尔的艺术理念成为组成整体文化的一部分,个体与整体建立统一关系时,相互之间的影响会改变两者原本的意图,“维米尔”个性精神的在展览宗旨要下被削减。如上述作品与维米尔的另一幅作品《被打断奏乐的女孩》共同组建一个意图:“爱人唯独爱一人”(‘а lоvеr оught tо lоvе оnlу оnе’),该意图的论证是由两幅作品中图像的相关性及文字记录共同得出。但在上述展览中,作品《坐在维金纳琴旁的年轻女子》的由于艺术品放置于“伦勃朗和他的时代”这一文化语境的原因,“爱人唯独爱一人”的意图被遮挡,而巴洛克时期荷兰整体的时代文化意图被加强,这就服务于“伦勃朗和他的时代”文化场域,而图像在观者接收时的意图也随之改变,转向描绘荷兰十七世纪的时代风貌。其次,巡展将空间的局限进一步打破,表现方式为区域性的拆解和全球化的重构。从观者的角度看,是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的节省,进一步缩减文化的边界。该论点可从教育方向进行说明:“伦勃朗和他的时代:美国莱顿收藏馆藏品展”中“维米尔”带到中国,国内的观者可以直观艺术品图像,不同于复制品渠道的呈现,在视觉意义上是对物象的真实接触。在艺术心理学上,同一作品的不同场域中观看,细微的差别导致心理认同上的巨大差异。意识总是选择“通感”更强的一方。这种心理取舍是一种先验理性的判断,发生在与展出艺术品相遇之前,但转折在于与艺术图像相遇后判断发生了改变。交流展对于观者的艺术体验是普遍的。大航海时代开始,文化艺术的区域边界开始不断消解,“伦勃朗和他的时代:美国莱顿收藏馆藏品展”对于向往维米尔、伦勃朗等大师的国内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近距离的观赏空间。中外艺术能够更好地进行比较性的研究,这种研究不局限于绘画本身,更多是依托于绘画图像而展开的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及历史上相关技艺、材料学的研究,这是艺术图像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在公共艺术空间下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维米尔”的真实体验,但由于策展方建立的场域不同,意图也会有所不同。图像坚守了初始的显示特征,但精神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如伊瑟尔所言:“艺术作品的结构是一种召唤性的结构,只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才能填补和具体化这个艺术图示中的空白和不确定点,完成这个召唤结构。”[10]
三、作为商品画的“维米尔”
虽然艺术品具有商品属性,但这里商品画通常指那些大批量生产的装饰绘画作品。艺术图像从区域到场域的变化离不开商品画的承接,图像载体的变化让艺术精神扩散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维米尔”得到不同区域的认同不仅因其艺术创作本身的价值,图像的传播渠道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艺术图像的载体作为对复制品,传播的渠道又将建立不同的场域从而形成新的精神表现。建立在复制品之上是否还原了艺术品本身的图像真实性?图像的真实与否相较于精神上的“守真”是否一致?观者面对艺术复制品时,传播渠道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过去直至现在,国内外艺术复制品都曾混杂在真迹中共同展览出售。随着时间的推移,油画复制品逐渐发展成为商品画走进大众的视野,其中油画复制品又以安格尔的《泉》为代表的学院派艺术和凡·高的《向日葵》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为最,当然不乏当代观念性的艺术品。其中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油画复制品更是成为商品画中的佼佼者,该作品被数以万计的复制成油画形式进行商业活动在各大艺术集散地。现代工业精神艺术首要提及波普艺术,如爱德华·路希·史密斯所言:“沃霍尔很快就从汤罐头的单一呈现发展到复合呈现,而相同的形象一次又一次得到重复,好像要消除它在孤立状态中单独被观察时也许会产生的特殊意义。”[11]与之不同,“维米尔”商品画建立在对原作的图像再现基础上,这种再现的生产行为虽然具备工业化生产的特质,但在物质被批量生产的同时必然伴随其(艺术复制品商品画)艺术价值的消解,当然这种消解是仅限于复制品而非艺术品本身,这种价值消解直接体现在商品买卖的价格上。丹纳曾言:“群众的趣味完全由境遇决定”,这证明现代商品画的购买者审美境遇可以接收“维米尔”图像。抛开艺术价值消解的问题来观察图像的真实性:维米尔油画复制品中图像特质并未被改变,视觉上沉稳安静的风格特质与原作一般无二。图像风格的继承是对“维米尔”的价值肯定,更是对艺术家本身认知上的真实还原。回到商品画艺术价值消解的语境中,视觉上的还原不能脱离“假”的标签——是复制品非艺术品,在观者与商品画产生互动过程中就否定了艺术品的概念。但这不等同于否认其传播行为的价值,油画复制品对于艺术图像传播肯定是具有正面推动性的。同时推动性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来自将商品画置于何处,也就是放置过程中因接收渠道的变化,艺术图像原本的意图被改变了轨迹,且在传达的精神同样被篡改。例如:在娱乐为主的消费场所,油画复制品更多提供一种享乐的精神服务,如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妇女》油画复制品放置在酒店的场域中,人们往往忽略其本身艺术价值,而更多仅在视觉直观上认可它的美。这种认可是是有预备性的,预备情绪是由情绪造成的。同样情绪不仅来自作品,也来自渠道建立的场域。若将同一幅复制品放置在咖啡厅,由于场域的变化观者对图像判断也会改变。若“维米尔”商品画放置在一场关于艺术家本人的学术会议上,无论是图像审美或精神价值将占据主导位置(研讨会的方向也是构成场域的重要因素如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也将在精神范围内有所不同)。商品画的图像传播是一种增减性的精神活动,这种增减与前文中原作的图像传播最大的区别基于一个拟定“假”的概念,这种概念对于观者和创造者在事物产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影响判断。事实上这一判断本身通向“真”的意图。笔者认为,认知上建立“假”以作前提,就是对“假”有了真的认知。而油画复制品在不同场域中的研究,其“真”就具备了更多的方向及可能。
四、媒介传播下的维米尔
艺术是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生产形态。艺术图像在现当代传播中更多依赖于纸质载体和电子载体,这是由于现代生产形态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激光束扫描方式转化为图像激光扫描技术;20世纪80年代喷墨技术将颜料进行点喷,该技术可以印刷出更加清晰的图像。以维米尔的艺术为例,由于油画艺术的视觉特殊性(色彩、明暗、薄厚、透明度等),所需的印刷技术需要更高的标准来还原图像的呈现,在技术得到解决的先决条件下才能更好地完成图像的传播。对于图像的真实性而言,优质的纸质、电子图像载体与油画复制品比较同样稳定性。首先纸质复制品也更容易保存,现代技术也解决了随时间失色的问题;其次,电子复制品的本质是数据,相较于实物而言数据的保存复制更具便捷性。观者通过纸质、电子渠道接收艺术图像,缺少了空间场域的影响。这导致是观者对于“维米尔”精神的接收仅来自图像和附属文字的解说,无疑在特定接收行为中受渠道之外的影响越少。当观者受外在影响越少,对于图像意图的接收越单一,在纸质图像的传播渠道中,观者和艺术家意图处于一种更狭窄的场域。与纸质载体相同,电子载体的渠道也被约束在艺术图像和文字解说,不同的是其数据化、时效性、可接收范围变广的特征被加强:1.基于数据化的方式,现代技术将图像进行数据化的处理,再所需展示虚拟空间中重新整理呈现,相较于之前所有的传播渠道,电子传播在时间上更快捷;2.加之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艺术图像的接收人群、空间范围、时间范围都得到扩张。范围的扩张与艺术精神意图的传播成并列关系,两者亦步亦趋。以维米尔的艺术为例,无论是在艺术传播还是美术教育交流,纸质、电子复制品都将艺术由区域向场域转化,推动艺术传播一体化进程。艺术传播一体化并不是消解地域文化,而是将区域文化放置在现当代的交流渠道中。正如施旭升教授所言“显然,在当今全球化与消费化的浪潮席卷之下,如果没有了地域文化的依托,艺术就可能永远是在漂泊之中,永无归期。”[12]
回溯观之,纸质、电子渠道的传播引导更多观者到展览与艺术品本体直接对话。西方艺术品在中国展出,观者先接收展出新闻在参与展览活动。纸质、电子渠道提供了一个更为纯粹的精神接收场域,这一点源自前文提及的:在该渠道中观者对于“维米尔”精神的接收仅来自图像和附属文字的解说。
艺术品具有商品属性,并且可生产衍生品。以维米尔的艺术图像为例,2022年08月,国外小学馆旗下专门销售周边威士忌产品的电子商务网站Whiskу·Меw与国外国家美术馆合作推出了国外国家美术馆艺术藏品主题独立装瓶单一麦芽威士忌套装。本套装中包含两款酒,其中一款名为——フェルメール『ヴァージナルの前に座る若い女性』ラベル グレンマレイ2007。这款酒的酒标上使用的是约翰内斯·维米尔(Jоhаnnеs Vеrmееr)的著名画作《坐在维纳金琴前的少女》。作品由维米尔1670-1672年创作,现收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艺术图像的精神意图在融入商品的时候发生了转化,前文提到该作品与维米尔的另一幅作品《被打断奏乐的女孩》共同组建一个意图:“爱人唯独爱一人”(‘а lоvеr оught tо lоvе оnlу оnе’)。而在商品渠道中,该作品图像精神为提高商品的文化价值,主要突出古典主义的精神特质来描绘商品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制作的精良。这种意图的转化在提高商品价值之外,同时通过商品的流通渠道传播“维米尔”。
在影视作品中,艺术图像也常被作为创作的素材。《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2003年被英国导演彼得·韦伯(Реtеr Wеbbеr)拍摄成电影。彼得·韦伯将自己对于古典主义的理解通过故事画面呈现,并由此获得第76届奥斯卡奖的三项提名(最佳摄影、最佳服装设计、最佳艺术指导)。[13]在图像上,电影总体还原了油画原作的视觉特征,但由于拍摄目的是架构电影语言,难免与原作有所差别。面对画面和处理画面的呈现是电影拍摄重要的组成,画面色彩表现卓越的影片不乏其例,彼得·韦伯的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给电影画面的表现提供了不同的视觉和思维方式,成为不同艺术形式借鉴和表现的经典范例。[14]
电影艺术是将静止的平面上的三维视觉转为运动的平面上的三维视觉,VR技术就是将观者置于技术创造三维艺术世界当中。近几年的VR技术发展在游戏、电影等方面发展迅速,艺术创作同样运用了这项新的技术。VR的使用让艺术家在虚拟的三维空间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和塑造前人的艺术形象,观者在VR创造的三维空间里观赏互动、参与创造。现代艺术工作人员在虚拟空间按照《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形象创造一个女孩,是否该思考,这一新出现的事物是维米尔的少女或者仅借用前者形象创造出来的新的艺术观念。这一点类似于杜尚的《泉》,但不同点在于杜尚的《泉》是一种赋予现成品艺术公信力的行为,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本身具备艺术公信力,那这种创作行为就是借用艺术公信力下的衍生艺术创作。这时,艺术传播和艺术行为将成为一个表达艺术精神的整体。
五、结语
以荷兰艺术家维米尔为例,笔者进行了简单的思考。传播渠道作为整个艺术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搭建艺术与观者的桥梁。图像在渠道中的传播实质上就是艺术在不同价值体系中追求“真实”的过程。前文提到的“误读”,实际上是观者在接收过程中求真的结果。图像在现当代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是能够维持基本的固有表征,但固有表征的维持并不代表观者接收的一致性。因渠道变化会引起观者在艺术精神接收上的转译。自然,认识也将不同。
至此,我们再来讨论关于渠道、图像、艺术精神的问题。
渠道既是方式又是载体,既提出如何处理又参与处理什么。渠道提供了将艺术置于何处的途径、拆解艺术的工具以及重组艺术图像的外力。渠道是建立语境的驱动元素,同时影响了图像在展示空间中的固有状态和再现形式。
在渠道之上形成了综合语境,但这个语境并不完全依赖于渠道,因观者在接收通过艺术图像和艺术精神时,会因无法预知的其他因素(自身的情绪、自然环境的变化、区域文化的影响、他人的介入等)而发生倾斜。
艺术精神根据对图像的判断而来,由于图像和渠道的变化,艺术精神的判断也产生了变化。但变化走向哪里同样是未知数。如何理解这句话,需引用数学上的概念:源发的图像精神是“1”,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予以不同的运算方式和参与条件会导致运算结果的不同。在艺术哲学的思考中,创作和接收是不稳定的,对“真实”的体悟也全然不同。通过艺术图像接收艺术精神也存在特定条件,条件的建立也需要锚定的坐标来协同完成,当然锚定在哪里和如何锚定也是问题的关键。
以维米尔艺术语言为基石,传统形式的写实油画语言在现当代语境该走向何处?艺术精神的发展是否必须抛弃传统的绘画技法和表现方式?如果将传统油画语言放置在不同渠道建立的场域中,我们必须应该重新面对写实油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