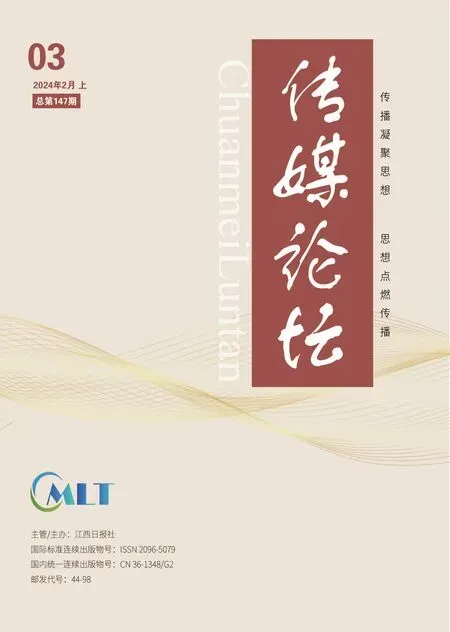人设贩卖、情感越界:全景敞视下“低龄妈妈粉”的媒介角色展演
姜伟东
正如乔尔·莫克尔所言,任何进化系统都有链接过去和现在的某些动态特性,过去以某种方式约束或者影响着现在。[1]中国的饭圈文化研究一般可以追溯至改革开放后期,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剧”“港星”“台星”的浸入,中国的粉丝追星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娱乐产业的发力和媒介的全面展示,客观上刺激了粉丝对于偶像的全方位追寻,粉丝在全景媒介展示和消费时代的背景之下,成为大众娱乐生活最具争议和话题性的群体,中国娱乐文化的发展见证了粉丝族群从“消费主义的牺牲者”渐进演化为具有文本的“抵抗与生产能力”的小历史。[2]女性更容易成为粉丝,女性构成了粉丝文化的主体,其原因主要有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偶像崇拜是人的正常心理,但是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从众,并更容易具有补偿心态和爱恋心态。[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Z世代”女生为主要成员的粉丝群体,主要是指男性明星的女性粉丝群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她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将偶像称为自己的孩子,希望偶像能够一直保持积极向上、阳光正面的形象,将自己比作是家庭中“操心的老母亲”形象,明确地规范了粉丝和偶像的关系是:妈妈-孩子。“妈妈粉”隐匿于粉丝群体的总体昵称之下,她们从行为上把一个群体分成自我和他者,一方面拥有他者的群体归属,另一方面拥有自己独特的追星行为和体验。
本文尝试突破“粉都”“饭圈文化”等固有的研究角度,深入探索粉丝群体新生力量,在行为、消费、年龄上都极具鲜明特征的“低龄妈妈粉”的群体形成、媒介角色展演以及对于偶像群体的作用力等内容,探讨其产生路径和传播机制。
一、“低龄妈妈粉”的角色生成和心理特征
“当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加入趣缘群体之后,这一群体就成了个人进行社会化的‘同辈群体’,群体其他成员就成了该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者’”。[4]“Z世代”的学生群体,是典型的互联网原住民,生活中没有过多负担,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和空闲时间,对于旁观者的异样眼光,也呈现出一种异于普通族群、特立独行的荣耀之感,以及能够为偶像牺牲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一)情感越界——由仰视到监视
根据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的理论,当今的媒介环境呈现了全景信息,使得权力展示出自动化和非个性化的特征,[5]权力没有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任何人都可以去充当监视者的角色,偶像的培养体系使得妈妈粉可以看得到偶像的一举一动。多位受访者明确表示,偶像事业上升期禁止谈恋爱,“他们必须对得起比赛时候在舞台上的承诺,热爱舞台,努力发展,出道之后立马谈恋爱,那我们的付出就打水漂了”(MF11)。“妈妈粉”对偶像的关注,与妈妈对孩子望子成龙的教育理念异曲同工,每一步都需要她们严格把关。
某偶像的粉丝群体曾经在线下举行过抵制活动,人人举手幅,喊口号,希望他能接正剧,拒绝出演为圈钱策划的水剧。妈妈粉会揣测偶像心情不佳或者身体不佳,由此喊话偶像助理、经纪公司,发起刷屏行为。粉丝能贡献的强大购买力、曝光量和话题热度,带来粉丝的权力增长,于是粉丝的崇拜行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仰望到参与、从幕后到幕前,参与偶像生活的全方位形塑。
(二)人设贩卖与人的淹没
Z世代在成长过程中,先天伴随着三种抹不去的基因: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互联网带来的游戏迷恋和为兴趣买单的消费特性[6]。他们成长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成长道路上对周遭世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寻找一个行为模仿的对象,刚好现代娱乐产业和造星运动构筑的“现实梦境”,为他们提供了一众偶像。在媒介和资本的相互作用之下,非面对面的准社会交往中的亲密关系得到了强有力的夯实。Z世代妈妈粉清楚自己在消费的是“空中楼阁”,“我知道追星是把自己藏在乌托邦里,但是这能够让我短暂地跳出我现实的烦恼,这何乐而不为”(MF01)。如同被访者MF04所言,当她知道自己的任姓偶像(源自一档乐队选秀节目)私下里跟站姐吃饭被曝光的时候,怒火无法压制,就在微博上公开发出对偶像严厉的训诫。该事件以任姓偶像在个人账号上郑重道歉为结束。以此可以看出偶像个人的情感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必须遵从的规则。社交网络提供给粉丝群体可以发挥能量的超级空间,这种技术性共谋与新媒体赋权下的虚拟互动关系,真正地影响了现实生活,个体集合力量成为整体,整体对偶像的规劝、助力、纠正,成为“妈妈粉”这一特殊族群的粉丝标签和身份标识。
(三)女性主体意识觉醒
西蒙娜·德·波伏娃从历史、生物、精神分析等方面全面地论述了女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存在的位置、价值和处境,一直以来女性以生育、安抚等次级功能服务于部落或社会,以他者、财产等角色存在于家庭和社会之中。
1.生理性和社会性集于一身
我们甚至可以把还未出道未爆火的偶像比作妈妈粉群体的胚胎生命,胎儿牢牢地安置在妈妈粉的保护之中,两个机体相互适应。妈妈粉认为自己掌握着塑造生命走向的主动权,“完整拥有腹中果实”[7]。妈妈粉可以按照自己脑海中的完美男孩的形象来要求和敦促偶像快速成长,为偶像消费、应援,男性成为“被爱和被保护”的客体。
2.媒介赋权下对偶像的形塑
“从破坏社会控制支配体系的能力来看,几乎所有的公共传播媒介都具有激进的潜在力量。它们能够提供获得针对现有秩序的新的思想和观念的途径。”[8]新媒介对私人领域的展现,使私密空间成了公共场所[9]。“妈妈粉”群体掌握了搬运内容、生产内容、传播内容的主动权,开拓了属于自己小群体的交流空间。“我们不愿按照传统的观点去生活,也不愿意接纳二元化性别的标准,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完成对偶像的二次性别创造”(MF09),在虚拟空间中,言语和行为不似现实生活中那般受限,可以解放自己的欲望和想法,尽情地表达。在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下,关于媒介使用具有显著而持续的被性别化的特征,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性别不同导致不同的媒介使用行为,进而出现了某些媒介专门为女性受众服务。[10]布尔迪厄认为:“那些自认为合法文化卫道士最不可忍受的,是那些明令严格区分的优劣品味,却亵渎地合流到了一起。”[11]当前女性的经济独立和消费诉求使得传统男性气质发生松动,以女性消费为主体的“男色经济”崛起,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文化消费时尚。媒介塑造商品符号价值的过程就是消费主义在媒介的影响下运作和生产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媒介文化表征消费主义特征与倾向的过程与范式。[12]
二、过度沉浸,虚拟关系中的情感越界
(一)情感关系的绑定
“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做能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3]在妈妈粉的情感投射中,能够在偶像的身上看到的任何一种特质甚至一个瞬间的小动作,都可能成为击中“我们内心的点”(MF05),令她们为之付出。
偶像取得新成绩的时候,“妈妈粉”会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骄傲和满足,类似于“妈妈的好大儿”“孩子真争气”(MF02、MF03),“妈妈粉”的构建使粉丝更具话语权,没有人会质疑一个“母亲”的殷切期盼。在“妈妈粉”的世界里,也存在着“别人家的孩子”这个概念,比如“不能输,要赢,要更好”(MF06)“孩子输了就是我们的失职”(MF07)。“儿子排名的落后,就是我们当妈的无能”(MF14),表面上是粉丝为了偶像争夺出道机会和更好的商业资源,建立明确的区隔和群体文化认同,背后则是出品方和制作方遵从娱乐产业的规则,将出道机会变为粉丝之间消费能力的竞争,获取粉丝参与黏性和更多的经济利益。
(二)行为模式的确立
经纪公司会为旗下艺人在官网设置粉丝会员模式,会员可以享受到见面会门票优先抢、定制周边购买权、物料抢先看等特权。受访者MF01认为这是经纪公司对粉丝群体的PUA,但即便明知道是如此,还是会一年接一年地续费,因为“孩子在他们手里”。为了保护他们的“孩子”,成熟的粉丝群体内部管理等级分明,职能划分如下:文案组主要负责控评等文字内容的输出;美工组负责P图等图像编辑工作;视频组负责剪辑偶像或者跟偶像相关利于宣传的视频内容;反黑站负责监视和举报处理黑粉和负面的言论;数据组负责检测数据、超话、打榜等跟流量相关的工作。所有粉丝群组必须跨媒体跨时空进行联动,这种供养式的行为角色和责任划分,与家庭抚养孩子属于相同类型。
三、结语
(一)存在即观点,在场的表达
Z世代有着“互联网原住民”的明确标签,追星与其日常生活中各项活动的逻辑逐渐趋同。[14]她们的追星行为,去掉了对主流价值观的反抗和叛逆,与网络民族主义和粉丝民族主义倡导存在一致的价值取向。肖战的妈妈粉对于肖战为北京冬奥会献唱主题曲一事,感到“非常自豪”“心潮澎湃的成就扑面而来”(MF08、MF13)。
在场是一种交往中流动的状态,受媒介技术的制约或者增强。[15]媒介的存在提供了追星通道,也阻隔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真实的互动,这种阻隔也赋予了粉丝“在场”新的时空意义。“妈妈粉”的行为逻辑消解了传统家庭的妈妈角色对孩子予取予求的期待和要求,转化成一片赤诚。这种操心坚守着对偶像遥远而又“亲密”的爱。她们并不屈从于传统的父权社会的束缚,也不遵循二元性别的理论的教导,跻身于资本和娱乐场域的中心地位。“妈妈粉”通过无私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的角色扮演,无畏其他人对自己污名化的异化描述,彰显网络文化与青少年亚文化多元、开放、变化的日常场景。
(二)焦虑与享受,虚拟的成就感
在粉丝文化的研究领域中,追星行为被认定是对现实的逃避、对焦虑的妥协,但从Z世代的成长轨迹中,能够窥探到,他们目的性很明确地找到了对抗焦虑的办法——恰当地把生活中诸多仪式演化成应对机制。[16]追星的仪式感教给他们如何从社会层面来管理和化解焦虑。Z世代的接受度门槛较低,他们成长在“小屏时代”,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并不清晰,他们接受虚拟,享受虚拟,也满意与在虚拟世界中获取的愉悦和满足。“我知道是假的,我也知道最终会消失的,没关系,追星以外的东西也并不能保证真实而长久”“虚拟的成就感也是成就感”(MF06、MF07)。偶像发新歌的时候,妈妈粉不仅会在第一时间购买和欣赏,还会为了能够冲到平台播放量排名的榜首,还会连续不断循环播放,甚至在做其他事情的同时也会静音播放。
(三)区隔他者,自我形象的建构
根据最优特异性理论,个体都有渴望能被群体接纳,即同化的需要。[17]成为哪个偶像的“妈妈粉”,并不会让这个群体羞于启齿,群体内部会在为偶像争气的光环笼罩之下,延伸出社会化范畴中的对自我的认可和满足。“妈妈粉”会在日常追星的行为中,将自己的标签通过应援、控评文案、见面会物料等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有意识地建设身份区隔,是最直接地进行“妈妈粉”媒介形象展演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妈妈粉”来说,她们渴望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获得更广更深的参与感。“妈妈粉”的自我建构与群体行为的形成,也体现了Z世代青少年在社会发展与新媒体技术赋能中寻找自我、寻找发声的渠道,尝试构建愉悦自我的氛围和更有话语权的粉丝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