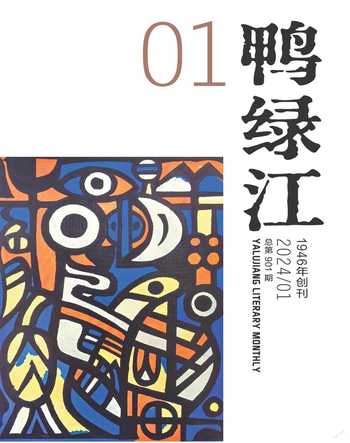小小说二题
丛棣
诗人
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如果真有人这么问,梁栋定会点头称是,且一脸诚恳。
每个人在学生时代都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好老师,那种“好”是唯一的,排他的。有时就是一种单纯的感受,就算能说出来,别人也很难理解。
韩老师就是梁栋心目中的好老师。直到现在梁栋仍想不通,韩老师怎么会是体育老师呢?他可以教语文,再不济,教音乐和美术也行啊。教体育的韩老师看上去弱不禁风,一脸稚气,分明就是个大孩子嘛。事实上,他比梁栋他们也大不了几岁,据说大学念了一半就不念了,也不知因为什么,来他们初中代课,但明显压不住课。他的体育课以游戏为主,动不动就把体育组的各种球全放出来,让大伙儿在操场上可劲撒欢儿。同学们玩着高兴,他在旁边看着高兴,就是校长和主任不高兴,时常会当着学生的面敲打他几句。他会挠挠头,龇牙一笑,牙齿很白。
值得一提的是,韩老师是城里人,住单身宿舍。梁栋去过他的宿舍,一溜瓦房把头那间,以前是仓库。墙上挂着一把木吉他,还贴着几张素描,画上的女子很好看,梁栋认出来了,是医务室的小赵老师。除了一张单人床和简易炉灶,房间里只剩下书了,堆得到处都是。梁栋过去就是为了看书、借书,都是些诗词歌赋世界名著什么的。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韩老师眼睛一亮,像是梁栋身上有什么在闪光,被他及时捕捉到了。
梁栋其貌不扬,学习成绩中下,做数学题和背英语单词最让他头疼,语文还好,他学得挺起劲儿,就是语文老师年老昏聩,照本宣科,不光很少提问他,还常给他的作文判低分。他不服气,曾把作文本拿给韩老师看,问,你看是跑题了吗?韩老师沉吟片刻,一拍大腿,好!写得好啊,别管他给多少分,就这么写准没错!
一开始梁栋不相信,谁知韩老师点评起来头头是道,目光炯炯,不容置疑。时间一长,竟发觉两人很谈得来,梁栋有事没事都爱过去坐坐,看看书,或是听韩老师弹琴唱歌。韩老师唱歌很好听,而且那些歌都是他自己写的。韩老师还会写诗,常饱含深情地读给梁栋听。有的地方能听懂,有的地方就朦朦胧胧的,直听得梁栋脸红耳热,隐隐觉得那是写给女生的。在韩老师的感召下,梁栋也迷恋上了这种逶逶迤迤的文体,长长短短写了不少,拿给韩老师看,就会收获他赞许的目光,还会一如既往地啧啧着:不错,真不错啊!也是从那时开始,梁栋暗自篡改了自己的理想,将来他要成为一名作家,不,是诗人……
后来,梁栋没能考上高中,也是偏科太厉害了。再后来,韩老师回城了,据说当初他就是奔着小赵老师过来的。小赵老师是在城里念的中学,两人曾是同学,念书时就好上了。小赵老师先考的卫校,他后来上了一所很像样的大学,但是没念完。两人的恋情终于大白天下,还是被校长抓了现行的,是的,这所初中的校长也姓赵。所以,韩老师走的时候有些声名狼藉……
梁栋一直没走出去,如今人们都叫他“梁三”,还会在前面添个“杀猪的”。杀猪的梁三,小镇只此一号,一提都知道。长久以来,梁栋很配合人们给他的定位,一脸横肉,粗声大气,身上总是油渍麻花的。近年中学同学时常聚会,叫上班主任,还有那个已经很老很老的语文老师,梁栋也会晃着膀子到场。多是些衣锦还乡的同学,免不了要动情地回忆一下学生时代,说这个老师好,那个老师也好,就是没听见谁提起过韩老师,好像都集体失忆了一般,忘记了那个给大家代过一年半体育课的大孩子。
没人知道,梁栋始终跟韩老师有联系。逢年过节,梁栋会特意进城,带些上好的里脊肉过去。韩老师过得很不好,还住着小瓦房,不比原先的单身宿舍大多少。他没孩子,倒是有一个粗俗的老婆,面目凶恶,跟他说话从没好气儿。韩老师身体不济,像是提前步入了老年,一度给某大院打更。梁栋没再见过他弹琴唱歌,也没再听过他朗诵情诗,他面对梁栋时甚至已无话可说,偶尔龇牙一笑,牙齿很白。
又是一次同学会,开席没多久梁栋就喝多了,在一片笑语喧哗中,梁栋趴在酒桌上呜呜起来,很大声,给所有人都看蒙了。没人知道,几天前梁栋刚去看过韩老师,其时韩老师已是弥留之际,单薄如纸,嘴唇翕动,似有话要说。梁栋将耳朵贴近,听见韩老师在问他:写吗,现在还写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韩老师使劲皱皱面皮,说,那就好,那就好哇……
梁栋没有撒谎,他一直在写,偷偷地写,有时只能在心里默念给自己听。现在他要大声朗读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平复了一下心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缓缓展平,颤声道:这是一首诗,是我写给韩老师的……
水手
“不是一头,而是一群鲸鱼。远远地,交替着沉浮,巨大的尾巴不时地拍打着海面,喷射出的水雾有数米高,在斜阳的映射下,变幻成一道道彩虹……”
这是发生在印度洋上的一幕。其时李想正站在一艘远洋货轮的甲板上,目不转睛地观望着,并用文字记录下来,连同自己的心情。还有很多天方夜谭般的奇遇,裹着风雨雷电,被他一并塞进信封。
信都是他亲手交给我的,每次厚厚一沓。他说,你慢慢看。我也会给他一沓,里面写的都是我的生活琐屑,以及我们这座小城的日常。不用叮嘱,我知道他会细水长流,慢慢看。我们的交流无须托付邮路,也没什么时效性。每次他下船回来,我俩都要很正式地见个面,再很正式地互换信件。他说,你文笔真好,谢谢你。其实我觉得他文笔也不错,视野更开阔,时常会让我如临其境,感同身受,但我一直沒说。没记错的话,整整三年,我们只见了五面……
我们是初中同学,两家离得不远,走得却不近,读书时他好像跟谁都不近。我知道他家境不好,父亲早逝,母亲在街道印刷厂做临时工,他还有个小他很多的妹妹。那时他瘦瘦高高,面皮白净,坐在我后面,不爱说话。他的学习成绩一般,喜欢偷看大书,曾向我借过两本。借的时候低着头,脸通红,像做了错事。还的时候也是,我也是自那时发现的,面皮白净的人格外爱脸红。初二的时候,从广州回来的叔叔送我个随身听,就是袖珍录音机,听卡带的那种。还是日本三洋的,在当时是稀罕物,全校应该也没几个。我经常偷偷带到学校,课间休息,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分享。每个耳朵轮流挂一个耳机,也要排很久的队。时常有人情不自禁地哼唱出来:“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后面的几乎变成了一段小合唱,难以抑制,有几次险些惊动了走廊里的老师。
那时候,郑智化的《水手》正流行,我们百听不厌。
终于有一次,李想在放学路上叫住了我,那一声好像动用了他体内不多的元气,以致脸红得发紫,头再低也难掩饰。他嗫嚅着,能借我听听吗,《水手》那盘,就一晚,行吗?随身听我从不外借,那次却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他,还很痛快,也许,也许是怕一旦拒绝他会哭吧。经过这件事,我俩的友谊并没有升级,他还是那么不合群,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后面,有时偷看大书,有时偷偷发呆。只是在那年的元旦茶话会上,他结结实实地露了一次脸,也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击鼓传花嘛。鼓點骤停,花传到谁手里,谁就得站出来出个节目。李想把红花捧出了白花的效果,勾头弓腰,哭丧着脸,很快将茶话会带入了追悼会的气氛中。冷场。继续冷场。最后是谁推了他一把吧,或者是他绊了自己一下,礼节性的掌声终于让他站稳了脚跟。他唱了《水手》,前两句声音还微微发颤,后面就渐入佳境了,几乎技惊四座。到后来他的眼中已有泪光闪烁,唱词铿锵,很快引发了一场大合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我一直认为,那是李想生命中的高光时刻。追忆往事时,这段很难绕过,出乎意料的是李想对此反应冷淡,匆忙岔开话题,即便他已是一名真正的水手了。初中毕业后,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听别人说,他母亲后来也病逝了,他高中也没念完,四处打工,供小妹读书。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小城,进了一家机关单位。小城很小,我们是在街上碰见的,我没认出他,是他喊的我。像是另一个人,身形粗壮,皮肤黝黑,只是笑起来还是那样腼腆。他说,我去年上的船,第一次休假。又说,一起吃个饭吧……
从此,李想再回来我们都会出去坐坐,他的话还是那么少,只能由我不停地发问,好在我对海上生活一直很好奇。他的回答总是很简短,“很苦的”“怎么不孤独”“习惯就好”……
他也会说,“继续给我写信”“你的文笔真好”“还是家里好”……
我曾买了很多书送给他,还送过他MP4和小收音机,觉着多个水手的朋友也不错。他会送我一些外国钱币和纪念邮票什么的,让我觉得有个水手朋友真挺好的。整整三年,我们见了五面。后来他到底没有做到三副,在信中他说真的厌倦了,他想上岸了。他亲手将信交到我手中,其时他已经下船了,彻底不做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目送他到街对面,绿灯都快闪过了,他还犹疑地站在马路中间,看上去很恍惚,与周遭的人群车流格格不入……
从此,李想再没找过我。同学聚会他也没到场,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听说已搬到了另一座城市,生意做得很大,都是听说。意兴阑珊的一众老同学,又从酒店转战到KTV,借着酒劲儿干号着,硬撑着,好像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也不知是谁点了郑智化的《水手》,顿时群情激昂,如回光返照。那是一段合唱,也是一段绝唱:“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其时我正在卫生间,听到了,不由得也喉咙洞开,大声呕吐。同时泪眼蒙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