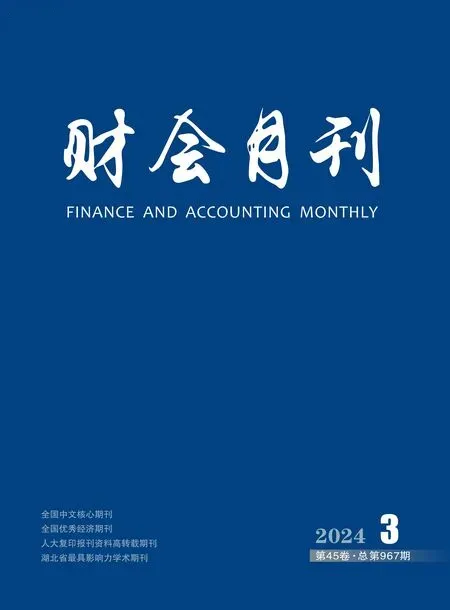论现行并购商誉计量的会计逻辑困境
谢德仁(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并购商誉及其会计处理是近几年会计准则制定和资本市场中的热点问题,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20年就发布了关于如何改进业务合并和商誉会计处理的讨论稿(IASB,2020a)。2020年11月,IASB在其公布的《同一控制下的业务合并(讨论稿)》中再次讨论了并购商誉的相关会计处理问题(IASB,2020b)①。在我国学术界,徐经长等(2017)、谢德仁(2019、2023)、张为国和解学竟(2020)、谢纪刚和张秋生(2020)、李明和彭川(2021)等都对并购商誉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从中国知网中搜索可发现,学术界关于商誉的研究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但这些文献雷同之处颇多。笔者虽为保证研究的创新性而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粗读与细读,但为节约篇幅起见,无意在本文中就此一一综述,因为这些文章都没有论及本文将要分析的现行并购商誉计量方法的会计逻辑困境问题。为分析简便起见,本文以下的讨论不涉及廉价并购(bargain purchase)的情形。需指出的是,本文旨在分析指出现行会计准则关于并购商誉计量的会计逻辑困境,重在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以抛砖引玉,期冀学术界对此展开深入讨论。
除引言外,本文还包括三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介绍现行会计准则关于并购商誉的性质认定和计量方法;第三部分分析现行会计准则关于并购商誉计量的会计逻辑困境;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现行会计准则关于并购商誉的性质认定与计量方法简析
1.并购商誉的性质是资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关于业务合并的现行会计处理是由IASB(2008)发布并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相关准则相协调的修订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 号——业务合并》(IFRS 3)来规范的。IFRS 3把商誉定义为:商誉是一项资产,其代表那些在业务合并中所收购的、无法单独辨识与确认的其他所有资产(other assets)所创造的未来经济利益。这个定义中所谓的“无法单独辨识与确认的资产”也就是“不可辨认资产”。这是本文后续讨论的基础,即并购商誉是一项资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收购方所有不可辨认资产的集合,而非仅仅是业务合并会计处理中的一个“递延借项”。为讨论简便起见,本文把被收购方的商誉理解为一项而非一组不可辨认资产。此外,需指出的是,IFRS 3对于业务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新购买法(acquisition method)转向了基于财务报表体系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的现行价值计量观(谢德仁,2023),具体是采用现行价值中的公允价值来计量业务合并。
2.并购商誉计量方法。如果并购商誉是一项可辨认资产,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那么就可以直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予以计量。令人遗憾的是,商誉是不可辨认资产,无法从企业整体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交易,也不是源自法律授权或合约权利,故也不存在商誉自身的活跃交易市场。谢德仁(2023)曾指出:关于商誉本质的共识性理解是企业未来超额收益或超额盈利能力,但这应该溯源至稀缺的企业家才能,而非企业各类资本之间的协同效应;将商誉溯源至企业家才能,不会影响商誉的不可辨认资产之性质,因为企业家才能本身也是不可辨认资产。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中,依据可分离原则或合约—法律权利原则来判断资产是否属于不可辨认资产。企业家才能既无法从企业整体资产的价值中分离出来,又不是依赖合约—法律权利而形成,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恰是基于企业合约所没有明确约定的剩余控制权(企业资本提供者签订的合约给予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少量业已明确的决策权之外的控制权)。企业家才能包括了企业家发现商业机会的能力、追求风险和管控风险的能力、聚合资源的能力、运气好坏和格局大小,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的企业家才能是无法脱离其创办或者管理着的具体企业而存在的,适配于A 公司的企业家才能未必能够适配于B公司,同理,A公司或B公司更换了不适配的企业家才能,企业价值会发生巨大变化,甚至公司原本适配的企业家才能随着公司发展和环境变化而可能变得不适配。总之,作为最稀缺的一类资本(资产),企业家才能是不可辨认资产,其没有活跃的交易市场,难以直接由市场来定价。正如Yang和Ng(1995)所指出的,企业是一种间接定价制度,它通过把剩余索取权安排给企业家享有以作为对其服务的间接定价,从而可以把交易效率极低的经营劳动(管理知识的生产或管理服务)卷入分工,而同时避免对其直接定价和买卖,因其直接定价成本太高,难度太大。我们亦不得不承认,企业家才能之中包含着很大比重的“运气”成分,这也使得其难以被市场直接定价,从而无法从具体企业中分离出来进行交易。
因此,采用通常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是无法计量出并购商誉公允价值的。退而求其次,按照并购商誉的上述定义,如果能够估计出业务合并中所收购的不可辨认资产将创造的未来经济利益,然后采用合适的折现率,就可以计量出并购商誉在收购日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折现值,这可以作为并购商誉收购日公允价值的一种替代计量。换言之,既然商誉代表着企业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和超额收益,那么可以通过预测企业的未来超额收益,然后予以折现以计量并购商誉的公允价值。这个思路在理论上虽可行,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较低,作为不可辨认资产的商誉并不能独立创造未来经济利益,也难以合理估计其不确定的寿命周期内所能给企业带来的未来超额收益,因为企业未来期间的超额收益随着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企业家才能(包括企业家的运气)之不确定而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那么该如何计量并购商誉在收购日的公允价值呢?
IFRS 3 第32 段规定,收购方应当在收购日按照如下金额计量并购商誉:
由公式(1)可以看出,IFRS 3关于并购商誉计量的基本思路是,以被收购方净资产收购日的公允价值与其可辨认净资产收购日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为基础,然后加上收购方在收购日为并购协同效应所支付的那部分对价于收购日的公允价值。谢德仁(2023)论证指出,收购方在收购日为并购协同效应所支付的对价不应该被纳入并购商誉的计量,并建议在收购日将之予以费用化。若此,并购商誉其实就是被收购方于收购日的自身商誉。
按照IFRS 3,且假定被收购方非控制性权益也是按照被收购方净资产收购日的公允价值来计量②,则被收购方净资产收购日的公允价值与其可辨认净资产收购日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所计量的是被收购方自身商誉于收购日的公允价值。对这一关于被收购方自身商誉在收购日的公允价值的间接计量思路与方法,不妨梳理一下其思考路径:
公式(2)中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包括被收购方在收购日资产负债表表内和表外的全部资产与负债③。不妨进一步把资产区分为可辨认资产和不可辨认资产,其中,不可辨认资产之价值就全部归于“商誉”(或者说由商誉来代表),且假定负债都是可辨认的,那么:
下面把“负债的公允价值”移到公式(3)中的左侧,得到:
接着,把公式(4)的左侧重新组合,得到公式(5):
无疑,公式(2)~公式(4)无论是在数理逻辑上还是在会计逻辑上都是成立的。但紧接着,会计准则继续往前“走了一小步”,虽然数理逻辑依旧成立,可是会计逻辑上就出现了笔者后面将分析指出的“错了一大步”,陷入困境。会计准则上的这“一小步”就是把“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负债的公允价值”定义为“可辨认净资产(identifiable net assets)的公允价值”(参见IFRS 3 第19 段),则公式(5)变成:
至此,会计准则对于并购商誉公允价值的间接计量思路与方法就跃然纸上了,即由公式(6)直接推出:
在公式(7)中恢复使用前面暂时省略的“被收购方”“收购日”等概念,公式(7)就可重新表述如下:
公式(1)无非是在公式(8)的基础上,加上了收购方在业务合并发生时为部分并购协同效应所支付的对价的公允价值。如果在分步合并的情形下,收购方最后一步只是收购了被收购方极小比例的权益而发生业务合并,收购方最后一步为并购协同效应所支付的对价就可能极低,公式(1)就基本等价于公式(8)了,亦即此情形下的并购商誉计量就是被收购方净资产在收购日的公允价值与其可辨认净资产在收购日的公允价值之差额。需指出的是,这看似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业务合并,其实还杂糅了基于财务报表体系以利润表为中心的成本计量观思维(谢德仁,2023)。为此,IFRS 3 的规定只不过是在公式(8)的基础上加上了收购方已为之支付了对价的那部分并购协同效应,一起作为并购商誉的初始计量,但其计量思路是基于公式(8)的。如前所述,谢德仁(2023)认为收购方为并购协同效应所支付的对价不应该纳入并购商誉的计量,而是直接予以费用化。当然,前述计量思路与方法也适用并购日后的每一个计量日,并购商誉的减值测试中也可使用它,把公式(8)中的“收购日”改成“计量日”即可。进而言之,理论上企业自创商誉的计量也可沿用该计量思路。
三、现行并购商誉计量的会计逻辑困境分析
现行会计准则关于并购商誉计量方法的会计逻辑困境体现于前述公式(1)、(6)、(7)和(8)中,这些公式在数理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在会计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兹分析如下。
首先,如果净资产可以区分为可辨认净资产和不可辨认净资产两部分,那么可辨认净资产就是净资产的一部分,它是不能和商誉的公允价值相加的。这是因为,资产是企业所控制的经济资源,而负债和净资产都是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索取权,负债、净资产抑或它们中的一部分与资产(或者部分资产)相加都是没有经济意义的。
其次,可辨认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可以被称作“可辨认净资产”吗?换言之,从会计逻辑上,净资产可以区分为可辨认净资产与不可辨认净资产这两个部分吗?何谓净资产的“可辨认”?在会计逻辑上,不存在可辨认净资产。净资产和负债一样,作为其他主体对某个企业主体的索取权,其所谓的可辨认与否应该是指索取权的拥有者是否明晰。负债的债权人一般是明晰、可辨认的(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即使是“产品质量保证”这类负债,其索取权拥有者虽不直接指向企业具体的消费者,但是指向企业整体意义上的消费者,也还是可辨认的。因此,会计准则中没有提及过“可辨认负债”的概念,默认负债都是可辨认的。至于净资产,尽管实践中存在着名义股东和实际股东分离的情形(如合法的股份代持协议),但无论如何,股权的名义拥有者和实际拥有者都还是明晰的,是可辨认的!为此,净资产是无法也不应区分为可辨认净资产和不可辨认净资产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可辨认净资产”的经济本质呢?存在“不可辨认的净资产”吗?“不可辨认的净资产”的经济本质又是什么呢?没有“不可辨认的净资产”,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可辨认净资产”。还需指出的是,无论是法律形式上还是经济实质上,一般而言,企业都是以包含可辨认资产和商誉在内的总资产一起对债权人的优先“固定”索取权和股东的剩余索取权承担义务的,负债并不会直接对应于可辨认资产(即使是企业以特定资产抵押或质押而形成的负债,债权人的索取权也不限于特定资产)。
最后,并购商誉现行计量方法的会计逻辑困境更在于,用净资产的价值及其变动来计量资产的价值,这在本原意义上违背了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关于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及其间的基本逻辑关系之界定。
在IASB(2018)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被定义为企业总资产扣除负债之后的剩余利益。换言之,利益相关者对一家企业的全部索取权中,凡是不符合负债定义的索取权都属于所有者权益。故按照IASB 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所有者权益不是一个类似于资产和负债一样能够独立存在的财务报表要素,而是由资产和负债来定义和计量的、依赖于资产和负债之存在的“存在”。其实,长期以来,财务会计与报告概念框架都未能从经济本质上定义清楚“所有者权益”,而是基于资产和负债从计量视角简单定义了“所有者权益”,这一处理使得“所有者权益”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财务报表准要素”。金融工具的创新又使得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索取权边界日趋模糊,这就使得所有者权益的性质和边界更趋模糊,进而产生一系列难解的会计准则制定和会计处理问题(如可转换可回售优先股和带有回售选择权的普通股的会计处理难题)④。
基于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对所有者权益的上述定义,当采用被收购方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之差来计量商誉的公允价值时,并购商誉计量的会计逻辑困境就产生了。因为商誉作为一项资产,虽然不可辨认,但其本质上终究是一项资产,本来是用来定义和计量净资产的,结果却反过来由净资产与其“不可名状”的组成部分(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之差来计量,这在会计逻辑上陷入了困境!在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逻辑上,商誉(作为资产)与净资产之间,到底谁应该是定义和计量的主导者?无疑,现行会计准则关于并购商誉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在现行财务会计与报告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怎么能由净资产及其组成部分的价值及其价值变动来计量资产的价值及其价值变动呢⑤?
综上可见,并购商誉计量的会计逻辑困境不仅在于把可辨认净资产(作为净资产的一部分)与商誉这项资产相加,还在于“可辨认净资产”本身也是一个没有被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和相关会计准则认真、准确地从经济本质上定义过且在会计逻辑上不能成立的错误概念,更在于商誉作为资产和净资产之间“谁应计量谁”的逻辑困境。并购商誉计量陷入会计逻辑困境的底层成因在于,所有者权益作为财务报表要素在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没有被从经济本质上予以清晰定义,而后具体会计准则又在此基础之上从计量视角创设出一个经济本质上不成立的概念“可辨认净资产”。
四、结论
本文基于IASB 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和IFRS 3 分析指出,采用被收购方净资产收购日的公允价值与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收购日的公允价值之差来计量被收购方自创商誉的公允价值在会计逻辑上是错误的,且“可辨认净资产”这一概念也是不成立的,由此形成了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上的“被计量者”(所有者权益)和“计量者”(作为资产的商誉)之间“谁应计量谁”的并购商誉计量之会计逻辑困境。
当然,本文的全部分析都是基于IASB现行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来构筑财务报表体系的理念和IFRS 3把商誉视作一项真正的资产而展开。如果回到旧购买法(purchase method)和其背后所基于的以利润表为财务报表体系之中心的理念及成本计量观,把商誉视作是收购方支付的收购成本与所收购比例的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收购日公允价值之差额,仅仅是业务合并及其可能的后续相关会计处理的一个递延借项,而不是一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资产,那么就应该采取分期摊销(含减值测试和确认减值损失)乃至直接在并购日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的处理方法(谢德仁,2019、2023),本文的前述分析则需要推倒重来。需再次指出的是,本文只是提出现行并购商誉计量陷入了会计逻辑困境这一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该问题和如何更好地计量并购商誉,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注 释】
①IASB 于2023 年11月14日的会议上做出决定,终止“同一控制下的业务合并”项目。
②按照IFRS 3,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非控制性权益,也可以按照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收购日公允价值来计量,若此,则不会确认“非控制性权益所对应的商誉”,此所谓不完全商誉法。谢德仁(2023)对这一处理方法进行了批评,其指出,按照IFRS 3所要求的新购买法,这一处理方法是没有任何逻辑支撑的,且从会计理论逻辑来看,不存在“非控制性权益所对应的商誉”。上述IFRS 3的会计处理方法导致收购方可以通过分步收购被收购方权益来减少确认商誉,因为第一步完成收购时保持尽量大比例的非控制性权益,对非控制性权益仅仅按照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收购日公允价值来计量,无需确认相关的商誉;然后再完成后续收购时,是在保持控制权情形下收购子公司的非控制性权益,IFRS 3规定视同权益性交易(equity transaction)来进行会计处理,按照收购方在购买非控制性权益时点的合并财务报表中非控制性权益的账面价值进行计量,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超过这一账面价值的部分直接冲减收购方的所有者权益(我国规定是先冲减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以冲减时,冲减留存收益)。Zeng等(2024)基于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的案例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剖析。
③为行文简便起见,以下暂略去“被收购方”“收购日”和“全部”等字样。
④由此所思,笔者也想郑重呼吁,不能直接从计量视角来定义一项财务报表要素及其具体分类,这在会计逻辑上是错误的,在会计实践上也是非常危险的,而应从经济本质上予以定义。
⑤当然,这在当代会计实践中倒并非孤例:如现行会计准则在采用两项交易观对员工股权激励进行会计处理时,会计准则认为由于股权激励要换取到的未来员工服务的公允价值无法直接计量,所以采用发行的权益工具(股权激励工具)在授予日(grant day)的公允价值来计量未来员工服务这一资产;再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这一规定其实也不符合会计逻辑,因为发行多少公允价值的权益性证券本身依赖于要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及投资方愿意支付的其他因素溢价)。
【 主要参考文献】
李明,彭川.商誉理应减值还是摊销?——兼评IASB《讨论稿》[J].会计研究,2021(1):26 ~43.
谢德仁.商誉这颗“雷”:减值还是摊销?[J].会计之友,2019(4):2 ~5.
谢德仁.并购协同效应与并购商誉计量——基于业务合并会计之新购买法的分析[J].会计研究,2023(7):18 ~29.
谢纪刚,张秋生.上市公司并购的价值构成与商誉减值会计新模式——兼论《企业合并:披露、商誉与减值(讨论稿)》[J].会计研究,2020(12):18 ~28.
徐经长,张东旭,刘欢欢.并购商誉信息会影响债务资本成本吗?[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3):109 ~118.
张为国,解学竟.商誉会计准则:政治过程、改革争议与我们的评论[J].会计研究,2020(12):3 ~17.
IASB.IFRS3 Business Combinations,2008.
IASB.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porting,2018.
IASB.Discussion Paper "Business Combinations-Disclosures,Goodwill and Impairment",2020a.
IASB.Business Combinations under Common Control(Standards Discussion Paper,DP/2020/2),2020b.
Yang X.,Ng Y-K..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95(26):107 ~128.
Zeng C.,Zhang W.,Zuo L..Accounting for Goodwill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Two-step Acquisitions[Z].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2024.